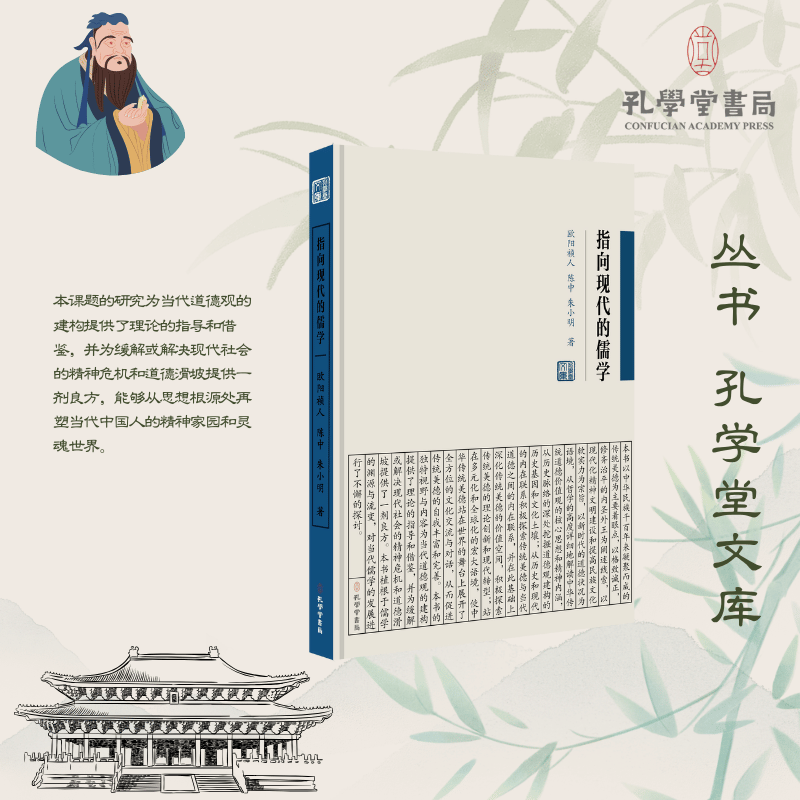
出版社: 孔学堂书局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4.56
折扣购买: 指向现代的儒学
ISBN: 9787807703617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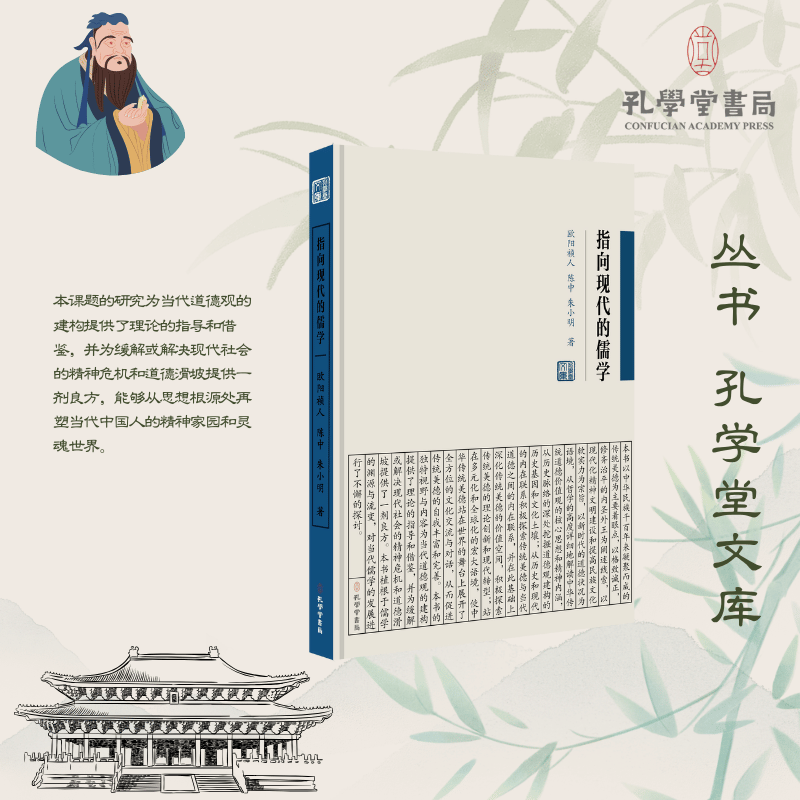
欧阳祯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阳明学研究》杂志执行主编,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陆九渊研究委员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王阳明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曾子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周易》研究学会副会长,贵州省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第一节 论《大学》与《中庸》的天人关系 《大学》《中庸》是中国人的圣典,在中国古代,其是中国人名副其实的精神 家园和灵魂归宿。从这两部经典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性是其核心的、根 本性的、基石性的内容之一,天人关系始终是这两部经典的重中之重。这一思想不 仅是两部圣典的精神原点,而且也是它们理论的依托。从世界范围来看,宗教性是 所有古代经典都必然存在的一种基本现象,但是,由于当代的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没 有宗教的时代,对这两部经典的宗教性解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本 文在这个方面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以就教于相关专家。 (一) 《大学》一文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出自《礼记》, 是先秦儒学的圣典。 虽然它是南宋以后读书人的必读书目,也是科举考试的基本教材之一,地位十分崇 高,但是,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根据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的说 法, “格物之说,古今聚讼者有七十二家”①之多。由此可见,这是千百年来聚讼 不已的一个大问题。笔者在系统了解了相关的论点之后,深以为,虽然古代学人的 学术功底深厚,研究态度也很严谨,但是,毕竟受到了时代和知识视域的局限,尤 其是对史前文明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完全不了解,因而终究没有得到“格物、致 知”的正解,进而对先秦儒家的真谛没有透彻领悟,因此,这个重大的问题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 在训诂学界的前贤时彦看来,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应该都不成问题了。他 们的相关资料以及论证过程如下:《说文解字》:“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甲骨文中的“止”都呈脚板形。“夊”,“夊,行迟曳夊,夊象人 两胫有所躧也”,就是“止”倒着的形状。“各”是脚趾向居所走来。所以,有 到达的意思。在注释《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时,郑玄注:“格, 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 好来也。”(《礼记正义》卷六十六)。章太炎认为,古代各家的相关注释都有问 题,唯独郑玄的注释“其义乃至卓”“盖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之义, 在学术史上意义重大。只有郑玄的注释,“上契孔子,而下与新建知行合一之义适 相会”。① 由于“格物”的“格”本是“各”,“各”是客人脚趾向主人居所走来,所以 古人的解释是“至也、来也”。清代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各,古格字, 故从夊。夊有至义,亦有止义;格训为至,亦训为止矣。”《尔雅 ·释诂》云: “格,至也。”《释言》云:“格,来也。”《礼记 ·月令》云:“则蝗虫为灾, 暴风来格。”郑玄注:“格,至也。”“各”又作“彳各”,《方言》卷一云: “彳各,至也。”郭璞注:“古格字。”则“各——彳各、格”为古今字,“彳 各——格”为通用字,就“到达”义而言,从“彳”(半边路)比从“木”更符合 造字本义,然经典习惯用“格”。“致知”的“致”本是“至”,“至”的本义是 来到、到达,《说文 ·夊部》:“致,送诣也,从夊,从至”,则“至”是自动的 “来到、达到”,“致”是使动的“送到、使到达”。“格物”与“致知”,明显 是一个并列的结构,但是,前者是条件,后者是结果。只有“格物”才能够“致 知”。“物”来了,“知”就会来。这个解释是否正确?笔者认为,至少从字面的 意义上来讲,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 基于天道生生大德化境中的仁,感于人则立于身心性命。然而因为种种的世俗之习的交感和物化异化之遮蔽,回归开显仁的生命境界,即孔子所谓“知德”“上达”,《大学》所谓“明”,《中庸》所谓“率性”“修道”和孟子所谓“必有事焉”,则需要一个修养觉证的过程,其本则仍然基于个个鲜活的主体之人本身,并以身心为本根。 孟子曾在与公孙丑的问答中,谈及如下一段话:“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告子所言不得于心则勿求于气是正确的或者说可以这么做的,即不得道义和自我心安,就不能任气逞强。而如果在言语或者说道义之理上不得逞,就不用再在自我内心去寻求或者说反观自正,这是不可以的。孟子进而指出,在一般的表象上看来,人由心和身二者构成,心即所谓的心志,而身则由气所充沛构成,在这二者之间,心志是身气的统帅,因此“志至”“气次”。所以孟子进一步认为一个人应该持守心志,不能任气逞强而暴躁。公孙丑似乎越听越无法明白孟子之意,便追问:既然说“志至”“气次”,又何故还要说持其志无暴其气呢?孟子则回答他,这么说是因为心志专一则会动气,也就是在心志高度虚灵专一无杂时,身气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同样,如果身气达到高度的纯一凝练时,心志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孟子怕公孙丑难于理解,又举例作比喻说明这种关联的变化,他形容这种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的微妙情形,正如一个人突然跌倒或者急促奔跑,这本来只是身气的变化,但会马上影响到心志的波动。在此,孟子之意也许同样说明,一个人如果要准备做急促的奔跑或者其他高难度或无法预知、控制的动作或竞技时,这本来是心志的准备,却马上会让人产生身气的紧张或者说急促巨大的波动。 上述孟子与公孙丑的问答对话中,核心是“志至”“气次”,在如上解说中之所以只引而未作释义,正因为其重要而又不易说明。所以,在《公孙丑上》中,当公孙丑继续追问涉及所谓的气及“浩然之气”时,孟子也只能摇摇头,因为这桩事或者说这种境界是很难用言语说清楚并告诉别人的,正如孔子所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心意也无法通过语言得到完全地表达,更何况涉及天道性命的神奇微妙的生命修养体证境界,这样的溟会体证境界更难用语言告诉别人。如果告诉一个毫无体证者,有时甚至是对牛弹琴,所以正如孔子感叹“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而老子更指出“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第四十一章),所以孟子说“难言”。 如上所述,先秦儒家的仁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身心性命的修养境界,是基于天道神气一元本体的生命境界,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天道生化神圣境界在人自我生命上的体证和感应通化,而绝对不可以用西方所谓社会关系学、等级概念、秩序等等极其庸俗的概念范畴去理解、格义儒家的仁,如果这样的话,便当下将神圣灵动的天道性命之境理解为逻辑论证和理性推理及其思维判断的西方惯常套路,便永远不会明白达到“人能弘道”的难知难言之生命境界。 上文所说的“志至”“气次”,这两个概念本来是指同一个身心性命的修养变化境界,但正如西方从柏拉图将理念与现象世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态以来,西方哲学文化思维中一直将身心作为二元论无法调和。近代的笛卡尔试图探索解决,但也无能为力,最后竟落到以所谓的“松腺体”作为破除化解身心二元论的历史性悖论和理论桎梏的境地,实在让人感到人类的无能与有限性。近代以来,不少西方偏激的学说传入中国,被国人称道和大加运用,以为利器,故对中国哲学展开了一场所谓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或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等等的格义和批判,实在是无知和傲慢,丑陋和无救!正因西方学说的思维在历史上长久以来形成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唯物、唯心的思维模式,毫无疑问,这样的模式根本无法理喻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主流哲学文化!如果强力为之,那无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