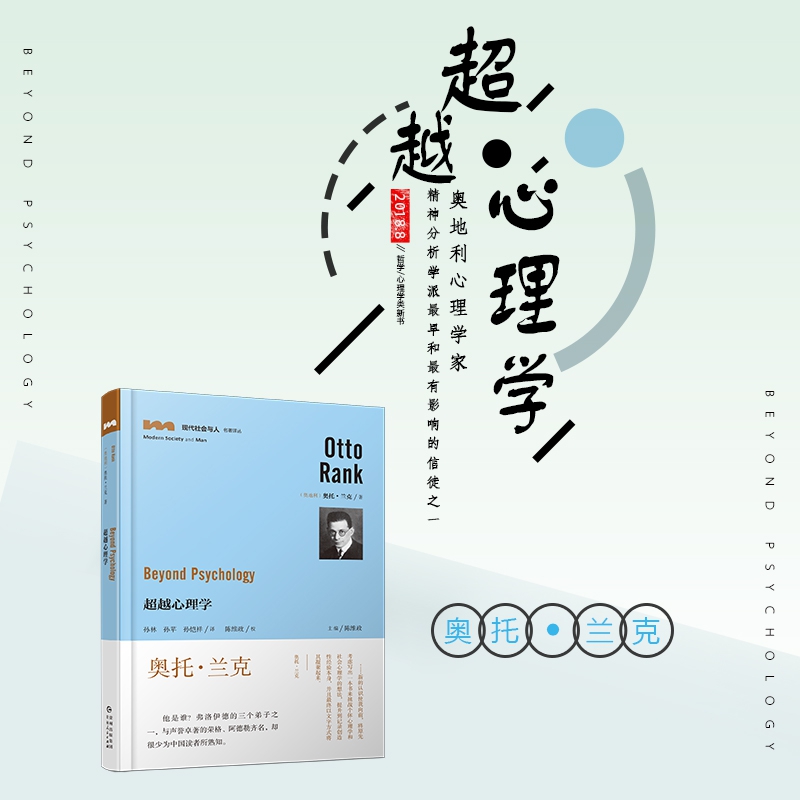
出版社: 贵州人民
原售价: 46.00
折扣价: 32.04
折扣购买: 超越心理学/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ISBN: 978722114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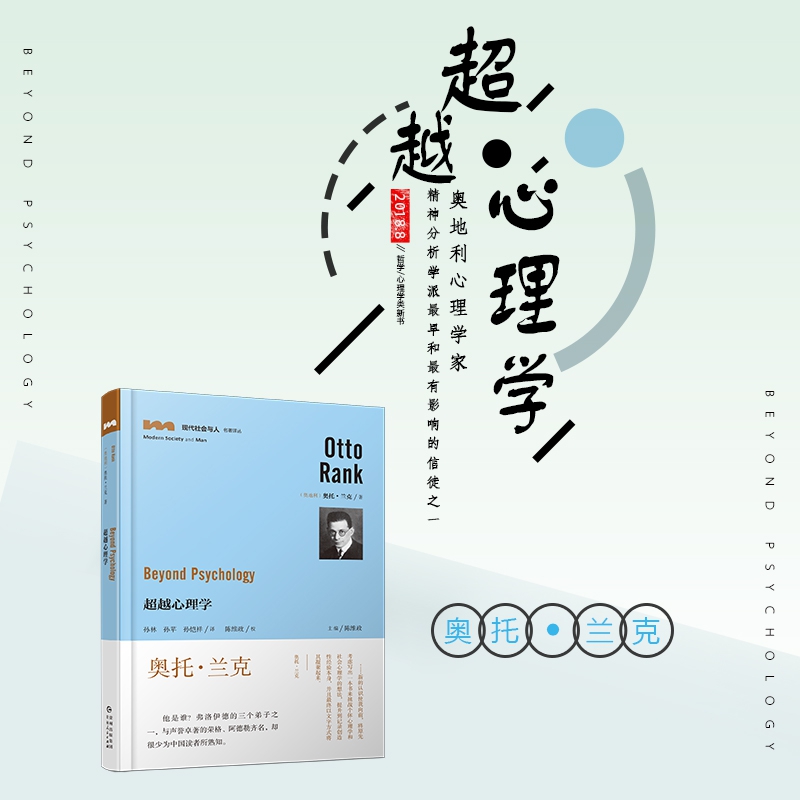
奥托·兰克 ( Otto Rank, 1884.04.22 - 1939.10.31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早和*有影响的信徒之一。 1919 年他和弗洛伊德等人创立了**精神分析学出版社,1924年以前一直任社长。大约1920年左右,他开始在维也纳担任精神分析临*医生。兰克的代表作是1924年出版的《出生创伤》一书,在这本书中兰克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虽然弗洛伊德赞同并且随意引用过兰克早期发表的一些著述,但他激烈反对《出生创伤》这部著作。该书阐释的原理使弗洛伊德感到烦恼,也使精神分析圈内的其他成员感到烦恼。由这本书引起的争论导致兰克被开除出精神分析圈子,并且也*终导致他把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对比。1924年,兰克离开维也纳,在巴黎和纽约继续他的临*实践和著作,同时还从事教学工作。1936年定居纽约。在这段时间,他一方面修正从维也纳那种传统的社会条件之下发展出来的弗洛伊德学说,使之适应于当代美国这样一个工业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创立他的“自我结构的精神分析”学说。 兰克在心理学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提出的意志疗法(亦为意愿治疗,Will Therapy)。在心理治疗中,兰克动员病人以意志来对抗逃避痛苦与冲突的倾向,鼓励病人在治疗中采取一个*主动、负责的角色。
在人类历**我们见到了两条有关变化的原则,交替起着作用,这两条原则似乎代表着某种亘古不变的困境。一条原则是,要改善人的处境,就得改变人自己。另一条原则是,为了生活得*好,人就应该改变生存制度。孰优孰劣,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充满了悲痛与忧伤,这两条有关变化的原则实际上似乎也相互重叠。我们碰巧出生在文明社会中,而个人则一直奋力地想与文明社会的影响做斗争。我们愈来愈意识到这种人类冲突中固有的两股动力。人总是想凭意志来控制那些无法控制的境况,这种永恒的冲突戏剧般地集中体现在了当代称之为世界大战,即两种相互对立的势力的冲撞之中。战前,个体心理学,即人们称之为教育和治疗工具的科学,蓬勃发展,个人主义也随之高涨,与之相对的反制力量也接踵而至。 这股反制的力量,自发而规模宏大,鲜明地表现了反映战后时代特征的社会、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政客、教育家,以及心理学家们,都各自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对付各种急诊病,以求消解这一冲突;与此同时,像历**常常出现的那样,无法预见到的事件却又从他们手中夺去了主动权,不断地改造各种体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远远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便是赶上事件的自发进程。因为这些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个人和社会。在我看来,这种赶上进程的做法有这几层意思,不仅仅是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想到我们该怎么办,还涉及如何顺应事件的发展,实实在在地活在其中,在改革的激流中学会游泳。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知道各种危险的潜流。所有布满社会危机的时代,比如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不允许人做过多的反思,而是要人尽快行动。19世纪的唯理智论的**在世界大战中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狂热行动的阶段。我们很容易便能从狂热的行动中发现那种事事两难的情况:我们的头脑,尽管是出了名的敏捷,却总是跟不上那不断发生的事件汇合而成的汹涌向前的洪流。头脑中萦绕着过去美好的时光,又憧憬着光明的未来,我们便常常对现在感到无可奈何,因为我们甚而一刻也停不下当今的各种潮流,并将其引向*容易理解的方向。情况似乎是这样,但我们还得了解这样的事实:人不停地想用自己的意志来控制生命中的各种无理性力量,而生命却时常对人的这种努力做出反抗,以保持自己的样子。无论我们以什么名目企求这种自以为是的目的,迟早会遇到反抗,也许以理性的怀疑论,或是悲观论形式出现,比如,希腊人因此而毁灭了。或者,具体的背叛实则是出自我们*挫的人性。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事实仍然是事实,迄今为止,*激进的,即*重要的变化都是通过战争或革命来实现的。战争或革命实际改变了秩序,制度改变了人,或者应当说,人被改变了。当新的秩序通过暴力建立起来之后,教育—就其*广泛的含义而言—过去总是,现在也是下一步行动,即改造人的行动的*重要手段。给人灌输思想的这种做法,既有力量,也有弱点,因为灌输的做法本身便缺乏灵活性。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体制易于变得**化,正像**制度一样,而后者往往先为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哲学基础。自亚里士多德宣称**应当按照**的法规来教育年轻一代以来,从古至今,这条原则一直是在人类历**我们见到了两条有关变化的原则,交替起着作用,这两条原则似乎代表着某种亘古不变的困境。一条原则是,要改善人的处境,就得改变人自己。另一条原则是,为了生活得*好,人就应该改变生存制度。孰优孰劣,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充满了悲痛与忧伤,这两条有关变化的原则实际上似乎也相互重叠。我们碰巧出生在文明社会中,而个人则一直奋力地想与文明社会的影响做斗争。我们愈来愈意识到这种人类冲突中固有的两股动力。人总是想凭意志来控制那些无法控制的境况,这种永恒的冲突戏剧般地集中体现在了当代称之为世界大战,即两种相互对立的势力的冲撞之中。战前,个体心理学,即人们称之为教育和治疗工具的科学,蓬勃发展,个人主义也随之高涨,与之相对的反制力量也接踵而至。 这股反制的力量,自发而规模宏大,鲜明地表现了反映战后时代特征的社会、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政客、教育家,以及心理学家们,都各自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对付各种急诊病,以求消解这一冲突;与此同时,像历**常常出现的那样,无法预见到的事件却又从他们手中夺去了主动权,不断地改造各种体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远远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便是赶上事件的自发进程。因为这些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个人和社会。在我看来,这种赶上进程的做法有这几层意思,不仅仅是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想到我们该怎么办,还涉及如何顺应事件的发展,实实在在地活在其中,在改革的激流中学会游泳。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知道各种危险的潜流。所有布满社会危机的时代,比如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不允许人做过多的反思,而是要人尽快行动。19世纪的唯理智论的**在世界大战中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狂热行动的阶段。我们很容易便能从狂热的行动中发现那种事事两难的情况:我们的头脑,尽管是出了名的敏捷,却总是跟不上那不断发生的事件汇合而成的汹涌向前的洪流。头脑中萦绕着过去美好的时光,又憧憬着光明的未来,我们便常常对现在感到无可奈何,因为我们甚而一刻也停不下当今的各种潮流,并将其引向*容易理解的方向。情况似乎是这样,但我们还得了解这样的事实:人不停地想用自己的意志来控制生命中的各种无理性力量,而生命却时常对人的这种努力做出反抗,以保持自己的样子。无论我们以什么名目企求这种自以为是的目的,迟早会遇到反抗,也许以理性的怀疑论,或是悲观论形式出现,比如,希腊人因此而毁灭了。或者,具体的背叛实则是出自我们*挫的人性。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事实仍然是事实,迄今为止,*激进的,即*重要的变化都是通过战争或革命来实现的。战争或革命实际改变了秩序,制度改变了人,或者应当说,人被改变了。当新的秩序通过暴力建立起来之后,教育—就其*广泛的含义而言—过去总是,现在也是下一步行动,即改造人的行动的*重要手段。给人灌输思想的这种做法,既有力量,也有弱点,因为灌输的做法本身便缺乏灵活性。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体制易于变得**化,正像**制度一样,而后者往往先为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哲学基础。自亚里士多德宣称**应当按照**的法规来教育年轻一代以来,从古至今,这条原则一直是强大****的指导方针。在现代的各个危急时刻,我们看到,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教育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德国的传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是“学校教师”赢了1866年征服奥地利的战争。 就*近的例子而言,人们常说,(英国)伊顿公学出身的青年挡不住*过希特勒纪律严格训练的年轻人。实际上,臭名昭著的德国人的*国主义精神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学校纪律在战争年代的延伸。即使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尽管他们不喜欢什么制度或理论,但也承认:滑铁卢大胜,也是学校教育赢得的。而个性化的法国人,在1870年的大败之后,则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的“**文科中学”优于法国的“公立中学”。然而,在当今时期,现代教育者困惑于不稳定的社会秩序,又缺乏普遍认可的理想,便试图用一种以科学心理学为基的*个性化的教育来代替传统教育中的顺应哲学。进步的教育家不是要个人去适应不断变化因而也基础不稳的社会秩序,而是宣称,当代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让人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改变社会。他们进而心照不宣地宣告,传统教育已经破产,传统教育的本质是灌输,维护集体意识形态,而不是培育个人自我的发展。于是,某些进步的教育家所设计的有关个体差异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与美国实行的全民教育理念**相反的情况。实际上,美国的进步教育,*确切地说,某些进步的学校,*到了责难,因为他们迎合了“特权”群体的需要,这些群体的人有钱供子女上那些“以孩子为中心”的学校。在大动荡的时代,个人需要*大的内在安全感,以便度过他所处的那个不断变化的环境,因为到处都是大风暴,威胁着自我的生存。这样一来,强化自我意识的教育体制便*为人所向往。社会影响,总是以某种方式驱使人趋向同一性,而这种强化自我意识的教育体制则将人与趋同的社会影响分隔开来。不过,这种教育需要某种来自异类意识形态的威胁,因为这能使本国的进步教育家意识到危险。关于这一点,我在1930年写的书《现代教育》中便已经指出。1939年举行的进步教育协会底特律年会认为,有必要重新界定个人主义理念的含义。底特律会议强调,作为与以“孩子为中心”的办学概念相反的观点,以培养**价值观为导向的涉及社会行动计划的教育理论十分重要。强大****的指导方针。在现代的各个危急时刻,我们看到,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教育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德国的传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是“学校教师”赢了1866年征服奥地利的战争。 就*近的例子而言,人们常说,(英国)伊顿公学出身的青年挡不住*过希特勒纪严格训练的年轻人。实际上,臭名昭著的德国人的*国主义精神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学校纪律在战争年代的延伸。即使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尽管他们不喜欢什么制度或理论,但也承认:滑铁卢大胜,也是学校教育赢得的。而个性化的法国人,在1870年的大败之后,则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的“**文科中学”优于法国的“公立中学”。然而,在当今时期,现代教育者困惑于不稳定的社会秩序,又缺乏普遍认可的理想,便试图用一种以科学心理学为基的*个性化的教育来代替传统教育中的顺应哲学。进步的教育家不是要个人去适应不断变化因而也基础不稳的社会秩序,而是宣称,当代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让人知道自己有能力去改变社会。他们进而心照不宣地宣告,传统教育已经破产,传统教育的本质是灌输,维护集体意识形态,而不是培育个人自我的发展。于是,某些进步的教育家所设计的有关个体差异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与美国实行的全民教育理念**相反的情况。实际上,美国的进步教育,*确切地说,某些进步的学校,*到了责难,因为他们迎合了“特权”群体的需要,这些群体的人有钱供子女上那些“以孩子为中心”的学校。在大动荡的时代,个人需要*大的内在安全感,以便度过他所处的那个不断变化的环境,因为到处都是大风暴,威胁着自我的生存。这样一来,强化自我意识的教育体制便*为人所向往。社会影响,总是以某种方式驱使人趋向同一性,而这种强化自我意识的教育体制则将人与趋同的社会影响分隔开来。不过,这种教育需要某种来自异类意识形态的威胁,因为这能使本国的进步教育家意识到危险。关于这一点,我在1930年写的书《现代教育》中便已经指出。1939年举行的进步教育协会底特律年会认为,有必要重新界定个人主义理念的含义。底特律会议强调,作为与以“孩子为中心”的办学概念相反的观点,以培养**价值观为导向的涉及社会行动计划的教育理论十分重要。 ?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玉”,“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作为一面镜子,一扇窗户,系统地考察和介绍了西方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学术成果。 ?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作为现当代西方**学者对人的微观研究之集萃, 主要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行为学、伦理学、**学等不同领域和不同视角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意识、行为、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进行全面深刻地分析,力图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地位和关系,以及未来的演变。 ? 本书作者是谁?他是弗洛伊德的三个弟子之一,与声誉卓著的荣格、阿德勒齐名,却很少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 全书涉及哲学、人类学、**学、文学、语言学及心理学等领域的发展过程,即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了与东方文明的对照,充分展现了兰克的渊博知识和独到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