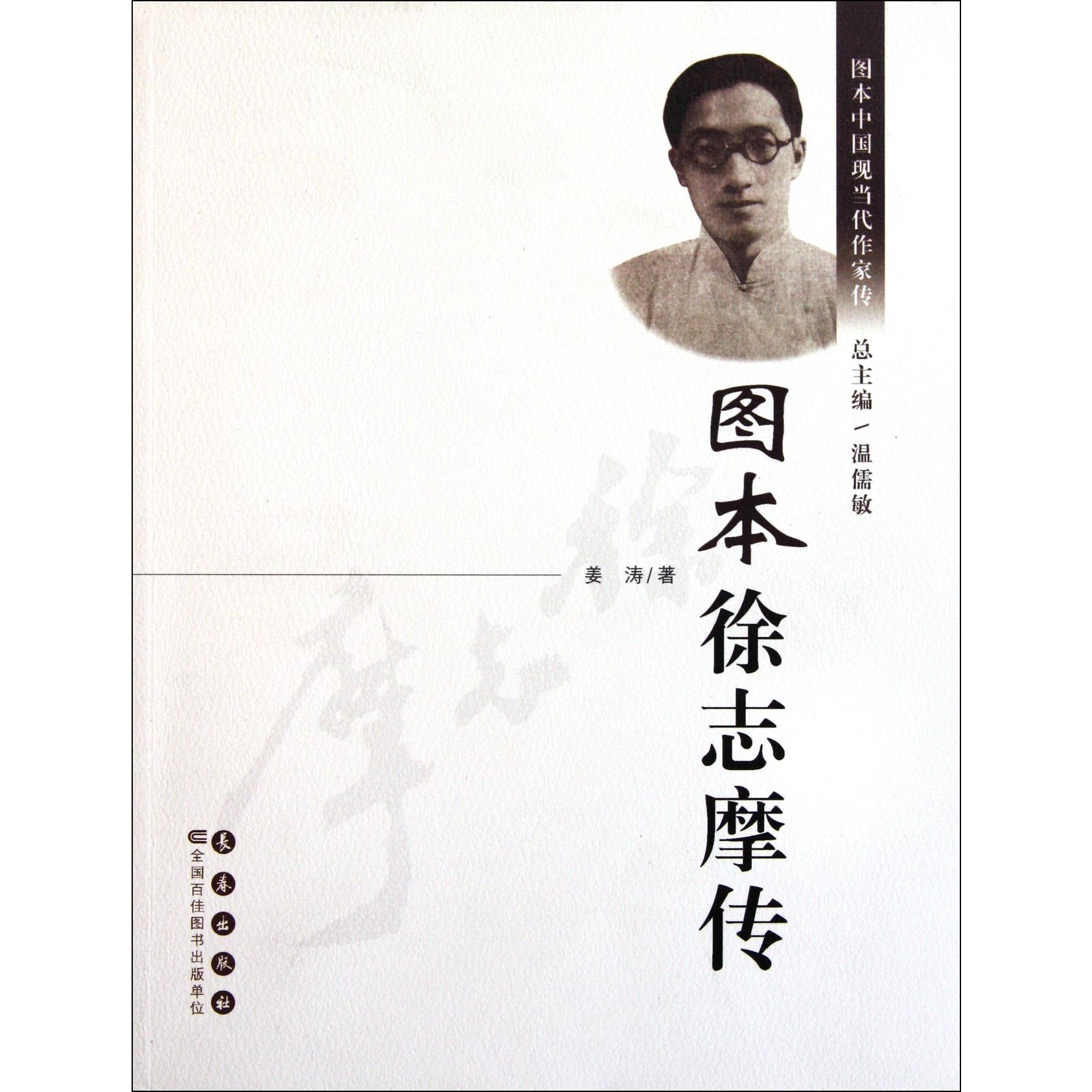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春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19.60
折扣购买: 图本徐志摩传/图本中国现当代作家传
ISBN: 9787544518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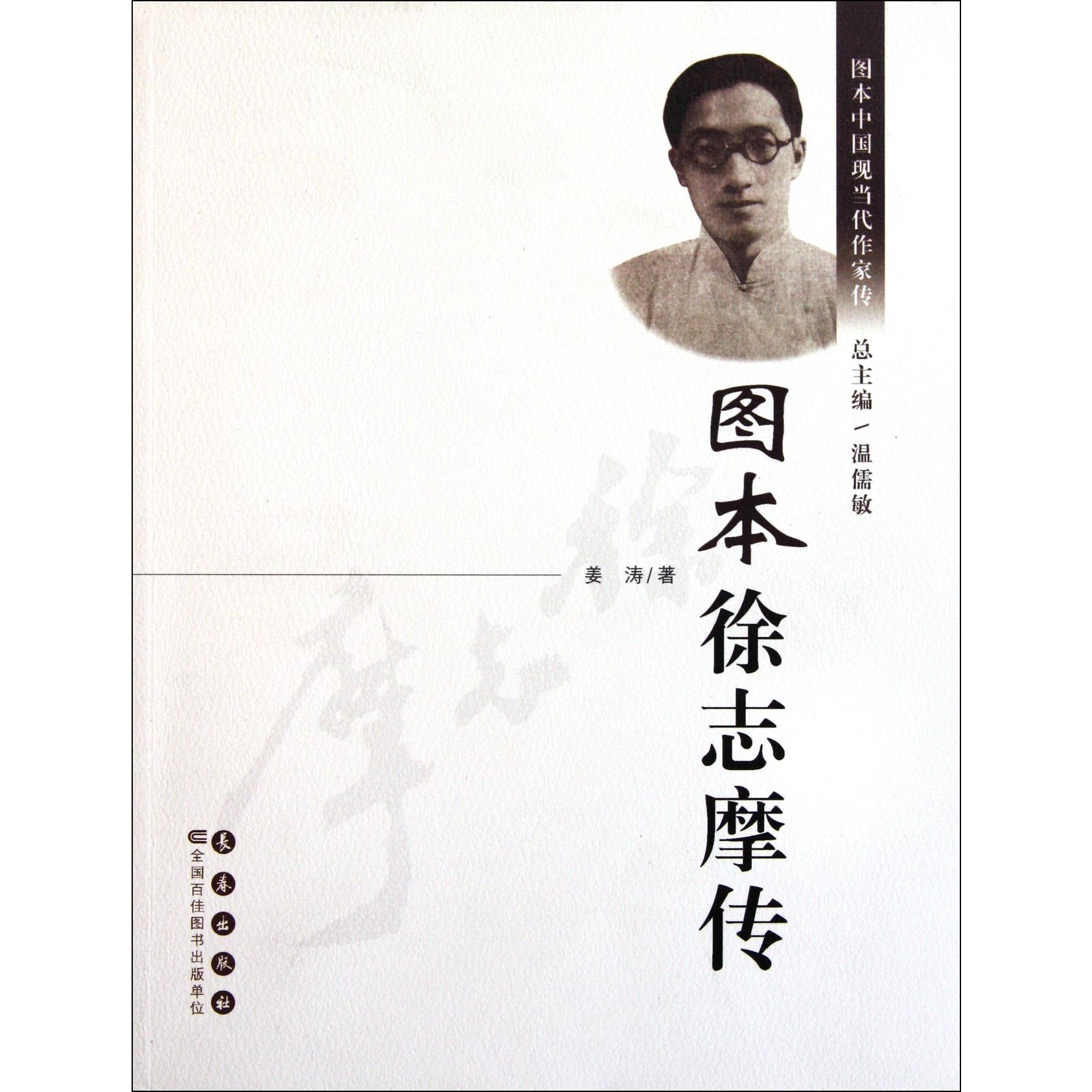
姜涛,1970年代生,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出身,后因写诗早早“弃工从文”,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也间或从事当代诗歌的批评,著有诗集《鸟经》,研究专著《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等。
在浙江海宁,有个地方叫硖石镇。镇的两边有东、西两山,像一对恋人 相 望,中间有一条河流过,人称硖河。这里风景明秀,十分富庶,是大米和蚕 丝 的集散之地。镇上有一大户人家,姓徐,祖上是宋南渡时从汴京(今开封)迁 到江南的,世代经商。到了20世纪初,已成为当地的首富。 徐家的主人叫徐申如,他为人精明、眼光远大,曾担任硖石的商会会长 , 除了继承祖上传下来的酱园、钱庄 以外,还投资兴办了硖石电灯厂、 蚕丝厂、布厂,在上海还有银庄票 号,于沪杭一带的金融实业界小有 影响。1908年,江浙两省筹建沪杭 铁路,按原来的规划,火车从上海 出发,直接开到杭州。徐申如以集 资股东的身份,力争铁路改道经过 硖石。当时镇上有人反对,还合伙 捣毁过徐家,但徐申如坚持到底, 最后顺遂了心愿。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开发交通,硖石后来的繁荣,多少要 归 功于这条“绕了弯”的铁路。 1897年,在徐氏老宅第四进院子的楼上,降生 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诗人徐志摩。最初,徐申 如给宝贝儿子取的名字是章塘,字槱森。“志摩”二 字,是徐申如在儿子长大后又为他取的别号。作为 家中的独子,幼年的诗人自然得到了不少长辈的疼 爱,在山野和乡村中无忧无虑地成长,基本没什么 波澜。后来,他在一篇散文中曾这样写道: 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 湖,草地,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斓,星月的隐现,田野 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老师,我的官觉 是他们忠谨的学生,受教的弟子。 将自然认作是开蒙的老师,这样的说法在浪漫派的诗人那里,当然屡 见不鲜。但望子成龙的徐申如肯定不这样看,他对儿子的学业,从小就抓得 很紧。徐志摩4岁人家塾读书,自5岁起师从一位古怪的老师——查桐轸, 又字桐荪。这位老师学问很好,但十分邋遢,不刷牙,不洗头,也很少洗脸 ,据 说他终其一生也没洗过一次澡,如此不讲卫生,真是相当罕见。跟着这样的 老师读几年书,学生会受什么影响呢?长大后,徐志摩这样反省过自己:“ 因 懒而散漫,美其称日落拓,余父母皆勤而能励,儿子何以懒散若是,岂查桐 荪 先生之遗教邪!”13岁的时候,徐志摩的眼睛近视了,家人为他配了副眼镜 , 他那戴金丝边眼镜的经典形象,此时也就大致确立了。第一次试戴的时候, 天已昏暗,这个小孩仰头一望,突然看到一片伟大蓝净的陌生天空,还有千 百只神眼闪闪发光,一直穿过眼镜直贯到他的灵魂深处。他不禁大声叫道: “好天,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 戴上了眼镜,少年徐志摩重新认识了世界,也即将开始自己的“云游” 了。1910年初,他离开家乡,来到杭州求 学,进入了当时全省最有名气的杭州府 中。在他的同学中,有个转学来的乡下少 年,很是特别。大概由于环境的陌生,他 总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无论在课堂 上,还是宿舍中,都像蜗牛似的蜷伏,连 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这个少年后来 也出了大名,他就是作家郁达夫。 在郁达夫的眼里,和自己畏缩的情 态相反,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 奇人十分活跃,总是交头接耳,跳来跳 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其中的一个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 生 得特别大,给人的感觉是,“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让郁达夫诧 异 的是,这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 用 功,那样的爱看小说,考起试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最高。俗话说:三岁 看 老。少年时代的徐志摩,聪明、好动、爱玩耍、兴趣广泛。成年之后,他性 情也 大致没变。过了十几年,郁达夫在北京又遇到了老同学,当年头大的小孩已 游历了欧美,长于社交,但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以及笑起来的样子,同记 忆 中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不少人出身贫寒,或年幼时家道中落,看见过世人 的真面目,体验过人生的挫败与困顿,所以日后难免性格狂狷,思想激进。 徐 志摩则不同,出身于富商之家,从小衣食无忧,成人后除感情生活一波三折 外,其他方面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生活上虽没极尽奢华,但基本也算处优养 尊,所结交的也都是学者名流、绅士显贵。他的文化性格,他的行为方式, 自 然与那些“穷小子”不同。1923年,徐志摩在上海曾与好友胡适、朱经农, 一 同拜访了郭沫若,他们的见面,颇具戏剧性。在日记中,徐志摩记录了当时 的 一幕: 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 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 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 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 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 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 笑谛视,不识何意。经农竞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 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 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 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竞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这真是一场尴尬的会面。本来,对于郭沫若的新诗,徐志摩很喜欢,读 后 还曾惊叹“华族潜灵,斐然竟露”。在早期的诗坛上,还有人将二人写作并 举, 分别代表新诗的不同阶段。但生活环境和经历的差别,使他们分属两种不同 类型的作家,彼此之间的隔阂,也终难打破。有趣的是,比较一下他们年轻 时 的照片,海边赤裸的郭沫若,一身英武,一脸“狂叛”之气;徐志摩则显得 温文 尔雅,眼神里还不乏天真。P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