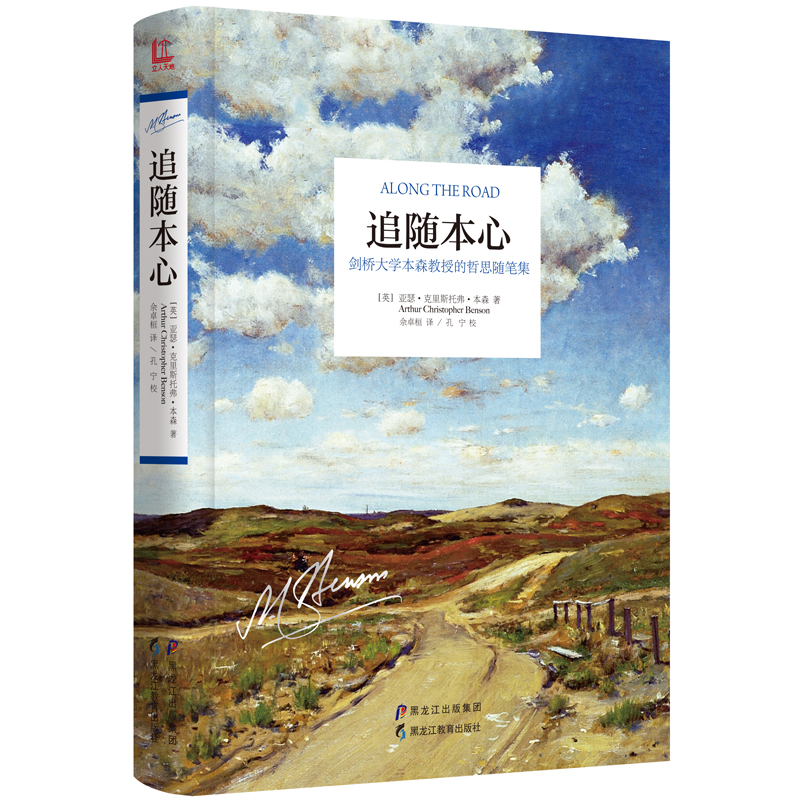
出版社: 黑龙江教育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22.70
折扣购买: 追随本心(剑桥大学本森教授的哲思随笔集)
ISBN: 9787531691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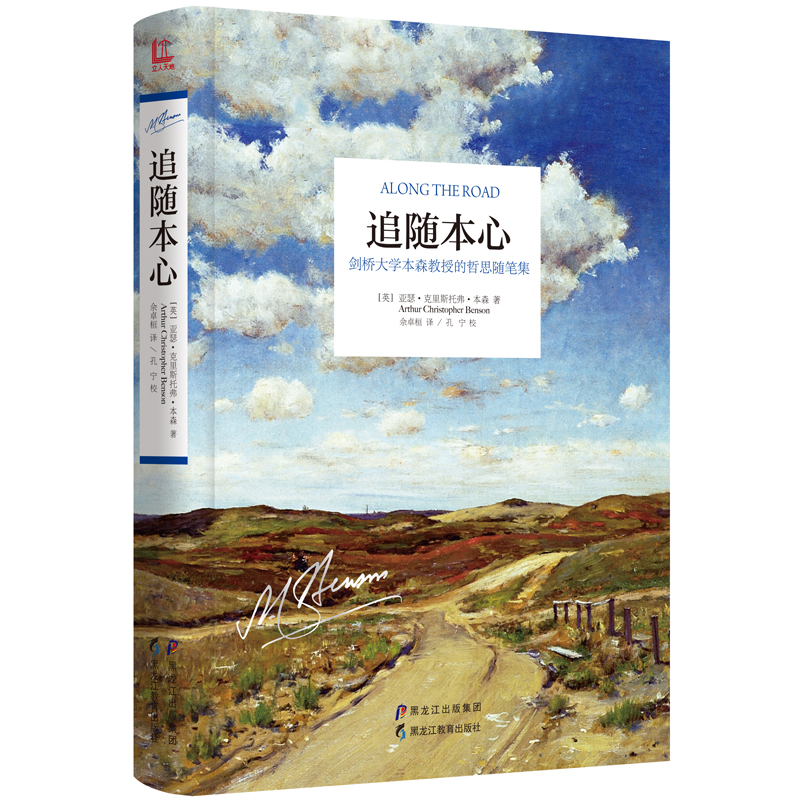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1862—1925),英国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作家,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第28任院长。他的父亲是19世纪末坎特伯雷大主教爱德华·怀特·本森,其舅舅是著名的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因此,本森家族所富有的文化和著述的传统,也很自然地遗传到他身上。但不幸的是,同样遗传在他身上的还有家族性精神病。他本人患有狂躁抑郁性的精神病,虽然身患疾病,但本森仍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多产作家。他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并于1885—1903年期间,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的莫德林学院讲授英国文学。1906年后,他出任格雷欣学校校长。1915—1925年,他担任莫德林学院院长。 他的诗歌和散文著述颇丰。令人惊叹的是,他在人生最后的20年间,每天坚持写日记,写下了世上最长的400万字的日记,给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代表作有:《仰望星空》(At Large)、《自由之旅》(Escape and Other Essays)、《大学之窗》(From a College Window)、《圣坛之火》(The Altar Fire)、《为师之道》(The Schoolmaster)、《剑桥论道》(CambridgeEssayson Education)、《阿城信札》(The Upton Letters)、《我心无惧》(Where No Fear Was)、《向死而生》(TheGate of Death)、《对话寂静》(The Silent Isle)、《无冕之王》(Men of Might)、《安静的家》(The House of Quiet)、《静水之旁》(Beside Still Waters)、《追随本心》(Along the Road)、《生命之泉》(Water Springs)、《雅致生活》(The Thread of Gold)、《黑夜炉火》(Thy Rod and Thy Staff)、《花香满园》(Joyous Gard)、《论罗斯金》(Ruskin,A Study in Personality)、《障山及其他故事》(The Hill of Trouble and Other Stories)、《曙光中的少年》(The Child of the Dawn)等。
岁月的胜利 不久前,我参观了英格兰北部一座极有特色的教 堂,让人觉得非常有趣。教堂的官方名称是卡梅尔高 地教堂,但附近的人则有一个更富浪漫色彩的叫法: 高地上的圣·安东尼。教堂离肯德尔不远,这一带地 势渐趋向海平面下降。教区里可见离离青草,树木繁 茂,还有那古老而似梦境的农舍——竖框的窗子,石 块覆盖的地板表层抹着粗灰泥,圆圆的烟囱,木制的 长廊,一一收入眼帘。峡谷的一边,是石灰岩的断崖 ,沿途有一些荒凉的梯地,一些碎石堆;而在另一边 ,峭壁并不壮观,高地上石楠丛生。 教堂坐落的位置极佳,处于地势低矮的灌木丛与 牧场往开阔高地延伸地带之间。地势向四周倾斜,望 过去,映入眼帘的,是隆起的田埂与突出的岩石,稀 疏的灌木环绕其间。在苍翠的峡谷中,泉水从灯芯草 间冒出来,气息间仿佛洋溢着滴滴水声的乐音。教堂 所处位置的地势很低,几乎有一半隐藏在地面之下。 塔楼上的窗户,与造工粗糙、歪斜的石板相得益彰。 教堂虽然在形式与设计上美感不足,但像一个从此处 土壤中自然生长起来的活物,充满生气。从门廊到教 堂耳堂之间,摆放着矮矮的石板长凳。在夏季安息日 的早晨,想必有不少人在这里八卦闲谈,还有牧羊人 坐在这里用乡野淳朴的粗言谈天说地。教堂散发出古 色古香的味道,东边有一扇宽大、多竖框的窗户,玻 璃是14世纪遗留下来的,锈迹斑斑,乍看不那么牢固 ,在拼凑的过程中似乎没有多少艺术上的考量。环视 教堂,可见深红、浅蓝的混搭,这儿一块,那儿一块 。一个十字架,一两个斜接的圣人像,其中一个是圣 ·莱昂纳德,他手里拿着锁链;另一个是圣·安东尼 ,一只爱玩的小猪弯曲着身子,蜷缩在他手中牧杖的 底部。还有一些画面似乎只是表示一种坚信礼,还有 各种有趣而奇怪的场景,诸如布帘覆盖着祭台,上面 放着一些圣酒瓶,而在圣餐杯里则有方形的亚麻制的 卡片。在祭具室里,我发现一大堆做工一致的玻璃, 尖顶饰物与圣体龛虽然做工粗糙,却也有一种生气。 教堂地面铺着形状不规则的石板,顺着山丘下陡的方 向缓慢下沉。东墙上悬挂着一幅画工粗糙的十诫图像 。综观来看,这个教堂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 里面的长凳了。长凳形状各异,有的高高竖起;有的 小凳子是用粗糙的橡木制成,上面还有朴素的尖顶饰 物。为了彰显此教堂的与众不同,在近东边的一角, 是货真价实的詹姆斯一世时期的长凳,凳子上还有镶 板的华盖与壁柱;而在另一边,应该就是被遮挡住的 小礼堂。小礼堂的长凳无论在制模与镶板上,都可谓 雕刻精美,颜色艳丽。雕刻的圣人头像显然被人用削 尖的工具细心打磨掉了,这样只是为了新教徒可以进 行更加虔诚的祷告。 这是一个小地方,但从关于此地的历史文献来看 ,由肇始到今世,此处的新奇、有趣、美丽,经过了 光阴的流逝,人事的变迁,仍然存在。诚然,这里也 需要重修,但时间甚短,这才是真正的难点所在。一 方面,为毁掉教堂里面那些不搭调的附属物感到遗憾 。再者,要是那样的话,这里也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 上的圣堂了。其实,真正缺乏的,是细如发丝般的修 复工作,将任何有趣与富有特色的事物保留下来,同 时让它显得温馨如常,给人家一般的感觉,亦不乏应 有的肃穆。当然,最让人担忧的,就是那些热心的捐 助者或野心勃勃的建筑师想在此“大展身手”,将之 改建成与其他教堂无异的建筑,这才是英国教堂建筑 的真正可悲之处。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参观了很多教 堂。虽然这些教堂很多独特之处以及有趣的细节都得 到了细心的保存,但很多教堂实际上都已重建过。人 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眼前的这些教堂都是新建的。因 为无论模仿得多么逼真,这也只是一份复制品而已, 最多也只能算是精美的赝品。其中真正流失的,是岁 月流逝之美——原先的半色调,随意的不规则,凹陷 的表面,细微的沉降,风雨的痕迹,正是这些让古老 的建筑显得和谐、静美,尽管原始的设计是那么简朴 与平实。 真是众口难调啊!让教堂成为其所处村落的象征 性建筑,兼具实用与舒适的特点,代表某种明确的宗 教传统,这是极为自然且值得赞许的。最后一点,也 是最让人恐惧的,就是这个并非顺应自然与进步的传 统,而是中世纪主义的死灰复燃,只能是一片死水。 但当一切尘埃落定之时,人们将乔治王时代甚至詹姆 斯一世时代的所有痕迹都从教堂中扫出去的本能,的 确显示着这些东西正在走向历史,至少有这个征兆。 虽然这有点冒犯且显得不雅,但这正如人类的感恩之 情会让哲学家们捶胸顿足,忧伤不已。 也许,修复教堂的正确原则应该是这样的:任何 坚固、昂贵或做工精美的东西,无论是纪念碑、窗户 或教堂的家具,都应该保留下来,即便这些东西可能 与我们现在的鉴赏品位并不搭调。转移一些不搭调的 东西的最大限度,也应该是将它们从一个显眼的位置 挪至不显眼的角落。即便一些物品做工低劣,或是现 在为大众所批判,都应该细心地保存起来,等待人们 日后鉴赏品位的变化。 19世纪初,修复斯基普顿教堂时,教堂里壮观的 都铎时代屏风被人视为是粗俗的,给人不安的感觉。 我的一位远房亲戚居住在教堂附近,去央求将这些拆 掉的材料送给他,教堂方面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就将 这些材料装在箱子里统一存放在仓库中。多年以后, 当基督教会的传统再次占据上风,这座教堂再一次被 翻修,此时很多人埋怨当年丢掉了屏风材料,这位亲 戚交出了这些材料,宣告了自己的某种胜利,当年都 铎时代的审美风格才得以完整地重现。那些狂热的教 堂建筑改造者总是昂着自信的头颅,毫无顾虑地说: “这些让人恐惧的东西应被清除掉。”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P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