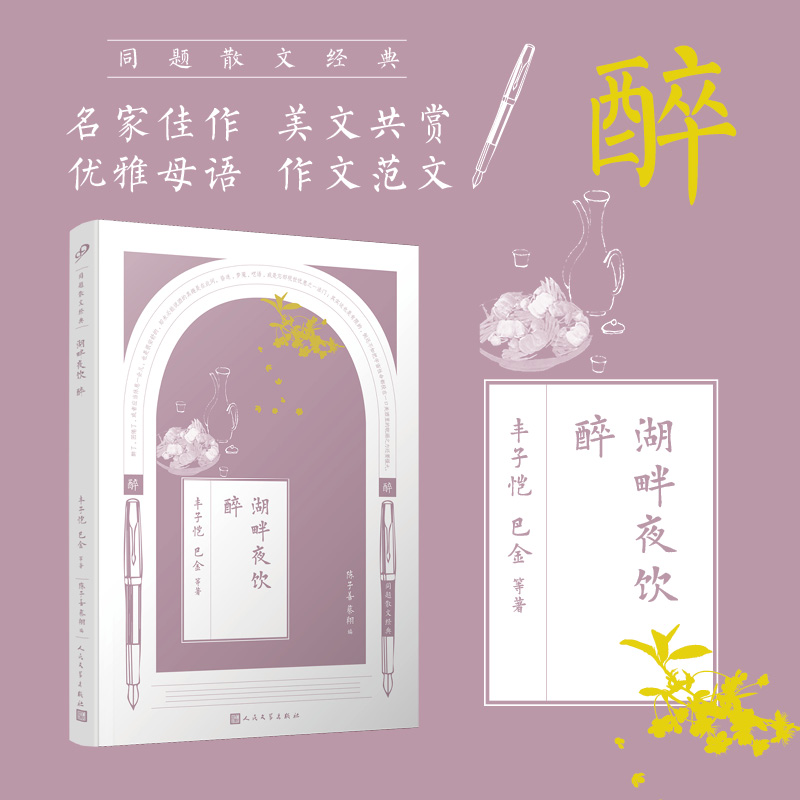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22.70
折扣购买: 湖畔夜饮醉/同题散文经典
ISBN: 9787020126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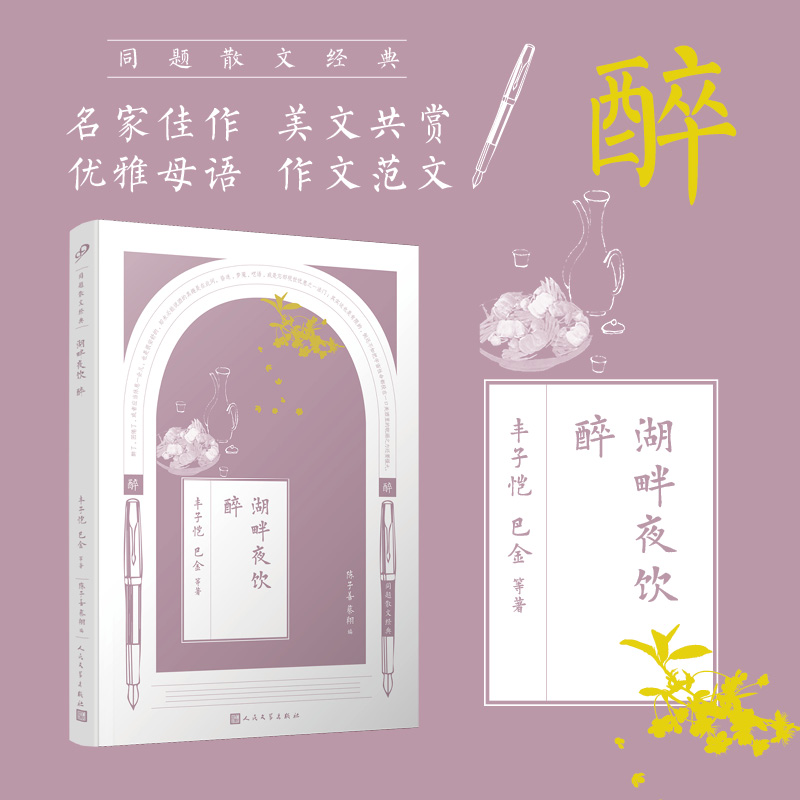
作者简介: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现属桐乡)人,原名丰润,又名丰仁。中国漫画家、作家、翻译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主要文学作品有《缘缘堂续笔》《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率真集》《丰子恺散文选集》、丰子恺文集》等,另有漫画集《子恺漫画全集》等多种。译著有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初恋》、猎人笔记》,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等。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原名李尧棠。中国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散文集《随想录》。1982年获“国际但丁文学奖”。 编者简介: 陈子善,著名学者、书人、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数据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蔡翔,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
谈酒 ◎周作人 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虽是京兆人,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因为儿歌里说,“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nio”———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语。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只有煮的时候的手法极不容易,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俗称“酒头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有一个远房亲戚,我们叫他“七斤公公”,———他是我舅父的族叔,但是在他家里做短工,所以舅母只叫他作“七斤老”,有时也听见她叫“老七斤”,是这样的酒头工,每年去帮人家做酒;他喜吸旱烟,说玩话,打马将,但是不大喝酒(海边的人喝一两碗是不算能喝,照市价计算也不值十文钱的酒),所以生意很好,时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诸暨嵊县去。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只需走到缸边屈着身听,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好像是螃蟹吐沫(儿童称为蟹煮饭)的样子,便拿来煮就得了;早一点酒还未成,迟一点就变酸了。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别人仍不能知道,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正如古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 大人家饮酒多用酒盅,以表示其斯文,实在是不对的。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浅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槟杯。平常起码总是两碗,合一“串筒”,价值似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可倒而不可筛,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筛出来的不大好吃。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荡”(置水于器内,摇荡而洗涤之谓)串筒,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客嫌酒淡,常起争执,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以勿荡串筒,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能饮者多索竹叶青,通称曰“本色”,“元红”系状元红之略,则着色者,唯外行人喜饮之。在外省有所谓花雕者,唯本地酒店中却没有这样东西。相传昔时人家生女,则酿酒贮花雕(一种有花纹的酒坛)中,至女儿出嫁时用以饷客,但此风今已不存,嫁女时偶用花雕,也只临时买元红充数,饮者不以为珍品。有些喝酒的人预备家酿,却有极好的,每年做醇酒若干坛,按次第埋园中,二十年后掘取,即每岁皆得饮二十年陈的老酒了。此种陈酒例不发售,故无处可买,我只有一回在旧日业师家里喝过这样好酒,至今还不曾忘记。 我既是酒乡的一个土著,又这样的喜欢谈酒,好像一定是个与“三酉”结不解缘的酒徒了。其实却大不然。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至少要花费两点钟,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但我却是不肖,不,或者可以说有志未逮,因为我很喜欢喝酒而不会喝,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自从辛酉患病后,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定量是勃阑地每回二十格阑姆,葡萄酒与老酒等倍之,六年以后酒量一点没有进步,到现在只要喝下一百格阑姆的花雕,便立刻变成关夫子了。(以前大家笑谈称作“赤化”,此刻自然应当谨慎,虽然是说笑话。)有些有不醉之量的,愈饮愈是脸白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可以欣羡,只可惜他们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好像是美人之不肯显示她的颜色,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黄酒比较的便宜一点,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其实别的酒也未尝不好。白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泡,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虽然可喝少许,也总觉得不很和善。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只是仿佛新酒模样,味道不很静定。葡萄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勃阑地。我觉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至于酒则很有功夫,决不下于中国。天天喝洋酒当然是一个大的漏卮,正如吸烟卷一般,但不必一定进国货党,咬定牙根要抽净丝,随便喝一点什么酒其实都是无所不可的,至少是我个人这样地想。 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 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有人说,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所以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罢。醉了,困倦了,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昏迷,梦魇,呓语,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其实这也是有限的,倒还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里的耽溺之力还要强大。我喝着酒,一面也怀着“杞天之虑”,生恐强硬的礼教反动之后将引起颓废的风气,结果是借醇酒妇人以避礼教的迫害,沙宁(Sanin)时代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那么杞天终于只是杞天,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罢? 酒话 ◎黄裳 酒,有时我也还是喝一点的,但已非复当日的豪情。喝酒,好像也是和年岁有关的。大抵是年轻时能喝,等到年纪逐渐加大,酒量也就逐渐减低。不过,也许有例外。 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已经记不起来了。印象中最早一次自斟自饮,是四十多年前在成都的事。那时我从沦陷的上海辗转来到成都,袋里只剩下了大约四角钱的样子,但终于在 旅馆里住下来了,因为随身还带着一只箱子,可以做抵。走到街上去吃晚饭,不知怎地选了一家小酒店,坐下来要了一碗(二两)大曲,慢慢地吃了,又要了两只肉包子当饭,用尽了袋里的余钱。老实说,我实在是一点借酒浇愁的意思也没有,欢欢喜喜第一次领略了四川曲酒之美,不由得想起了李商隐的诗“美酒成都堪送老”,觉得飘飘然,却一点都不能领会诗人哀伤的心情。 这以后,只要袋里有点钱就总要上酒馆去坐坐,有时候也拉朋友一起去。重庆的酒店里有近十种不同等级的曲酒,价钱高低不一。堂倌用不同的酒盏筛酒上来,最后算账就按照不同的酒盏数目计算,一些都不会错。记得价钱最贵的一种是红糟曲酒,使用的是一只玻璃杯。这样喝着喝着,面前往往有一叠酒盏摞在那里,于是始有点“酒徒”的意味了。还有不能忘记的是在扬子江边的茶馆里吃橘精酒,那和大曲比起来简直就算不上是酒,但无事时喝一点也是挺有意思的。 总之,我是在四川学会了喝酒的。在我的记忆里也只有大曲才算得上是酒的正宗。 回到上海以后,又有过一次愉快的吃酒经验。P先生的母亲从四川到上海来了,随身带着一坛绿豆烧,也是四川的名产。那天我在他家吃饭,喝了很不少,只差一点没喝醉。时间也是晚上九十点钟,该到报社去上班了,摇摇晃晃地赶了去,还写了一篇短评。 这些喝酒的回忆都是很愉快的。正是因为“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酒是可以解忧的。“文化大革命”中,市面上什么白酒都没有了,只有橱窗里还陈列着“冯了性药酒”,是用白酒浸的,也并未尝过,只不过在闲谈中偶然提起,不料被人捉住,作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把柄,狠狠地被斗了一通。直到这时,我还是不懂得酒是可以解忧的。曹雪芹“酒渴如狂”,照我想也是他实在想喝酒了,并不是想逃避什么人间的忧患。这才是真能懂得酒的趣味的。 1987年9月14日 “同题散文经典” 丛书全套32册,将人生需要面对的32个主题“一网打尽”:从自然的山、河、湖、海、春、夏、秋、冬、风、花、雪、月、鸟、虫、狗、猫,到人文的衣、食、住、行、父、兄、师、友、醉、生、梦、死、烟、茶、园、艺,主题丰富、独特且贴近生活,能满足读者对不同主题散文的阅读需求。有些已进入课本和考题,有些未来将是学生课文和考题选取的宝库;同时,该系列也是成人休闲阅读,提升文学素养的必备佳品。 ★精选跨越百年的名家名篇,作者阵容强大,名篇脍炙人口。名家齐聚一堂: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郁达夫、朱自清、周作人、林语堂、萧红、周瘦鹃、梁遇春、冰心、张恨水、丰子恺、巴金、汪曾祺、王安忆、迟子建、余华、阿来、叶兆言、苏童...... ★精心编排,新颖独特:将不同名家创作的相同主题的经典散文编选在一起,形成每册内容相对集中的格局,这种同题编排方式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视角,便于对比阅读和深入理解同一主题下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与思想内涵。 ★汇聚顶尖作家佳作,全面呈现汉语表达的辽远与幽微;浸润个体生命体验,以散文的目光走进中国文化。能快速提升孩子的阅读理解能力、作文水平等语文素养。 ★涵盖自然、人文等诸多主题,蕴含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能够帮助孩子开阔视野,养成多元思维方式,使其精神世界更加丰富。 ★主题丰富多样且趣味十足,篇幅适中,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找到乐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