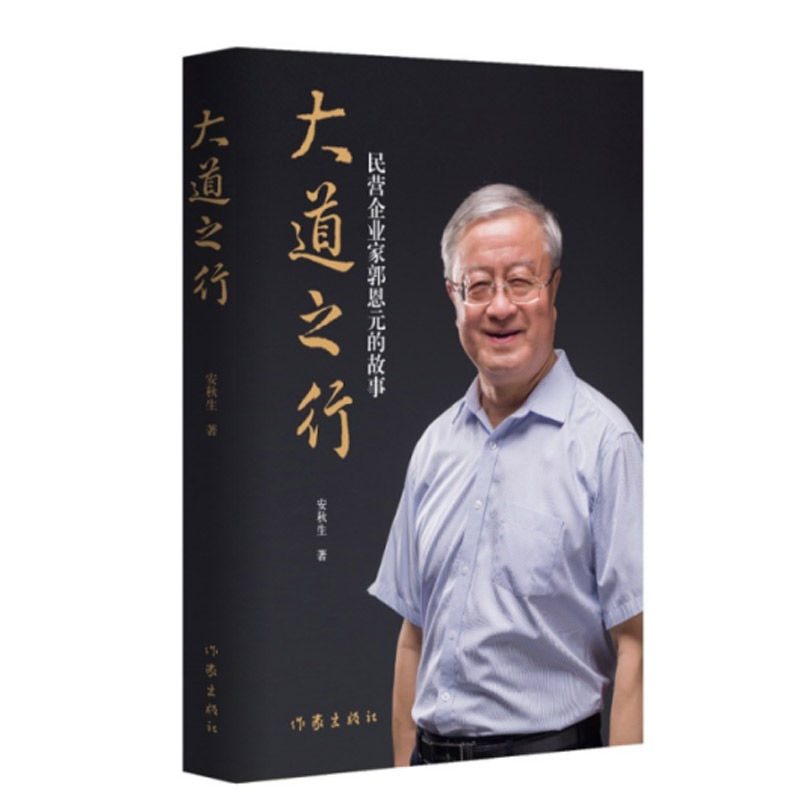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46.64
折扣购买: 大道之行
ISBN: 9787521201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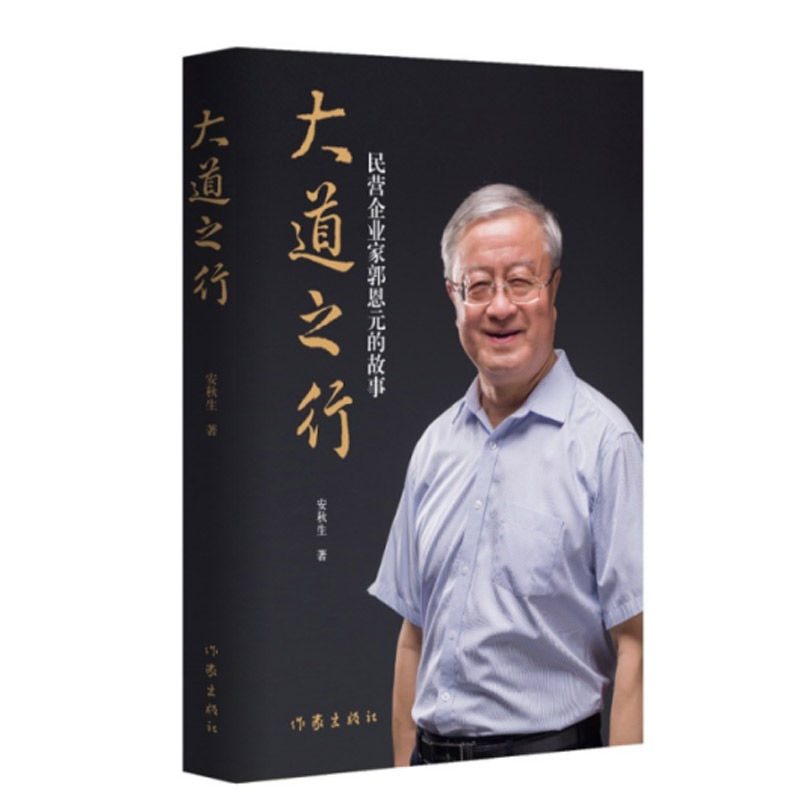
安秋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邯郸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邯郸市散文学会主席,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协散文艺委会副主任。著有诗集《心如四季》、散文集《永远的虹》《把手给我》《角色》、纪实文学《药鬼子纪事》等。
引 子 我们这时代,有两个词最容易被人当作话题:财富,人生。 把两个词放到一起,又形成两个新词:人生财富,财富人生。 顺序一颠倒,意义大不同。 拥有大量物质财富的人,他们获取财富的努力、过程、成果、体验等,构成他的财富人生。 任何一个人,他们的健康、知识、经验、阅历、名声、荣誉、德性等非物质的东西,都叫作人生财富。 有的人可能拥有财富人生,但不一定获得太多人生财富;有的人拥有太多人生财富,但没有财富人生。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造就了一个富人阶层,众多的富豪以炫目的色彩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各种各样的活剧。富人们的人生,大约可以称之为财富人生吧。 以“关注实践和实践者”为口号的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 2003年4月来到中国。《福布斯》中文版制定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每年更新一次中国富豪排名(只包含大陆地区)。在福布斯2007中国富豪榜400人全榜单上,郭恩元家族排名199位。而在2009年11月出炉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郭恩元家族排名353位。 民营企业家郭恩元,1948年出生,河北武安人,时任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有着严格的入选标准与程序。既然登榜,郭恩元家族,已属中国著名富豪之一的事实不容置疑。 人们或许不知,此前二十年,郭恩元只是太行山区一家乡镇小厂的厂长;此前三十年,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 富豪如何创造财富神话,总是人们喜欢探求的秘密。那么,郭恩元怎样从大山里的一位普通农民,一路奔跑,在几十年后跻身百亿富翁的行列?也就是说,他拥有什么样传奇的财富人生? 另一方面,富豪们的人生财富,又决定了他们是否值得尊敬。那么,郭恩元又是怎样一个人?他与其他富豪有何不同? 许多经验告诉我们,生活并非一场盛大的红毯宴会,谁也没有可能步履轻盈还获得喝彩一片。郭恩元的生命历程中,有过多少艰苦的奋斗和执着的坚持,以及痛苦的蜕变? 带着无数的问题,我走进了地处太行深处的河北普阳钢铁公司,走近了郭恩元。 第一章 小厂大业 一方水土和一个时代 郭恩元1948年春出生于河北省武安县阳邑镇柏林村。按中国的十二生肖算,这一年是鼠年。 武安地处太行山东麓,河北、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处,早在一万多年前,在这块土地上就有先人繁衍生息。战国时代这里正式设县,并开始了冶铁,因为位置重要屡屡发生战事,“武安瓦震”便是赵国与秦国之间的一场战争留下的典故。武安地域广阔,最多时达两千平方公里有余,地势上西高东低,兼具山地、丘陵、平原等地貌特点,历史上山场广阔,林木茂盛,物产较为丰富,地下蕴藏着多种矿藏,其中煤、铁、石灰岩、非金属资源尤为丰富。从明朝中叶开始,这里的人们大规模外出经商,创造了“最多商贾”的地域现象,逐步形成一支著名的商帮——武安商帮,以经营绸缎、药材为主。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一度垄断东北的药业,“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抗日战争时期,武安西部属于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1945年全境解放。 阳邑镇位于武安最西端,是出入武安的“西大门”,背山临川,为南洺河之阳的一座古城邑。这里扼西川之口,是河北通往山西的要冲,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货物集散地,商业极为繁盛,一条商业街长达1.5公里,清末民初即有“小上海”之美称。民国版《武安县志》记载:阳邑镇为西疆要区,人烟稠密,市肆栉比,为柿饼、桃仁集散市场,居者农商各半,武安的山货以核桃仁为大宗,柿饼、柿脔、花椒等次之。阳邑镇最称发达,每年秋季,客商云集,市面颇为繁盛……武安自古有谚云:武安县八大镇,数了阳邑数和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太行根据地的商贸中心。 柏林是阳邑镇管辖的村庄之一,距阳邑五华里,相传建村于秦代,因为古代多长柏树得名。这是一个特大村庄,现有人口达七千多人,新中国成立后分为东街、西街、前街、寨上四个行政村。柏林村历史上水源缺乏,靠旱池、水窖引水蓄水为用,为了争夺水源保卫生存权利,曾与邻村械斗和兴讼,民风颇为强悍。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武安县抗日政府的后方基地,薄一波、杨秀峰等领导人曾生活战斗在这里。1940年,八路军在柏林村征兵,曾一次征集一个整编连。同年,八路军还在柏林村南一座小山包前摆开战场狙击日寇,打过一场惨烈的战役,史称“孤的山战役”。解放战争期间随刘邓大军南下,柏林子弟兵勇猛顽强作战勇敢,曾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一百多人。 郭恩元,便出生在柏林西街一个窄狭的院落里。 郭恩元的家庭,是一个真正如草根一般平凡的农民之家。他的祖上,都是默默无闻之辈,除在家谱上可能留下一个名字之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被人提起。但郭家祖祖辈辈为人忠厚家风纯朴,郭恩元的父亲郭锦堂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一年有半年以上时间赶着家里的三头骡子给八路军、解放军往前线运送物资,是周边有名的支前模范。淮海战役期间,老人家曾经一走七十二天杳无音讯,在家里人焦急得近乎绝望时,才平安返回。 人民公社时期,郭锦堂曾担任生产队保管员近十年、饲养员六年。他在担任饲养员期间尽心尽力,能用跟别人一样多的草料把集体的牲口喂养得膘壮体肥,深得父老乡亲的称道。 从祖辈父辈那里继承而来的良好家风,对郭恩元的事业最有帮助的便是这种脚踏实地的秉性,干什么事都踏踏实实,干什么事都竭尽全力,不投机、不取巧、不偷懒、不使滑。还有宽厚的性格,遇事让别人沾光,把吃亏留给自己。 像许许多多同时代的有志青年一样,出生在山区农村的郭恩元懂得,生活留给农村孩子的出路甚为逼仄,要跳出农门出人头地,面前只有两条道儿比较现实,一是当兵,二是上学。 郭恩元为自己选择了上学。他认为自己更适合读书,更适合通过读书掌握知识来改变命运,因为从小学起,他就一直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他认定自己有实力有才华一步一步考上大学。 在阳邑中学读书时,少年郭恩元有两个特点给人印象较深:第一是特别喜欢数理化,喜欢到了痴迷;第二是个“杠子头”,爱抬杠出了名。同时,他也是喜欢对身边事物“琢磨”的人。 在上初中时的一个暑假里,参加生产队劳动之余,郭恩元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改变住房条件。那时,农村房屋的内墙都是泥土墙,看上去黑乎乎的不美观,每年过年大扫除时,总是尘土飞扬很是呛人。能不能也像学校的教室那样,把家里的房子改为“沙灰墙”呢?郭恩元把想法告诉了父母。父母认为这是小孩子家的“异想天开”。经不住郭恩元反复述说“沙灰墙”的好处,父母询问街坊邻居,有人说住“沙灰墙”的房子生病后“不出汗”对身体不好。郭恩元对此付之一笑说:学校那么多学生,没听说谁因此不能出汗。按照郭恩元的建议屋墙改造完成后,整个房间干净亮堂起来,街坊邻居大为惊叹,都说从小看大,三岁看老,郭锦堂家的二小子可真不简单。大家纷纷来向郭恩元讨教沙灰抹墙的方法,动手把自己的家“装修”一新。 那时候全国人民学雷锋,郭恩元就特别喜欢雷锋的“钉子精神”,喜欢用“钉子”的“钻劲”激励自己。他学习认真,肯下苦功,课堂内外,不管什么问题,非要弄出个究竟,非要刨根问底“研究透”,非要与人辩出个是非高低。 初中毕业时,一些与他成绩不相上下的同学选择考取中专,因为上中专可以早上班,早拿工资,同学们劝郭恩元也走这条路。郭恩元不为所动,坚持报考武安县第一中学读高中。 郭恩元早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中专毕业生当个教师或者小职员,每月充其量拿二三十块钱薪水,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与大学毕业的人相比,都差出很大一截,更不用说事业发展上,天地也是那样狭窄。所以上中专,那不是郭恩元想要的前程! 郭恩元以优异成绩顺利考入武安一中。高中上了一年,他与那个时代的所有学子一样,笃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如既往发奋读书,在数理化等主要课程上名列前茅,在老师同学眼里,郭恩元“又红又专”,是理所当然的大学苗子,正常走下去,考大学绝对没问题。 还有,他喜欢打篮球,在学校篮球队里是一个绝对称职的后卫。 风云突变,天道弄人。郭恩元高中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武安中学作为本县的最高学府,理所当然首先被“发动”起来,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放下书本,投身到运动之中。 父母亲天生胆小,得知学校乱哄哄的局面甚是担忧,担心儿子在外边闯祸,更担心儿子遭遇不测,在家里连觉也睡不好。他们觉得儿子即便留在学校,也是白耽误工夫,读不成书,便三番五次捎信让郭恩元回家。恰巧郭恩元崴了脚,1967年秋,郭恩元回到老家柏林,在家里住了百十多天。父母亲苦口婆心力劝儿子退学回家,郭恩元暂时脱离开学校那个狂热的环境,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就答应了父母,反身去学校取行李。 那个年代,全国各大学的招生相继无限期地停止,他的大学梦早已破灭了。 看似阴差阳错,实质上郭恩元的命运,是一代人共同的宿命。 小小舞台,也能亮出自己的“精彩” 1968年春节前夕,郭恩元回到柏林村,身份由学生转换成为一名青年农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知识青年回乡可能有两个选择,一是教学,二是参军。柏林村虽然地处山区,但同样受到“文革”运动的洗礼,派性非常严重,郭恩元因为在武安一中参加“保皇派”的经历受到歧视,既无法教学也无法当兵,只好重操老祖宗的本行——种地(好在此时有一句口号很漂亮:为革命种田)。除此外,郭恩元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知道哪扇门还为自己开着。 回到老家虽然灰头土脸前途渺茫,但农家子弟没有资格颓废,更没有人听你长吁短叹。“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可为的”,这句风行一时的“最高指示”,给了被发落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体面的理由——在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生即是知识青年,回得乡来就是文化人,就是村里的“秀才”了。 宽厚的乡亲们并不在意郭恩元为了什么回到农村,正如某出戏里的一句台词:只要肯回来,就是好样的,农村敞开怀抱欢迎。乡亲们看重这个年轻的文化人,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三年半(1969—1971)之后,让他当上了第四生产队会计。在当时的农村,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都算是文化人能够占据的“重要岗位”。 会计在生产队里大小也算个“干部”,是这个生产队几十户一百多口子的当家人之一,除了记账算账拨拉手中的算盘,也介入生产队的日常管理。读过书的郭恩元渐渐参与决策,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用在生产队的工作上。 有一年,阳邑公社开会,向各村推广杂交玉米种子,柏林村五十六个生产队没有一个购买,原因是买种子要花钱,万一用了这些种子并不能增产,那就“赔”了,大家谁都不愿意去“冒险”。郭恩元听老师讲过杂交种子,相信杂交种子的优势,一下子购买了五十多亩的种子,在他管辖的土地上大面积种植。 到了秋季,郭恩元的第四生产队玉米喜获丰收,三百亩地的产量,每亩平均破天荒达到了四百多斤,创造了阳邑公社有史以来玉米亩产量“过黄河”的纪录(亩产四百斤以上为“过黄河”,六百斤以上为“跨长江”)。 这件事在十里八乡反响强烈,金灿灿的收成,让大家佩服起郭恩元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眼光。第二年,阳邑公社农场的杂交玉米种子不待推销,还没脱粒,在场上便被各生产队疯抢一空。 “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有蜻蜓立上头”。一个小小的会计也有这么大的作用。郭恩元脑子里的“小九九”,也随着手下的算盘珠开始拨动起来。 柏林西街与周围的村庄一样,是一片“望天收”的黄土地。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个汗珠摔八瓣,实在换不来多少果实。除了把打出的粮食卖给国家,别的没有收入,年底一算账,每个工分只有可怜巴巴的三两毛钱,去供销社仅够买一包廉价的烟卷。这还必须是风调雨顺好年景,要是赶上老天爷不长眼,受点旱灾涝灾啥的,社员们连肚子都难以填饱。 郭恩元深知乡亲们的不容易,再多的劳动,再多的汗水,在柏林这样的苦寒地方,抛进这片贫瘠的土地,也甭想让它长出更多的东西。农民就该一辈一辈受穷?他不甘;农民只会种地?他不信!咋办?他思谋了好久,鼓起了勇气,和队长谈起了自己的想法: “咱不能想办法搞点副业,多挣点钱?” 队长很感兴趣,用目光把郭恩元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说:“那你就出去跑跑,看看能不能找点副业活儿干。” 郭恩元从姐姐家借来一辆自行车,骑着它,开始在武安范围内“调查走访”。他先是顺着公路跑,然后沿着铁路线跑,从阳邑到后山,从后山又到下白石、矿山,又到磁山、野河,花了半个月时间,总共走了武安城及周边的七个公社十几个工矿,在一个在建的车站找到了“商机”。他与地方铁路指挥部负责人商议,揽下了为地方铁路拉石子、料石等活儿。 按照工程进度的需要,郭恩元计算,得出动三十辆排子车才能拿得下这个活儿,而他队里排子车只有两辆。跟队长一说,队长吓了一跳,咱没有这个金刚钻,咋揽人家的瓷器活儿?缺少这么多排子车,咋办? 咋办?自己造! 郭恩元第一次表现出他的魄力。他把远远近近的木匠都找来,为他砍树造车。 拉车一般都用驴骡马这类大牲畜,生产队只有驴和牛。郭恩元说,驴不够,牛也可以拉车嘛。 这个冬天,当别队的社员都在“猫冬”,或者扛把镢头刨刨堰头混个工分的时候,郭恩元带着柏林西街各生产队的劳动力,牵着牛,赶着驴,在建筑工地忙活了整整一百多天,大队人马干到阴历腊月二十四,回来时,还捎带着往涉县造纸厂卖了一批麦秸,直到腊月二十八才全部回到柏林。其间结账分红,哇!第四生产队的工分日值破天荒达到了一块多,家家分红,户户数钱!手里有了票子,割肉的割肉,扯布的扯布,买鞭炮的买鞭炮,好喝酒的家伙还奢侈一把,平生第一次拎回了茅台酒,大家扎扎实实过了一个宽裕年。 吃水想起打井人,这时候大家都说,郭恩元这个年轻人不吭不哈,倒真是不简单,有头脑,有眼光,有办法,有魄力,以后咱就听他的,准没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郭恩元所在的队始终坚持农业副业一起抓,部分劳力常年在外揽活干,农闲季节则全员出动,大家伙儿共同努力,他们这个队的分红比其他队都高,工分日值保持在了八九毛以上。别小看这不到一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了,算一算,一个青壮劳力的月收入,超过了一般公职人员呢(当时第四生产队的农业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执行的都是“小包工”,效率很高,所以工分比较“毛”,有的劳力最高一天可以挣110分,40—60分是常事)。 日后,不大爱谈自己过往的郭恩元却偶尔同人聊起这段经历,善于听话的人会听出老郭对这段经历有几分得意,有几分炫耀。或许郭恩元想用这段“史实”证明,即便是留在生产队当农民,他也不会是一个“一般”的农民,而会是一个有头脑有作为的新型农民。 郭恩元的指挥才能和改革意识也在此时表现出来。 有一年,郭恩元的生产队种了七十多亩谷子,“薅小苗”的时间紧迫,弄不好就会荒地。当时,各生产队出工有惯例,都是早上8点敲钟集合,慢慢腾腾走到地里动手干活儿,就到了9点半。干一个多钟头,天大热了,就收工回家。下午也这样,磨磨蹭蹭干一会儿就草草收工,一天下来,总计劳动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效率不像话,但谁也没有想怎么去改变。郭恩元和队长商量,要想不荒地,就得改变“作业模式”。他安排社员凌晨4点就下地,趁凉快干活儿,早饭在田间吃,由生产队安排“绿豆小米干饭”,专人送到地头,大家只需下地时自带咸菜就可吃上“工作餐”,省去了回家吃饭来来回回的时间。到上午11点多天热了,就收工好好休息。下午3点多上工,越干越凉快,干到晚9点多收工。算一算,每天可以干十一个小时以上,大大加快了日进度。这样紧抓挠,不到二十天时间,十二名社员就把七十多亩的谷子全都锄好了。 锄完头遍地,刚巧连续几天下雨,第四生产队地里的谷苗清清爽爽长势良好,别的生产队却因为没有锄完荒了不少地,草苗抱成一团。“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季的收成打了水漂。学习这个经验,自第二年开始,各个生产队纷纷仿照第四生产队,改变了“作业模式”。 自古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生产队期间,各级都重视积肥,各生产队都有自己多个积肥点,春耕之前或麦收之后集中运到地里,这项工作叫“转粪”。多年来,生产队转粪都是靠“担挑筐抬”,一个大粪堆,十几个劳力七八天才能弄完,耗时不说,人还受罪。郭恩元提出用排子车拉粪,一些老农表示反对,说排子车进地会把地轧“死”(瓷实之意),郭恩元说,轧死了再安排人刨。他力排众议,集中社员动用排子车拉运,一个大粪堆,一个早晨就运完了。相比别的生产队,转粪效率提升了几十倍以上。 还有一件事,至今在柏林被人们津津乐道。“文革”后期恢复自留地,郭恩元家里分了半亩自留地,他在这块地里种小麦。下种的时候,他一反常规,半亩地竟然播下了二十六斤种子,而乡亲们一亩地满打满算也只是下五斤左右,他是别人的十倍。一个老庄稼把式看到后,对郭恩元摇摇头说,没见过你这个种法,麦子这样稠,等着收麦秸吧,肯定少不了。 结果却让老把式大为吃惊,郭恩元的半亩麦子长势良好籽粒饱满,产量达到了五百多斤,一时引起了轰动。这样高的小麦产量,老人们听都不曾听说过。 郭恩元连续几年靠密植获得丰收后,老把式宣告自己真的服了气,他对郭恩元说:“我种了一辈子的地,竟然不抵你这个没有种过地的年轻人。” 郭恩元说:“您老种地凭的是老农经验,我是执行毛主席的农业八字方针‘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科学种田,合理密植,肥水供应充足,产量自然就高了。” 此后,老把式逢人便说:“我种了大半辈子的地,都在瞎忙活,郭恩元有头脑了不起,不服不行,不相信科学不行。” 就这样,郭恩元的家庭每年自产小麦五百斤,加上生产队分给的小麦五百多斤,一家人就能够常年吃上白面了。郭恩元说,在柏林村,乃至整个阳邑镇,他家是最先解决“吃细粮”问题的。 1985年前后,郭恩元和他的妻子又靠种好责任田彻底解决了“花钱”问题。怎么解决的呢?他打破了只种粮食的传统,在承包田种植了3.6亩山楂树、0.7亩苹果树,收获之后运到邯郸市场集中批发,短时间就销售一空。仅此一项,每年收入最少六千多元,多时达到一万两千多元,再加上他在修配厂的工资收入,郭恩元全家五口人便脱贫致富,花钱从此再不犯难。——这是后话,一并记在这里。 由于在“生产队会计”这个小小的舞台上崭露头角,郭恩元被公社党委书记发现,将他选调到当时颇为热门的公社农机修造厂工作,从而为他的人生之路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和机器说话,和车床交朋友 郭恩元在小学读书时,便知道一句鼓舞亿万中国人的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迟到而缓慢,武安这个山区县似乎更是如此。据《武安县志》记载:1948年,本县开进第一台拖拉机;50年代初,平区开始使用耘锄,1958年前后推广双铧犁,1954年11月,伯延建起第一个拖拉机站;1969年以后,各公社逐步建起拖拉机站。与拖拉机逐步用于耕播的同时,脱粒、排灌、植保、运输等机具也在逐年增加。农机具在农业生产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农机具的维修和小改进、小制造就越来越紧迫,“农机修造厂”于是应运而生。 公社办农机修造厂(修配厂),是1970年代的一大经济现象。有了它,农村距机械化的美好前景,似乎近了一大步。 阳邑公社拖拉机站诞生于1968年,虽然只有两三台拖拉机,但在山里人的眼里,已经是了不起的“先进武器”。阳邑作为武安第一大镇,又有悠久的工商传统,经济发展上理应先进一步,除了推行农业机械化,六十年代还先后办起了石子厂、石料厂等企业摊点。 当时的口号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业一概叫作“副业”,有了“副”,人民公社的发展才算得“全面”。 1972年,阳邑公社拖拉机站计划成立修配厂。农村办工厂,要啥没啥,缺资金,缺设备,更缺人才,起步很难。没有厂房可以建,没有机器设备也可以买,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从哪里来?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武肇林决定放开视野选拔人才,从公社管辖的十六个大队中挑选管理人员,郭恩元这个高中生进入了他的视野。 1972年5月10日,郭恩元正式到公社农机修配厂筹建处上班,继续担任会计,报酬是“工分加补贴”,即在修配厂上一天班,阳邑公社给柏林西街第四生产队开具12分工分,同时一天发给几毛钱的生活补贴(6毛)。郭恩元感到待遇不低,比在生产队干农活,优越了许多。 修配厂的厂址选在阳邑南河一片空地上。要建厂,公社又拿不出多少钱,只能小打小闹,因陋就简,“穷拼兑”。盖厂房没有原料,就拆了一座老戏楼和一座神庙,把砖头瓦块梁檩木石等旧物料派作新用,盖起几间房子算是车间。设备买不起新的,就从武安棉油厂买来一台旧皮带式机床,一台“牛头”刨床,两台平口钳,然后自己动手垒了一盘烘炉。 修配厂一次招收了十七名青年工人,经短期培训后,分为车工、钳工、焊工、锻工。随之采购原材料,于1972年10月正式“开张”,主营业务是维修农机具和锻打一些锄、镢、镰等小型农具。 后来,修配厂又从武安机械厂买来一台旧皮带式机床,陆续添置了四台“20”式机床、一台齿轮式机床、三盘烘炉、一台电焊机。 在修配厂里,郭恩元的职务是会计,厂小,业务少,会计的工作量也不大,一本明细账总账,十几本分类账,一个月制几次传票,就是全部工作内容。干这么点事,郭恩元是“手捏烂杏”,不费多少力气。事多事少,郭恩元总是按时上下班,每天早来晚回,风雨无阻,穿梭于阳邑至柏林的“两点一线”之间。 修配厂的工人多数和郭恩元岁数不相上下,二十岁出头,正在不知愁的年月。年轻人在一起,除了干活就是玩,那时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也买不起酒喝,扑克、象棋、军棋、跳棋就成了业余生活的主角,一有空,就凑到一堆甩上两把战上两盘。打扑克起初的玩法是“下台”、“争上游”,后来兴起一种“升级”,四个人打对家玩配合,输赢差数记得清楚,大家乐此不疲兴高采烈,一玩一个大半宿。 郭恩元与众不同,他不喜欢下象棋,也不喜欢打扑克,“娱乐”哪个圈里也没有他的身影。他手边总是有很多书本,没事了就复习高中课程——他心中,还藏着一个考大学的梦。工友们起头还拽他参加打扑克,看他一点都打不起精神,也就不再招呼他。 郭恩元显得有些不合群,甚至有些孤独。他本来也可以溜溜逛逛混日月,但他不乐见宝贵的光阴毫无意义地白白流逝。 郭恩元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除了看报读书,还喜欢学习尝试,喜欢钻研探索问题。这时候,他对厂里各式各样的机器设备感起了兴趣,尤其是各式车床,他都想去亲手摆弄一下试试,工友们歇息的时候,正是他上车“练手”的好时机。 在机器面前,郭恩元表现出少有的悟性,别人用尽吃奶劲儿都学不会学不好的操作,他在旁边瞅上几眼,就能看出门道。当然,他会在心里对照书本上的知识,一边操作一边琢磨其原理。渐渐地,他把厂子里能够摸到的十八般兵器一一摸熟,玩得像模像样,尤其是皮带车床上一些被人视为“核心技术”的活儿,他不仅拿得起来,而且俨然行家里手。 当时学习这些,郭恩元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感兴趣而已。他感到与机器在一起,不仅有乐趣,而且常常获得意外的哲思。 有时候,郭恩元会在车间来回转悠。 他看到,这边机床开着,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戴着浅蓝色工作帽和黑框子防护眼镜的工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操作机器。螺栓的毛坯固定在车床上,以均匀的速度旋转着,慢慢地、慢慢地靠近了车刀。嗤嗤嗤,被车削下来的铁屑形成了一个个粗细相近的螺旋状的卷,因为车削时产生的高温,铁卷呈钢蓝色。 郭恩元俯下身,捡起一条铁卷仔细端详着。他想到,一件毛坯变成一个合格零件的过程,恰如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有“迎难而上”的锐气,不怕任何困难,坦然接受磨砺;其次要敢于舍弃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才可能成就一个新的自己…… 另一边,两盘烘炉开着一盘,一个小伙子光着膀子在拉动风箱,一把即将成形的镢头在烘炉上烧着,为避免热量流失,镢头坯上还盖着两片古老的蓝瓦,红中带蓝的火苗子在风箱有节奏的鼓风下有节奏地冒出来,四周围弥漫着一股煤炭燃烧的特有的香味。 镢头坯烧好了,师傅用钳子夹住,放在了铁砧上,拉风箱的小伙子已经大锤在手,与此同时,师傅手里的“小叫锤”敲在了已经烧软了的镢头坯上。小叫锤“叮”地一响,大铁锤“咚”的一声就砸在了小叫锤刚才砸中的位置,速度极快,准确无误,而且节奏分明。小叫锤在铁砧上轻轻敲击两声,大锤就在原来位置上连击两遍,叮咚之声不绝于耳,形成一节动听的乐曲。渐渐地,镢头在连续不断的敲击下,呈现出了预期的形状。 郭恩元久久琢磨“小叫锤”扮演的角色:它力量不大,却发挥着指挥和引领的作用,好比乐队、军队等任何一个团队,都必须有一个小叫锤,有它“智慧”的指挥,有大家“力量”的配合……郭恩元一次次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段经历,为郭恩元以后办现代化大型工厂,在设备问题上奠定了足够的自信。以后几十年里,他无数次选择采购大型设备,还经常主持对机器装备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亲自充演“总工”的角色。 郭恩元独来独往沉默寡言的个性,慢慢得到工友们的理解和认可。大家感觉到,郭恩元的脑子一刻都没有闲着,他脑子里想的事,与他们大不一样。 一天,石文彦等人围到郭恩元身边,对他说: “大家都知道你念书多,爱琢磨事,都说你脑袋瓜子聪明,一学就会,一点就通,还说你在生产队当会计就能给队里挣大钱,你倒是给咱厂想想办法,让咱大伙多挣点钱呀。” 刚说了几句,农机站站长兼任修配厂厂长的靳武廷不知从哪儿闪了出来:“大家都闲了?呵呵,开啥会呢?”大家赶忙回到自己的岗位,各自忙各自的去了。 “恩元,你别走。”靳武廷叫住郭恩元,站着便宣布了一个决定:“别管账了,去阳邑街上吧,那儿三个白铁匠敲白铁桶,你去那边开票收钱吧,整天闲着没事干也不好,是不是?” 然后,靳武廷把嗓门提高了一度,不知是给在干活的工人说还是给郭恩元说:“上个月的生活费,还得推迟几天再发,这钱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出力流汗挣来的!”厂长的话说得没错,但此时在工人的耳朵里,却有另外一种味道。 当时面临生存危机的,不只是阳邑公社修配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武安县四十多个公社,社社办有农机修造厂,几乎个顶个的不景气,问题出在修造厂的经营宗旨是“为农业服务”,业务量普遍不足,简单的维修和几乎是“纯手工”的制造,以及极其有限的“季节性”需求,注定了他们一年得有半年闲着没活干。 在阳邑老街给白铁匠开票的那七八个月里,郭恩元的脑海里时不时地翻腾起那天工友们说过的话。没错,修配厂不赚钱,有的月还亏损,工人的生活费自然无法按时发放,照这样下去,能够维持多久?万一修配厂散了摊子,自己该怎么办?再回生产队去犁耙耩种?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不光是我,这一干人怎么办?让大家都脱下工装再回去种地? 年轻的郭恩元当时对社队工业的前景看得并不清楚,但他隐隐觉得,这小打小闹的小作坊式的经营,这一天几毛钱的补助加工分,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农村办工厂,农民变工人,这都是早早晚晚的事,因为工业化是中国的必然方向。更何况这期间,国家已经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建设雄厚的工业基础,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眼下的一切都不明朗,但作为一个不甘平庸的知识青年,郭恩元觉得,必须为投身崭新的事业做好准备,等待一飞冲天的机会。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为修配厂持续亏损忧心的,不但有靳武廷、郭恩元,还有阳邑公社党委书记武肇林。本来办修配厂是为农业服务,并不指望它给社里赚多少钱,但起码要自己顾住自己维持正常运转。修配厂亏损,拖累得整个拖拉机站账面上一直是糟糕的赤字。不能按时发钱,免不了人心浮动,老实巴交的车床工因为拿不到生活费而焦躁,机灵油滑的拖拉机司机利用“方向盘”浑水摸鱼,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人心涣散,那只有关门大吉了。武肇林食不甘味,终于拿出了一个划小核算单位的决策:修配厂与拖拉机站分家,另起炉灶,单独核算,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也别再受拖累。修配厂是骡子是马,把他拉出来,单个溜溜。 第二天,双眼熬得通红的武肇林把自己的想法在会上跟其他社领导通了气,大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于是发文宣布:1975年1月1日起,修配厂脱离拖拉机站,单立门户,郭恩元担任修配厂厂长。 郭恩元上任后,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研究修配厂当前怎么办和今后的出路。念语录对此时的郭恩元来说,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他真心认为,毛主席的话最提气最鼓劲最励志: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郭恩元劲头很足,但大家内心里并不看好这样的“分家”,并不相信郭恩元当了厂长有能耐把修配厂救活。特别是被任命为拖拉机站站长的李冯贺和靳武廷,尽管他们和郭恩元在一口锅里吃饭、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了两年有余,但对这个喜欢“琢磨”的年轻人并无信心。 人们倒是觉得有理由替修配厂悲观。修配厂和拖拉机站不一样,拖拉机站当时有七辆车,其中有三辆波兰“奔奔”、两辆“东方红75”,当时的农村,拖拉机属于先进运输工具,“嘣嘣嘣”一发动,出去跑趟活儿,多少就能挣点钱。修配厂有什么好家当?几台烂机床,几盘烘炉,能干啥好活儿?干啥活儿能赚钱?怎样才能揽到活儿?一系列问题,想想都让人头疼。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虽然比别人多念过几年书,有啥高招能打开局面? “等着瞧吧,看他这头三脚咋着往外踢!” 年轻的郭恩元却是不温不火,一副信心满满的姿态。是他不知道修配厂面临的困难?不是;是他不知道有人相约要看他的笑话?也不是。啥都看在眼里,啥都记在心上,还能处变不惊镇定从容,这就是郭恩元个性上的独特之处了。 人分几种,是否自信,自信几何,人跟人差距很大。郭恩元向来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任何时候活人都不该让尿憋死,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相信路都在自己的脚下。郭恩元的自信与生俱来,而且在经过几十年的披荆斩棘之后,一直得以保持。 ——此处需要插叙的是,郭恩元像他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人一样,崇拜毛泽东,视毛泽东为终生的偶像。他尤其敬佩毛主席身上大无畏的豪迈气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都是他钟爱的诗句。 郭恩元走马上任,先给手下的二十多号人开会鼓劲:“别人说咱们离开拖拉机站不行,我不信这个邪!咱不傻不苶,个顶个都有技术在身,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好好干,咱一定会翻身,将来一定要超过他们!” 以石文彦为首的一帮子工人,也是暗中憋着一股子劲:“恩元,你说咋干就咋干,他们看咱不行,咱们非要不蒸馒头争口气!” 其实早在阳邑三里长街看着白铁匠叮叮当当敲打白铁桶的时候,郭恩元就在思考修配厂何去何从的问题。他想透了一件事:单单靠“为农业生产服务”,单单靠在阳邑本社范围内折腾,坐等上门有啥活儿干啥,不去想别的生财之道,修配厂是铁定没有出路的。修配厂要想办下去,必须打开眼界,拓宽思路,主动出击,走出阳邑,到外边去,找到长期的活儿干,找到赚钱的活儿干,才有可能扭亏为盈,走出生存之路。 郭恩元把厂子的事务简单做了安排,就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他走矿山,进工厂,起早贪黑,马不停蹄,四处去给修配厂找活儿。 地处峰峰矿区的峰峰金属支架厂是一个比较大的央企工厂。一天,郭恩元走进了这个厂供应部的办公室,堵住了孙部长。 民营企业家郭恩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