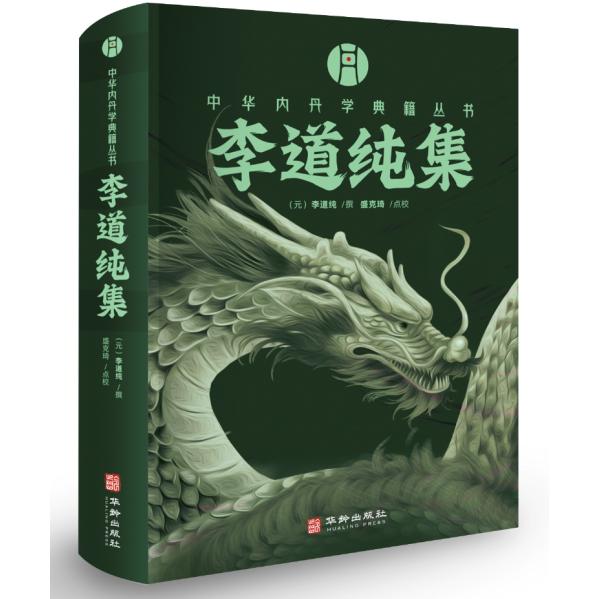
出版社: 华龄
原售价: 89.00
折扣价: 57.85
折扣购买: 李道纯集
ISBN: 9787516928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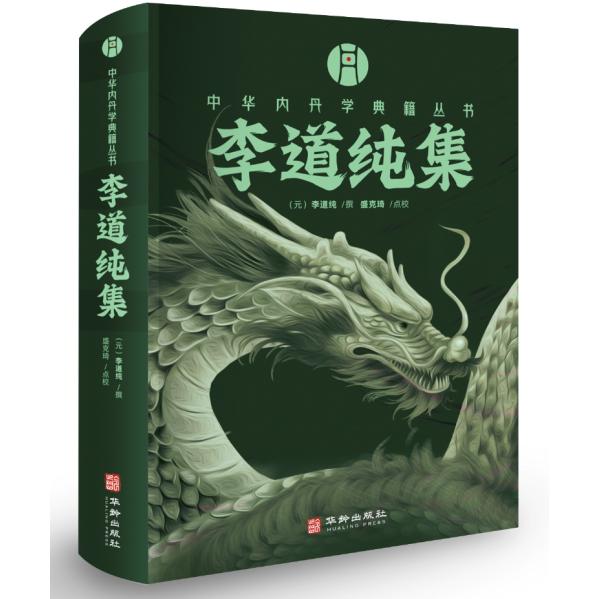
李道纯,字元素,都梁(今湖南武冈县)人,号清庵,别号莹蟾子。正史无传,生卒不详,主要生活年代是宋末元初之际。李道纯博学多才,广参遍访,曾遇异人点开心易,通阴阳阖辟之机,达性命混合之理,后得道飞升。李原是南宗白玉蟾弟子王金蟾的门人,是白玉蟾二传弟子,属南宗第七代。入元后自称全真道士,加入全真道,是江南最早的全真道士之一。其丹法远溯《易》《老》,近源《参同》《悟真》,阐述白玉蟾南宗一派丹法心传,但是他的丹道思想更具全真教派道儒释三教融合的特色。因此李道纯是一位道兼南北、学贯三教的一代宗师,是元初杰出的内丹学家。 盛克琦(曾用名盛克奇)河北唐山人。原籍天津蓟县。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丹道与养生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河北省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唐山市道教协会副会长。道学大江西派第6代。师承于陈毓照先生(1926—2012),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胡孚琛教授悉心指导,学习传统道家文化。主要著作:《全真选读》《西游记探幽》等十余部古籍整理作品。
《道德会元》卷上 都梁清庵莹蟾子李道纯元素 述 道○ “道”之可以道者,非真常之道也。夫真常之“道”,始于无始,名于无名,拟议即乖,开口即错。设若可道,“道”是甚么?即不可道,何以见“道”?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如何即是?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参学事毕。其或未然,须索向二六时中,兴居服食处,回头转脑处,校勘这令巍巍地、活泼泼地,不与诸缘作对底是个甚么?校勘来,校勘去,校勘到校勘不得处,忽然摸着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这个元是自家有的,自历劫以来不曾变易,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又道:“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况覆载之间,头头物物,都是这个;亘古亘今,只是这个;生天生地,只是这个。至于日用平常,动静作息,只是这个。一切有形,皆有败坏,惟有这个常在。天地虚空,亦有败坏,只有这个不坏。只这个铁眼铜睛觑不破,为甚觑不破?只伤他不曾觌面相逢,纵饶觌面相逢,也是蹉过。且道蹉向甚么处去?不得乱走,毕竟作么会?清庵向这里分明举似,只是欠人承当,倘遇知音,剔起眉毛荐取。咄!昨夜江头新雨过,今朝依旧远山青。 颂曰:至道之极,虚无空寂,无象无形,无名无质。 视之不见,抟之不得,听之不闻,觅无踪迹。 大无不包,细无不入,生育天地,长养万物。 运化无穷,隐显莫测,不可知知,不可识识。 太上老子,舌头无骨,向此经中,分明露出。 多言数穷,不如一默,这○便是,休更疑惑。 德 “德”之一字,亦是强名,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执持。凡有施设、积功、累行,便是不德也。只恁么,不修习,不用功,死灰槁木,待德之自来,终身无德也。这个“德”字,愈求愈远,愈执愈失。经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云:“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只这两句,多少分明,只是欠人承当。若是个信得及的,便把从前学解见知,声闻缘觉,一切掀倒,向平常履践处,把个“损”字来受用,损之又损,损来损去,损到损不得处,自然玄德昭著,方信“无为”之有益。经云:“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又云:“玄德深矣,远矣。”会么?咦!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则知君不可见。 颂曰:河沙妙德,总在心则,不可施为,何劳修积? 愈探愈深,愈执愈失,放下头头,掀翻物物。 后己先人,守雌抱一,纯一不杂,其德乃实。 修齐治平,皆从此出,妙用难量,是谓玄德。 经 “经”之一字,亦是强名。始者圣人为见世人随情逐幻,嗜欲迷真,中心业识之扰攘,灵地无明之炽盛,是以天真丧失,横夭伤残,不能复其本元,于是用方便力,开善诱门,接引群迷,使归正道。故著书设教,强名曰经。经者,径也,众所通行之大路也。虽然,读是经者,却不可泥在语言三昧上,亦不可离了此经向外寻求。须是向自己分上着意,把这五千余言,细细咀嚼,点点画画,不要放过,忽然嚼得一句半句透,这一部经都在自己,方信道开口不在舌头上。到这里,打开自己宝藏,把出自己经来,横拈倒用。不惟这一部经,至于三十六部尊经,一大藏教典,从头彻尾转一遍,只消一喝,都竟还委悉么?平地起风波,清天轰霹雳。谛听!谛听! 颂曰:此一卷经,妙用难评,人人本具,物物圆成。 堂堂蓦直,坦坦宽平,历劫不变,亘古无更。 头头应用,处处通津,未曾举起,已自分明。 不是我家真的子,谁人敢向里头行? 第一章[ 底本本无章目,校者划归一体化所加,下同。] 道○,可道,非常道(开口即错);名(唤做甚么),可名,非常名(唤作一物即不中)。无名(道也),天地之始(先乎覆载);有名(强名曰道),万物之母(生生不息)。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无心运化),常有欲以观其徼(徼,音叫。有意操持)。此两者(于不见中亲见,于亲见中不见),同出而异名(一体,一用),同谓之玄(体用一源),玄之又玄(形神俱妙),众妙之门(百千法门,皆从此出)。 上一章。虚无自然,真常之道,本无可道。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元始祖炁,化生诸天,随时应变之道也。道本无名,可名之名,非真常之名。天地运化,长养万物,著于形迹之名也。虚心无为,则能见无名之妙;有心运用,则能见有名之徼。妙,即神也。徼,即形也。知徼而不知妙则不精,知妙而不知徼则不备,徼妙两全,形神俱妙,是谓玄之又玄。三十六部尊经,皆从此出,是谓众妙之门。且道此经,从甚么处出?咄! 颂曰:昆仑山顶上,元始黍珠中。 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君通。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恶,乌路切。美是恶之因);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善是不善之由)。故有无相生(有生无,无生有),难易相成(易,以豉切。难事易,易事难),长短相形(长则短,短则长),高下相倾(才有高,便有下),声音相和(有声音,便有和),前后相随(前随后,后随前)。是以圣人(忘其美恶),处无为之事(忘其有无),行不言之教(忘其难易)。万物作而不辞(忘物),生而不有(忘形),为而不恃(忘情),功成不居(忘我)。夫惟不居(忘其所自),是以不去(去,上声。一切忘尽,真一常存)。 上二章。美之与恶,善与不善,如影随形,自然相待。至于有无、难易,互相倚伏。有美便有恶,有善便有不善,是以圣人不辞不有,不恃不居,彼此两忘,有无不立,是以常存而不去也。此一章,发明首章“体道”之义,使学者知“同出异名”之理,离此用而即此用,不堕于偏枯也。 颂曰:人有美恶,我无彼此。 一切掀翻,众泡归水。 目前指出千般有,我道其中一也无。 第三章 不尚贤(绝圣弃智),使民不争(忘我);不贵难得之货(绝巧弃利),使民不为盗(忘物);不见可欲(转物应机),使心不乱(忘情)。是以圣人虚其心(全性),实其腹(全命),弱其志(全神),强其骨(全形)。常使民无知无欲(空诸所有),使夫知者不敢为(夫,音扶,后同。知,音智。识法者恐)。为无为(寂然不动),则无不治(治,音持。感而遂通)。 上三章。不尚贤,接上章“处无为之事”也。谓不矜自己之贤能,则民淳;不贵奇货,则民富;不见可欲,则心定。圣人治平天下,必以修身为本。“虚心实腹”一节,皆修之要虚心而后志弱,志弱而后无知,无知故能忘我,此“不尚贤”也。实腹而后骨强,骨强而后无欲,无欲故能忘物,此“不贵难得之货”也。二理相须,足以了全性命矣。 颂曰:实腹真常在,虚心道自存。 不劳施寸刃,谈笑定乾坤。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太虚同体),或不盈(不自满),渊乎似万物之宗(不自见)。挫其锐(不露锋芒),解其纷(不随世变),和其光(不自明),同其尘(不自是)。湛兮似若存(常应常静),吾不知谁之子(上无复祖),象帝之先(唯道为身)。 上四章。上云“为无为”,故次之以“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谓不自满也。不自满者,必受益。挫锐解纷,虚中忘我之谓也。“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超虚无之外也。 颂曰:不识谁之子,焉知象帝先? 为君明说破,太极未分前 。 第五章 天地不仁(无为),以万物为刍狗(刍,牎愈切。爱养万物不为主);圣人不仁(效天),以百姓为刍狗(万民皈[ 皈,《道藏》本作“归”。]之,而不为主)。天地之间(虚中),其犹橐籥乎(虚用)?虚而不屈(无心),动而愈出(应变无穷)。多言数穷(数,所各切。○说不得),不如守中(虚中而已)。 上五章。天覆地载,化民育物,可谓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圣人爱民治国,亦复如是;修身养命,亦复如是。结上章“道冲而用之”之义也。 颂曰:无底谓之橐,三孔谓之籥。 中间一窍子,无人摸得着。 摸得着,为君吹出无声乐。 第六章 谷神不死(虚灵不昧),是谓玄牝(牝,婢忍切。一阴一阳)。玄牝之门(一阖一辟),是谓天地根(生天生地)。绵绵若存(无休无息),用之不勤(应用不穷)。 上六章。谷神不死,虚灵不昧也。接上章“守中”之义也。虚灵不昧,神变无方;阴阳不测,一阖一辟;往来不息,莫知其极;动静不忒,不劳功力,生生化化而无穷。 颂曰:阖辟应乾坤,斯为玄牝门。 自从无出入,三界独称尊。 第七章 天长地久(无休无息)。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无为),以其不自生(无心),故能长生[ 生,《道藏》本作“久”。](不迁不变)。是以圣人(效天),后其身而身先(忘我),外其身而身存(忘形)。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其无我,故能成我)。 上七章。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生不息。圣人不自圣,故与天地合德。接上章“用之不勤”之义也。 颂曰:道本至虚,至虚无始, 透得此虚,太虚同体。 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 第八章 上善若水(以柔处卑)。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随方逐圆),处众人之所恶(能容纳秽恶),故几于道(几,平声。合道)。居善地(利物),心善渊(容物),与善仁(生物),言善信(应物),政善治(治,平声。化物),事善能(成物),动善时(顺物)。夫惟不争,故无尤(物我如一)。 上八章。接上章“后己先人”。所谓水者,取柔和、谦卑、处下之义。利物无争,故无尤。 颂曰:无争神寂静,自足气和平, 放下这点子,黄河几度清。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音以。天道亏盈而益谦);揣而锐之,不可长[ 长,底本作“常”,依《道藏》本和通行本《道德经》改。]保(揣,楚委切。地道变盈而流谦);金玉满堂,莫知能守(鬼神害盈而福谦);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遗,去声。咎,上声。人道恶盈而好谦)。功成、名遂、身退(收拾归来),天之道(天地合德)。 上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接上章“上善若水”之义。功成、名遂、身退,戒盈劝谦之义。 颂曰:急走不离影,回来堕堑坑。 只今当脚住,陆地变平沉。 若解转身些子力,潜藏飞跃总由心。 第十章 载营魄(不得乱走),抱一能无离(离,平声。二物混成,如母携婴);专气致柔,能婴儿(纯一不杂,反朴还淳);涤除玄览,能无疵(不见不闻,尘净鉴明);爱民治国,能无为(治,音持。不动不摇,道泰时清);天门开阖,能为雌(出有入无,不伐不矜);明白四达,能无知(黜聪屏智,和光同尘)。生之畜之(畜,凶入声。斡旋四德,长养群情),生而不有(功成行满,隐迹潜形),为而不恃(忘其所自,默默昏昏),长而不宰(长,上声。退有余地,一任天更),是谓玄德(道隆德备,脱体全真)。 上十章。载营魄,犹车载物之喻。魄好运动,好驰骋,好刚锐,故曰“营魄”。魄属阴,阴盛则害阳,情盛则役性。能制伏者,抱一无离,致柔无疵。无为为雌,无知使阴魄不能肆其情,至于魄伏阴消,则神灵性寂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忘其所自,不用拘束,自然不动,如获宝满载而归,故曰“载营魄”。自抱一以下,纯是“载营魄”之义,接上章“功成身退”,而续下章“三十辐,共一毂,有车之用”也。 颂曰:事向无心得,无心也太难。 悟来弹指顷,迷后隔千山。 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犹万法同一心),当其无(数车无车),有车之用(辐来辏毂,成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埏,扇,平声。和土作器),当其无(数器无器),有器之用(水土假合,成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开户凿牖),当其无(数室无室),有室之用(户牖通达,成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以有利无),无之以为用(以无用有)。 上十一章。以辐辏毂,利车之用,即总万法归心,全神之妙也。辐不辏毂,何以名车?法不归心,无以通神。毂虚其中,车所以运行;心虚其中,神所以通变。故虚为实利,实为虚用,虚实相通,去来无碍。即上章载营魄”之义也。至于无物可载,毂辐两忘,车复无也,犹心法双忘,神归虚也。器与室,并同此义。 颂曰:铁壁千重,银山万座。 拨转机轮,蓦直透过。 要知山下路,但问去来人。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眼被色眩),五音令人耳聋(耳被声惑),五味令人口爽(口被味瞒),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心为情使),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行,去声。意为物转)。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为,去声。内境不出,外境不入),故去彼取此(去,羌吕切。收视返听)。 上十二章。上章发明“虚用”。虚其用,则不为声色眩,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盲”。色声味物,皆是根尘。一切世人皆受盗,惟有道者,不受他瞒。视听言动,非礼勿为,则六贼化为六神通也,故去彼取此。 颂曰:见色神无定,闻声丧太和。 掀翻无一事,赤手造弥罗。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宠是辱先),贵大患若身(贵为患始)。何谓宠辱若惊(谛听下文)?宠为上,辱为下(宠得也,故居上),得之若惊(无失),失之若惊(有得),是谓宠辱若惊(如是)。何谓贵大患若身(设问)?吾所以大患者(何哉),为吾有身(为,去声,下同。有身便有患),及吾无身(忘形无累),吾有何患(忘贵无患)?故贵以身为天下(外其身者,贵其身者也),若可寄天下(以此为天下,则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后其身者,爱其身者也),若可托天下(以此为天下,则可托天下)。 上十三章。接上章“为腹不为目”,忘我之义,故次之以“宠辱若惊”。宠辱贵患,互相倚伏。苟能思患而预防之,则终身无患。推此道而治平天下,则天下永无危殆。有国者,忧天下如忧一身,则天下乐推而不厌。 颂曰:有辱何尝辱,居荣未必荣。 预防无过失,犹更涉途程。 争似全身都放下,也无得失也无惊。 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大象无形),听之不闻名曰希(大音希声),抟之不得名曰微(道隐无名),此三者不可致诘(如何说得),故混而为一(殊途同归)。在上不皦(莫见乎隐),在下不昧(莫显乎微)。绳绳不可名(虽有条目,实无名唤),复归于无物(藏身处,没踪迹),是谓无状之状(不见中亲见),无象之象(象,上声。亲见中不见),是谓惚恍(浑浑沦沦)。迎之不见其首(无始),随之不见其后(后,上声。无终)。执古之道(无为),以御今之有(统摄万有)。以知古始(无为),是谓道纪(因无彰有)。 上十四章。希、夷、微,道之极也。混而为一,返本也;不皦不昧,和其光也;无象无状,藏其用也。末后一句,总证前三章,而发下章之秘也。 颂曰:这个话靶,难模难画。 八面玲珑,全无缝罅。 恍惚窈冥中有象,这些消息共谁论? 第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存其无象),微妙玄通(清净光明),深不可识(视之不见)。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强,上声。以有会无)。豫兮若冬涉川(寒彻骨),犹兮若畏四邻(慎独),俨兮其若容(致敬),涣兮[ “其若容(致敬),涣兮”,《道藏》本漏缺。]若冰将释(无疑),敦兮其若朴(朴,音扑。如愚),旷兮其若谷(虚中),浑兮其若浊(浑,平声。同尘)。孰能浊以动之徐清(清者,浊之源)?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静者,动之机)?保此道者,不欲盈(虚者,实之本),夫惟不盈(冲虚),故能弊不新成(埋光铲彩)。 上十五章。接上章“道纪”之义,发明后学存诚致敬,常慎其独,不住于相,而抱一潜虚为日用,至于顿息诸缘,销镕万幻,扰之则不浊,澄之则不清,是谓微妙玄通,深隐也。 颂曰:微妙玄通,随人脚转。 瞎却眼睛,一物不见。 不如归去来,识取虚皇面。 李道纯是元代著名内丹理论家,是融合道家南北二宗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选取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和集》《三天易髓》《全真集玄秘要》《道德会元》《清庵莹蟾子语录》《太上大通经注》《无上赤文洞古真经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注》《周易尚占》等,经过汇校,整理,简体标点,为学习和研究提供较好的参考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