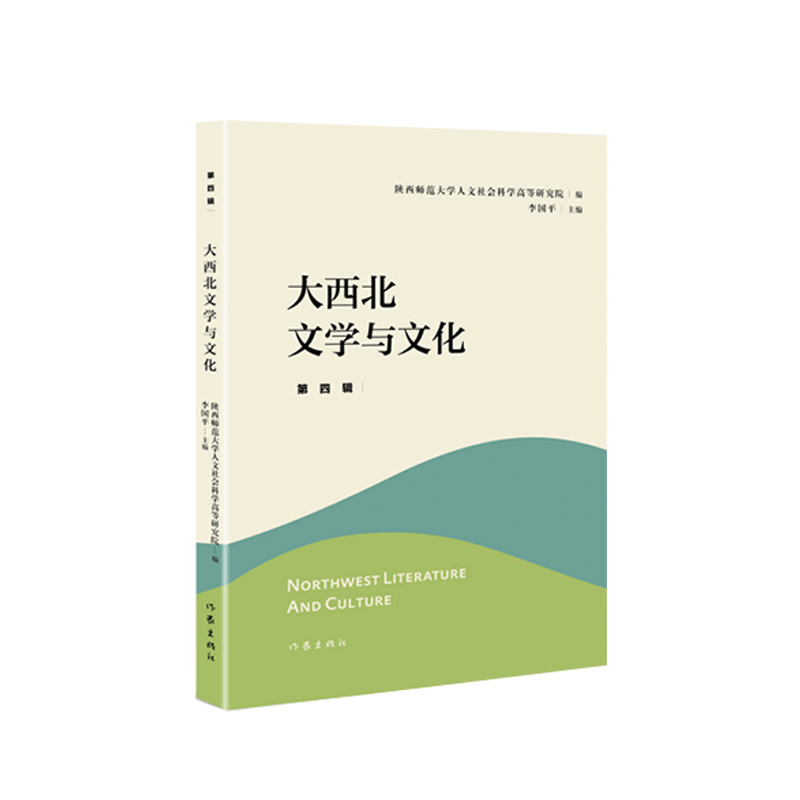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7.00
折扣购买: 大西北文学与文化·第四辑
ISBN: 97875212186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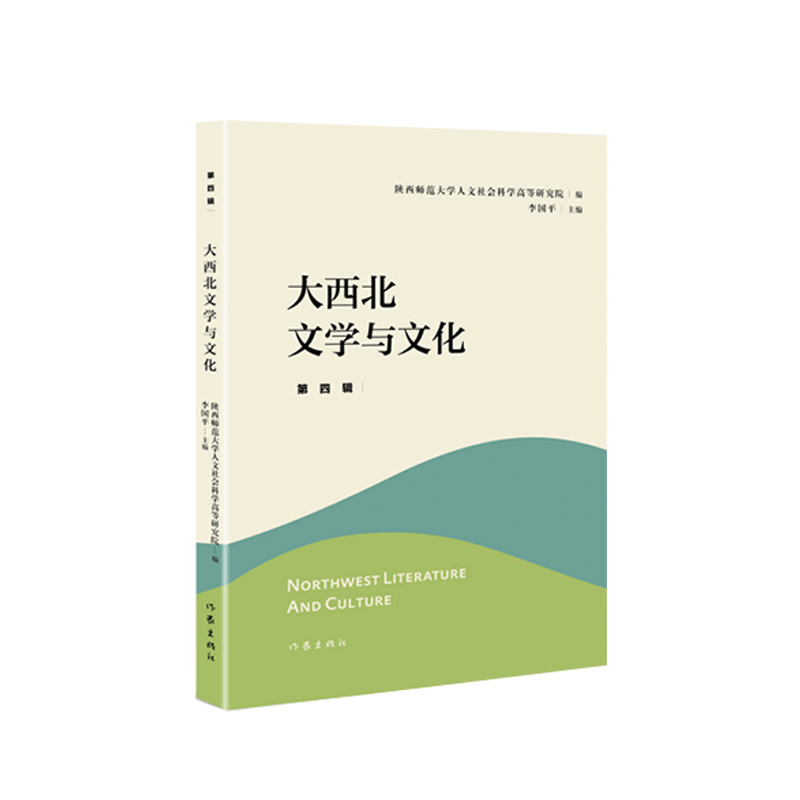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编
当代文学研究 现实主义、本土性与当下文学 孟繁华 内容提要: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耳熟能详,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有不同内涵。中国在接受现实主义的过程当中非常曲折。有恩格斯的经典理论;有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理论;还有斯大林理论,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土性是和所谓的世界性,和全球化这样一个概念相对而言的。重提地方性知识,重提地方性经验,或者本土性,就是对普遍性的一种质疑。这个理论我觉得在今天的语境当中特别有它的道理。 关键词:现实主义;本土性;当下文学 一、关于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耳熟能详,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有不同内涵。现实主义文学的原话语,或者原理论是恩格斯提出的。大家知道恩格斯有一封著名的信叫《致玛·哈克奈斯》,哈克奈斯当时创作了一部作品,这个作品叫《城市姑娘》,恩格斯在讨论《城市姑娘》这部作品时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经典的概念。他怎么说呢?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恩格斯的原话。这里面恩格斯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细节,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另外一个就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我们都知道,现实主义是文学专业必讲的一个理论。这些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文学理论也好,文学创作也好,沐浴了“欧风美雨”,很多作家、理论家、批评家都在追逐西方的理论和创作潮流。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大家放弃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去追逐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等等这样的创作,在特殊的历史环境里面,我觉得是合理的。大家知道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是一体化的状态。在文学批评领域里面,我们知道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批评长期地占领着文学批评领域,这对我们的文学批评构成了严重的伤害,也为我们文学创作带来了某些弊端。特别是“文革”前后,大家知道文学作品越来越模式化、同质化、雷同化,这和庸俗社会学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为了打破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一体化的状态,文学界接受了西方的观念,这叫二次西风东渐,“欧风美雨”二次东渐,接受了现代的西方文学、后现代文学,也包括先锋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有道理,有价值,使我们文学创作能够更多样,更多元,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读者满足他们多样化的要求。这是有文学史价值,有文学史意义的。 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相信每一个读者对80年代初期,或者是整个80年代我们所经历的这种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讲述出某个作品。这些文学潮流使我们眼界大开,看到了西方一二百年来整个文学发展状况。我们是跟着说,接着说,但是难以对着说。特别是70年代末期一直到现在,现实主义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当年最激进的先锋文学的实验者,现在都后退50里下寨,都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上。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很熟悉的像余华,像格非,这两个作家是先锋五虎将的作家,也就是说在先锋文学潮流里,他们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比如像格非的《褐色鸟群》《迷舟》;比如余华的《鲜血梅花》《虚构》《现实一种》等作品。现在我们都记得这些小说,但是会记住这些小说的具体内容吗?我们能复述这些小说的内容吗?不能。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是概念性的文学,是观念性的文学,他们强调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强调实验性。文学在一个时段里面离开了读者,离开了大众,和文学的这种实验性有极大的关系。当时很多作家强调我的作品不是给当下读者读,是给未来的读者读的。这个情况当然不是仅仅中国的文学史是这个样子。比如前一段我们接触过一个翻译作品,德国的作品,叫作《红桃J》,被称为德国最新小说选,序言是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评论家写的,他说当德国的作家们走进了实验之后,德国的作品远离了德国的当代,读者也远离了德国文学,因为德国的作家不热爱他们的当代。回过头来观照中国的先锋文学,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吗?我想也可以。作家注意形式的意识形态,注意先锋,注意实验,他和读者关注的当下生活构成了距离。当作家不关心当下生活的时候,当下的读者就有资格,也有理由远离我们的文学。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看法。9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重新又在文学批评界和创作界被接受。当然,这个时候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我们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现实主义。 所以我说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它是一个不断吸纳的概念,不断被丰富的一个概念。我们还用余华、格非这样的作家来举例说明的话,比如格非获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获得很好的评价,比如像《望春风》《隐身衣》,这个大家都读过,这些作品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但是这里面同时也容纳了、也包含了且融会了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等等的修辞和技巧。所以这些作品丰富了我们现实主义的内涵,丰富了现实主义的方法。余华也一样,从《在细雨中呼喊》以后,他写了《活着》,《活着》每年大概销售近百册,像《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后来的《兄弟》《第七天》等作品。如果余华和格非不回到现实主义这个道路上,他们是今天的余华和格非吗?当然不是。当然我们也记得一些先锋文学作家,当回过头来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面对当下生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书写,于是迅速被遗忘。 还有一点,前几年习总书记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习总书记也提到典型人物。这个理论当然就是恩格斯提出的理论,是原理论。我们有一段时间认为现实主义也好,典型理论也好,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我们可以不再去谈了的理论,这是错误的,理论没有新旧,就像真理没有新旧一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包括总书记能够重新讨论现实主义,重新提倡作家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多么的重要。我可以问我们的在座的读者,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作品,读了这么多年的文学,我们记住多少人物呢?记不住多少人物。但是我们读过去经典作品,我们与其说记住了这部作品,毋宁说记住了这部作品的人物。比如你读《三国演义》,关张赵马黄、孔明诸葛亮、曹操等等都能记住;读《水浒传》,一百零八将都能记住;读《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我们都能记住;读《西游记》,师徒四人我们都能记住,记住的都是人物。写人物是一个作品的基本要素,不仅是近代的或者明清以降的小说是这样,像《史记》《左传》这样的作品不都是写人物吗?《史记》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些人物大家都能记住。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人物的创造越来越贫乏,在人物创造方面我觉得还不如80年代,80年代我们记得很多文学人物,新世纪以来我们创作了多少人物?人物很重要。比如像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在一个时段里面,或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是我们的榜样,无论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是我们的榜样。这个榜样我觉得它不是没有道理,比如说在彼得堡时期,当时的伟大作家都在那里生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等,这些大作家都曾经在彼得堡生活过。这些伟大的作家在他们那个时代共同创造了一个人,这个人物叫“多余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多余的人”一直影响着整个文学100多年。英国的漂泊者,美国的遁世者,日本的厌世者,中国的零余者,这些人不都是多余的人吗?所以我曾经讲过俄罗斯文学如果只创造了一个人物,就是创造了这个“多余的人”,有了这个人物,俄罗斯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强国,他们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是了不起的,这就是人物形象的魅力。所以塑造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的核心要素。 但是中国在接受现实主义的过程当中非常曲折。开始当然我们也接受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但是中国在接受现实主义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恩格斯的理论,原理论;另外一个是列宁的理论。大家知道列宁有《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样一篇文章,开始翻译的时候翻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翻译错了,后来纠正了,是《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但是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讲文学是整个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就是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特别功利要求,文学在那个时代应该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就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这个理论没有问题。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家知道,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关于文学理论的经典文献。如果回到中国的语境,1942年大家知道是什么年代,是国家民族危亡的年代,整个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能够通过文学艺术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有错误吗?没有错误。在鸳鸯蝴蝶派面前,在张爱玲面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文艺面前,我们应该站在哪一方面,这不是很清楚嘛。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能够走向民间,实现我们的情感方式和话语方式的“转译”。“转”是转折的转,“译”是翻译的译。所谓的“转译”就是我们不要再用“五四”那套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老百姓听不懂,要走向民间,向民众学习,用民众的语言,学习民众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后来我们创造了延安文艺。对延安文艺现在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在我看来,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没有问题的。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要求我们要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艺术,这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误。但是可能有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里面,我们会提出一些不同的阐释,不同的看法。尤其进入共和国时期以后,我们把和战争时期的经验全面地推广到了和平时期,把延安局部地区的经验全面地推广到全国,这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列宁当时说“文学艺术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同时他还有后半句,“文学艺术应该是一个最自由广阔的天地”。我们有时候往往强调前半部分,不管后面。但是进入到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时候,延安地区的经验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呢?当然也有合理性。战争时期我们要实行民族全员动员,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一穷二白这样的一个国家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仍然是必要的。 从1949年到1966年,我们当代文学把它称为“十七年”。这17年我们的文学创作大家知道有很重要的经典作品,当代文学史,包括批评界都叫“三红一创保山青林”,“三红”就是《红日》《红岩》《红旗谱》,“一创”就是《创业史》,“保山青林”就是《保卫延安》《山乡巨变》《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这八大名著为什么重要,是因为这17年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我们的文学艺术为了构建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特别是像《创业史》这样的作品,梁生宝的道路,后来浩然的《艳阳天》的肖长春的道路,《金光大道》高大全的道路等,他们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与其说那个时候我们的作家在创作小说,毋宁说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然这些作品刚刚发表的时候也引起一些争议,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八大经典最著名的、最重要的、艺术成就最高的就是《创业史》,但恰恰是《创业史》刚刚发表的时候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北大的严先生,在当时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论《创业史》。他认为《创业史》写得最好的人物不是梁生宝,是梁三老汉。梁生宝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他代表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但是在进行互助组初级社进入高级社当中,梁三老汉表现的是犹豫不决符合他的身份,更符合一个人的真实心理。面对历史巨变,他充满犹豫不决,徘徊迷茫,是符合人性的。所以严先生认为《创业史》里面写得最好的是梁三老汉。当时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叫邵荃麟,他也支持严先生的看法。后来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短篇小说座谈会上,邵荃麟先生提出来“中间人物论”,他说农村就像茅公所说,是两头小,中间大,就是先进的人物和特别落后的人物少,处于中间的人物多。这符不符合农村的现实呢?当然符合。我们不仅在《创业史》里面看到了梁三老汉,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里面看到了亭面糊,在浩然的《艳阳天》里面看到了弯弯绕,特别是赵树理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大多是中间人物。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界站在了梁三老汉一边;但是社会历史的发展站在了梁生宝那边,也就是说梁生宝代表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代表了当时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 是不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文学作品完全是个同步关系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一段历史结束之后,这些文学作品就一点价值没有了。像梁生宝这样的青年,后来的文学创作追随者络绎不绝。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少平、孙少安他们不就是梁生宝的子孙吗?比如河北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他前两年写了一部作品,叫作《金谷银山》,《金谷银山》里面有一个重要人物范少山,范少山口袋里面揣着一本书,就是《创业史》,他本来是一个北京做小生意的人,后来自己的家乡白羊峪遇到了重大的困难,白羊峪是半山腰的一个贫困的山村,不适合人居,政府花了巨资找了一个适合人居的地方建了农舍,但是农民故土难离,他们就是不走,这个时候范少山揣着《创业史》回到村里,帮着村里创业致富,发现了500年前的金谷子,金种子,苹果的种子。当然这个小说的合理性是怎样,我们姑且不谈,但是范少山是梁生宝的追随者,孙少平、孙少安是梁生宝的追随者。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大家看扶贫的一些作品,虚构和非虚构的,那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是梁生宝的传人。也就是说我们衡量或者评价一个作品的时候,络绎不绝是我们评价一部作品最重要的一个尺度。为什么这么多人追随梁生宝呢?这个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们能够说前期社会主义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就连像《创业史》的作品一起否定掉,这是不客观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过程。我们的思想政策、思想路线等等,不断地发生调整,不断在发生变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试错过程当中的调整和变化。后来洪子诚老师讲不确定性也是一种力量。这个看法我是同意的。 在我们接受现实主义过程当中,刚才讲了恩格斯的经典理论,讲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理论。那么还有一种理论是什么?就是斯大林的理论。就是说在1930年前后,当时苏维埃政权有五大常委,其中一个常委叫格隆斯基,格隆斯基是管意识形态的,他有一天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文学创作应该有一个口号,斯大林同志说好,叫什么口号?说叫“共产主义现实主义”,斯大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后来说不行,太早。我们应该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就在斯大林的办公室诞生了。 斯大林是怎么具体阐释的呢?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告诫我们的作家,我们正在建构的是一座共产主义的高楼大厦,要告诫作家们,要看到共产主义未来的远景,不要让他们的脚手架底下东翻西倒。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歌颂光明,不能够暴露黑暗。这个理论在一段时期里面我们也接受,特别是苏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现实主义作了定义之后,我们都重复了苏联关于现实主义的概念。它也非常深切地影响了我们当时的文学创作。 我们50年代有很多颂歌大家都知道,包括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等等,他们都写了很多歌颂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比如像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年龄大的读者都会知道,比如像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十月颂歌》等等,还有闻捷的《天山牧歌》《吐鲁番情歌》。《吐鲁番情歌》非常有代表性,闻捷一方面对新生活有一种拥抱歌颂的热情,另外一方面那个时代的痕迹特别地鲜明。 对50年代的文学评价,很多批评家和学者的看法很不一样,有的人把50年代的创作完全否定掉,这个是不公平、不客观的。我举两个例子,我们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可能知道。一个是王蒙,王蒙现在还是活跃的作家,他几乎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他在50年代创作了一部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最初发表时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又改回原名),还有一篇是宗璞的《红豆》,这两部作品在1957年反右斗争当中都被打成毒草。在1980年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重放的鲜花》,把这两部作品都重新出版了,这两部作品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写反对官僚主义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青年人叫林震,他看到了组织部的整个生活状态,看到了组织部的这些工作人员是怎样工作的,有的非常油滑,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是用一种反对的情绪来讲述这个故事;《红豆》是一种倒叙手法,写一个年轻人当时追求革命,抛弃了爱情。后来姚文元写文章批判《红豆》,他说虽然写江玫参加革命抛弃了爱情,但是通篇是江玫对于爱情念念不忘的泪水。这两个作品为什么重要?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是那个时代有难度的写作。为什么有难度呢?一个方面作家真心地要拥抱我们这个时代,拥抱社会主义国家。另外一个方面,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又不肯放弃文学创作的规律,他们尊重个人的体验,尊重个人的感受。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作家还没有学会说谎和油滑,所以那个时代的经验是重要的。 再回过头来重读一下这些作品,有些作品可能时间越久,我们越能够认识和领会这部作品的价值。所以我们阅读一定要选择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是经过历史的淘洗,留下来的真正的人类精神和情感的重要遗产。当然,文学经典有时代性,文学经典的确立是一个不断对话的过程,每一个时代由于时代性,由于时代的需要,对于经典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所以经典作品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构建和不断颠覆的过程当中。读经典作品就是能够去领略我们不同时代最优秀的文学头脑他对于人的思想、精领域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对世道人心他是怎样表达的。另外一种文学史经典——这是我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很多作品未必是文学经典,但是这些作品文学史一定要去讲述它,如果不去讲述这些作品,我们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就难以讲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时期初期发表的两部作品,一个是卢新华的《伤痕》,一个是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两部作品我们在座的很多读者都知道。这两部作品如果我们现在阅读,可能会觉得写得过于简单,也有概念化的成分。但是作为新时期文学,或者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你不从它讲起是不能讲清楚的。所以文学史经典和文学经典是两个概念。 回过头来说,我们现在讲文学经典的话,大家知道基本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创造的。美国的耶鲁“四人帮”有一个著名的批评家,叫哈罗德·布鲁姆,他编的一个选本特别流行,这个选本叫作《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是对先锋文学、后现代文学非常热衷的一个批评家。80年代他有一部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叫作《影响的焦虑》,影响了我们一代学者,是非常著名的一部学术著作。但是到了2000年前后,他突然峰回路转,他编了《西方正典》,这些作品几乎全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批评家,从事了一生的文学研究,有全球影响的批评家,仍然选择了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创作作品,他没有他的道理吗?这本书是博士生、硕士研究生,包括大学生都必读的一个选本。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这个选本,大家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