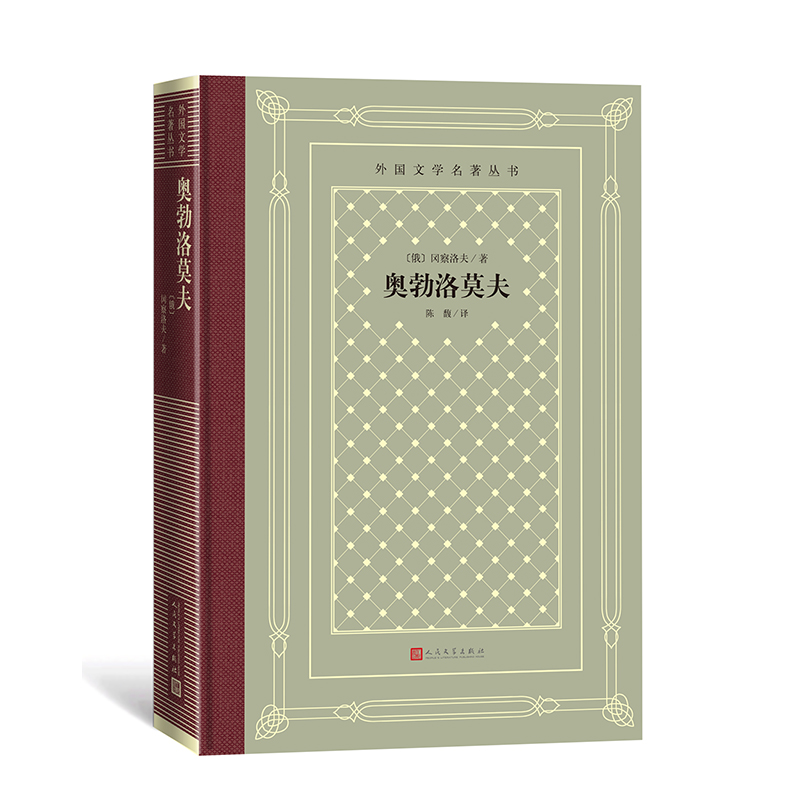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86.00
折扣价: 46.50
折扣购买: 奥勃洛莫夫/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020152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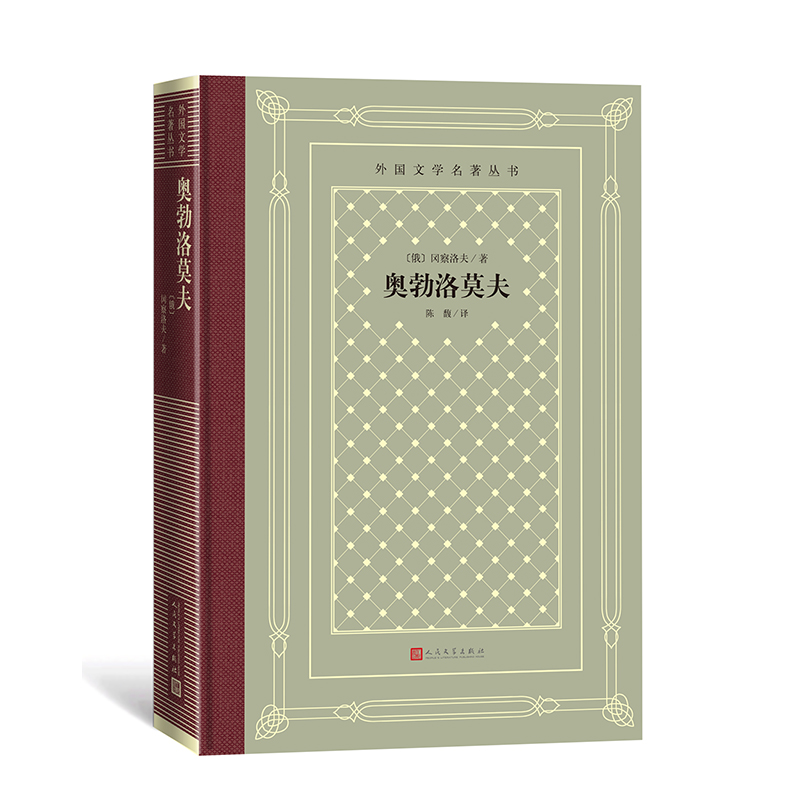
作者: 冈察洛夫(1812—1891),十九世纪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代表作有《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悬崖》等。 译者: 陈馥(1934年— ),云南大理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历任北京俄语学院教师、新华通讯社对外部及国际部新闻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编审。主要译著有《布宁文集》《奥勃洛莫夫》《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合译)等。
译本序 冈察洛夫于一八一二年出生在俄国一个半地主半商人的家庭。一八三一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长期在政府部门任公职,但始终坚持文学创作。 一八四七年,冈察洛夫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描写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兴起时,一个耽于幻想、温情脉脉的地主少爷如何顺应时势,放弃浪漫主义,成为一个冷冰冰的实业家的故事。小说立刻博得与他同时代的俄国大评论家别林斯基的好评,他特别赞赏作家独到的“描绘的本领”。 一八四九年,冈察洛夫发表了《奥勃洛莫夫的梦》。这是未来巨著《奥勃洛莫夫》中的一章,但是没有写完,因为冈察洛夫于一八五二年随俄国海军上将普佳金作了一次环球考察,回国后将旅途见闻写成一部游记《战舰巴拉达号》。 一八五九年,《奥勃洛莫夫》终于问世。同时代人斯卡比切夫斯基说:“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才能理解这部小说在公众中引起了怎样的骚动,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怎样令人震惊的影响。它发表在农奴制取消前三年社会强烈动荡的时期,当时整个文学界正掀起对昏昏沉沉、怠惰与停滞的讨伐。这部小说宛如一颗炸弹,投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一八六九年,冈察洛夫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悬崖》。作品通过女主人公的爱情波折,表现了四五十年代俄国青年对新生活的追求。冈察洛夫坚持他的三部小说乃是一个整体,反映了俄国由农奴制度向废除农奴制过渡时期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旧生活、昏昏沉沉、觉醒”。三部曲中,《奥勃洛莫夫》是最符合作家创作才能特征的一部伟大杰作。在这部小说里,冈察洛夫的“描绘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正是由于这种精雕细刻的文风,原本并不复杂的情节竟发展成一部洋洋洒洒的巨著。 故事开始时,受过高等教育但已退职达十二年之久的奥勃洛莫夫正躺在沙发床上。他“三十二三岁了,中等身材,面目可亲,眼睛是深灰色的,不过从他脸上看不出他有什么明确的思想,或者专注于什么事情”。而奥勃洛莫夫的衣着可以说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作者写道:“奥勃洛莫夫的家常服装跟他那沉静的面容和柔弱的身子真是再相称不过了!他穿一件用波斯料子缝制的大袍……宽宽的,足可以把他裹上两圈。”而为了更舒服自在,奥勃洛莫夫在家里总是穿一双长长的、软软的、肥肥大大的便鞋,早上“他下床的时候,眼睛不必看地板,只要一伸腿,两只脚总是能够准确无误地插进鞋里”。从奥勃洛莫夫那缺乏明确的思想的淡漠的脸相,到他那似乎被赋予生命的大袍与便鞋,绝不限于外表的逼真,而是直透入人物的灵魂和性格的核心。这是一个在农奴主寄生生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慵懒成性的、丧失了意志与行动能力的人。 和果戈理一样,冈察洛夫也通过人物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来丰富和突出形象。在奥勃洛莫夫的书斋里,“挂在墙上的画框周围雕花似的结着布满灰尘的蜘蛛网。镜子照不见人,倒成了可以在上面画符号记事的牌子”。“难得有一天早晨他吃饭用的桌子上不残留着些面包渣,不摆着前一天晚饭后没有收走的搁着盐罐和啃过的骨头的盘子”。“书架上有两三本翻开的书和一张报纸,写字台上有一瓶墨水和几支鹅毛笔,但是翻开的书页上有一层灰尘,纸也黄了,显然是早就扔在那里的,报纸则是去年的,那瓶墨水呢,如果把笔插进去,从里面准会嗡的一声飞出一只吓坏了的苍蝇来。”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冈察洛夫的描绘酷似十七世纪荷兰画派精美绝伦的市民生活风俗画。而俄国大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则精确地抓住了作家创作方法的独特之处。他说:“冈察洛夫才能的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形象……他绝不迷离于对象的某一个方面,也不会迷离于某一事件的某一瞬间,而是把这对象转来转去,从四面八方来观察他,期待着这一现象的所有瞬间的完全显现,到那时候他才开始艺术加工。” 奥勃洛莫夫在彼得堡他的寓所里,由他的农奴仆人扎哈尔侍候着。他躺着,坐着,过了一天又一天。这一天清晨,他原想起床,但眼下需要就田庄收入的问题给村长回信,这件事竟弄得他心烦意乱。他只有继续躺在床上,空想着如何应付。他就这样在床上吃了早饭,又接待了客人,忽而坐起来,忽而躺下去,忽而把脚伸出床外想穿上便鞋,忽而又把脚缩回来,忽而似清醒,忽而似做梦,直挨到下午四时还未起床,而小说的第一部已到尾声。无怪乎与冈察洛夫同时代的俄国作家谢德林读后说:“想起来都可怕,这只是第一天,而他竟能这样躺上三百六十五天!” 至于搬家,那更是奥勃洛莫夫无法忍受的痛苦了。当扎哈尔向他提出,既然“别人”都能搬家,他们自然也可以搬时,他竟勃然大怒道:“照你看,我是‘别人’吗?”对于他说来,“别人”是那些需要自己刷靴子和穿衣服,不奔波劳碌就没有饭吃的人。而他本人呢,“感谢上帝!我这辈子还没有自己动手穿过袜子!”一个懒惰已深入骨髓的地主老爷就这样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靠三百五十个农奴养活他,却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而洋洋自得。 作者在《奥勃洛莫夫的梦》这一章中形象地说明,奥勃洛莫夫田庄这个典型的俄国家长制地主庄园生活环境正是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摇篮。这片“乐土”保证奥勃洛莫夫家的人平静地走完由生到死的人生之路。在这里,吃与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整个上午主人们都在仔细讨论并决定一天的食谱,而厨房里剁肉和切菜的声音直传到村子里。午餐后则是死一般的静寂:在屋子里、树荫下、马厩里,到处可以听见均匀的午睡的鼾声。接着又是吃,吃了睡,睡了吃。好动的小奥勃洛莫夫原想上山涧和打谷场去玩耍,但只要他一动,就有一群大人在身后阻止他,惟恐他跌伤或晒得头疼,他只有静下来。他幼小的心灵日复一日吸吮着这里的一切,终于形成了自己未来的生活纲领。当读者在第一章中见到他的时候,他已人到中年,只会这里躺躺,那里坐坐了。 但在好友施托尔茨的一再敦促下,奇迹发生了。奥勃洛莫夫振作起来,整理行装,预备去巴黎。不仅如此,他竟堕入情网。他不再总是睡觉,他的眼睛开始发光,他穿上燕尾服,不停地拜访奥莉加。而奥莉加看到奥勃洛莫夫内心的温柔与善良,也爱上了他,并且抱着满腔热忱,决心唤醒这个沉睡的生命。但是,当爱情发展到需要负担起成家立业的艰辛职责的时候,奥勃洛莫夫陷入烦恼与痛苦之中。他想,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有幸福和安宁呢?于是,在昙花一现的回光返照之后,他退缩了。他找出种种借口,连连失约,终于两人不得不分手。后来他和会做馅饼并且善于服侍他的房东太太普舍尼岑夫人这个善良的小市民女人结合了,在维堡区的一处庭院里找到了另一个奥勃洛莫夫田庄,吃着,睡着,缓缓地、过早地进了坟墓。正如他最终向施托尔茨所说的:“我已经永远脱离了你想带我去的那个世界……我的弱点已经使我跟这个坑长在一起了,你若把我拉开,我就会死。”这一场面冈察洛夫写得十分动情,犹如一首哀歌。同时也是对农奴制度的强烈控诉。 一部成功的作品总会给文学宝库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奥勃洛莫夫》一书的贡献在于:在冈察洛夫之前虽然有很多作品谴责农奴制度,但没有一部小说描写了主人公整个一生,并通过他如此有力地表现出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如何戕害了一个人的灵魂,使他从不会穿袜子开始,而以不会生活告终,任什么也不能挽救他这种走向毁灭的命运。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在反农奴制斗争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冈察洛夫企图用施托尔茨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面,树立起一个理想人物。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事业开拓者,最后也是他赢得了奥莉加的心。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施托尔茨“写得不好,苍白无力,表现得太赤裸裸了”。 虽然这个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俄国社会对资本主义化的要求,但是只有奥莉加才是俄国进步阵营承认的理想人物。她对待生活严肃认真,对人既热情又有理智。她爱上奥勃洛莫夫,以“足以使顽石活起来”的努力去挽救他。但是当她确知自己不可能成功的时候,她痛苦却毅然地离开了他。她和充满活力的施托尔茨结合了,又并不满足于那种没有理想的平庸生活。她说:“我逐渐变得对什么也不满足了。”奥莉加是俄国文学史上众多优秀俄罗斯妇女形象中的一个,她们都很坚强,有高尚的追求,与市侩习气格格不入。 冈察洛夫对次要角色的心理特征也是从不疏忽的。例如农奴仆人扎哈尔为了缅怀昔日奥勃洛莫夫家族的显赫,总是身着旧时代的号衣,并按老规矩留着“宽极了的连鬓胡子,从里面似乎就要飞出两三只小鸟来”。而那个不停地在做点心和做饭的房东太太普舍尼岑夫人的滚圆的胳膊肘儿,永远活动不止,“敏捷地画着圆圈”,更是十分传神。对于奥勃洛莫夫来说,这胳膊肘儿正是他童年时代奥勃洛莫夫田庄“美好”生活的再现。他仿佛在这胳膊肘儿的不停活动中找到了安宁,回到了故园。 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冈察洛夫在批判和否定农奴制度与地主阶级人物时,毫无疾厉色,没有辛辣的讽刺,相反,时常温情脉脉,几乎要一洒同情之泪。这恐怕是和冈察洛夫对文学应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看法相联系的。在《奥勃洛莫夫》中,主人公曾向友人谈到,对于写作,怨气和嘲笑是不够的,“你们尽管去写盗贼、娼妓、狂妄自大的糊涂虫好了,但是别忘了他们是人……你们以为思想不需要心灵吗?不对,能使思想结出果实的是爱。你们应该向堕落的人伸出手去把他拉起来。如果他濒于毁灭,应该为他痛哭,而不是嘲笑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英国评论家V.S.普里契特曾说:“在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疯狂的文学中,冈察洛夫的小说,照我的感觉,其感情是最柔和、最富于同情心的。”但是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冈察洛夫对自己的主人公的一些赞扬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毕竟无力完成自己任何一个良好的意愿。 在典型问题上,冈察洛夫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于一八七六年二月十一日致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道:“您说,‘新诞生了这样一个典型’,请原谅我斗胆指出其中的矛盾。如果是新诞生的,那就不是典型……典型是由长时期多次的重复、现象与人物的沉淀而形成的……”这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但却与他的描绘本领珠联璧合。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物才容许作家有充分时间来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从而完成这样丰满而生动的描写。善于紧跟时代并作出迅速反应的屠格涅夫的小说,就完全不同了。 《奥勃洛莫夫》创作于一百多年前,艺术创作原则也只能供借鉴。但是这部作品却使作家冈察洛夫和他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不朽。奥勃洛莫夫的形象是历史的、具体的,但是奥勃洛莫夫性格或气质却具有一般的意义,它在不同时间会不同程度地再现于不同人物的身上。 作家的一个同时代人说得好:“冈察洛夫在我们的文学中占有一个无人能取代的位置,任何其他即使更耀眼的光辉也不能完全掩盖他的光辉。” 张秋华 一九九四年九月 第一部 伊利亚·伊利奇·奥勃洛莫夫早晨在他寓所里的床上躺着,这是戈罗霍夫大街圣彼得堡市中心的一条大街,因商人戈洛霍夫在此建房而得名。上几幢大楼房当中的一幢,里面住的人多得能赶上一座小县城。 这个人三十二三岁了,中等身材,面目可亲,眼睛是深灰色的,不过从他脸上看不出他有什么明确的思想,或者专注于什么事情。思想像一只鸟儿无拘无束地在他脸上游逛,在他眼睛里翻飞,或者栖息到两片半张着的嘴唇上,躲进额头的皱纹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他脸上就温和而平静地漾出一种无忧无虑的神情,这无忧无虑的神情又从脸上转移到整个体态上,甚至转移到睡袍的褶缝里。 他的脸上偶尔也会出现一种近乎倦怠或者无聊的表情,使得他的目光黯淡下去。不过无论倦怠也罢,无聊也罢,片刻都不能从他的脸上逐去那占主导地位的基本表情——温和;不仅不能从他的脸上逐去,也不能从他的整个心灵上逐去,而他的心灵明明白白地表露在他的眼睛里,微笑里,头和手的每一个动作里。一个只看表面现象的冷眼旁观的人,对奥勃洛莫夫瞟上一眼以后会说:“他想必是一位好好先生,憨厚老实!”看问题深一点、心肠热一点的人,在长时间观察过他的面孔以后,却会含着微笑饶有兴致地琢磨着走开。 奥勃洛莫夫的脸色既不是红润的,也不是黝黑的,更不是白净的,而是难以分辨的,或者说给人这种印象,大约因为他还不到发福的年纪已经发福,不知是缺少运动还是缺少新鲜空气,也许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吧。总的说来,由于他的脖子、胖胖的小手、柔软的肩膀肤色都过于白净,他的身体对于一个男子汉就显得太娇嫩了。 即使在他受到惊扰的时候,他的动作也是柔和的,不失一种慵懒的优雅风度。一旦愁云从他的心头升到颜面上来,那目光就模糊了,额头上会出现许多皱纹,神色中变幻着疑惑,忧郁,惶恐。不过这种惊惧很少定型为明确的思想,更少变为意向,往往化作一声叹息,消逝在漠然的或者半睡半醒的心态中。 奥勃洛莫夫的家常服装与他的沉静的面容和柔弱的身子真是再相称不过了!他穿一件用波斯衣料缝制的大袍,不缀穗子,不镶天鹅绒,也不掐腰,没有一处会让人联想到欧洲,是一件真正东方式的大袍,宽大得可以把他的身子裹上两圈。袖子也是按照通常的亚洲式样做成,从手指到肩头越往上越肥大。这袍子虽然已经不新了,有些地方磨得失去了原先的自然光泽,但是它的东方色彩依旧鲜明,料子也依旧结实。 在奥勃洛莫夫眼里,大袍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好处,它软和,舒服,穿在身上无拘无束,像个听话的奴仆一般顺从身子的任意摆动。 奥勃洛莫夫在家从来不系领带,也不穿西服背心,因为他喜欢自由自在。他脚下那双便鞋也是长长的,软软的,肥肥大大的。他下床的时候,眼睛不必看地板,只要放下两条腿,两只脚立刻就能准确无误地插进鞋子里。 奥勃洛莫夫躺着并不像病人或者困了想睡觉的人那样出于需要,也不像累了的人想歇一下那样出于偶然,更不像懒汉那样以此为享受。卧床只不过是他的正常状态罢了。他在家的时候(他几乎天天在家)总是躺着,而且总是在我们见到他的那个兼做卧室、书房和会客室的屋子里。他还有三个房间,不过他很少去,要去也是在早上仆人打扫他的书房的时候,并且不是每天去,因为不是每天都打扫书房。那三个房间里的家具全都罩着,窗帘也不拉上去。 奥勃洛莫夫所在的房间乍一看好像布置得很好。那里有一张红木文书桌、两张织锦面长沙发、几扇绣着些自然界没有的鸟儿和果实的漂亮屏风。此外还有丝绸窗帘、地毯、几幅油画、青铜器、瓷器,以及许多好看的小玩意儿。 但是一个老练而又注重品味的人把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扫上一眼就会发现,主人不过是想勉强维持一个起码的体面的假象原文为拉丁语。,能不再为此操心就行。奥勃洛莫夫在布置自己的书房的时候显然只求做到这一点。讲究的人不会喜欢这些笨重难看的红木椅子和摇摇晃晃的书架。一张沙发的靠背已经塌了下去,用胶粘合的木头有些地方已经脱胶。 那些油画、花瓶、小玩意儿也都具有同样的特征。 主人自己对自己的书房陈设态度如此冷漠、不经心,他的目光似乎在问:“是谁把这些东西弄来摆在我屋里的?”由于他对自己的财物态度冷漠,或许还由于他对伺候他的扎哈尔态度更加冷漠,那书房仔细看看真是脏乱得惊人。 挂在墙上的画框周围雕花似的结着布满灰尘的蜘蛛网。镜子照不见人和物,倒成了可以在上面画符号记事的碑牌。地毯上污迹斑斑。沙发上扔着毛巾。桌子上难得有一天早晨不摆着前一天晚饭后没有收走的搁着盐罐和啃过的骨头的盘子,不残留着一些面包渣。 如果没有这只盘子,没有刚抽完烟支在床边的长烟袋,没有躺在床上的主人,那真会让人以为这间屋子没有人住——什么东西都蒙着一层灰,失去了原先的色泽,简直没有一点迹象表明有活人存在。虽说书架上有两三本翻开的书和一张报纸,书桌上有一瓶墨水和几支鹅毛笔,但是翻开的书页上有一层灰,纸也黄了,显然是早就扔在那里的;报纸是去年的,而那瓶墨水呢,如果把笔插进去,从里面准会嗡的一声飞出一只吓坏了的苍蝇来。 这天奥勃洛莫夫比平日醒得早,大约才八点钟。他心事重重,脸上的表情时而像是恐惧,时而像是苦闷,时而又像是懊丧。他显然为内心的斗争所苦,可是理智还没有出来帮他的忙。 原来奥勃洛莫夫昨天收到他那个领地上的村长由乡下寄来的一封信,内容令人不快。一个村长能写些什么令人不快的话,那是尽人皆知的,不外乎收成不好、租交不上来、进款减少之类。其实这位村长去年和前年给东家老爷写的也是这样的信,不过最近这封信给他的刺激还是像任何出人意料的坏消息一样强烈。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必须想办法采取一些措施。其实,说句公道话,奥勃洛莫夫还是关心自己的事务的。几年前,在收到村长寄来的第一封使他不愉快的信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构思旨在整顿他的庄园的各种改革的蓝图。 根据这个蓝图,他要采取种种新的经济的、警察的以及其他性质的措施。不过这个蓝图还远远没有达到周密的程度,而村长却年年写来使他不愉快的信,催他行动,自然也就打破了他的平静。他意识到在蓝图形成以前非采取果断的措施不可了。 奥勃洛莫夫一睁开眼睛就打算起身,洗漱,喝茶,然后仔细考虑考虑,好歹想出个点子,拿张纸记下来,总而言之,认认真真来做这件事。 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他还躺在那儿,为这个打算苦恼着,后来转念一想,喝完茶再干也来得及,而茶照例可以在床上喝,何况躺着思考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就这么办了。喝完茶以后,他从床上抬起半个身子,几乎要起来了,这时候他看了看鞋子,甚至开始从床上放下一只脚去,却又立刻把脚缩了回来。 时钟敲过九点半,奥勃洛莫夫浑身一震。 “我到底怎么啦?”他懊丧地说出声来,“真不像话,该做事了!只要一放任自己,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