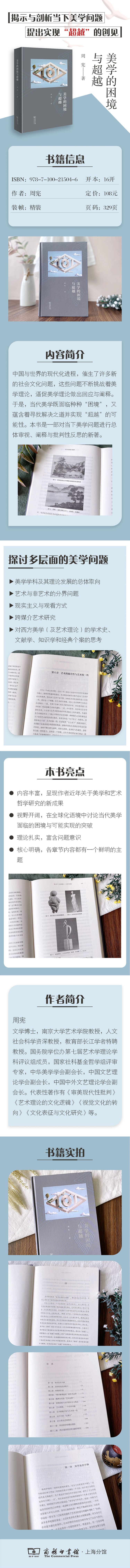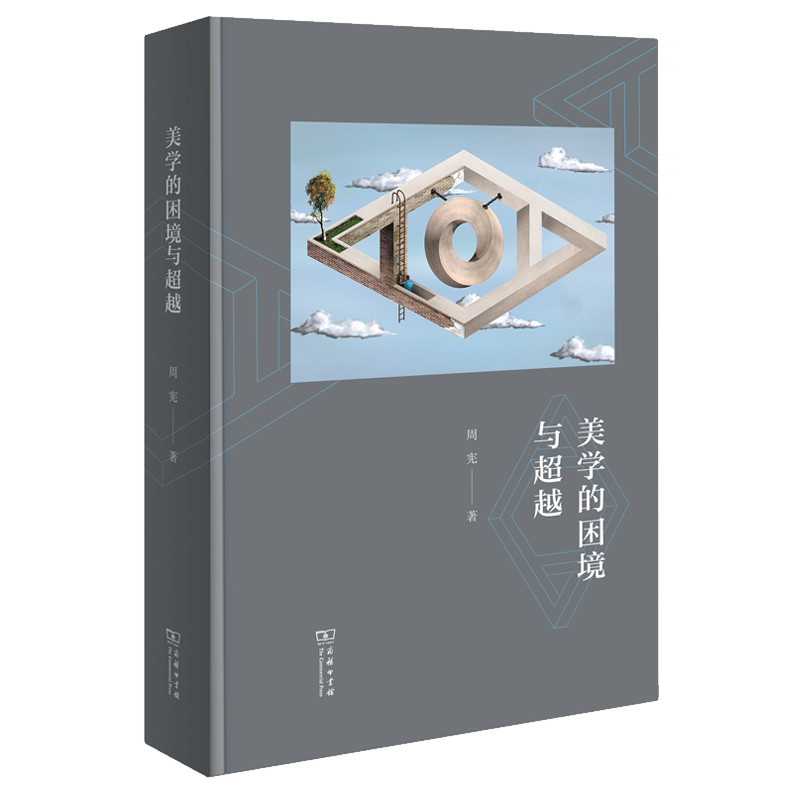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08.00
折扣价: 74.60
折扣购买: 美学的困境与超越(精)
ISBN: 9787100215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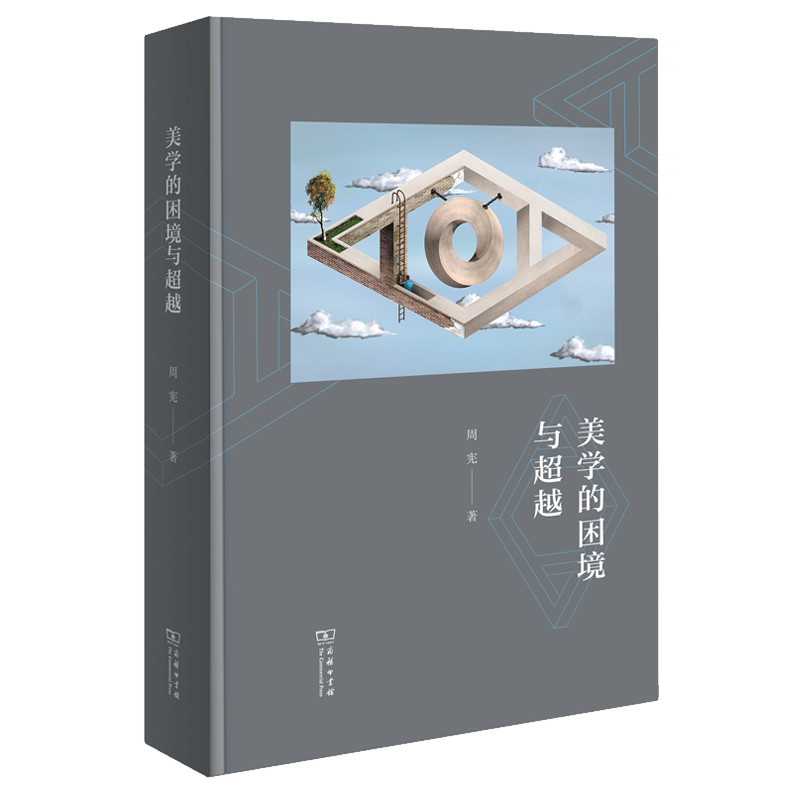
周宪,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办第七届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组评审专家,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代表性著作有《审美现代性批判》《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视觉文化的转向》《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等。
如果我们深入到当代美学内部,不难发现两种不同的美学形态。一种可名之为“自足性美学”,即把美学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知识系统,强调美学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学术性;另一种则可称之为“介入性美学”,将美学当作参与并深度介入现实世界的方式,强调美学的批判性和现实参与性。照理说,两种路向本不应抵牾对立,但随着学术体制的完善和科层化,随着知识的系统建构和高度专业化,前者对后者的压制甚至取代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一问题似未引起足够关注,美学研究者们已习惯于科层化和封闭的学术体制,却在不知不觉中与介入性美学传统渐行渐远了。 无论中外,早期的美学常常是作为社会和文化的反思者甚至批评者而出现的。无论道家美学对当时社会的激进批判,抑或希腊美学对悲剧功能的界说,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思考介入社会文化的特性,这一传统后来一直延续着。作为知识系统或学科的美学,则是18世纪中叶美学命名后出现的,它是现代性分化的后果,是知识生产专业化和学院化的产物。美学史的这一复杂情况,历史地决定了美学后来发展的不同路向。在启蒙运动高峰期,鲍姆加通率先提出了建立美学学科的设想。他对美学做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这个规定首先确认了美学是一门科学,所以他使用了一系列术语来界说——“理论”“认识论”“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科学”,等等。他还提到美学的“大姐”是逻辑学,美学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向逻辑学看齐。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学创始之初就暗含了不同的取向,今天流行的自足性美学并不是新鲜事,只不过在不可通约性消失的后现代语境中,这一取向才变得十分显著了。诚如哈贝马斯在讨论现代性时指出的那样,随着古老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瓦解,知识被区分为三个自主的领域——科学、道德和艺术。“科学话语、道德理论和法学,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渐次被体制化了。每个文化领域都和一些文化职业相对应,因此每个文化领域的问题成为本领域专家所关注的对象。” 进入后现代时期,知识生产出现了更为深刻的转变。利奥塔发现,当代(后现代)科学知识有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发展,他特别强调科学叙事中语言的差异性游戏,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特殊的术语和概念,学科知识越来越趋向自我指涉而非现实世界。于是,在科学知识的探索中,解放的和启蒙的大叙事日渐衰落,这就意味着各门知识的可通约性的丧失。于是,“科学玩的是自己的游戏”成为现实: 我们陷入这种或那种特殊知识的实证主义,学者变成科学家,高产出的研究任务变成无人能全面控制的分散任务。思辨哲学,或者说人文哲学,从此只好取消自己的合法化功能,这解释了哲学为什么在它仍然企图承担合法化功能的地方陷入危机,以及为什么在它出于现实考虑而放弃合法化功能的地方降为逻辑学研究或思想史研究。 在今天的美学研究中,解放的和启蒙的大叙事也日趋衰落,各种分离琐屑的小叙事日趋流行。美学研究的视野从启蒙时代对真、善、美等大观念的关切,日益转向了娱乐、快感、体验、时尚、身体、手机、界面、物性考量,一些原本属于美学家思考的大问题、大叙事和大观念,慢慢地在美学中销声匿迹了。美学家已从启蒙时代规则的“立法者”,转变为现象的“阐释者”(鲍曼语) ,成为各式“职业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利奥塔语)。许多美学理论或派别,比如分析美学、解释学美学或符号学美学等,就带有这类“玩的是自己的游戏”(利奥塔语)之性质。在一个狭小的学术圈子里,热衷于各种概念和定义的语言或语境条件的分析,强调论述和分析方式、分析技术的完美等。这类研究越是精致和技术化,就越发缺少带有震撼性的思想观念,与审美实践、社会文化的大问题就距离越远。依我之见,这类高度技术性的研究还带有明显的“原子化”倾向,拘泥于细枝末节问题,缺乏理论总体性和现实关联性,已经落入精于语言分析技巧的游戏性把玩。萨义德说得好:“专门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专门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对当下美学问题进行总体审视、阐释与批判性反思的新著。 本书系作者近年关于美学和艺术哲学研究的新成果,视野开阔,在全球化语境中讨论当代美学面临的困境与可能实现的突破,理论扎实,富含问题意识。各章节内容都有一个鲜明的核心主题,涉及美学知识学和方法论、艺术边界问题、现实主义再现危机、跨媒介艺术和美学史问题等,同时这些主题背后又有一条清晰的逻辑脉络,从美学领域的经典问题过渡到既传统又新颖的跨媒介艺术,贯穿传统与当代、中方与西方,对于当代美学危机面临的“困境”进行揭示与剖析,并对如何进行“超越”提出思路与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