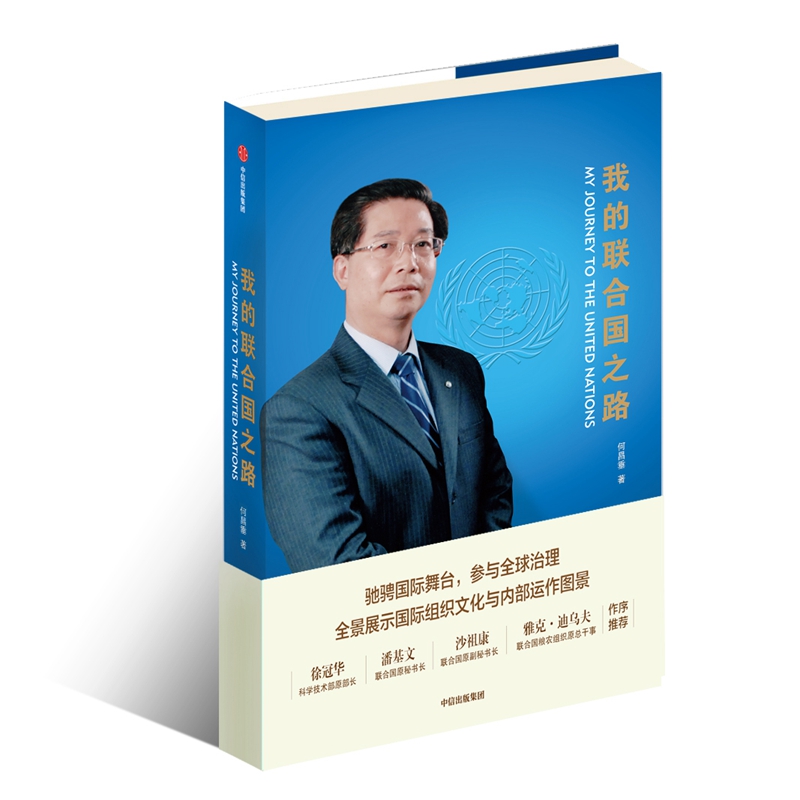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7.20
折扣购买: 我的联合国之路
ISBN: 9787521707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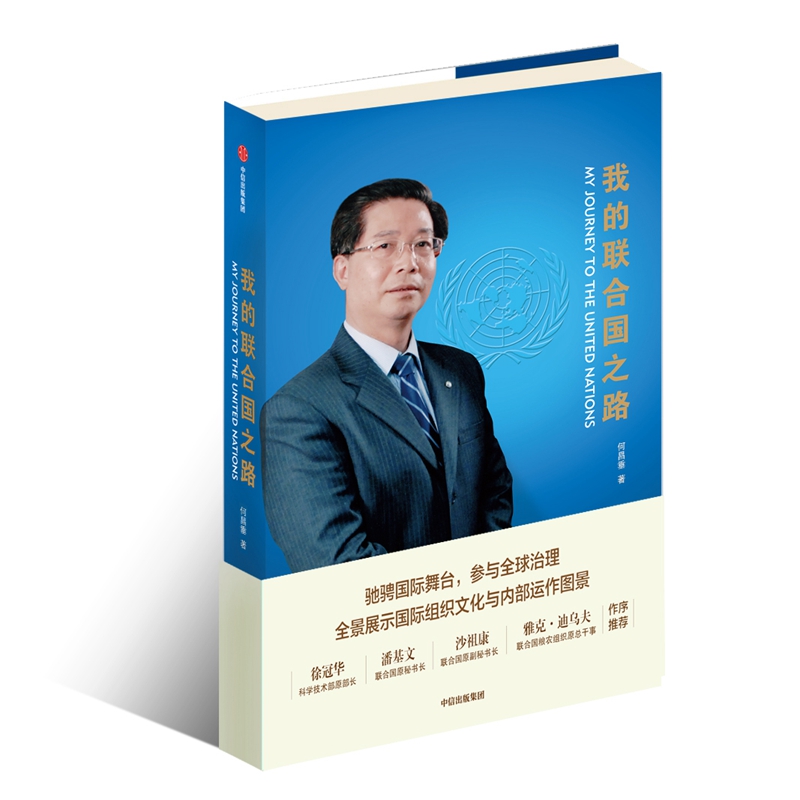
何昌垂,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联合国副秘书长级别)。曾任国家遥感中心负责人、国家863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等职,后来被国家派出任职联合国25年。
建立 “ 三机构” 协调机制 罗马三个农业和粮食安全组织, 即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应对成员国面临突发灾难时的协调、 合作机制和能力, 不断遭国际社会诟病。 2010 年 1 月 12 日发生在加勒比海岛国海地的里氏 7. 0 级大地震, 是我上任副总干事后面临的第一场考验。 别看海地体量很小, 但由于海地人性格外向, 素有直言不讳的文化, 他们的代表在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一向很有 “ 声音”, 很有影响。秘书处对这些岛国的意见也一向认真倾听、 重视。 这一点粮农组织的老职员都知道。 这次地震是自 1770 年以来海地最严重的一次大地震, 使这个西半球最不发达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包括总统府和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地在内的数百栋建筑坍塌, 首都太子港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受灾情况严重。 死亡人数超过 20 多万, 近 20 万人受伤, 几乎可以与我国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相比。 据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有关部门的快速调查估计, 此次大地震将使海地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逾 300 万人沦为难民。 海地政府完全陷入瘫痪。 国际社会做出了最快速的反应, 纷纷伸出援手, 向海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之后的第二天, 即 1 月 13 日就决定派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联合国驻海地维和部队前任负责人埃德蒙·穆莱特前往海地, 他本人也将尽快访问海地。 他同时宣布向海地提供 1 000 万美元的紧急援助。 世界银行、 欧盟以及约 30 个国家相继发表声明, 承诺给予资金和实物支援。 中国政府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一支由 68 人组成的救援队, 乘坐专机, 携带总价值约 1 200 万元人民币的 10 余吨救灾物资, 于当地时间 14 日凌晨就到达海地首都太子港, 并马上投入了搜救行动。 情势发展日益严重。 我经历过两场大型地震。 一场是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 当时我在北京, 凌晨 3 点多被震醒, 从地理所 917 大楼 7 层仓促出逃时, 头部被震落的天花板击中。 我虽无大碍, 但对于那场导致24 万人死难的地震终生难忘。 另一场则是 2004 年 12 月发生在印度洋的海啸。 我亲自指挥粮农组织进行救援行动。 我对这类灾难有特殊的敏感和警觉, 何况我现在是主管运营的副总干事。 我天天盯着电视、 电台和各种报纸, 看着不同渠道报来的信息。 我很清楚, 这次灾害的影响可不比 2004 年我在泰国曼谷经历的印度洋海啸小, 我们机构必须立即行动。 四面八方都在告急, 一时间信息异常混乱。 这倒是在我的预料之中, 因为 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时我们就有过相似经历。 当时海地通信中断, 粮农组织在当地的代表我们还无法联系上, 无论如何, 大难当头匹夫有责, 我们绝对不可缺位! 总部以最快的速度启动紧急预案, 决定马上从总部和地区办抽调人员, 从速登岛, 开展快速评估和需求调查, 安排紧急救助, 并决定先从技术合作计划紧急救援项目调拨一些资金。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紧急救灾方面的网络更加广泛, 运作体系非常成熟, 这是它的比较优势。 它实际上在震后的第三天就已经向当地灾民发放饼干等救灾物资。 而同在罗马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由于职能所限, 主要侧重灾后重建, 故而行动一般会稍微滞后。 按常理, 这本无可非议。 面对饥饿、 死亡和社会混乱的局面, 眼看着从城市向农村地区逃离的大批难民,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联合国的、 政府间的、 非政府间的组织, 不想尽力多做些力所能及之事, 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愿意落下, 承担得起滞后的诘难。 一时间, 海岛上参与救援的各路人马人满为患, 甚至忙中添乱, 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巨大压力, 引起了不必要的混乱。协调各方救灾力量成为现实、 急迫的问题。 应该承认, 罗马三机构同样缺乏协调。 这很快引起不少诟病, 特别是各国常驻代表的批评和责难。 的确, 这三机构原本存在分工不明和职能重叠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机构间利益的分割和竞争, 在救灾行动中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一些国家的代表, 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大使, 本来对罗马三机构的协调不力就有看法, 心存芥蒂; 还有一些国家在早些时候就曾建议把这三机构合并, 以便减少重复, 减少投资, 提高效率, 其最终目的是减少对多边组织的捐款。 出于这些考虑, 或许还有其他不便告人的怨气, 他们抓住了海地救援中确实存在的一些协调问题, 在各种场合和这三机构的各种会议, 大做文章, 大肆发挥, 发出尖锐的批评, 一浪高过一浪, 一时间大有 “ 黑云压城城欲摧” 之势, 其中美国驻罗马三机构的大使艾瑟琳·卡森的言辞尤为激烈。 卡森大使为此还多次来到我的办公室, 围绕三机构在海地的救援行动, 对 “粮农组织总干事管理失败 ( 她的原话是 ‘ failed governance’),没有起到罗马三机构协调人的职责” 等问题表示关切。 事实上, 法国、比利时以及欧盟代表也先后约见我, 提出了同样问题, 特别对我们三机构在海地地区 “各干各的, 碎片化的行动” 表示强烈不满。 其实, 他们并没有说出非常具体的例子, 我们认为他们多少带有一些 “ 想当然” 的印象主义和 “ 情绪化” 的批评。 因为他们这几个人谁也没有到实地考察过———他们和我一样, 都只是在罗马听取汇报, 做出判断, 结果自然有片面之处。 但他们代表的是成员国, 又是捐助国, 秘书处须得认真倾听、 深刻反思。 公平地说, 包括粮农组织总干事在内的三机构领导人对海地地震还是相当上心的。 总干事随时听取我们的汇报。 可能是考虑到我刚刚到罗马, 方方面面情况还有待熟悉, 也可能是出于事态严重, 政治影响大, 总干事决定亲自过问所有与海地有关的事情。 这本是好事。 但他决定由总干事办公室主任作为联系人, 把我和主管知识的副总干事吉姆放在一边, 这让所有人纳闷。 按理说, 办公厅主要负责机构的行政协调和对外联络, 一般不管具体技术和运营问题, 况且办公厅主任勒俊并不懂具体业务。 这样的安排无形中增加了一个层次, 自然影响效率, 而对于紧急救援事务, 时间就是生命! 事实上, 在一段时间里, 办公厅主任不得不事事找我商量、 请教。 因为我负责运营, 紧急救援也归我直接管辖。 不久, 他索性让我出面, 包括接待海地、 美国和巴西等国家大使, 主持各种技术性会谈, 召集罗马三机构间的协调会议等事宜。 作为主管运营的副总干事, 我自认 “ 国难当头, 匹夫有责”, 而且相信 “特事特办” 不会有错。 在没有总干事的明确要求下, 我多次主动召集紧急救援司司长罗恒·托马斯、 技术合作部助理总干事宋西以及拉美地区代表开碰头会, 或电话商量对策; 我还主动联络和召集三机构的二把手 (与我级别对等), 坚持在具体运营层面上保持良好沟通和必要的磋商。 在这种紧急关头, 总得有人去主动推进, 帮忙、 不添乱是我的原则。 按我的建议, 我们于 2 月 16 日召开了一次罗马三机构二把手的正式会议。 会议由我主持, 大家认真讨论了当前的情况, 达到三点共识。一是制订两步走的阶段计划: 第一步为 “6 周计划”, 提出如何赶在春播前紧急救援和部分地区恢复生产的农业投入方案; 第二步是编制此后6 个月至 3 年内生产与灾后重建总体计划。 会议同意成立三方联合技术组起草具体文件, 并要求在一周内出第一稿。 二是下周末由三机构一把手联名签署一份给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署副秘书长的备忘录, 提出 6 周计划的预算要求。 三是决定成立三方协调机制, 三机构各指定一名高管代表一把手参加至少每两周举行一次的会议, 并在技术层面保持经常性的接触、 通气与磋商。 我们强调, 需要各自向机构的一把手报告, 取得他们的支持。 我高兴的是, 总干事和其他两个机构的领导人对我们的主动性都表示了肯定和赞赏, 并同意我们会上提出的三点建议。 迪乌夫还决定, 改由我作为粮农组织的联系人, 并负责牵头召集三方联合技术组机制 ( 按机构职能, 粮农组织有牵头协调的职责, 所以我理所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然而一周之后, 迪乌夫总干事突然改变主意, 决定不给主管人道主义的副秘书长致备忘录, 改为以他个人名义, 代表罗马三机构的领导人, 向美国国会参议员乔治·麦加文发一封信。 这是一封普通的函件, 阐述目前国际社会对农口救援重视不够, 资金严重不足的关切; 信中提到我们估计短期内海地农业救灾至少需要资金 4 500 万美元, 而实际筹措到位的不过 180 万美元, 缺口巨大, 可谓杯水车薪, 根本无法应对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 信中还强烈希望美国发挥作用, 和其他捐助国一起加大对农业领域的救助力度。 我记忆中此信发出后即石沉大海, 总干事并没有收到麦加文的回信, 我也记不起后来有什么积极的效果。 我对迪乌夫总干事的这个决定很担心, 并向他明确表示我的不同看法。 我说, 我们单方面改变这个决定将会影响我们三机构后面的合作。他听了很不耐烦地说: “ 难道我作为粮农组织的总干事向成员国提交一些信息, 需要经过它们两个组织的批准?” 我认为迪乌夫总干事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有问题。 我预感到我们将面临其他两个单位的指责, 甚至认为我们言而无信, 我还担心三机构刚刚同意建立的协调机制会受到影响。 果不其然, 此信一经发出, 立即引起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严重不满。 我很快接到这两个机构负责人的电话, 他们几乎在电话那头咆哮 “ 真没法与你们合作”; 接着我就收到他们的电子邮件, 对我们没有事先和他们商量, 就改变主意、 采取单方的行动正式表示强烈不满。 听说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执行主任意见最大, 她来自美国, 是共和党人, 她对迪乌夫给美国参议员、 民主党人去信, 尤其不满。 后来我才听说, 迪乌夫总干事事先曾与麦加文参议员有过交谈, 大概是麦加文先生建议迪乌夫提供一份书面材料。 这位麦加文参议员倒是长期关注粮食安全与营养问题。 他是美国参议院 “营养与人类需求选择委员会” 主席, 曾发起 “ 美国国家食品劵和校园午餐计划” 的立法并获得通过。 他还致力于在非洲地区推动校园午餐, 注重儿童营养、 儿童教育特别是女童教育。 我与麦加文参议员有过一面之交。 那是 2010 年 5 月 20 日, 总干事请我陪他与麦加文共进工作早餐。 那次简单的早餐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谈了海地情况, 列出了很多需要紧急办的事。 麦加文知道我来自中国, 我们的话题也涉及中国的一些事。 麦加文说他对粮食危机的认识始于马歇尔将军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一句话: 他在中国遇到了比军队更强大的敌人, 那就是饥荒。 我向他介绍了当今中国粮食安全现状, 以及中国政府领导人高度重视农业和粮食的政策和主要举措。 总干事插话说: 中国用不到全世界 9% 的耕地面积解决了全球 20% 人口的粮食安全, 这是给粮农组织的 “奖励” ( bonus)。 我们还谈到计划生育和儿童营养等问题。 麦加文介绍了他在非洲的一些工作, 强调了计划生育、 儿童教育以及长远粮食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 麦加文说: “ 我老了, 要是能亲眼到中国看看就好了。” 老先生当时已经 88 岁, 但非常健谈, 也很谦和。那次交谈我印象颇为深刻。 没想到在两年之后, 2012 年 10 月他去世了。 作为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你总要经常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和不同的要求, 有时还特别苛刻, 你得时时刻刻准备及时地应对。 与此同时, 你还得有一定的度量和胸怀, 时时准备接受各方包括你的上级、 周围的同事以及外部的合作伙伴的抱怨、 批评, 甚至责难。 但你要记得, 秘书处的责任是 “时刻准备着”, 随时向成员国和合作伙伴提供满意的服务。 特别是成员国代表, 他们是老板, 个别人还时不时摆架子, 财大气粗, 表示他们总是有理。 请记住: 你的责任是多听、 少说、 多思考; 遵循的金律是想办法、 出方案、 重行动; 他们衡量你的标准是解决问题, 得到结果。 一直以来, 罗马三机构领导之间经常意见相左是公开的秘密, 属常态。 有源自机构职能的重叠, 有来自部门利益之争, 也有属个人 “ 化学反应” 不良问题。 给麦加文去信的确让我们为难, 特别是对刚成立的三方联合协调机制造成的冲击。 但我交代要尽量在工作层面弥补, 诚心在协调上下功夫, 克服 “各自为政, 碎片化行动”。 好在大家都希望给成员国一个新形象。 我对粮农组织相关官员强调, 除坚持定期召集粮农组织内部协调会议外, 要主动到粮食计划署、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和它们的执行副主任阿米尔以及副总裁卡宾当面磋商。 我们必须承认,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代表对我们三机构协调不力的意见, 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有些问题过去在其他地方就有所存在。 面对海地的灾民, 我们没有理由考虑各自部门的利益。 说严重点, 那是不负责任。 保持经常性接触, 使我们三机构的几位副手有了更实际的共识, 也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想法。 我们都同意: 一是要加强在实地调查工作的协调; 二是及时分享从现场收集的各种信息; 三是最大限度相互借助和利用三方各自的优势资源, 采取统一计划, 形成合力。 我们相信, 按照这三点原则行事, 可以使罗马三机构在海地灾区的 “行动更具互补性、 一致性, 结果也将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 鉴于我们三人都是联合国机构间人道主义救援指导委员会的成员, 我们还决定根据这三原则, 提前协商我们每次到日内瓦参会的共同立场。 我们在三机构的第二把手层面建立的这种磋商机制一直得以持续, 而且在其他紧急救援行动中也沿用了这种模式。 2010 年 7 月巴基斯坦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水灾, 面对这场 “ 毁灭性灾害”, 粮农组织立即加入了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紧急救援行动。 我们迅速组织了快速评估, 巴基斯坦从北到南 1 000 多千米的距离, 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被洪水淹没, 17% 的农作物可能绝收, 120 万头牲畜和 600 万只家禽损失,受灾人口达 1 700 万, 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超过 2 000 人。 根据前方报告, 需要直接救援的人口达 800 万。 老天竟如此不公, 让这个本来就很贫穷的国家国民不济, 社会不稳, 生灵涂炭, 雪上加霜。 基于海地地震初期我们被成员国批评 “ 协调不力” 的教训, 罗马三机构在巴基斯坦特大水灾的第一时间就启动了联合紧急救援机制。 从7 月底到 8 月初, 我们连续三次召集三方协调会议。 在吸取海地救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我们提前组织了信息共享机制, 分析各方掌握的现有情况, 磋商研究共同计划, 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行动。 这次, 粮农组织有效利用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分布在巴基斯坦全国从北到南各地的 100 多个非政府组织粮食发放网点, 网点在粮农组织的技术专家指导下, 派发农机具、 种子和化肥等; 而世界粮食计划署则利用粮农组织的国家办公室的便捷和在实地具有的专家团队, 组织当地服务, 调配运力, 开展实时监控和反馈, 等等。 通过总部的协调和野外的协作, 紧急救援的总体效果和实际影响比应对海地地震初期出现的 “ 集体忙乱” 和 “ 整体被动” 要好很多了。 经验告诉我们, 由于灾区救援工作的急迫性和特殊性, 时间就是生命, 不能完全按照普通发展项目的决策程序, 按部就班。 在大灾和巨灾面前, 赖以决策的信息来源往往比较有限, 且滞后、 粗糙, 缺乏精准和可靠性。 有时信息太混乱, 可信度极低, 甚至根本无法采集到信息, 资讯空白, 给决策工作带来巨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保障秘书处和灾区所有可能信息渠道的畅通, 特别是加强与当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沟通, 至关重要。 我们还学会了无论怎么忙, 必须建立一种透明的沟通机制, 让成员国特别是捐助方及时知道秘书处的计划, 了解我们的行动方案, 掌握项目的进展状况。 我们利用罗马三机构的各种主要会议, 主动协调组织通报三机构的情况, 如关于加强海地救灾和灾后重建协调工作的各种决定, 巴基斯坦的救灾项目建议以及救援经费需求更新和筹措情况。 这些做法本身谈不上是创新, 却帮助增强了秘书处与成员国的互动和联动, 效果的确不错。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 及时的沟通和透明的资讯, 是获得成员国更好的理解和更广泛支持的重要基础。 但凡没有偏见, 人们就会看到, 在海地地震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罗马三机构在紧急救援工作的协调和联合行动的效率明显提升, 也积累了一些很好的实践经验。 单以粮农组织为例, 从 2010 年到 2012 年的 3 年时间, 我们为海地紧急救援和后续行动安排了 40 多个救援和灾后农业恢复重建项目, 筹措了约 4 500 多万美元的资金。 而在巴基斯坦, 从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 到 2013 年年初我退休离开联合国, 粮农组织通过与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等部门, 欧盟、 英国、 美国、 法国、 加拿大和瑞典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 筹集了大约 1. 35 亿美元的紧急农业援助资金, 用于采购种子、 化肥、 农机具等, 落实了 50 多个项目, 帮助当地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恢复农民生计, 重建农村家园。 应该承认, 不管我们如何努力, 问题依旧存在, 主要机构间协调不力的根子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美国政府换届, 奥巴马上任后, 决定推荐美国驻罗马三机构的代表, 也就是曾经对我们 “ 协调不力” 意见最为激烈的艾瑟琳·卡森大使, 取代同样来自美国的希兰女士, 出任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执行主任。 然而, 三机构间的协调并没有比卡森任大使时要求的标准强多少。 我与卡森有过一次对话, 希望她在任内能够帮助推动“罗马三巨头” 更好沟通, 她只好承认: “ 不是那么容易, 看来得走着瞧。” 国际组织的职能重复, 协调困难。 联合国的改革也往往只是治标, 很少能真正治本, 积重难返, 终成疑难杂症。 我很早就观察到这个问题, 也在多个场合表示我的不满。 我认为, 成员国才是始作俑者, 它们往往在发现一个组织的平庸甚至失败时, 企图用建立一个新组织的办法取而代之, 结果造成 “ 山头林立”, 反而事与愿违、 适得其反。 2006 年, 我曾对联合国粮农组织独立外部评价团和英国驻罗马三机构的常驻代表建议: 联合国成员国本身治理机制的改革, 才是联合国改革的原点。 我认为, 这应该是罗马三个涉农组织改革, 甚至是今后联合国系统改革的一个重点。 这是一本朴实而难掩其光华的好书。作者从一个贫苦渔民子弟通过自己的奋斗一步步成长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级高级官员,这样的故事难道不能激励到你吗? 作者年届70,仍不抛一腔报国的热忱,怀着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初心,总结了自己从科研人员到科员管理人员,从国内公务员到国际高级公务员的种种历程。作者希望以此书激发青年站在国际舞台,代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热忱;更希望中国籍国际公务员能进得去、站得住、做得好、升得上、有话语、有影响;也希望一代代人能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在时代的浪潮中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