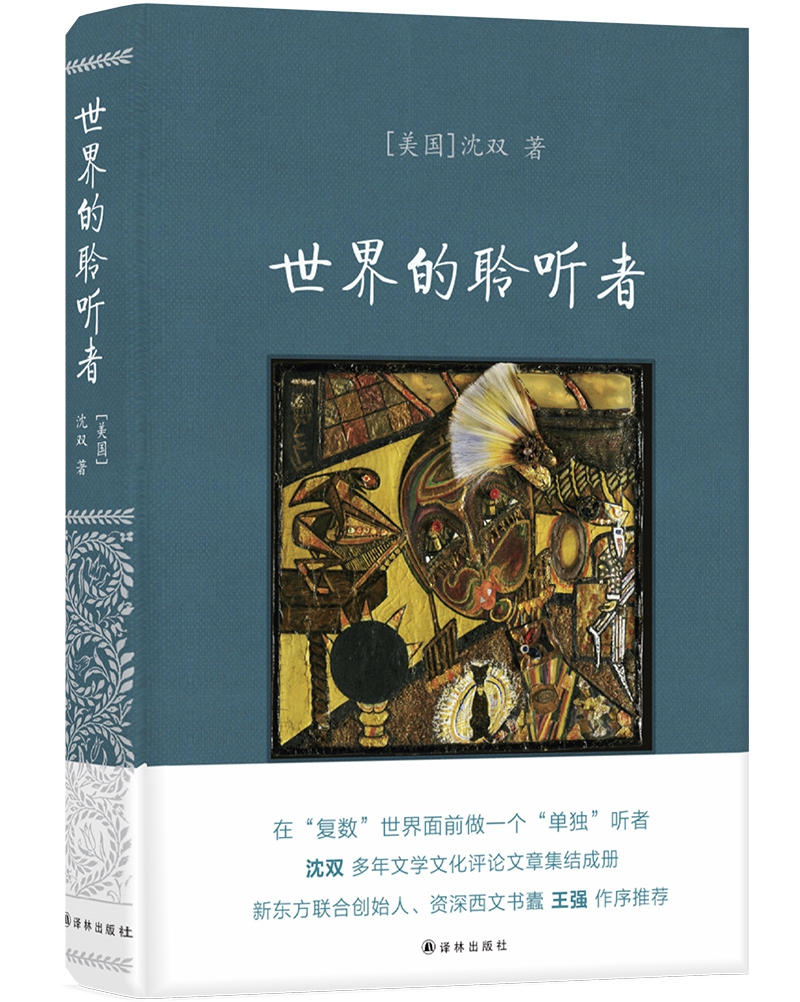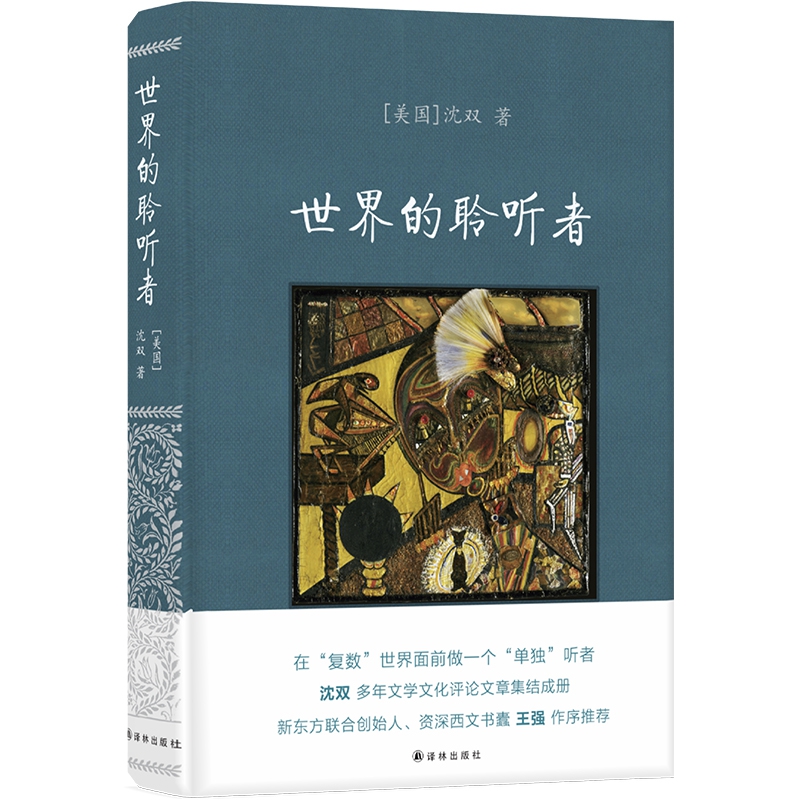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24.20
折扣购买: 世界的聆听者
ISBN: 97875447825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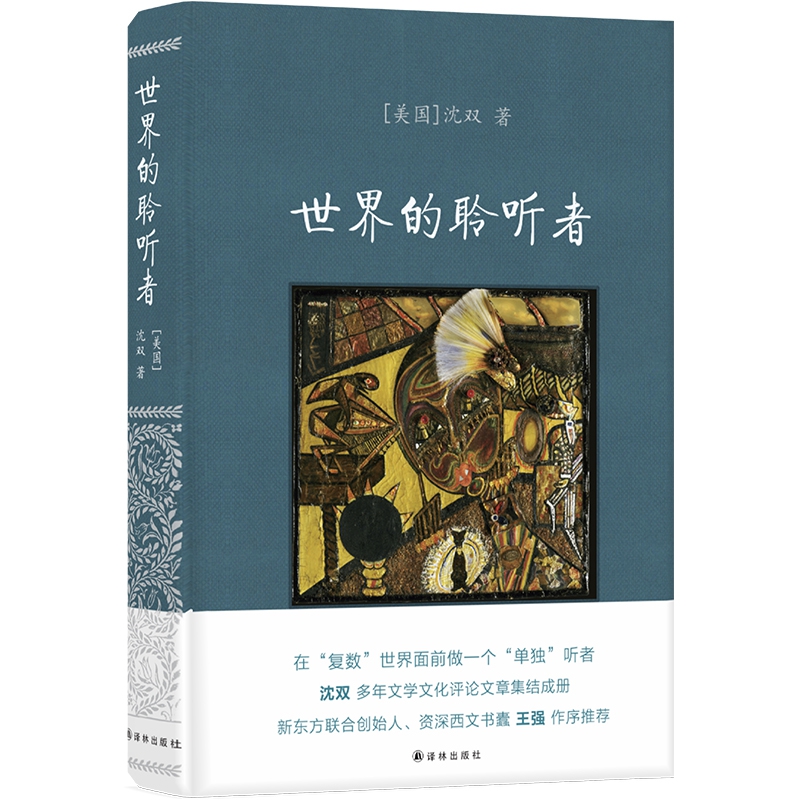
沈双 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比较文学系,广泛关注美国文学文化以及任何与跨文化交流相关的话题。曾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并为中英文杂志和期刊撰写过多篇评论文章。
在纽约读木心 我在大学英语系教的一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专题”课里,别出心裁地安排了横光利一的小说《上海》,作为现代文学的案例研究。讲二十世纪文学以及现代派而不以英美为中心,这是要费一番口舌向系里解释的。怎样做的解释我已经忘记,只记得心里一直纳闷 :横光利一小说的“中心”在哪里?它是属于上海的还是东京的?后来看了一篇作者的访谈录,中间一段话大意是说“上海的公共租界的问题是最令人费解的,然而它所面临的正是整个世界未来的问题。说来也很简单,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上海的租界一样具有如此完整的现代特性……思考这个地方就是对整个世界进行思考”。我突然明白关键不在于上海还是东京,原来,描写的对象是整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像是对于现代的理解一样,人各有异,但是把当时的上海看成一个国际竞技场却是很多人不约而同阐发的一种心情。最近读了木心的《上海赋》,我以为实际上是用不同的口气讲了同一个意思。木心并不赞同鲁迅的“南北之分刚柔之别”,觉得“小看了海派”,“海派是大的,是上海的都市性格,先地灵而人杰,后人杰而地灵,上海是暴起的,早熟的,英气勃勃的,其俊爽豪迈可与世界各大都会格争雄长”。但是又说,上海没有文化渊源,没有上流社会,所以作不出“正传”,写海派只能写出“上海无海派”,正是和横光利一写到的上海一方面代表了整个世界的未来,另一方面预示着这个世界的问题,同出一辙。未来是一个充满了危机的未来,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气魄把这份危机感涵纳其中的,在这个意义上“海派是大的”,就如同横光利一所说,“思考这个地方就是对整个世界进行思考”。 木心与横光利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木心对大时代的逝去表达了无限的怅惘。“再会吧,再会吧,从前的上海人。”他写起上海来无论多么铺陈叠嶂,描述起来不管怎样事无巨细,好像都让你觉得有所欠缺,就因为有这个“大”字垫底。试想一下,的确,怎么写都没有办法写尽这个世界的,除非通过象征(allegory),然而木心又不愿牺牲感性的经验的一面,拒绝象征。“到了无可奈何时才产生象征”,所以只能反写,正所谓“要写海派,只能写成‘上海无海派’”,通过身体经验历史,很快会遭遇极限的。通过城市来描写世界亦然。 其实我本来迫不及待地找来木心的散文来看,不是因为上海,而是因为纽约。纽约和上海一样,也配得上一个“大”字,但是“大”的方式却不一样。木心说,这里“遍地都有我愿意同情而同情不了的人人物物事事”,意思是说纽约的隔膜和异化,这我也有同感。木心描写的地方,林肯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哈德逊河畔,甚至离市区甚远的琼美卡,都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恰恰如此,我对它们视而不见。实际上这就是纽约的态度—视而不见。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想同情却同情不了的人和事。对此大部分人都走进自己的空间,躲进了各自的职业,自说自话,不管有没有人听。小部分人没完没了地追求新奇,不断跨界。所以纽约的“大”和海派之大不一样,不在于物质的丰富,社会结构的复杂,而在于心理的冲击力太大。一般人慢慢养就了同一种反应,不管对任何人和事,都以同一种心态对待。 木心的不凡之处,在于他居然可以让心理出去散个步时迷了路,居然可以让心理不断地接受挑战而不厌。我自己也许会听到林肯中心的鼓声产生一种“冒着大雨”也要追随这声音的欲望,但是我不再会为“同车人的啜泣”所打动,也不可能对琼美卡马路上的花朵以及千篇一律的住宅产生任何想法。能够把哥伦布发现的刻板单一的新大陆演化成哥伦比亚的重重叠叠的阴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在这里生活越久越难。所以美国文学中的游记是很好看的,传达的都是来自别的社会的新鲜角度。木心能不断地写美国的心灵游记,来自某种心力,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2006年5月 异地的本地特色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什么是它的本地文化,这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大致想来,本地性一般归结于某些文体特点、语言风格,但是本地文化是否必须要呈现这些特点和风格呢?我的同事曾经在一部研究美国文学的专著中指出,十八世纪美国的书商大张旗鼓地推销美国图书时,完全不关心文体或语言风格,所谓的“美国性”是没有办法从文本中表现出来的。书商们把购买美版图书描述成一种爱国行为,把书看成无异于其他商品的器物,和中国人在某一时刻抵制日货抵制美货的逻辑没有两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流通界定了文化产品的属性,写作和阅读都在其次。 我现在所居住的城市香港和以前住的纽约有一点大不相同 :在香港,本地性还算得上是一个问题 ;而在纽约,它已经是一个心领神会但是不愿公开谈的话题。不愿谈,并不因为有了一些公认的本地化的标志,而是因为社会变化太快,移民太多,每一种对本地化正面的叙述都有点跟不上变化的节奏,总是显得很保守,很小家子气。因此聪明人都不愿去谈本地特点,谈美国性,怕被理解成排外,或者故步自封。 在美国,但凡一件事反着说总比正着说占便宜,批判的姿态本身就是一个地方色彩。 然而香港是华人社会,我们对待范畴的态度和美国的习惯很不一样。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后,一位很敏锐的香港学者撰书指出,从八十年代中英会谈开始生产的香港电影,不断以香港为题,喋喋不休地叙说着香港的故事,这一时期的电影就代表了香港文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似乎十年之后的情形有所改变。现在香港有的文艺作品并不以香港为主体,而是把它作为背景,甚至作为方法和角度。这样一来实际上对读者的挑战更大,更不能够现实主义地解读小说和电影了。香港已经嵌进了别的地方的故事。 香港话剧团毛俊辉执导的话剧《万家之宝》就是一例。毛导在某一场合说这一话剧综合了曹禺的三个剧本,是为了向香港观众介绍这一伟大的剧作家,但是因为作品的时代十分久远,而且地处北方,不加修改恐怕观众不会接受。因此第一段选自《原野》,以非常现代的简洁的方式处理 ;第二段选自《北京人》,用英文演,仍然很现代,突出的是两个女人的心理,而不是复杂的大家庭的人际关系 ;第三段选自《日出》,背景是七十年代的香港,陈白露的沉浮放到正在腾飞的城市里来看,她不像一个堕落了却还有反省能力的女人,而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在股场上失意了的暴发户。 我不觉得这个改编十分成功,导演看起来过于小心,生怕毁坏了原作的完整性似的。而且导演声称要反映后殖民城市的生活,我怎么也没有看出来究竟。第二段的英文对白能够投合这个城市比较西化的人的兴趣,但是我总觉得西化的中国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并没有被那些过于简单的台词传达出来。这一段的对白围绕着一个去留的问题和忠诚与背叛的问题,似乎在影射香港十年或二十年前的情况。但是导演没有进一步发挥,只停留在影射的层面,没有深度的思考。 然而,这个改编倒是代表了香港文化的一个路向,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我的几个同事就曾考察出各种各样的改编案例。看完戏我随便到附近的 HMV转了一圈,就买到了由吴回导演、李小龙扮演周冲的《雷雨》,以及改编自希区柯克的《后窗》的同名作品。我想应该去调查一下,香港观众是不是真的没有看过曹禺的作品,还是不知道这个名字?如果是后者,倒是不必担心了。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满城尽带黄金甲》,难道和曹禺有关吗? 原载于《新民周刊》 2007年第23期 学者沈双有着多年的国际行旅和文化生活体验,在她的眼中,世界会是何种面貌?纽约、上海、香港、伦敦,作者辗转于这些世界文化中心,借文本、戏剧、电影来展示文化的移植和碰撞:在纽约读木心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张爱玲的移民经历对她的自我翻译产生了什么影响?李安又在何种意义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借此聆听与思考,沈双试图抵达她内心的“真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