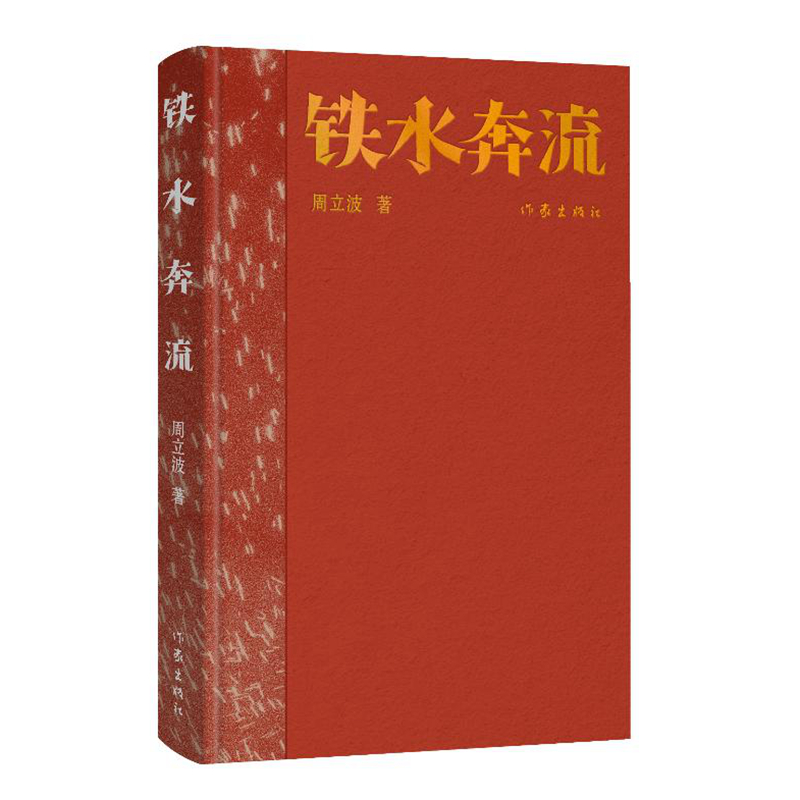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5.76
折扣购买: 铁水奔流(典藏版)
ISBN: 97875212305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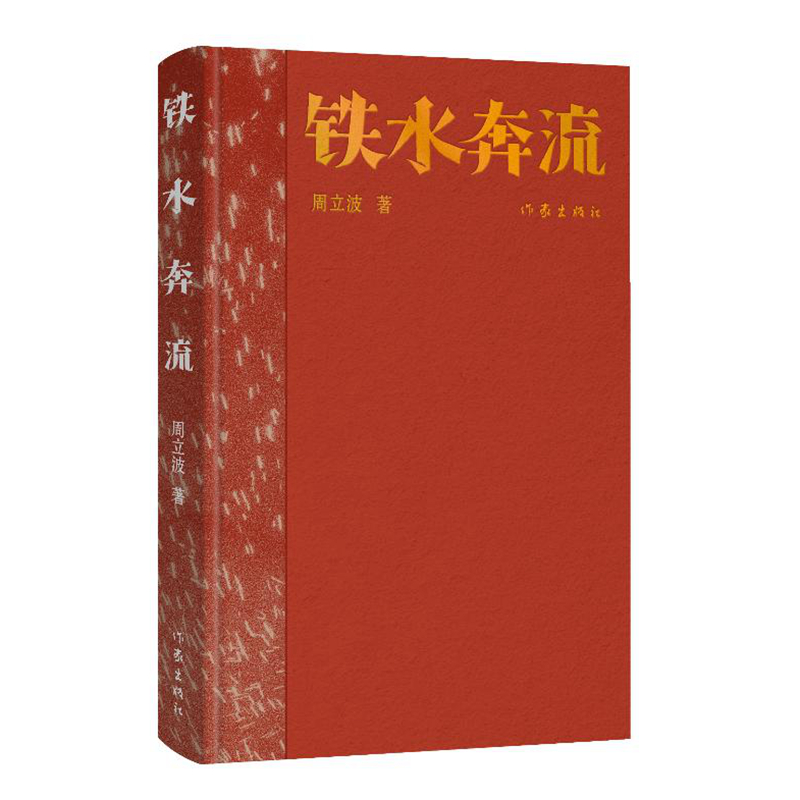
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1934年参加左联,曾任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和晋察冀边区战地记者,延安鲁艺教师,湖南省文联主席,湖南省作协主席等。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短篇小说集《铁门里》《山那边人家》,报告文学集《战场三记》《南下记》,译著《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等。
\"战争正在进行着。 骆驼山上,火烟翻滚。工厂东南,二十几门各种口径的大炮正对着山上不停地轰击,爆响如雷,山摇地动,浓黑的硝烟飘浮在山顶,通红的火焰冲上了天空。山上的铁旗杆子打断了,褪了色的青天白日旗像一片败叶,在风里飘落。碉堡着火了,小钢炮和机关枪都不吭声了。蒋匪官兵慌慌张张跑出来,在山上乱窜。紧跟着,一颗炮弹打中了他们,匪徒们有的倒了,有的连人带枪往山下直滚。山脚下,钢铁厂的工人纷纷拥出了车间,三个一伙,五个一堆,站在广场上和马路上。子弹流子叽叽地从头顶擦过,有好几颗落在他们的跟前,弹着点崩起的雪花和尘土扑上了裤腿,但他们都不害怕,也不躲闪。这些满手油泥、衣裳破烂的工人完全忘了身边的危险,只顾望着山上着火的碉堡,大家称心趁愿,拍手欢呼,并且按着各人不同的脾气,使唤自己惯用的字眼,七嘴八舌地发表各式各样的评论: “打得多棒。” “叫他们尝尝铁蛋。” “送上这些铁干粮,叫他们吃了一辈子也不饿。” “蒋该死算是恶贯满盈了。” “再下山来‘借’手表,‘借’金镏子吧,狼心兔胆的家伙。” “一炮就把铁旗杆子打折了。” “大王八窝也毁了。” “这后一炮也不算赖,干掉不少。” 两个山峰上的两个碉堡都垮了,蒋匪官兵死的死,滚的滚,逃的逃,跑的跑。一会儿,骆驼山上只剩两个碉堡空架子还在冒烟。工人们都转过身子,往东南探望,好奇地想发现炮兵阵地。烟囱、楼房和榆柳行子遮住了大家的视线。炮声停止了,只有步枪和机枪还在山前山后,厂里厂外,起起落落地发出连放和点射的爆响。 战事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早上。冷风吹木人的脸,雪花漫天地飘卷。钢铁厂的循环水池早结了冰,冰上落了一层雪。十四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的先头部队派遣了九个战士从正南插进碉堡重重的工厂区。厂里厂外,谣言纷起:有说要打的,有说要和的,也有人说打了再讲和,还有人说和了还得打。国民党驻军登时乱套了。匪徒们动手“借”东西,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抢劫。山下村和池边村的宿舍里发出了锅碗砸破,玻璃打碎的脆响,还夹杂着女人的哭泣和孩子的叫闹。有个高高大大的,军官模样的家伙,把美国式的大檐帽推到后脑瓜子上,露出冒汗的前额和蓬松的头发,从山下村一家人家的后门,急忙走出来,把手里的左轮手枪插进腰上的皮套里,把他“借”来的第九只手表,扣在左腕上。 瞧着这乱马人哗的样子,人们都粗声地叹气,低声地咒骂。凭着战争时世的多次的经验,大家也知道:兔崽子们狠狠捞一把,是在准备逃跑了。他们的确想逃跑,但一打听,解放军只来了几个,就又稳住了。驻厂的匪军头儿立即下一道命令:“固守工厂,以待援兵。”骆驼山顶,石头山上和大水池子东边的碉堡,也都重新分兵去把守,用机枪小炮控制着全厂。伪厂警队也活动起来了。他们的棉袄袖子上的白臂箍,写着两个字:“护厂”。工厂的东门和西门都有人守卫。厂里厂外,断绝了交通,工厂里的工人不准回家,宿舍里的工人不能进厂。 整个工厂是一片混乱、荒凉和漆黑。所有车间停工了,焦炉熄火了,烟囱不冒烟,送风机和回水泵早销声没息,三百来个大大小小的电滚子①停止了运转,机车瘫在铁轨上,渣车横在三岔口。赶到天黑,电灯全灭了,又下起雪来,这里那里,在伪厂警队打出来的电棒的强烈的闪光里,人们看见小朵的雪花,一阵紧一阵地飘落着,地面铺白了,树枝都变成了银枝。留在厂里的工人挤进地沟和防空洞里,去躲避风雪,顺便找个打盹的地方。煤渣路上,工厂门边,常常听到伪厂警们的一声两声装做威威势势的,却是嘶哑的吆喝: “口令,干什么的?” 厂里厂外,远远近近,夹杂在狗叫声里,驴鸣声里,也传来了稀稀落落的枪声。 十五日拂晓,一个伪厂警队员,肩上挂条枪,威风抖抖,走到地沟边,弯下腰去,对下面的工人们发表谈话道: “八路军消灭光了,快干活去,谁不去,就枪毙。” 话没有落音,大炮响了。他们的炮队早已撤退,他听了一下,觉得不对劲,正扭头要颠,地沟和防空洞里的工人蜂拥出来了。为首一个浓眉大眼的工人,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浑身油泥的青土布棉袄,脖子上围一条黑脏的白毛巾,腰上扎一根草绳,听到炮声,他大步流星地赶上伪厂警,拦住他问道: “八路军不是消灭光了吗?这是谁的炮?说呀。” 伪厂警瞪着眼睛,威胁地反问他道: “你叫什么名字?” 腰上扎着草绳的工人左手叉腰,往前迈上一步说: “我姓李,名大贵,你要怎样?” 伪厂警没有来得及回嘴,人群里先后扔出三块耐火砖,有一块差点打在他头上。正在这时,骆驼山上的碉堡,被炮轰穿了,枪声越来越稠密,他慌了手脚,趁大家往山上看时,他挤进人堆,悄悄溜走了。 骆驼山上的碉堡摧毁了,工人们都扭转头来,朝东南探望,好奇地想发现炮兵阵地,李大贵望着东面,忽然叫道: “来了。” 大家都朝东望去。通往工厂小东门的煤渣大路上,出现三个人,身穿草绿色军装,手提卡宾枪,头戴白兔皮帽子,在漫天飘舞的灰蒙蒙的雪花里,嘴里冒出一团团的白雾,急奔过来。李大贵拍手欢叫道: “解放军来了。” 旁边一个职员模样的人问道: “你怎么知道?” “你瞧,都没有帽花,解放军是不戴帽花的。” 职员模样的人又问道: “你怎么知道?” 李大贵没有回答,眼睛只顾看前面,三个解放军战士越跑越近了,他已经能清晰地看见他们脸上冒着热腾腾的汗气,胡子上、眉毛上都挂着细小的、闪亮的霜花。三个人跑到发电所的灰砖墙根下,工人们奔跑过来,为首一位高个子战士,两手握住枪,警惕地问道: “你们都是本厂工友吗?” 工人们都站住了。他们是头一回看见自己的军队,想亲近,又不敢放肆,都老远站着,看见战士提着卡宾枪,腰上佩着手榴弹,雄赳赳的模样,又听见他们这样地发问,连李大贵也一时怯住,没有作声,后面有些人想趁势溜了。为首的高个子战士好像猜出了大家的心理,笑着说道: “大伙别怕,别怕,咱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来保护工厂的。” 李大贵挤到前头来,大胆地说道: “不怕,不怕。我明白,你们就是解放军。” 高个子战士用衣袖擦干额上的雪水和汗珠,上下打量这位浓眉大眼、身板壮实的小伙子,看见他头戴破毡帽,身穿补丁摞补丁的青棉袄,腰上扎一根草绳,衣上脸上,尽是油泥,十指都是粗粗大大的,知道这是一个正经干活的工人,就移近一步,亲热地笑道: “这位工友,你怎么知道咱们就是解放军?” 李大贵忙说: “您不戴帽花,也不熊人。要是国民党那帮兔崽子,到咱们跟前,早骂开了:‘滚开,滚开。’你们毁了王八窝,叫他们都滚下山了,骂人滚蛋的,自己滚蛋了,这叫做现世现报。” 李大贵啰啰嗦嗦说上一大篇,战士们笑了,工人们也都笑着靠拢来,把三位战士紧紧地围在中间,几个人同时掏出烟卷,同时伸给客人们。战士们委婉地笑着拒绝了。为首的高个子战士从衣兜里掏出了烟包和木头烟斗。他往烟锅里塞满黄烟,跟工人对了一个火,吧嗒吧嗒,就抽开了。青年工人们拥到战士们跟前,愉快地、羡慕地瞅着他们胸前佩戴的各种颜色、各种金属的纪念章。一个小伙子指着一个铜质头像问: “这是谁?” 嘴里衔着烟斗的高个子战士,脸上发出愉快的、荣耀的神采,笑着回道: “毛主席。” 听到这话,大家越发挤上来,把战士围得更紧,他们争着要看早已听到的毛主席。 雪还飘落着,浓密的纯净的干雪,扑在战士们的脸庞上,化作雪水,顺脸颊淌下。高个子战士抽完一斗烟,把烟锅在枪柄上轻轻敲了敲,随后又放在嘴里,吹了吹,重新揣进衣兜里。他抬起右手,又用衣袖擦擦脸,正要走开,工厂北面,枪声又起了。战士们机警地挤出人群,离发电所,走到第一高炉下面的地沟边,横着枪,问工人道: “这里头有敌人吗?” 跟在他们背后的李大贵回答: “没有。都爬进王八窝去了。”他说着,抬手指指水池的东面。 高个子战士望着他指点的方向,远远看见水池的东面,一个小小土坡上,有一座红砖的圆形碉堡,碉堡上满是黑洞洞的枪眼。靠近碉堡,是机器房和变电所,还有送风室和水泵房,工人们说:“都是工厂的要害。”高个子战士心里盘算:要是联络炮兵,用大炮轰击,这座小碉堡只消几下就得了,就怕打坏了要紧的机器和设备。他跟两位战友离开工人们,一起跑到机器房背后,蹲在墙脚下,合计了一会儿,三个人下定了决心,就站起身来,机敏地从房屋、墙壁、倒渣车和废铁堆的后面,绕到碉堡的东北。三分钟后,他们出现在铁路旁边一块开阔地面上,离碉堡约莫还有四十米。工人们的眼睛都跟着他们移动。勇士们一手拿着揭了盖子的木柄手榴弹,一手提着卡宾枪,翻穿着大衣,扑在雪地上,侧着身子,用胳膊肘撑在地面上,敏捷地往碉堡的紧跟前爬去。 碉堡里没有动静。敌人好像没有发觉进逼的战士。在他们接近土坡,抬起身子的瞬间,枪眼里冷丁吐出两条通红的火舌,机枪子弹像一阵骤雨,蒙头盖脑撒过来,里边还夹杂着步枪的射击。高个子战士胳膊一伸,仰脸倒下了。他的两位战友慌忙爬过来,把他移到近边土坑里。一个战士扶起他的头,把自己的脸贴在他的鼻子上。鼻孔里只有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的出气了。另一个战士双手捏着他胳膊,颤声地叫道:“班长,班长,赵班长。”没有答应,不再动弹,呼吸也停了。一个战士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擦枪的红绸子,轻轻地、庄重地盖在闭了眼皮的他们的亲爱的战友的脸上。两个人握着枪,低着头,不说一句话,悲伤呛住了他们。他们的眼睛潮湿了。但在火线上,哀悼只能是很短促的。枪子纷纷落在两人的周围,敌人在跟前,复仇的怒焰烧干了悲怆的泪水,两人眼睛都红了,彼此看一眼,就一声不响,好像两只狂怒的猛虎一样,跳出土坑,蹦上土坡,冒着子弹的急雨,一下子扑到了碉堡墙边的死角,把手榴弹塞进了枪眼。工人们听见一声巨响,接着又一声,碉堡里的机枪和步枪立刻都成哑巴了,残匪在里边失魂落魄地叫唤: “咱们投降呵,别打了。” 接着,从碉堡的机关枪眼里伸出了一块挂在枪尖上的白绸子手帕,迎着寒风,哀求似的,不停地飘动。 枪声还没有停住,工人就从四面八方拥到土坑边,围着高个子战士。他躺在积雪的土坑里,盖着红绸的头脸冲着灰蒙蒙的飘雪的天空,两只手还紧紧地抓住手榴弹和卡宾枪。李大贵和另外三个工人跳下土坑,把烈士的遗体抬上来,轻轻放在雪地上。李大贵蹲下身子,摸摸他胸脯,寻找他的枪伤,发现他胸口中了三弹,致命的一颗穿透了心房。李大贵又揭开红绸子,摸摸他脸额,已经冰凉了。他凄惶地站起身来,静穆地摘下毡帽,工人们也都跟着脱下了帽子。李大贵寻思:“一刻钟以前,他还跟大家在一起谈笑,抽烟,用衣袖擦他脸上的汗珠和雪水,现在,为着保护工厂的要害,他躺下了,永远躺下了。”雪还在飘卷,小朵小朵的雪花落在象牙似的年轻的脸上,不再融化了。不大一会儿,纯净的、洁白的干雪盖住了他的结实的身体和端正的脸庞。 大队的攻击部队到来时,战斗已经结束了。俘虏押走后,工人们还是不散。李大贵和几个青年帮助战士们张罗烈士的后事。一口杨木棺材抬来了。烈士成殓时,钢铁厂木瓦工场的老瓦工邹云山,从新镇买来一大沓黄纸,在灵前烧化。 李大贵说道: “烧这干吗?他们不信这。把他葬在工厂的近边,给他立个碑,倒是正经。” 邹云山忙说: “你这主意好,快跟他们说。” 李大贵找着英雄连队的指导员,把他的意见说了。指导员同意,并且感谢他。 工人和战士把灵柩送到工厂北边的松树林子里。大伙动手挖土坑,修墓地。洋镐和铁铲,碰着冻硬的土地,发出深沉的声响。指导员坐在一株倒了的、盖着一溜积雪的松树上,从衣兜里掏出铅笔和本子,写了下面这碑文: “人民解放军英雄班长共产党员赵五孩之墓。” 写完以后,指导员用手背擦擦潮湿的眼窝,把这一页从本子上扯下,交给李大贵。他又呵着冻僵的手指,握住笔,在小本子上记下烈士阵亡的日期和地点,并且简要地记述他牺牲前后的情景和墓地松林的方位,准备汇报上级,通知烈属。 新坟筑成了,大伙离开时,邹云山眼瞅着坟堆,激动地、小声地叮咛: “好好待着吧,同志,赶清明再来看您,给您烧纸。” 说话的口气,好像坟里的人还活着一样。大家没有再作声,慢慢地移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松林,就都走散了。雪还没有停,天头早黑了。远远传来轰隆的炮响,石头山上也还有枪声。工人们有些家去,有些在工厂周围,好奇地、没有目的地到处溜达着。李大贵把指导员托付给他的字条小心揣在衣兜里,准备找石匠刻碑。在回家的路上,他脑子里总是闪现着赵五孩的象牙似的端正的脸庞。心里老念着: “真是好样的,真是好汉。” 李大贵的老家,河北容城,离老解放区不远,一九三八年春天,他的大哥李大富离开家乡,参加了八路军。因为这样,李大贵对于解放区跟解放军早就格外地关心。 他听到过解放军的许多故事,但光是听说,没有见过,这回亲眼看到了。他寻思道:“人家都那样勇敢,一个个跟猛虎一样。”溜达一阵,十二点过了,他想家去,又觉着家里太窄小、太憋闷。到了银顶街门口,他又拐回来,往工厂走去。小东门口,一大帮工人正在议论着什么。有人叫嚷道: “说话就拿石头山了。” 石头山上的碉堡给炮轰平了,蒋匪残兵还在石崖背后、杂树丛里,往山下放枪。 远远看去,黑糊糊的山顶和山腰,正不停地冒出星星点点的晃眼的闪光。李大贵看了一会儿,又盘算了一阵,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家也不回,迈开大步,急急忙忙往石头山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