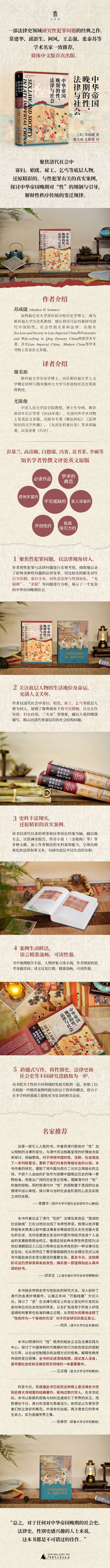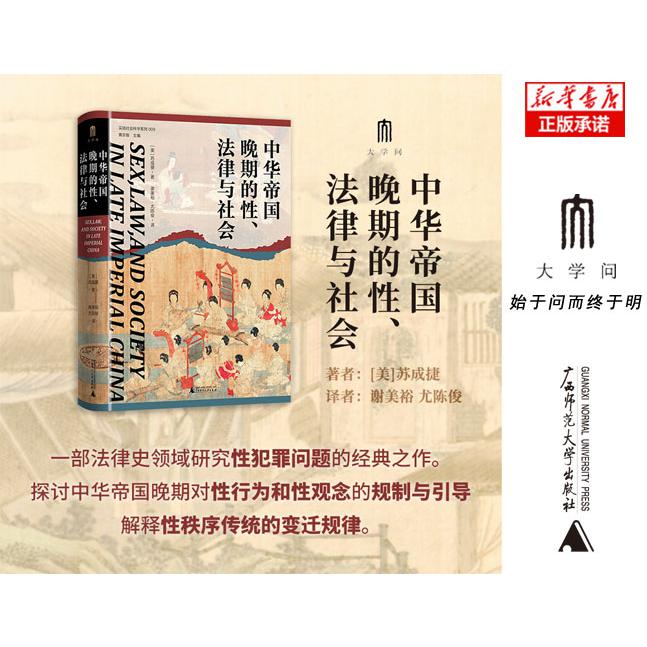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1.80
折扣购买: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ISBN: 97875598566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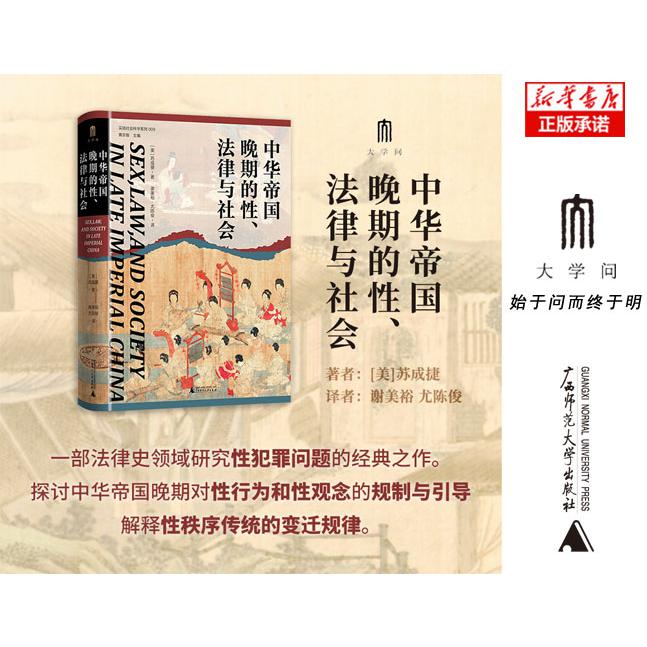
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现为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擅长利用司法档案研究清代中国的性、社会性别关系和法律。出版有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两部学术专著,并在Late Imperial China、Modern Chin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谢美裕(Meiyu Hiseh),现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学术研究兴趣为早期中国史、草原帝国等。 尤陈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8年度),学术研究兴趣为法律文化、法律史和法律社会学。在《法学研究》、Modern China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有专著《聚讼纷纭:清代的“健讼之风”话语及其表达性现实》《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以及译著《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在中国古代,丈夫对其妻子所拥有的包括使用暴力的权力在内的合法权威,并非绝对,也不能恣意妄为。丈夫对其妻子行使其权威,必须符合儒家所预设的那种家庭秩序的利益。妻子的顺从以及在性方面服从其丈夫的义务,也取决于这项根本原则。 ——编者按 义绝:夫妻间道德纽带的断绝 前已述及,丈夫对其妻子所拥有的包括使用暴力的权力在内的合法权威,并非绝对,也不能恣意妄为。丈夫对其妻子行使其权威,必须符合儒家所预设的那种家庭秩序的利益。妻子的顺从以及在性方面服从其丈夫的义务,也取决于这项根本原则。如下两种被中国帝制晚期的律典纳入“奸”罪的情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丈夫能够享有对其妻子的“性独占”的先决条件。这种性独占只能由丈夫本人享有,而不可与他人分享。 一、获得丈夫同意的非法的性交行为 倘若丈夫允许自己的妻子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则法律上将如何处置?本书中关于卖娼的那两章将详细讨论此问题,不过在这里可以先对我的主要观点做一概述。直到18世纪,法律上仍然容许卖娼,不过仅限于那些世袭贱民身份的女性,特别是乐户。清初的案件记录和其他史料表明,这些女子均有丈夫,并由其夫为她们招揽嫖客。针对奸罪的相关法律,并不适用于这些被认为不配由法律来加以约束的女子,良民男性享用此类女子的性服务,也不构成犯罪。 与此构成对比的是,若与良民女性发生任何形式的婚外性交行为,则会被作为奸罪论处。此外,若良民丈夫为自己妻妾的卖娼招揽嫖客,则无论是否征得其妻妾的同意或强迫她们如此行事,均被视为彻底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婚姻道德基础。易言之,这种行为将被纳入“不以义/礼交”的类别。早在12世纪的南宋时期,当时的一道法令便规定,犯有上述罪行的良民夫妇须强制离异。直至清朝结束,强制离异始终是对此种犯罪的惩罚之一。在元代,良民身份的丈夫若“纵妻为娼”,则会被视作一般的通奸加以惩处:丈夫、妻子和嫖客均将被依照已婚妇女“和奸”的法律规定处以相同的刑罚,即杖八十七,并强制这对夫妻离异,女方须被遣返娘家改嫁他人。明清时期的律典对这种犯罪的处刑规定与元代相同,只不过将杖刑数增加至九十下。那种支付报酬以从某位女子那里获得性服务的行为,并没有被处以任何额外的刑罚;被惩罚的乃是那种与不特定对象发生性关系的淫行,而非这种用金钱购买性服务的行为。 要知道,强制离异是一种严重的惩罚,至少对丈夫来说如此。在中国社会里面,结婚以往(可能现在仍然如此)被认为是真正成年的标志。而在贫苦农民当中,婚姻对男子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身份地位象征,其象征意义随着妻子来源短缺这种状况的加剧而递增(因此,在不少卖妻案件中,是妻子更希望被卖掉,而非丈夫迫切地想卖掉其妻子。受到此类法律影响的群体,是那些已濒临绝望而不得不考虑卖掉自己妻子的男子。一旦离婚,他们当中还有多少人能重新获得那些可供再婚的必需资源? 当时的法律是基于何种理由禁止这种性关系,进而强制存在这种情形的夫妇离异?元代的司法官员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可被视作代表了他们的后世同行们就此所持的基本立场。元代大德七年(1303),一位资深的官员称“夫纵妻奸”乃是“良为贱”,即良民身份之人在行事上却犹如贱民身份的娼妓那般。同年,刑部研议后认为:“人伦之始,夫妇为重,纵妻为娼,大伤风化……亲夫受钱,令妻与人通奸,已是义绝。”刑部将这种行为称为“义绝”(夫妻之间的道德义务纽带断绝),而这是自唐代至清代的历代律典中所规定的强制离异的法定条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传统中国的法律专家们将其分为“天合”关系(例如父子关系)与“人合”关系(例如婚姻和收养关系)。这两种关系皆被认为以“义”为其本质。“义”是一种将不同的义务赋予人际关系双方的道德纽带。而根据前述伏胜对性犯罪所下的那个经典定义,“义”当然也是使性交行为得以正当化的条件。人们可能在一种“天合”关系中违反了道德义务(例如不孝的行为),但在法律上,这种道德纽带无法改变,故而无法被割断(“绝”)。因此,就像清代的一些案件记录所表明的,如果良民身份的父亲为其女儿卖娼招揽嫖客,那么他将被惩处,不过其女最终仍将归他监护。然而在“人合”关系中,道德纽带可被割断。因此,若丈夫纵容或强迫妻子犯奸,则这对夫妇就应当被强制离异。 元明清三代的法律均使用“纵”这一术语来称呼丈夫纵容其妻犯奸的行为,这暗示夫妻双方均被视为主动行事的共犯。“纵”的字面含义是“放纵”或“放任”,它也可被用来表示“纵容”。按照儒家所设计的蓝图,丈夫的职责是训教其妻,给她提供道德指引,并为她的行事划定界限。于是,上述律文所用措辞反映出来的图景便是,若丈夫纵容其妻在性关系方面滥交,则他便是失责。正是由于这种失责,该名丈夫丧失了继续拥有其妻子的权利。 倘若丈夫并非“纵”,而是强迫其妻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则上述原则仍然适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对妻子的惩罚会有所不同。按照元代法律的规定,被“勒”为娼的妻子是否应受惩处,需“临事量情科断”。明律(清代沿用了其中相关的规定)对这种犯罪的处置是,被“抑勒为奸”的妻子不受任何处罚,仅是被遣返娘家,其丈夫应被杖一百,而与她发生性关系的另外那名男子则须被杖八十。在这里,由于丈夫的允许和强迫才是决定性因素,故而主要责任在于丈夫,而不是像在纵容妻子犯奸的案件中那样三方均承担相同的罪责。不过即便如此,此处对这两名男子的惩罚,仍远轻于对强奸同等身份地位女性之罪犯的法定处刑(绞监候)。事实上,元明清三代针对丈夫强迫其妻与其他男子犯奸的律文规定,均刻意避免使用“强”这一专门用以界定强奸罪名的字眼。这种“抑勒为奸”之罪名与强奸罪名的区别在于,该女子的丈夫允许另一名男子对她行奸。正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沈之奇在对相关律文的注释中所指出的,“凡抑勒妻妾……与人通奸,若妇女不从,奸夫因而强奸者,似难即坐以强奸之罪”。这种罪行有着违背女性意愿而发生非法的性关系的表象,但被强奸女子之夫的授意,使得此种罪行大异于“强奸之罪”,其严重程度也被认为远较后者为低。 二、被视为奸罪的卖妻行为 另一种导致夫妻义绝的罪行是“卖休”,即丈夫将其妻子嫁卖给另一名男子。管见所及,最早言及“卖休”之罪名的是元代的法律。元代的法律显然是将这种罪行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不过有些模棱两可。元代的法律在“户婚”门中规定:“诸夫妇不相睦,卖休买休者禁之,违者罪之。”这条法令并未明确指明惩处的具体方式,不过它接着补充规定称:“和离者,不坐。”此类犯罪的第二种形式,见于元代的法律的“奸匪”门之规定:“诸和奸,同谋以财买休,却娶为妻者,各杖九十七,奸妇归其夫。” 上述第一条法令仅禁止与其妻子相处不睦的丈夫将她卖给另一名男子,而并未提及“奸”。第二条法令则明确对因通奸而引起的卖妻行为加以禁止,即禁止男子将与他私通的奸妇从其本夫之处买来。在第二条法令中,法律上的重心在于通奸而非卖妻行为本身,故而只有通奸的双方受到惩处,其中女方则应被交还给之前将她卖掉的本夫。 然而,元代大德五年(1301)的一条法令规定,若丈夫将其妻子“卖休”给另一名男子,则属于“已是义绝”,该名妻子应“离异归宗”。促成这条法令出台的那起案件,看起来在卖妻行为之前并没有发生任何通奸的情形。除了规定没收卖妻所得的钱财,这条法令未规定其他任何刑罚。该法令虽然并未指明所针对的究竟是“义绝”的哪一种情形,不过看起来是认为前述两种情形当中的任何一种均将导致夫妻之间义绝,因此强制要求该女子须离开其本夫和买休的男子。 如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元明两代的法律在对卖妻行为的司法处置上有着很强的延续性。明律中有下述规定: 若用财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妇人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若买休人与妇人用计逼勒本夫休弃,其夫别无卖休之情者,不坐。买休人及妇人,各杖六十,徒一年。妇人余罪收赎,给付本夫,从其嫁卖。妾减一等。媒合人各减犯人罪一等。 这条法律看起来包含了前述元代大德五年法令中的那种逻辑,将本夫、买休的男子和妇人三方均同等处刑,并强制女方离开其本夫和买休的男子。该律文的后半部分则明确规定了何种情况下本夫无罪,即如果他是其妻与买休者之共谋的受害者。 这条律文乃是出现在明律的“刑律·犯奸”门当中。事实上,它是一条用以禁止丈夫纵容或抑勒其妻与人通奸的单独条款。与元代的法律不同,明律的“户律·婚姻”门当中并无使用“买休卖休”这一术语的规定。明律将该条款置于“刑律·犯奸”门之中,这显示了其试图将那种由妻子和买休的男子事先通奸所引发的卖妻行为纳入涵盖的范围。该律文后半部分的措辞便是在强调此点。然而,“奸”字完全没有出现在此律文的文字表述之中。到了16世纪,上述这种模棱两可(这也许是沿袭了元代法律中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在明代的司法官员中引发了一场关于此类罪行的确切性质究竟为何,以及其与“奸”这一更大的罪行类别之间是何关系的争论。其中尤其存在争议的是,那种事前并不涉及通奸情形的卖妻行为是否应当被问罪。 有一派司法官员主张应当对此律文采取广义解释,即主张禁止擅自卖妻的一切行为,而无须考虑其原初的动机。例如雷梦麟便如此认为: 律本奸条,不言奸夫而言买休人,不言奸妇而言本妇,则其买休卖休固不全因于奸者,但非嫁娶之正,凡苟合皆为奸也,故载于奸律。 也就是说,从本夫处买来一名女子为妻的行为,并不能构成正当的婚姻,因此,借由这种交易而发生的性结合,应被视为通奸。买休的男子在买来这名女子之前是否曾与她通奸,这并不是司法上要考虑的重点。从道德角度来看,无论是否存在上述所说的事先通奸情形,均应按照相同的方式治罪。这种对“买休卖休”律文的扩大解释,看上去相当契合那个将此类性犯罪概括为“不以义/礼交”的经典定义。而且,按照当时的一般观念,这种解释也很合乎情理。据小川阳一所言,在明代的白话小说中,“奸通”一词仅用于指称“非法的婚姻”(顾名思义,那种缺乏正当婚姻仪式的男女结合)。 不过另一派司法官员则主张应当对此律文采取狭义解释。例如明代隆庆二年(1568),大理寺少卿在上奏当中对适用此律文时普遍存在的混淆加以抱怨: 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矣。 简言之,大理寺少卿认为,当时的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形下可以离婚、再婚和卖妻,但这些正当的行为却常被与“买休卖休”相混淆;只有那种由事先便已发生的通奸行为直接推动的卖妻行为,才应当受到惩处。 皇帝对上述抱怨的响应,乃是下旨认可应当对该律文采取狭义解释。然而争议仍未平息。次年,都察院重申应当对此律文采取狭义解释,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看得买休卖休一律……今查本条……原文委无奸字,故议论不同,合无今后图财嫁卖者,问以不应,量追财入官。其贫病嫁卖,及后夫用财买娶, 别无买休卖休奸情者,俱不坐罪。 也就是说,都察院认为,纯粹基于钱财考虑的卖妻行为是另一回事,即便要对这种行为加以惩罚,也应从轻处置。只有当买妻者事前与女方有通奸情形时,才应对卖妻行为加以惩处。 这份奏折给出的上述方案,后来得到皇帝的允准。 尽管朝廷就此做出了上述明确声明,但倡导应当对上述律文采取广,在明代仍不乏其人。而正是这种针对该律文的广义解释,后来在清代成为主流。 清代律典的最初版本保留了明代的“买休卖休”律,但在该律文行间添入如下小注文字:“其因奸不陈告,而嫁卖与奸夫者,本夫杖一百,奸夫奸妇各尽本法。”这种将上引小注文字添入该律文之中的做法,无疑表明事前存在通奸只是适用此律文的诸多情形之一。如此一来,所有擅自卖妻的行为,均应被按照“买休卖休”律论处,因为此类行为被认为从本质上讲皆构成通奸。康熙五十四年(1715)时,律学家沈之奇就其中的关联做出如下解释: 盖卖休者自弃其妻,既失夫妇之伦;买休者谋娶人妻,亦失婚姻之正。有类于奸,故不入婚姻律而载于此。 清代18世纪经中央司法机构审理的案件之记录表明,“买休卖休”律被从严适用于各种卖妻行为,其中包括那些与事先通奸无涉的卖妻行为。实际上,贫穷显然是这种卖妻交易背后的主要动因。然而,至少一直到嘉庆朝晚期,刑部都始终极其严格地将卖妻行为视作“奸”的具体形式之一。 节选自[美]苏成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 1.“超级教授”黄宗智得意门生苏成捷代表之作,中文简体版首次出版。 2.学界期待已久,知名学者岸本美绪、王笛等曾在著作多次引用、评述,并长期关注此书动向; 3.系法律史领域性犯罪问题研究的经典之作,与时下热门的女性话题息息相关。作者从社会形态和观念变迁的角度,对性犯罪与法律问题进行宏观考察,关注如下问题:唐代以降的立法者们对性行为的管制、明清法律对强奸罪当事双方身份关注的区别、清代寡妇的性与财产、清代的同性恋法律与性别角色、娼妓的法律变迁问题等。 4.横跨法律、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该书没有沿袭传统史学对政治体制、制度和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关注,而是另辟蹊径,在法律史、社会史、性别史中进行跨越式写作; 5.在史料的使用上,该书以清代留下来的刑事和民事诉讼档案为轴,辅以地方志、民俗调查报告、传奇小说甚至是临床报告等多种文献,勾画出底层平民生活的众相,探讨大清律例、社会法律制度、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命运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