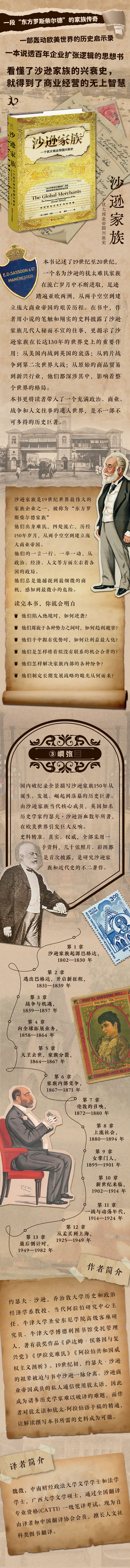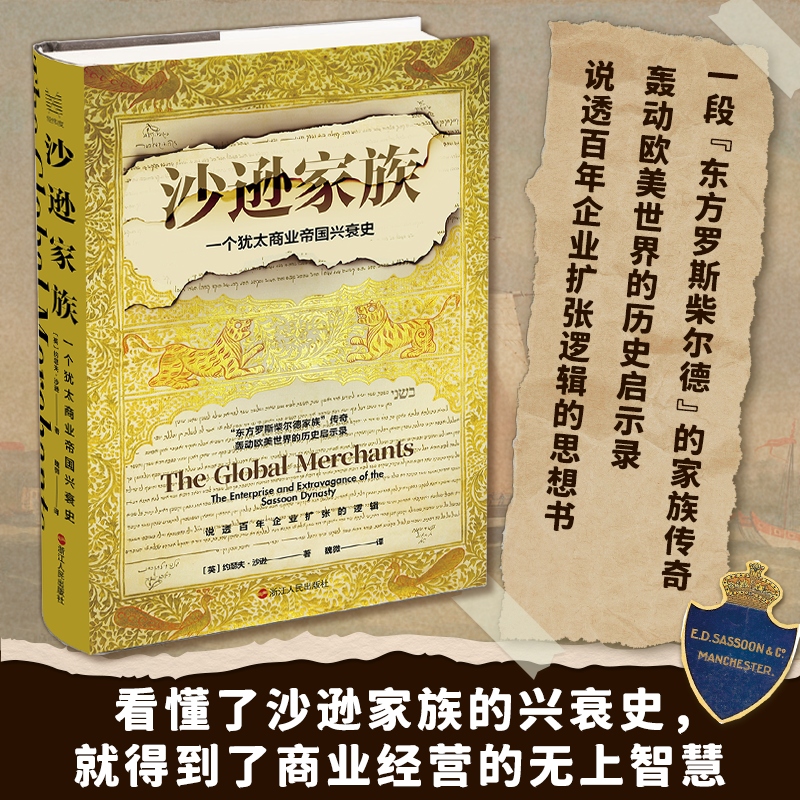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56.40
折扣购买: 沙逊家族(一个犹太商业帝国兴衰史)(精)
ISBN: 9787213110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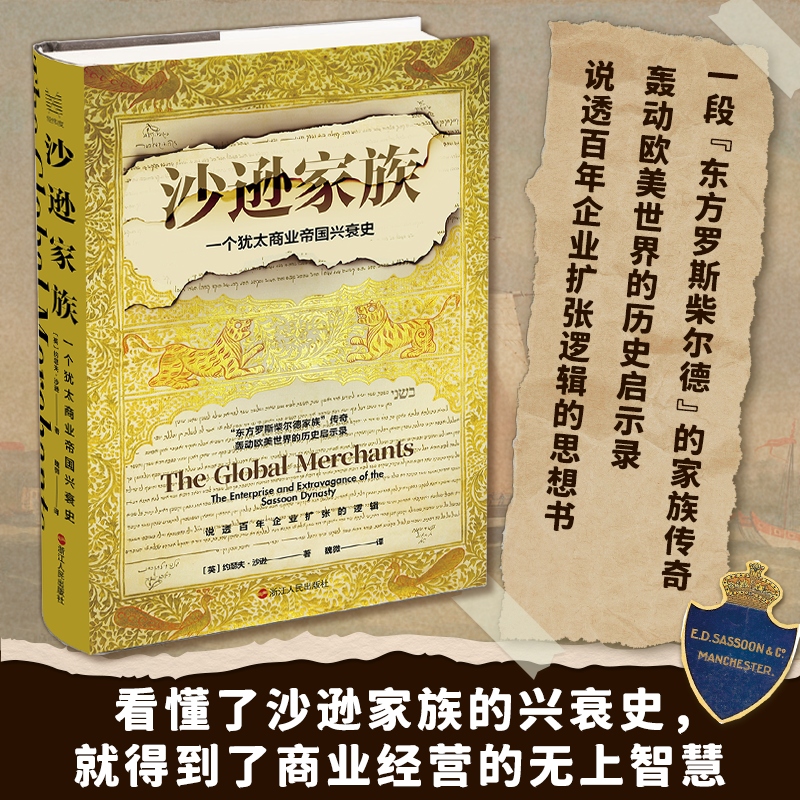
约瑟夫·沙逊,乔治敦大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受托管理人,著有获奖作品《萨达姆·侯赛因与复兴党》《伊拉克难民》《阿拉伯共和国威权主义剖析》。19世纪初,约瑟夫·沙逊的祖辈被迫与书中沙逊一脉分离。沙逊商业帝国成员的私人通信使用犹太语,因此成为诸多历史学家难以破译的难题,而作者对犹太语和犹太-阿拉伯语手稿的精通,让解读撰写本书所需的史料成为可能。 译者简介 魏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学学士和法学学士,广西大学文学硕士,通过全国翻译专业资格(CATTI)一级笔译考试。现为自由译者和中国翻译协会会员,擅长人文社科类图书翻译。
1824年,一位名叫大卫·贝斯·希勒尔(David D’Beth Hillel)的拉比离开祖国立陶宛,从此开启一段史无前例的旅程。他的足迹踏遍半个地球,走过巴勒斯坦、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库尔德斯坦和波斯,最后在 印度马德拉斯停下探索的脚步,并在当地登了一则广告,宣传自己笔下那 本有关旅途见闻的书,“此书记载了作者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通过五 种语言记录了对旅行者极为有用的词汇,即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波斯 语、印度斯坦语和英语”。1 希勒尔到任何地方,他都会试着描述当地的独 特信仰与文化,找出这些国家犹太居民与古老传统的联系。他在巴格达停 留了整整一年——这座重要城市坐落在富饶而辽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也被称为“两河流域的中间地带”(“两河”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 河)。希勒尔生动地描写了此地的生活:现代巴格达是一座大型城镇。底格里斯河从中穿行而过,河面横跨一 座大桥,桥下小船来来往往。镇上建筑均用砖块砌成……贵族阶层、希伯 来人(犹太人古称)和基督教徒混居在(波斯)这片土地上。这里的街道 和集市狭窄局促,给人印象十分简陋粗糙,不过贵族的房子内部装饰却非 常精美。2 (p .1) 拉比希勒尔到访的这座城市为8世纪的阿拔斯王朝所建,已有千年历 史。往后的五个世纪,巴格达蓬勃发展,成为伊斯兰教鼎盛时期的文化、 商业与知识中心。这座城市“天赋、进取与学习”的盛名至今难有其他城 市超越,就如19世纪另一名访客所述,“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遭遇人类史上 的黑暗时期,巴格达的哲学家却大放光彩,熠熠生辉”。3 1534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将巴格达变成下属行 省(wilaya)。随之而来的是波斯人与土耳其人连绵不断的冲突,某种程 度上这也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与波斯萨法维王朝恩怨的延续。萨法维王朝 无法接受逊尼派统治巴格达,这座城市因此衰落。4 土耳其人带来的格鲁吉 亚马穆鲁克骑兵成为当地统领。“马穆鲁克”(Mamluk)的意思是“被 拥有者”,他们并非阿拉伯人,而是获得自由的奴隶兵,大多来自高加索 地区,16世纪初土耳其人占领埃及、叙利亚和汉志省(Hejaz)后皈依伊 斯兰教。事实证明这帮看管人很有能耐,到18世纪中叶,马穆鲁克渐渐掌 握越来越多权力,成功篡取了原有政权。1747—1831年间,巴格达大多数 统治者都是马穆鲁克出身,独立统治奥斯曼帝国,而巴格达行省从行政区 划上来讲是帝国的组成部分。马穆鲁克执政期间,政府权力集中在帕夏 (Pasha,即高级官员)手中。这一职位相当于地区总督,当朝政权是强 是弱,从帕夏身上就能看出一二。最伟大的马穆鲁克统治者可能是大苏莱 曼(Suleiman)帕夏,他于1780—1802年在位并执掌巴格达。大苏莱曼帕 夏去世当年,巴格达再次陷入动荡与冲突。接下来三年,多位帕夏到任卸 任,无一不是精于阴谋布局,暗杀反派,有时连继任者也不放过。加上食 物短缺,这座城市越发民不聊生,很多地方掠夺哄抢都很猖獗。 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人占领犹地亚,犹太人被迫流亡到美索不达米 亚平原,并在此地定居了约2500年。这个后来被称为巴比伦犹太人的群体 拥有自己的语言,即巴格达犹太语,这是一种用希伯来字母书写的阿拉伯 方言。(p.2)巴格达省各城市都有蓬勃发展的犹太社区,当地的犹太人数 量很可能超过了阿拉伯东部其他地区。5 根据拉比希勒尔的著作,他访问巴 格达时,当地约有6000户犹太人,五个大型犹太教会堂。后来一名旅行者 估计,巴格达行省共50000户,犹太人占7000户,并指出他们在该省发挥 着重要作用,“商业贸易甚至政府管理都落到了少数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 手中”。6 当地位高权重的商人和银行家一般都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波 斯人。他们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自己家园所在的(各个)行省,还体现 在对奥斯曼帝国资本的控制。以西结·加贝(Ezekiel Gabbay)是巴格达 很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他于1811年帮助苏丹摆平了一位特别棘手的帕夏, 作为奖励,被君士坦丁堡朝廷任命为首席财务主管(sarraf bashi),成为 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最倚重的财务顾问之一。上任之后,以西结继续谋权谋 利,做起有利可图的生意,在帝国上下兜售行政职位。传言称,有时候 “多达五六十名帕夏聚集在这名位高权重的犹太人前厅”,恳求他帮上一 把,好在朝廷谋个一官半职,或继续为朝廷效犬马之劳。7 以西结在任期间 诸多荣誉加身,其兄弟也被任命为巴格达的首席财务主管(p.3)。8 兄弟二人均出身于经济条件优渥的犹太阶层,该阶层掌握着奥斯曼帝 国各行省长官的财源,还借钱给长官们用。拉比希勒尔对这群犹太人特别 感兴趣: 这名帕夏的财务主管是一名统领(犹太社区)的以色列人,普通犹太 人叫他“以色列之王”。他重权在握,随心所欲地对普通民众施以罚款或 者鞭刑,不管自己所为是否合法。古时候,帕夏的财务主管必须是大卫王 的后裔,并且采用世袭制。9 马穆鲁克统治期间,经商的大多都是犹太人,帕夏便从犹太社区挑选首席财务主管。担任该职务的人被称为“纳西”(希伯来语中指“王 子”),是社区在当地和朝廷行政机关的代表。纳西应该与社区的宗教领 袖首席拉比平级,其影响力还跨越了巴格达行省的范畴,扩散至波斯或 也门的其他犹太社区。10 这种世俗与精神并驾齐驱的双头制度一直持续到 1864年,之后土耳其人便任命单独领袖来管理社区事务,也就是首席拉比 (hakham bashi)。11 特权在握也意味着责任在肩,比如首席财务主管要 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为宗教事务出钱出力,还要支持跟自己信奉同一宗 教的人。一名到巴格达旅行的异教徒表示当时没见过犹太乞丐,“他们当 中要是有人落难受穷,其他更富有的犹太人就会出手救济”。12 无论是总 督(wali)还是帕夏,他们与财务主管的关系都很密切,但这层关系飘忽 不定,一旦恶化,财务主管就有可能被捕入狱,甚至有性命之忧。君士坦 丁堡朝廷与地方行省之间的政治较量一直都在上演,两个权力中心都在无 休止地盘算,怎样才能把权力的触须伸向对方,在朝廷或地方安插信得过 的人。一方面,财务主管需要跟苏丹在君士坦丁堡的朝廷保持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财务主管跟朝廷又不能走得太近,免得总督或帕夏感觉受到威 胁。正如拉比希勒尔所记载的,首席财务主管讲究的是身处两种权力之间 的平衡与分寸,而且父传子,子传孙,已有百余年历史(p.4)。不过到 19世纪,这个官职越来越“靠与其他犹太人竞争上岗,于是有人出钱买官 做,有些犹太人甚至不惜杀害对手或毁人名誉”。13 长期以来,官员任命 都受到现实政治主张的影响,不过18世纪之后官员的更迭确实更为频繁, 政治动荡成为新恐怖手段的温床:就在拉比希勒尔到访巴格达的那一年, 两名官员被谋害,凶手趁机上位。 1781年,苏丹准备任命沙逊·本·萨利赫·沙逊族长为法定(firman) 首席财务主管,并兼任巴格达犹太社区首领。当时,大苏莱曼帕夏刚刚掌 权不久,此前就有消息称巴格达当局有人想谋害沙逊族长。沙逊生于1750 年,跟巴格达最显赫的某犹太家族联姻之后成名。他与妻子育有六儿一 女,根据阿拉伯习俗,一般用长子名称来称呼其父母,因此沙逊族长也叫 艾布鲁本(即鲁本爸爸,其妻子则叫温姆鲁本,即鲁本妈妈)。关于鲁本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因病死于1802年,不过他的名字倒是代代相传, 沙逊一脉因此也称为“鲁本一家”。沙逊族长次子大卫生于1793年,长兄 早逝令他成为家业继承人,估计将来还会继承父亲的官职。大卫在父亲的 庇护下长大,可以说是巴格达地位最显赫的人,“犹太社区的首领,那一 代人眼中的王子”。14 当地无人不知,沙逊族长跟帕夏走动密切,跟苏丹 也有间接往来。有诗人赞美沙逊族长是“这世间最诚实公正的王子,为他 的人民和社区任劳任怨”。15 1808年,沙逊族长安排15岁的大卫迎娶14岁 的汉娜。新娘来自巴格达行省南部巴士拉一户富饶的犹太家庭(这次结褵 为沙逊族长添了长孙,即出生于1818年的阿卜杜拉,次孙伊莱亚斯,另外 还添了两名孙女:马扎尔·托弗和亚曼)。当时,沙逊族长已经是巴格达 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席财务主管之一,先是大苏莱曼帕夏掌权期间,时值 18世纪最后20年,是“马穆鲁克王朝在巴格达的黄金年代”16 ;后来两位 苏丹相继上任,沙逊族长仍稳坐首席财务主管一职。 到1816年底,沙逊族长已任职35年,就在此时,乌云开始团团笼罩。(p.5) 1810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任)首次 出军打算将马穆鲁克赶出巴格达。奥斯曼军队杀害了苏莱曼帕夏(大苏莱 曼帕夏的儿子),但最后还是没有夺回对巴格达行省的统治权。巴格达 随即陷入混乱,几名帕夏相继上台,宣称掌管巴格达,不过都是昙花一 现,因为位子还没坐稳,就会被下一任赶下台。这种走马观花似的权力 交接,意味着朝廷命官抵达巴格达之前,有的帕夏掌握了实权,有的帕 夏却空有头衔1 。萨义德(Sa‘id)帕夏于1813—1816年执掌巴格达,但幕 后主使却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马穆鲁克,名叫达乌德(Dawud)18 。此人是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奴隶,被人带到巴格达后,几经转手卖给他人,后 改宗伊斯兰教,为大苏莱曼帕夏效力。奥斯曼帝国档案馆勾勒出达乌德 的鲜明形象——他是天资聪颖的作家,也是骁勇善战的勇士,他慷慨、开 明与公正,但同时也残忍、腐败与贪婪19 。萨义德刚上任不久,达乌德便 计划谋反,他找来一位名叫以斯拉·本·尼西姆·加贝(Ezra ben Nissim Gabbay)的巴格达犹太人当帮手,此人想伺机赶走沙逊族长,自己当首席财务主管。以斯拉本身也有一座强大靠山——自家兄弟以西结。以西结 1811年被君士坦丁堡朝廷任命为首席财务主管,在整个奥斯曼帝国都是有 权有势的人物。有报道称荷兰副领事曾与奥斯曼帝国某地总督发生纷争, 请求以西结帮自己平息风波。20 1816年至1817年冬春之交,达乌德与萨义德发生几次小规模冲突, 最终萨义德被擒获并处死。达乌德掌权后不久,一纸法令抵达巴格达,宣 布沙逊族长任期结束,以斯拉·加贝成为新任首席财务主管。21 同时一道 诏书昭告天下,达乌德走马上任,这一唱一和,配合绝妙。殊不知,将诏 书送抵巴格达的,正是苏丹首席财务主管犹太人以西结的儿子,以斯拉的 侄子。22 当时,英国贸易商在巴格达颇具规模,东印度公司在20年前就已获准 在巴格达驻扎。他们一开始对达乌德寄予厚望,但很快意识到以此人的性 格,巴格达要想重现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和平几无可能。一位英国特派政 治代表用最憎恶的语言描述达乌德(p.6): 他是这世间最虚伪的人,行为残忍至极,发作起来常无来由。最庄重 的誓言与承诺,在他身上不过轻如鸿毛。他最忠实的奴仆都绝无可能知晓 他的真正喜好。越是让他笑脸相迎的人,往往也是他内心最憎恶的人。他 掌权期间的巴格达,上演的是一幕又一幕贪欲、迫害与背叛。23 英国人不喜欢达乌德,还有别的原因。此人仿效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打算削弱欧洲人(和波斯人)对巴格达的影响,但 跟阿里明显不同的是,达乌德性格变幻莫测,反复无常。24 就算是达乌德 最亲密的同伙、首席财务主管以斯拉本人都不能幸免于难:1818年,达乌 德帕夏打算贷款打理政务,以斯拉没有同意,结果达乌德“一时恼羞成 怒”,下令将以斯拉“用铁链绑住,送往地牢,第二天又放了出来”,原 因是奥斯曼帝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达乌德说情。25 达乌德一旦巩固政权,拉拢民心,就露出真面目,宣布不再向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纳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巴格达与波斯又 起摩擦。雪上加霜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对和平共处之后,巴格达跟库 尔德部落之间的冲突也突然激化。虽然苏丹支持达乌德打波斯和库尔德, 但达乌德哪边都没打赢。1819—1923年,巴格达行省人口大规模下降,原 因是“波斯人推行焦土政策”,导致饥荒,民众纷纷逃难。26 1823年,达 乌德宣布停战协议,但此举引起了君士坦丁堡朝廷的猜疑,奥斯曼帝国再 次打算结束马穆鲁克的自治状态。 达乌德帕夏统领巴格达之后,沙逊族长在劫难逃。达乌德没有把沙逊 当成盟友,还担心他跟君士坦丁堡朝廷的往来过于密切。从沙逊卸任到逃 出巴格达的13年间发生的一切,对理解沙逊家族为何会逃离深爱的家园十 分重要。达乌德与巴格达犹太社区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他靠犹太人 在苏丹王室的影响才走马上任;另一方面,他很快又因欺压犹太人而名震 四方。事实上,他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贪财,变本加厉地敛财就是他的根本 目的(p.7)。27 迫于向君士坦丁堡朝廷送钱的压力,达乌德开始问犹太人借钱。然 而,巴格达一些最富有的商人拒绝借钱,达乌德便将他们投入大牢,家里 交钱才能赎人,违令者处死。28 这套法子背后其实另有他人出谋划策,一 位是达乌德的老师,被犹太社区戏称为“告密者”;另一位是“犹太叛 徒”,为一名舞者冲昏头脑之后改宗伊斯兰教,为达乌德提供情报,借此 从犹太人手里榨取大量钱财。“三人组给巴格达犹太人带来巨大的灾难 和不幸”,犹太人开始“逃往达乌德的魔爪无法触及的远方”。29 正是从 这时起,巴格达的犹太社区开始分崩离析,很多犹太家庭开始穿过亚洲大 陆,逃往阿勒颇、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港,甚至一路远行到澳大利亚。 1826年,导致犹太人逃离巴格达的紧张局面变得更加严峻。当年, 苏丹称马穆鲁克是阻碍变革的反动力量,因此宣布废除他们的武装,此举 导致达乌德搜刮更多钱财来供养军队,同时还要对君士坦丁堡朝廷表示恭 顺。达乌德再次打起了身边最忠实拥趸的主意,八年前的故技重演,他再 次将以斯拉投入大牢,希望从他们家搜刮更多钱财。但这一次,君士坦丁堡朝廷没有派人来说情,因为即使有人说情,达乌德也是充耳不闻以斯 拉受不了牢狱之苦,很快丧命,他“为帕夏任劳任怨,却落得命丧牢狱的 下场”。30 有关以斯拉被迫害的资料主要来自沙逊族长的另一名后代——大 卫·所罗门·沙逊。他是一名档案学家兼历史学家,20世纪40年代写了第 一部有关巴格达犹太人历史的可信著作。根据书中所述,19世纪20年代晚 期,以斯拉被捕之后,达乌德还逮捕了大卫·沙逊,强迫他父亲,也就是 沙逊族长交赎金。大卫当时命悬一线,但“奇迹般逃脱”,个中细节已无 从考证。我们不清楚大卫是字面意义上的越狱,还是父亲花钱赎他出来, 不过为了获得真正自由,也出于再次被捕的恐惧,大卫都打算立即离开巴 格达。父子二人向少校R.泰勒(R.Taylor)征求意见,泰勒是英国驻巴格 达特派政治代表,直接向英属印度汇报,手中握有波斯湾和印度次大陆的 可靠情报(p.8)。沙逊族长专门租了一艘船将大卫送到巴士拉,按照父亲建 议,大卫在巴士拉没有停留太久,继续前往坐落在伊朗海湾东南800多千 米的港口城市布什尔。此举相当明智,因为达乌德帕夏确实又出尔反尔, 再次下令逮捕大卫,但大卫已经逃出他的“手掌心”。大约几个月之后, 沙逊族长也前往布什尔跟大卫会合。31 而沙逊族长已年到古稀,身体每况 愈下,从那往后,大卫只能靠自己闯荡未来,养活四个孩子和第二任妻 子——大卫的结发妻于1826年去世,之后他续弦再娶。这一家人当时除了 逃亡,别无他法。所谓难民,一般都是大难临头别无选择才会离开故土, 不过他们逃得正是时候。19世纪30年代的最后几年,巴格达行省遭遇变本 加厉的暴政,当局几乎全方位诉诸暴力手段。32 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起先因 为希腊闹独立分身乏术(希腊是首个脱离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并获得独立的 国家),又跟俄国打了几仗,巴格达马穆鲁克这时候闹独立,便成了苏丹 不得不拔的眼中钉。1829年,土耳其军队跟俄军交战惨败,苏丹派特使沙 迪克·埃芬迪(Sadiq Effendi)前往巴格达解除达乌德职务,重新安排非 马穆鲁克出身的新总督上任。(p.9) 达乌德帕夏原本不知道自己被撤职,对特使热情相迎。知道真相之后,本想拖延时间去觐见苏丹,但遭到时拒绝,33 于是“干脆铤而走险, 毫不犹豫且面不改色地杀害了苏丹的特使”。34 这次暗杀经过精心策划, 特使被杀当时,达乌德在会议厅外面等候,事成之后才进去验明沙迪克是 否身亡。一开始达乌德想瞒天过海,假装特使只是患病,结果当天傍晚就 走漏了风声。35 特使遇刺的消息迅速传开,一想到苏丹将对这次大不敬恼 羞成怒,第二天城里的食品价格立马上涨。巴格达被封锁,泰勒少校报告 称,“除了偷偷摸摸行动,整座城市无人能光明正大进出,哪怕有钱都买 不到任何蔬菜”。 特使遇刺之后,苏丹准备出军将马穆鲁克永远赶出巴格达,结果这 座城市偏又连遭不幸。1831年3月,巴格达暴发瘟疫,从犹太居民区蔓延 到整座城市。达乌德防疫不力,根本没有安排检疫,有篷马车继续在疫区 进进出出,将瘟疫传播到行省各地。整座城市的正常生活因此中断,食品 严重短缺,街头尸体成堆,法律和社会秩序瘫痪。屋漏偏逢连夜雨,巴格 达瘟疫当头又遇天灾:一场史无前例的滂沱大雨从天而降,底格里斯河发 起了大洪水。37 洪水决堤时,一位英国旅行者“就睡在房顶”,并生动描 写道,“我被咆哮着冲过大厅的洪水惊醒……没有哭喊,没有骚乱,没有 尖叫声,也没有哀号声……我就坐在墙头,眼看着洪水滚滚向前,席卷而 去”。38 一位当地人这样记载随后的灾难,“神降怒于这座城,所以才叫 那洪水冲毁巴格达的每个角落,才叫瘟疫夺去我等臣民的性命,叫死亡 笼罩大地。从来没人听说,巴格达史上遇此苦难”。另一位当地人这 样描述,“只有少数巴格达人在死亡、洪水和瘟疫当头逃了出去”。 据估计,当时逾15000人丧生,巴格达和周围灾区的人口从15万锐减到 8万(p.10)。 洪水和瘟疫也昭告达乌德的末日来临。许多巴格达人都想逃命,但 所有出口都危险重重。部落成员封锁了道路,船上挤满了人,而且也已遭 瘟疫侵染。达乌德和随从也想逃命,但又不想抛下平日“聚敛的金银财 宝”。42 英国驻巴格达公使和随行人员乘船逃往巴士拉,留下来的人躲在 家里,四周围起障碍物,将外人一律拦在门外,生怕他们将瘟疫带进来。 根据奥斯曼帝国档案馆的一份报道记载,洪水退去之后,达乌德离开巴格 达,结果发现他在各行省的拥趸都人间蒸发了,“他的军队和拥护者被瘟 疫摧毁,他的财务主管、宅邸、妻妾儿女和银行管理人员”统统被瘟疫带 走。43 另一份报道告知君士坦丁堡朝廷,称新任总督阿里帕夏与巴格达居 民和南方各部落修好: 巴格达城已将前任帕夏及仆从等脏污之人清洗。苏丹再次收回对巴格 达的统治大权,造反者犯下的所有破坏与恶行,现在都被苏丹带来的宁静 抚平。44 君士坦丁堡朝廷与桀骜不驯的巴格达之间的分裂结束,直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巴格达都将作为帝国的行省存在。达乌德被驱逐,朝廷开始搜罗 这位帕夏任期聚敛的财富。朝廷想算出达乌德“通过武力手段从巴格达、 巴士拉和基尔库克民众手中搜刮的财富”,拟了几个方案,搜查达乌德所 有行宫官署、家眷闺房和其他宅邸,还逮捕和审问了在以斯拉死后担任达 乌德首席财务主管的伊沙克(Ishaq),想从此人口中问出达乌德藏钱的 地点和数目。45 经审问调查,朝廷列了一份达乌德的受害者名单,范围之 广,遍布巴格达各宗各派和各个城市。调查还发现,有人被敲诈之后就惨 遭灭口。46 而达乌德本人凭着“嘴上功夫和个人风采”以及巨额财富,居 然没有被问极刑。后来,事情还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1845年达乌德 又得宠于新苏丹阿卜杜勒·马吉德(Abdul Majid),1851年去世前甚至还 捞到几个职位。47 沙逊族长出逃时仍是巴格达最有声望的犹太人之一,关于他逃亡的原 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害怕瘟疫和洪水,但他把其他子女都留在了巴格 达,天灾人祸过后,父子二人也没再回来。(p.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 故事仍以家族传说的形式继续流传不衰。1907年底,大卫逃出巴格达快80年之际,其孙子爱德华·沙逊议员就“东方”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其间讲 了一则故事,误将祖父大卫当成首席财务主管: 我祖父碰巧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务主管(演讲稿原文中巴格达一词为 Bagded)。或许他就是一介草民,跟帕夏打交道不懂拐弯抹角,或许当局 怀疑他敛财,想要治他,不管怎样,巴格达对他来说肯定太过危险。有谣 言称当局当时正在密谋对付他,我认为他应该是想着谨慎即大勇,于是携 家带口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故土,一路走走停停——可以想象,100年(前) 的旅行可不像现在坐在卧铺车里的那种旅行……很多犹太家庭后来也纷纷 离开巴格达,现在大家在印度看到如此繁荣昌盛的犹太社区核心,就这样 逐渐形成。 十年之后,沙逊家族另一位成员再次误将大卫当成首席财务主管。这 位成员在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位成员的信中解释大卫离开巴格达的原因: 大卫是犹太社区的首领,帮帕夏管理手下的犹太人。那时候奥斯曼帝 国可免征犹太人或基督徒参军,但必须得按人头缴纳一大笔钱来代替服兵 役。帕夏命令大卫·沙逊从犹太人手里收钱,但很多时候犹太人穷得交不 出钱,大卫不得不自己掏钱补贴。只要帕夏想筹钱,就从犹太人身上搜 刮,还威胁大卫·沙逊,如果凑不够钱,就得蹲大牢,被处死。帕夏开口 要钱的次数太多,大卫·沙逊无法满足这样的贪欲,所以一天夜里他逃出 巴格达,来到印度。我认为这才是真实的故事版本。 这类传说缺少信息支撑,只有一部分流传了下来。没有历史著作可以 让整个故事盖棺定论,因为确实无人知晓大卫到底何时逃到布什尔,也无 人知晓沙逊族长究竟何时跟儿子会合。(p.12)大卫于1828年跟第二任妻子 法哈在巴格达完婚,之后才离开巴格达,并且可能在1830年苏丹特使被刺 杀之前。也就是说,天灾还没降临,大卫就已经离开。有据可考的是,沙 逊族长于1830年客死布什尔,大卫因此前往孟买另谋生计。 父亲失势,使大卫像亡命徒一样逃离祖国,这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不 过,他跟最亲的家人成功躲过达乌德暴政,从此在异国他乡开启新的生活篇章。沙逊家族其他成员继续留在巴格达生活,迟早有一天,这家人又会 重拾巴格达经济精英的身份;沙逊族长的长子大卫也会走上经商致富的道 路,不过他将建立的是真正触及全球的商业帝国。另外,跟大卫手足不同 的是,他的后代不单在帝国一隅成就斐然,更是在全球各地商界都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商业成就。 1. 国内首部全景描写沙逊家族130年从诞生、发展、崛起到落幕的历史巨著。 2. 由沙逊家族当代核心成员,英国知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沙逊沥血数年所著,在欧美世界引发巨大反响。 3.本书史料精准、真实、权威,全部采用一手资料,几十张照片、彩图都是首次披露,是研究沙逊家族和近代史的不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