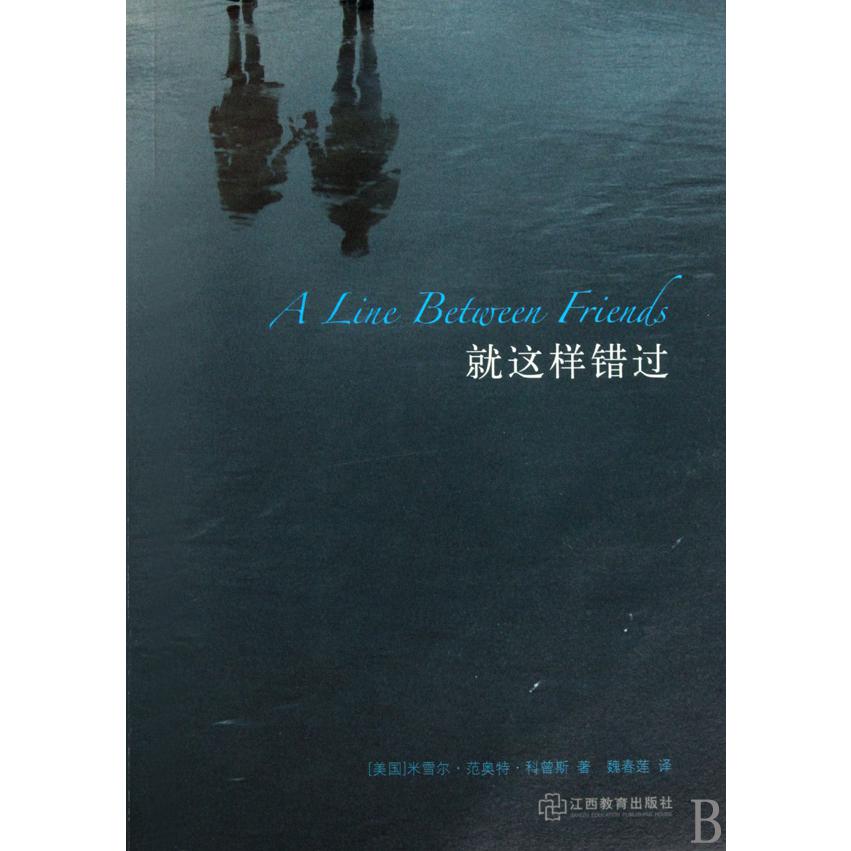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西教育
原售价: 25.00
折扣价: 16.75
折扣购买: 就这样错过
ISBN: 9787539256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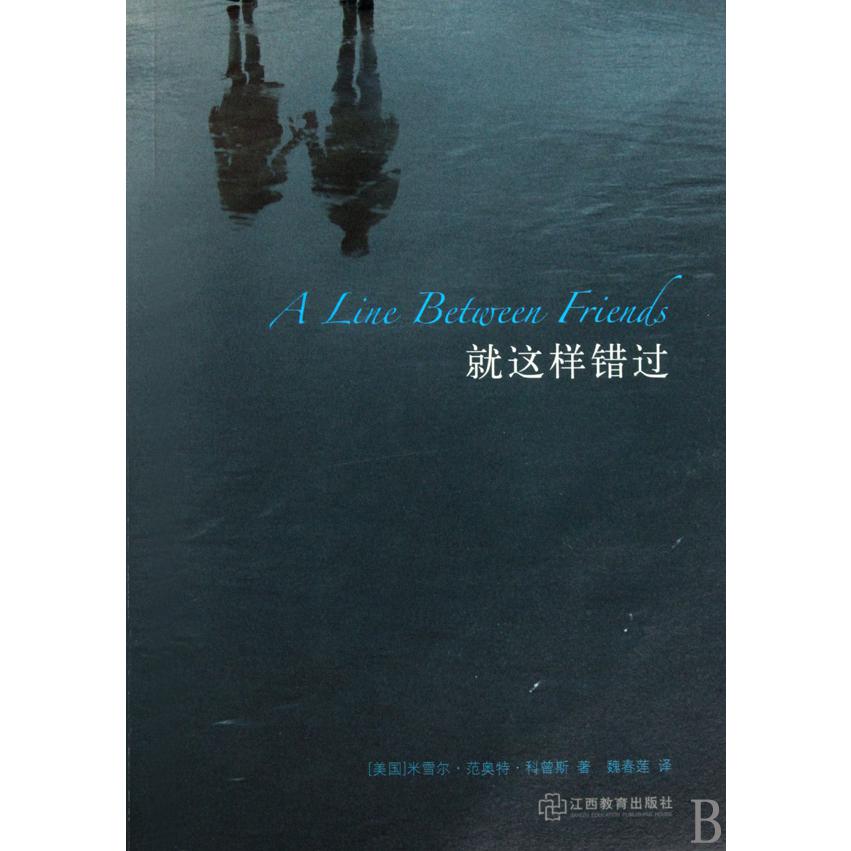
米雪尔·范奥特·科曾斯,曾做过新闻记者,报纸的专栏作家。目前她正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北部林区当地的飞盘高尔夫度假村工作。 《就这样错过》(The Line Between Friends)是麦肯纳出版公司举办的小说竞赛的大赢家,在读者中深受好评。这是作者的第一本小说。她之前还出版过两本非小说类作品:《我是你的梦想:北方森林主人的故事》(I’m Living Your DreamLife:The Story of a Northwoods ResortOwner)和《我希望我说过》(The Things I WishI’d Said)。
2 诺艾尔@1995年 在威斯康星州的明诺加镇,十二月是很寒冷的。明诺加是我丈夫的家乡 。在这里我就像一个外来移民,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孩突然被抛进了森林 ,她听到的不再是汽车喇叭声,而是鸟儿的鸣唱。男人们穿的不再是一本正 经的西服,而是宽松的橘黄色工装,女人们则很热衷于在每一件事上给人提 建议。在我怀孕后,她们更是热心地给我一切建议。 我的全名叫诺艾尔·蒙卡达·安德森,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布鲁克。布 鲁克位于郊区,路边有隔离带和停车的标志,房子多半有两层楼,邻居们都 相互认识。由于房子之间的间距很小,当有邻居打喷嚏时,我们会对着厨房 窗户喊:“上帝保佑你!” 我的父亲厄尔·蒙卡达高大英俊,有一头浅褐色的头发,二战使他的心 灵备受创伤。父亲总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作“战争”,而不是“二战”、 “大战”或者“结束战争的战争”,只是“战争”——仿佛这是历史上唯一 的重大战争。每天吃晚饭时,父亲就会给我们讲那些早已不新鲜的故事,从 如何穿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到妈妈因为他不会跳狐步舞而拒绝同他约会。父 亲的海军战友,更准确地说是他的战斗伙伴,教会了父亲跳舞,父亲因此才 赢得了母亲艾米莉·福尼埃的芳心。他们于一九四二年结婚,父亲穿着笔挺 的海军制服,母亲则穿着漂亮的婚纱。 父亲讲的战争故事时而带着格伦·米勒的节奏,时而充满了炮火般的节 拍。这就是我对父亲仅有的记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些事让父亲受了打击 ,总是绷着脸,我从没有听他讲过那个年代的事。我刚出生时,社会似乎还 合乎他的期望,但渐渐地他开始抱怨工人的笨拙和邻居的不道德,口气如老 橄榄般尖刻。 二战时期是父亲最辉煌的岁月,也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从那以后 ,他的日子就越来越黯淡了。 战争结束后,他从北大西洋回到了被称作“芝加哥郊区的玉米粉之都” 的伊利诺伊州,在其中一个沉闷的小镇阿尔戈安了家。伊利诺伊州。和厄尔 一起回来的还有他深谙世道的漂亮新娘。对这个处处都是蓝领工人的小镇, 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鄙夷。虽然厄尔在电子仪器和船上布线方面都受过培训 ,但他认为前者对他更适合,因此他选择了当电话维修工。薪水不错,养老 金也还可以。每个人获得了第一份工作时都觉得很幸运,在大萧条时期长大 的父亲更是觉得幸运。他口袋里有工资,还有一个红头发的美丽妻子。 刚开始,他们和厄尔的父母住在一起,这使得他们的蜜月不是那么甜蜜 。艾米莉的婆婆不愿同她讲话。一开始,厄尔还以为是艾米莉没有任何语法 错误的讲话和东海岸口音吓住了母亲,但一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任何好转 。于是厄尔花一万六千美元买了房,作为送给妻子的结婚周年礼物。这是一 幢白色的房子,有栅栏、壁炉,位于阿尔戈最大工厂的上风口二十五英里处 。 我唯一的姐姐詹妮特出生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婴儿潮,而我则生于肯尼 迪执政时期。那时的父亲像牛仔竞技表演冠军一样身手敏捷,在电线杆上爬 上爬下。公司配给他一辆生锈的一九五八年产老爷车,我们称这辆车为“咕 咕车”。父亲从不让我和姐姐坐这辆车。只有当车停在柏油马路边时,我和 姐姐才能坐进去享受一会儿。有时詹妮特偷了汽车钥匙,我们就溜进车里, 将收音机调到芝加哥WLS电台89赫兹,收听排名前十位的歌曲。“芝—加— 哥!”我们跟着歌手一起大叫。 每天下午,父亲回家时都一脸倦容。他压根儿就不理会我和詹妮特,但 却要吻母亲两次——在母亲的左右脸上各亲一次——然后,他就到地下室去 了。脱下工作服后,他会喝一点威士忌,之后就会一边听刺耳的唱片,一边 吹口哨,当然他还忘不了再来一点啤酒。我们在上面做作业,有时会听到地 下室传来有节奏的击打沙袋的声音。父亲上来吃晚饭时,又会开始讲他的战 争故事。在他吃完饭以前,我们是不能离开餐桌的。 父亲没有活过尼克松时期,他在客厅看黑白电视机里的越战报道时,犯 了心脏病。 父亲去世时,我只有八岁。一头红发的我很是安静,总是怯怯地站在姐 姐的影子里。我记得当人们用担架把父亲抬出去时,我紧紧地攥着姐姐的手 。父亲就像一片浮云,在这个温暖的日子里离开了我。前门关上了,我仍然 攥着姐姐的手。这时,黑白电视机里的晚间节目正在播报新的伤亡人数。“ 五百四十三人在战争中牺牲,”主持人严肃地说,“这是迄今为止越战中伤 亡最严重的一周。” “还有一个!”姐姐大喊一声。她推开我,嚎啕大哭起来。 几天后,父亲的战友们来参加他的葬礼。父亲的灵柩上盖着国旗,他的 战友对他敬了最后的军礼。对父亲来说,结束一切战争的不是二战,而是越 战。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姐姐——两个都喜欢支配别人的女人,担负起了抚 养我的义务。生活在母亲和姐姐之间,我觉得自己犹如挡书板中间可怜的书 一样。我只盼着能早点高中毕业上大学去。从父亲去世到我念高中的那段日 子,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挣脱约束,想干什么就 干什么。我清楚地记得,母亲第一次没有催我上床睡觉,而让我看了晚间电 视节目的情景,节目好像是讲一个叫罗丝·李的吉普赛脱衣舞女郎。我还记 得我参加了啦啦队。有一次,我设计的DNA分子三维图还获得了科学博览会 的杰出蓝带奖。有时,我会偷詹妮特的剃刀刮我腿上讨厌的腿毛。最有意思 的是,有一次我裙子上的背带滑掉了,生平第一次有男孩注意我。 像父亲一样,我也认为离开家的最初几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在南部的伊利诺伊州读了四年大学,那是一所离芝加哥很远的州立大 学。我渴望像霍勒斯·格里利一样从事新闻业,于是我来到了加州,希望能 够获得新闻学学位。 我深信大学里的朋友会伴我终身——或许当我离开人世时,他们会抬着 我的灵柩,为我写下令人伤感的颂歌。 我在大一时交的两个朋友是我的室友,克丽奥·金和露碧·帕帕斯。不 管我走到哪里,不管过去多久,她们都是我的朋友。虽说现在我住在威斯康 星州,克丽奥住在科罗拉多州,露碧住在罗德岛,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友 谊。只要我有麻烦,并且需要人倾听时,我就会打电话给露碧,她总会对我 说:“路易丝,大声唱起来!”毕竟我们俩都喜欢吉普赛女郎罗丝·李。而 我每次打电话给克丽奥,她都会直言不讳地说出她的观点。 尽管我们彼此距离遥远,但我们的友谊却更坚韧,因为我们都用心经营 这份友情。我们不仅仅在节日时互寄卡片,记住彼此的生日,更重要的是我 愿和她们分享生命中的一切悲欢荣辱。在某些方面,她们甚至比我的母亲和 姐姐更重要。 我大学里最好的异性朋友是乔尔·罗兰德。他很帅,金发,眼睛和我父 亲的一样是淡蓝色的。其实乔尔和我在高中时就认识了,尽管我们彼此不是 很了解。我们进了同一所大学后才成了朋友。这以后,我一直以为我们会是 终身的朋友。 我在加州的经历大致如下:一份不太好的工作,一份不错的工作,还有 一次可怕的订婚。后来我遇到了马克·安德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律系 的学生,并和他结了婚。像当年母亲追随父亲从纽约搬到芝加哥一样,两年 前,我跟着马克从旧金山搬到了东部的林区。 我们总是追随着我们的男人,这很有意思。 马克和我住在离明诺加镇十英里的一幢小木屋里。这里到处绿荫覆盖, 有松树、枫树、白杨和桦树,有“北大森林”的美誉。即使是最近的邻居, 也跟我们隔着好几英亩。我只知道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他们却似乎知道我的很多事。一次我听到住得最近的邻居、一对姓氏音节 比我的手指还多的夫妇在船上议论我,“你见过马克·安德森从加州带回来 的红头发女人吗?她比白杨树苗还苗条,真不知道她怎么熬过冬天。” 如果你以为这些当地人知道自己的谈话声会顺着河水飘过来,那你就错 了。我坐在码头边,双腿在波光粼粼的河水里晃悠。我听到了他们全部的谈 话。 当地人不喜欢有人来,新来的人代表着变化和发展。他们只喜欢树木长 高,小鱼长大。 P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