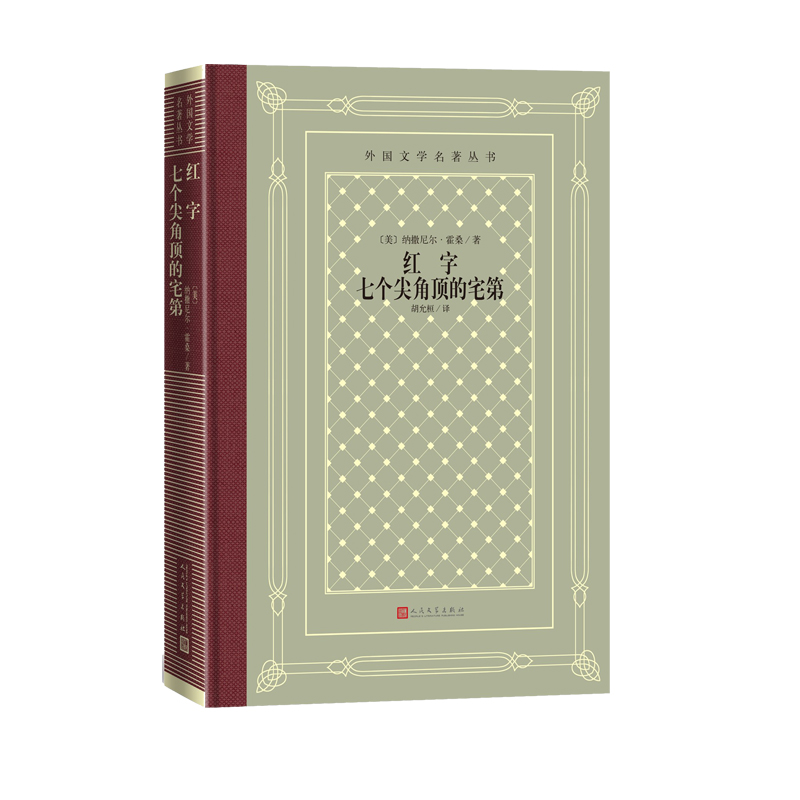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37.30
折扣购买: 红字 七个尖角顶的宅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020166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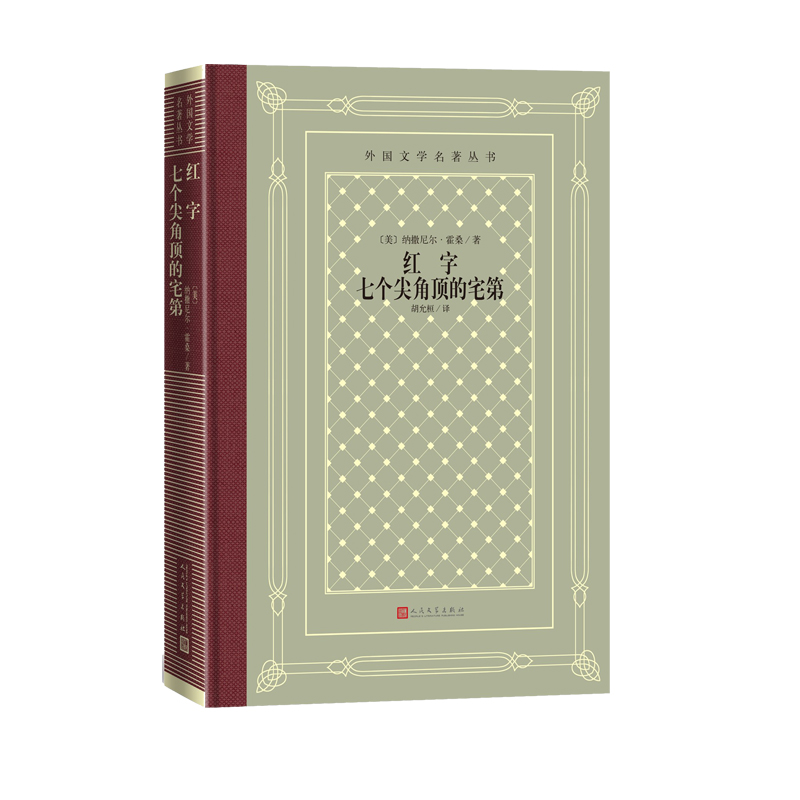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 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被称为美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红字》《七个尖角顶的宅第》,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古宅青苔》《雪影》等。其中《红字》已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亨利·詹姆斯、爱伦、坡、赫尔曼·梅尔维尔等文学大师都深受其影响。
精选内容 二百多年前一个夏日的上午,狱前街上牢房门前的草地上,满满地站着好大一群波士顿的居民,他们一个个都紧盯着布满铁钉的橡木牢门。如若换成其他百姓,或是推迟到新英格兰后来的历史阶段,这些蓄着胡须的好心肠的居民们板着的冷冰冰的面孔,可能是面临凶险的征兆,至少也预示着某个臭名昭著的罪犯即将受到人们期待已久的制裁,因为在那时,法庭的判决无非是认可公众舆论的裁处。但是,由于早年清教徒性格严峻,这种推测未免过于武断。也许,是一个慵懒的奴隶或是被家长送交给当局的一名逆子要在这笞刑柱上受到管教。也许,是一位唯信仰论者一种主张基督徒可以按照福音书中所阐明的受到感化的美德而摆脱道德法律约束的教派。、一位教友派或称“贵格派”或“公谊会”,是一个没有明确的教义,也没有常任牧师,而靠内心灵光指引的教派。的教友或信仰其它异端的教徒被鞭挞出城,或是一个闲散的印第安游民,因为喝了白人的烈酒满街胡闹,要挨着鞭子给赶进树林。也许,那是地方官的遗孀西宾斯老夫人那样生性恶毒的巫婆,将要给吊死在绞架上。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围观者总是摆出分毫不爽的庄严姿态;这倒十分符合早期移民的身份,因为他们将宗教和法律视同一体,二者在他们的品性中融溶为一,凡涉及公共纪律的条款,不管是最轻微的还是最严重的,都同样令他们肃然起敬和望而生畏。确实,一个站在刑台上的罪人能够从这样一些旁观者身上谋得的同情是少而又少、冷而又冷的。另外,如今只意味着某种令人冷嘲热讽的惩罚,在当时却可能被赋予同死刑一样严厉的色彩。 就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夏天的早晨,有一情况颇值一书:挤在人群中的好几位妇女,看来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刑罚都抱有特殊的兴趣。那年月没有那么多文明讲究,身着衬裙和撑裙的女人们公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中,只要有可能,便要扭动她们那并不娇弱的躯体,挤进最靠近刑台的人群中去,也不会给人什么不成体统的感觉。那些在英伦故土上出生和成长的媳妇和姑娘们,比起她们六七代之后的漂亮的后裔来,身体要粗壮些,精神也要粗犷些;因为通过家系承袭的链条,每代母亲遗传给她女儿的,即使不是较她为少的坚实有力的性格,总会是比较柔弱的体质、更加娇小和短暂的美貌和更加纤细的身材。当时在牢门附近站着的妇女们,和那位堪称代表女性的男子气概的伊丽莎白相距不足半个世纪。她们是那位女王的乡亲:她们家乡的牛肉和麦酒,佐以未经提炼的精神食粮,大量充实进她们的躯体。因此,明亮的晨曦所照射着的,是宽阔的肩膀、发育丰满的胸脯和又圆又红的双颊——她们都是在遥远的祖国本岛上长大成人的,远还没有在新英格兰的气氛中变得白皙与瘦削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些主妇们多数人一开口便是粗喉咙、大嗓门,要是在今天,她们的言谈无论是含义还是音量,都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 “婆娘们,”一个满脸横肉的五十岁的老婆子说,“我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要是我们这些上了一把年纪、名声又好的教会会友,能够处置海丝特·白兰那种坏女人,倒是给大伙办了件好事。你们觉得怎么样,婆娘们?要是那个破鞋站在眼下咱们这五个姐们儿跟前听候判决,她能够带着那些可敬的官老爷们赏给她的判决溜过去吗?老天爷,我才不信呢!” “听人说,”另一个女人说,“尊敬的丁梅斯代尔教长,就是她的牧师,为了在他的教众中出了这桩丑事,简直伤心透顶啦。” “那帮官老爷都是敬神的先生,可惜慈悲心太重喽——这可是真事,”第三个人老珠黄的婆娘补充说,“最起码,他们应该在海丝特·白兰的脑门上烙个记号。那总能让海丝特太太有点怕,我敢这么说。可她——那个破烂货——她才不在乎他们在她前襟上贴个什么呢!哼,你们等着瞧吧,她准会别上个胸针,或者是异教徒的什么首饰,挡住胸口,照样招摇过市!” “啊,不过,”一个手里领着孩子的年轻媳妇轻声插嘴说,“她要是想挡着那记号就随她去吧,反正她心里总会受折磨的。” “我们扯什么记号不记号的,管它是在她前襟上还是脑门上呢?”另一个女人叫嚷着,她在这几个自命的法官中长相最丑,也最不留情,“这女人给我们大伙都丢了脸,她就该死。难道说没有管这种事的法律吗?明明有嘛,圣经里和法典上全都写着呢。那就请这些不照章办事的官老爷们的太太小姐们去走邪路吧,那才叫自作自受呢!” “天哪,婆娘们,”人群中一个男人惊呼道,“女人看到绞刑架就害怕,除去这种廉耻之心,她们身上难道就没有德行了吗?别把话说得太重了!轻点,喂,婆娘们!牢门的锁在转呢,海丝特太太本人就要出来了。” 牢门从里面给一下子打开了,最先露面的是狱吏,他腰侧挎着剑,手中握着权杖,那副阴森可怖的模样像个暗影似的出现在日光之中。这个角色的尊容便是清教徒法典全部冷酷无情的象征和代表,对触犯法律的人最终和最直接执法则是他的差事。此时他伸出左手举着权杖,右手抓着一个年轻妇女的肩头,拽着她向前走;到了牢门口,她用了一个颇能说明她个性的力量和天生的尊严的动作,推开狱吏,像是出于她自主的意志一般走进露天地。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左右的婴儿,那孩子眨着眼睛,转动她的小脸躲避着过分耀眼的阳光——自从她降生以来,还只习惯于监狱中的土牢或其它暗室那种昏暗的光线呢。 当那年轻的妇女——就是婴儿的母亲——全身伫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激情,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然而,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索性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A。这个字母制作别致,体现了丰富而华美的匠心,佩在衣服上构成尽美尽善的装饰,而她的衣服把她那年月的情趣衬托得恰到好处,只是其艳丽程度大大超出了殖民地俭朴标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