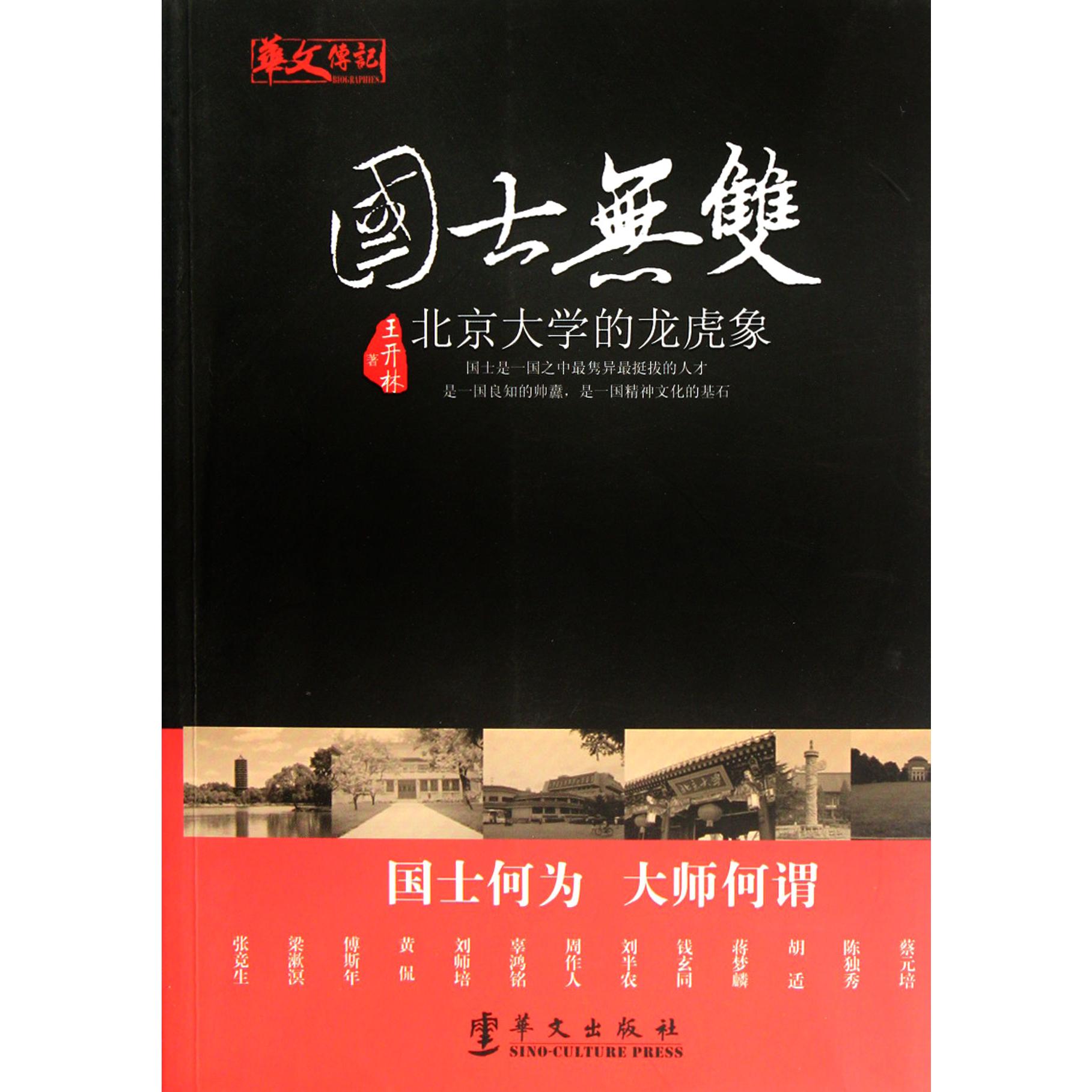
出版社: 华文
原售价: 34.80
折扣价: 22.62
折扣购买: 国士无双(北京大学的龙虎象)
ISBN: 9787507536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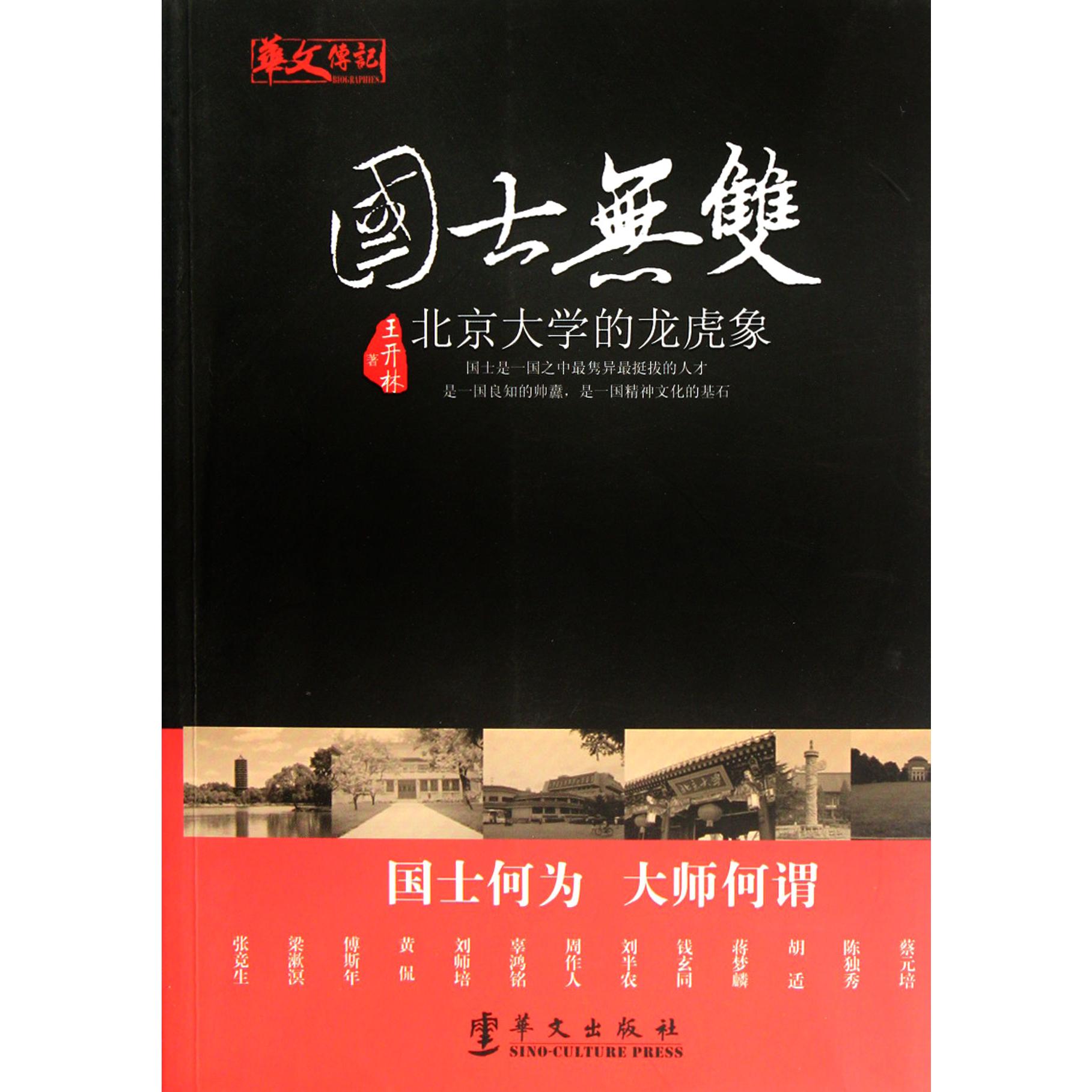
。。。
古今中外,方方面面的成功者甚多,我们不难从中遴选出自己推崇的对 象,但若将某住先贤推崇至大师与完人的极峰,这肯定是一件非常离谱的事 情。在现代中国,除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还有谁能够当此美誉而无愧 ?这并非笔者的一己私见,而是其同时代众多学人的共识。 一、如此翰林,绝无仅有 毛子水在《对于蔡元培的一些回忆》中讲到一件趣事。某次,北大名流 雅集,钱玄同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 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笑 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黄 山谷是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他的字体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如铁干 铜柯,似险峰危石,以刚劲奇崛著称。蔡先生的急中生智既见出他的涵养, 也见出他的幽默,满座闻之,皆忍俊不禁。 自唐代以迄于清代,一千二百多年间,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 ,去革封建专制王朝老命的,除了蔡元培,数不出第二人。自达摩东来,一 千五百多年间,和尚何其多,集情圣、诗人、画家和革命志士于一身的,除 了苏曼殊,也数不出第二人。他们是在“古今未有之变局”中禀赋特出的产 儿,是天地间绝无仅有的异数。 据教育家马相伯回忆,1901年,蔡元培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期 间,曾与张元济、汪康年一道拜他为师,学习拉丁文。每天清晨,蔡元培从 徐家汇徒步四五里路到土山湾马相伯家上课。由于求学的心情过于急切,第 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凌晨五点多钟,天边刚露出一丝曙色,他就在楼下 低声叫唤“相伯,相伯”。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来这里喊魂?他 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名士派头十足,他急忙摇手,对蔡元 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虽然有点败兴,蔡元培并没 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来到马相伯家中。这一年,蔡元培三十四岁 ,身为翰林已达八载,但他仍有程门立雪的虔诚劲头。 蔡元培一生的座右铭为“学不厌,教不倦”。他三度旅欧,精研西方哲 学,在巴黎访晤过居里夫人,在德国结识了爱因斯坦,两次高峰对话使他受 益良多。嗣后,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乃是积学深思所致,绝非 异想天开。宗教的顶礼膜拜常不免使上智下愚者堕入迷信的泥坑而难以自拔 ,美育的修身养性则使人的精神境界找获上升的阶梯而进路无穷。终其一生 ,蔡元培对学问抱持浓厚的兴趣,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情感,虽历经世乱,屡 遭挫折,却不曾泄过气、断过念、灰过心。 戊戌变法时期,王照、张元济劝导康有为以开办教育、培植人才为先鞭 ,以维新变法为后图,康氏则认为:强敌虎视鹰瞵于外,清廷河决鱼烂于内 ,譬若老房子着火,纵有观音大士千手千眼为助,犹恐扑救无暇,王、张之 议缓不济急,只好暂且作罢。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前,严复在英伦邂逅孙中 山,他开出的药方同样是“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孙中山略无迟 疑,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语作答,他认为,在清王朝旧体制的框架 下,教育犹如被巨石镇压着的笋尖,是无法舒展其身子骨的。 当初,康有为、粱启超倡导变法维新,炙手可热,蔡元培冷眼旁观,并 不睇好康、梁的“小臣架空术”,维新派把孤立无援的光绪皇帝的细腿当成 如来佛脚去抱,企图富国强兵,拯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清王朝,这岂不 是痴心妄想吗?改良教育和培植人才,如此重要的事情,康、梁竟认为无关 大局,根本不留意,全然不着手,徒然空言造势,似乎撒豆成兵,倒有几分 神汉巫公的派头。康有为所主导的“四不像”的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果然一 败涂地,蔡元培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败因:“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 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真心向往的是民主 政治,极力主张的是教育救国,他放着好好的翰林不做,弃官南下,回家乡 绍兴监理新式学堂,到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任总教习,与叶瀚等人发起成立中 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开办爱国女学。 1903年冬,蔡元培为使国人对帝俄觊觎中国东三省有所警觉和防范,创 办《俄事警闻》报。这一时期,他受蒲鲁东、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发表小说《新年梦》,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废除婚姻制度。但他很快就发 现此路不通,唯有以革命的霹雳手段刷新政治,才能使死气沉沉的社会获得 生机。于是,他参加杨笃生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陶成章等人秘密 创立光复会,出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由封建王朝的翰林转变为彻底 的革命党,蔡元培无疑是古今第一人。 蔡元培写过《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三十 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 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力的种子;又以暗杀于 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然而,与同时代的革命 党人相比,蔡元培的主张无疑是相对温和的,当民族革命被推向最高潮时, “誓杀尽鞑虏,流血满地球”的激烈言论是主旋律。邹容的《革命军》痛恨 满族人,仿佛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欲斩草除根而后快。P2-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