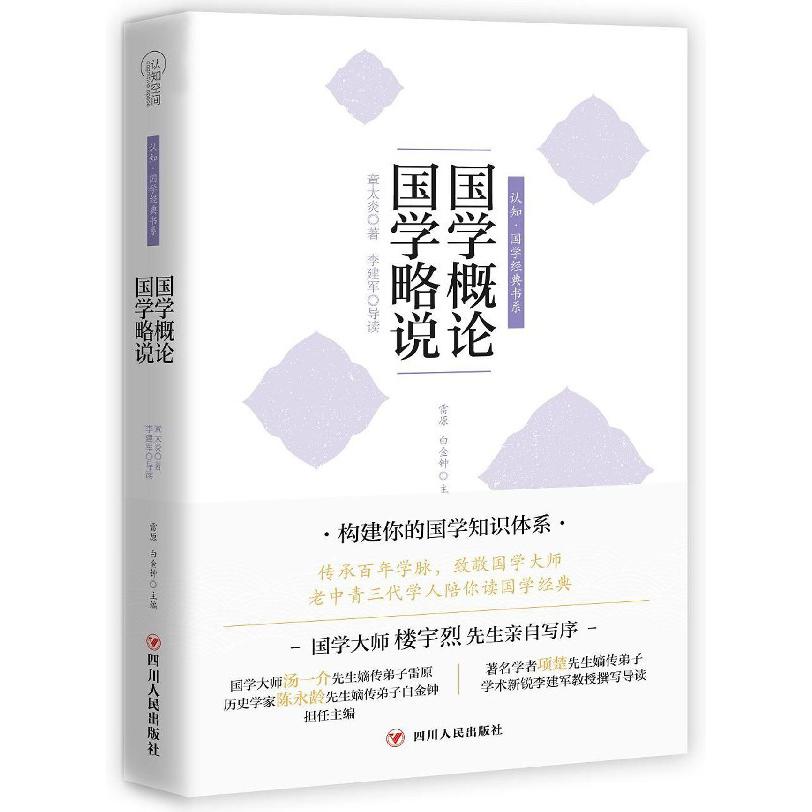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56.00
折扣价: 33.10
折扣购买: 国学概论国学略说/认知国学经典书系
ISBN: 9787220106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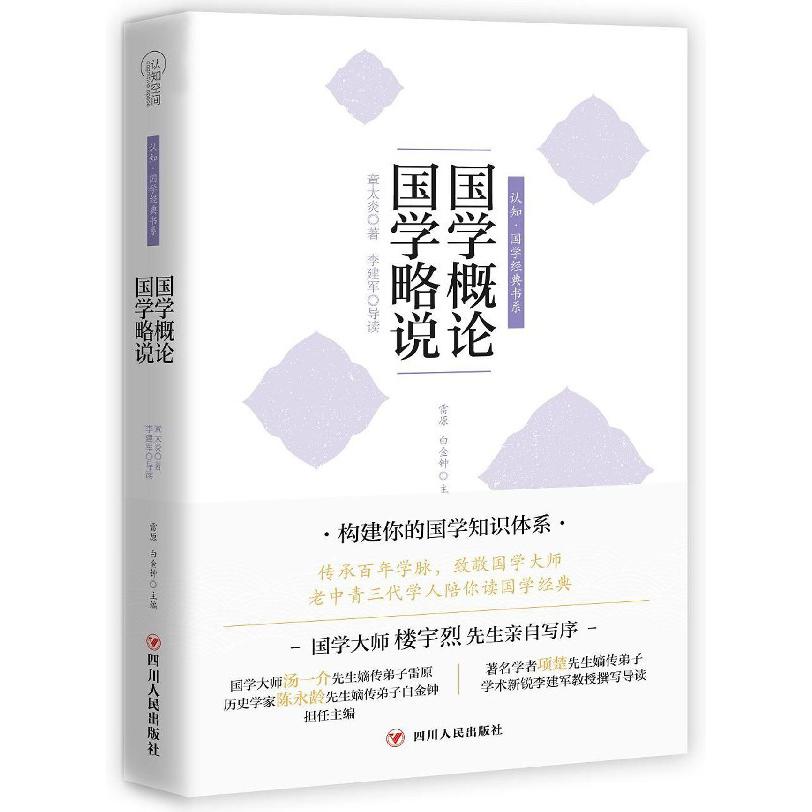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曾改名炳麟,后改名绛,号太炎。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经学家、中医文献学家、民族主义革命者。早年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经、子之学,晚年偏重理学。一生研究颇广,除经、子、理学外,在史学、文学、佛学、医学、政治学、书法等领域也学养深厚,多有建树。 李建*,四川大学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先后师从项楚先生、束景南先生等**学者,现为台州学院中文系教授。已在《国学研究》《北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宋代浙东文派研究》,主持两项**社科基金项目和多项省部级课题。荣获全国百篇**博士论文提名、浙江省**哲社**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浙江省级**教师暨省高校**教师等称号。入选浙江省首届“之**年社科学者”、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等省级人才项目。 "
"**章 概 论 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是第三次了。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鉴》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但还是不能讲;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或讲些事实夹些论断,也没甚意义。所以这些书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先把“国学概论”分作两部研究: 一、国学之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二)经典诸子非**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二、治国学之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二)通小学 (三)明地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五)辨文学应用 一、国学之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在古代书籍中,原有些记载是神话,若《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载,我们看了,觉得是怪诞极了。但此类神话,在王充《论衡》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些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载。又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那种神话,正史里也都没有。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 《诗经》记后稷的诞生,颇似可怪。因据《尔雅》所释“履帝武敏”,说是他的母亲,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但经毛公注释,训帝为皇帝,就等于平常的事实了。 《史记·高帝本纪》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高祖母之身,遂生高祖。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还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作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从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贤王都属假托;即如《尧典》所说“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等的话,有人很怀疑,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哪得有像这样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叙太古的事,不能详叙事实,往往只用几句极混统的话做考语,这种考语原*容易言过其实。譬如今人做行述,遇着没有事迹可记的人,每只用几句极好的考语;《尧典》中所载,也不过是一种考语,事实虽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 《禹贡》记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本有一博士,他说:“后世凿小小的运河,尚须数十年或数百年才告成功,他治这么大的水,哪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贡只是一种奇迹。我却以为大禹治水,他不过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亲身去,就游历一周也不能,何况凿成!在那时人民同*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经之营之,不*成之”了。《禹贡》记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过依报告录出,并不必由大禹亲自调查的。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驯者,可见他述的确实;我们翻看经史中,却也没载盘古、三皇的事;所以经史并非神话。 其他经史以外的书,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确有可疑者在。但《竹书纪年》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可存而不论。《穆天子传》也不在正经正史之列,不能以此混彼。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遂全目以为伪,这是错了! (二)经典诸子非**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教的《**》都是**,就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佛经”“**”的那个“经”字,是后人翻译时随意引用,并不和“经”字原意相符。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别的就称作线装书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 中国自古即薄于**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也是环境的关系:中国土地辽广,统治的方法亟待研究,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没感着困难。印度土地也大,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所以他们的**易于发达。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很冷淡。 老子很反对**,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对于**,也反对;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味“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礼记》一书很考究祭祀,这书却又出自汉代,未必是可靠。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是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份。须知**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耶稣教的上帝,是给一般人膜拜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了。 九流十家中,墨家讲天、鬼,阴阳家说阴阳生克,确含**的臭味;但墨子所谓“天”,阴阳家所谓“龙”“虎”,却也和**相去很远。 就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后世的历史,因为辞采不丰美,描写不入神,大家以为是记实的;对于古史,若《史记》《汉书》,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怀疑: 《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事,《项羽本纪》记项羽垓下之败,真是活龙活现。大家看了,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太史公并未眼见,也不过如《水浒传》里说武松、宋江,信手写去罢了。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慎之又慎。像伯夷、叔齐的事,曾经孔子讲及,所以他替二人作传。那许由、务光之流,就缺而不录了。项羽、荆轲的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太史公虽没亲见,但传说很多,他就可凭着那传说写出了。《史记》中详记武略,原不止项羽一人;但若夏侯婴、周勃、灌婴等传,对于他们的战功,只书得某城,斩首若干级,升什么官,竟像记一笔账似的;这也因没有特别的传说,只将报告记了一番就算了。如果太史公有意伪述,那么《刺客列传》除荆轲外,行刺的情形,只曹沫、专诸还有些叙述,豫让、聂政等竟**略过,这是什么道理呢?《水浒传》有百零八个好汉,所以施耐庵不能个个描摹,《刺客列传》只五个人,难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写吗?这都因荆轲行刺的情形有传说可凭,别人没有,所以如此的。 “商山四皓”一事,有人以为四个老人哪里能够使高祖这样听从,《史记》所载未必是实。但须知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为多数人所合力做成,而史家常在甲传中归功于甲,在乙传中又归功于乙。汉惠免废,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所以在《留侯世家》中如此说,并无可疑。 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如刘知几《史通》曾疑*始刮席事为不确;因为*始起自*泽时,已有英雄气概,何至为众所拥立时,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始的话。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得同子一般,这样愚的人怎能篡汉?这也是因汉室中兴,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 考《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但那只是县志之类,如所谓《周考》《周纪》者。*早是见于《庄子》,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一语。这所谓“小说”,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刘宋时有《世说新语》一书,所记多为有风趣的魏晋人的言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只时*多颠倒处,事实并非虚构。唐人始多笔记小说,且有因爱憎而特加揄扬或贬抑者,去事实稍远。《新唐书》因《旧唐书》所记事实不详备,多采取此等笔记。但司马温公作《通鉴》对于此等事实必由各方面搜罗证据,见有可疑者即删去,可见作史是极慎重将事的。和现在小说*相近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彼记宋徽宗游李师师家,写得**生动,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大约《水浒传》即脱胎于此书。古书中全属虚构者也非没有,但多专记神仙鬼怪,如宋人所辑《太平广记》之类,这与《聊斋志异》相当,非《水浒传》可比,而且正史中也向不采取。所以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但*与小说、传奇不同。 " "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章太炎 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蔡元培 所谓大师之作的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大抵就是这个样子。 章先生素以骂人知名,此书所论鄙薄者多,中意者少,果然是书如其人。 《诗经》《楚辞》,发自性情,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自老杜以后的历代诗作,多数斧凿痕迹严重,动辄引经据典,说是诗道中衰却也很在理。 ——豆瓣网友 水犹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