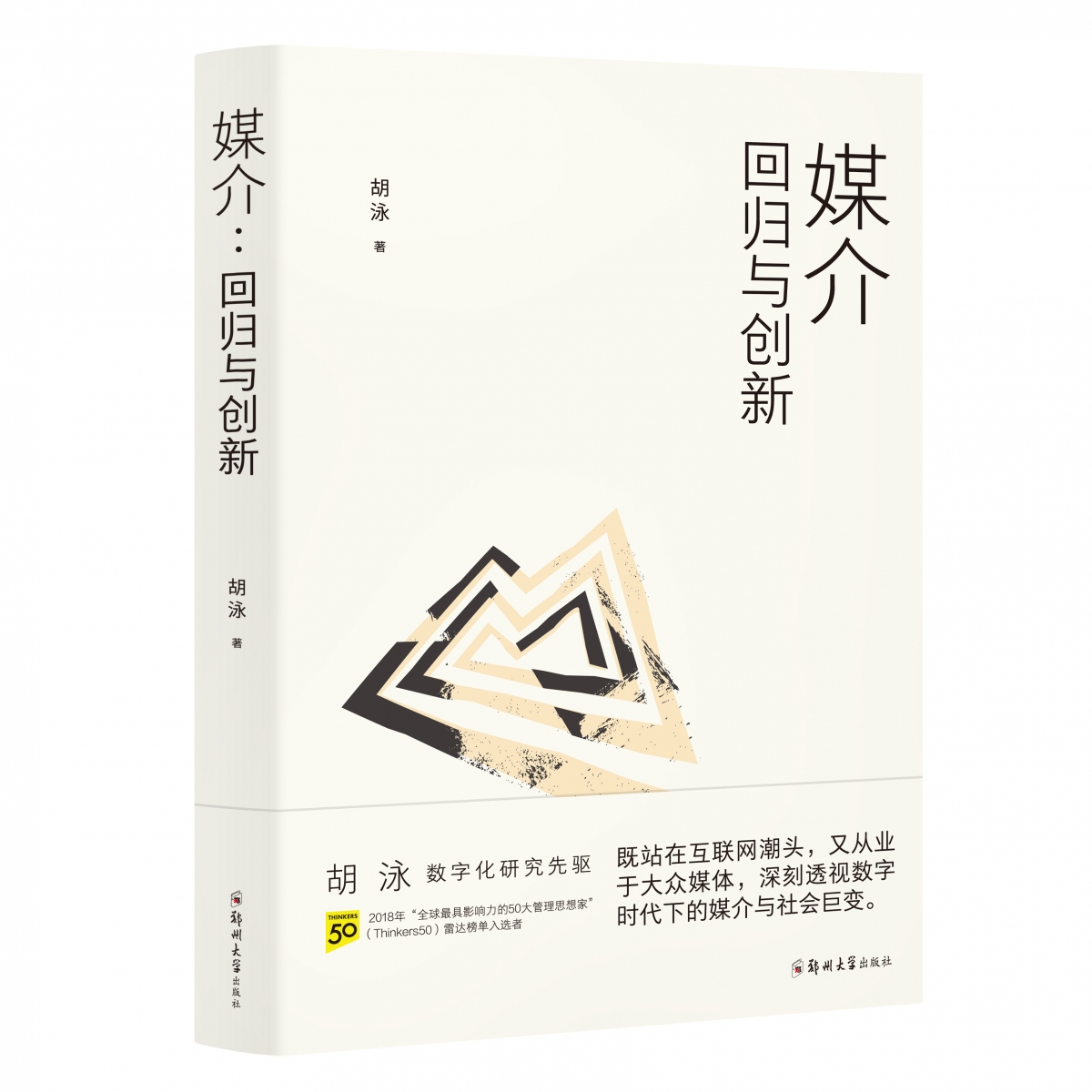
出版社: 郑州大学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5.50
折扣购买: 媒介:回归与创新
ISBN: 9787564587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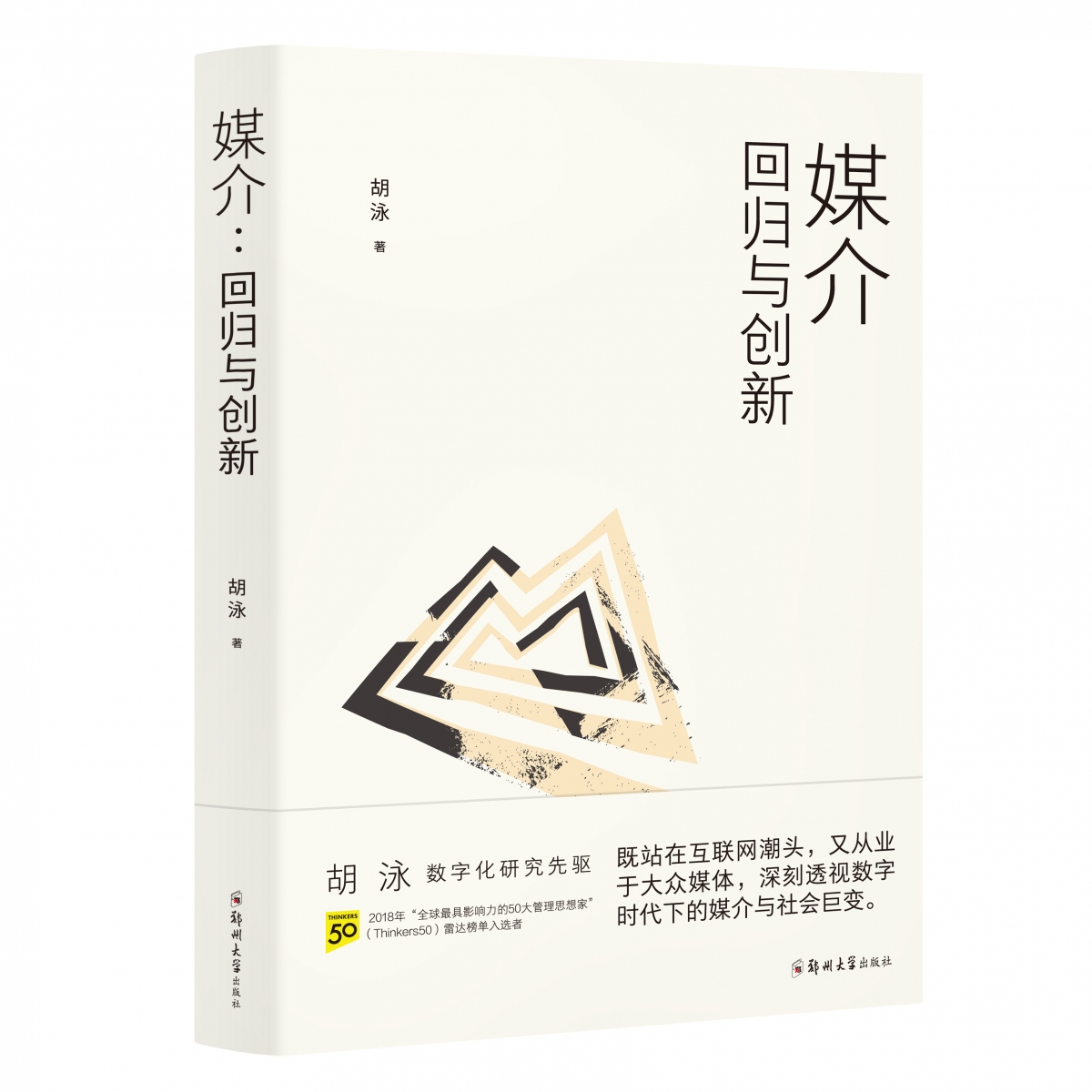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拥有11年的平面媒体经验、6年的电视媒体经验和3年的网络媒体经验,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著有《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信息渴望自由》等,译有《数字化生存》《人人时代》等,其中《数字化生存》是中国迈入信息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2018年,胡泳被全球首个管理思想家排行榜“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大管理思想家”(Thinkers50)选入雷达榜单,名列可能对未来组织机构的管理和领导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30位世界思想家之一。
如何在新媒体时代讲故事 你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刷存在感,但也要让别人讲述他们的故事。由此,你需要具有分享情怀,整个互联网都建立在慷慨的基础之上,没有慷慨就没有互联网。 我曾应邀给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开一个有关互联网的书单,我选了四本书。有两本书是我翻译的,《人人时代》《认知盈余》,另外两本是两家公司的成长史,《Facebook效应》和《孵化Twitter》。后两本公司史都非常好看。 为什么我给产品经理推荐这两本公司史?因为很多人在观察Facebook崛起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问题。Facebook成长过程中有的里程碑,如果不从产品经理角度考虑,可能不觉得那是里程碑,但一旦从一个产品经理的眼光来看,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里程碑。 2006年9月,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开发出一款叫作News Feed的应用,这是一种能够主动把用户主页上的变动向所有好友呈现的内置功能。在没有发明这个东西之前,你在使用Facebook的时候,不可能在你自己的主页上看到其他人干什么。 突然之间,你可以在你的主页上看到你所有好友的行踪。我个人觉得这是Facebook发展史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看到,后来Facebook对此做了进一步改动,加大了可视化的力度。在Facebook把News Feed用一种更突出、更亲近的方式展现出来以后,它声称,我们所有的News Feed最后所关注的都与你朋友的日常行为相关,这是News Feed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分享由情绪推动 我们把News Feed翻译成什么?有一种说法把它叫作“新鲜事”,但因为它的英文是News Feed,似乎有“新闻”这个词在里头(其实与新闻无关),我们也可以将它称为“动态时报”或者“动态消息”。归根结底,News Feed是一种向用户提供持续更新内容的数据格式,新闻在这里被平台加以重新定义了,因为它不像媒体对新闻的定义。现在,Facebook说,我们会把你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举一动都叫作新闻。 由于这样的一个定义,扎克伯格讲过一句令传统的新闻工作者为之侧目的话:“你们家门口有一只濒死的松鼠,可能比非洲无论多少濒死的贫民都会更加引起你的兴趣。”这样的价值观所代表的东西,对原来的新闻信息业有很大的颠覆。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在没有社交媒体之前,你每天收到的信息有多少是来自好友,又有多少是来自媒体?你可能会回答说,大部分信息是来自媒体的,只有少部分来自好友。然而今天这两者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你大部分的信息是来自好友,而不是来自新闻媒体。 这样一个方式本质上是分享。分享跟搜索有不同的运行机制:搜索用于发现信息,但分享通常来讲是由情绪推动的,这两者的逻辑非常不一样。 作为一个产品,News Feed的核心是“状态更新”,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新鲜事”。在电脑上展示状态的概念,最早其实是AOL发明的,即AOL做的离线消息。我们看《孵化Twitter》这本书,里面讲到Twitter的几个核心创始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杰克·多西(Jack Dorsey),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能不能把AOL的离线信息单独开发,做成一个应用:一个非常简洁的设计,一个长方形的对话框,上面写着你的状态是什么,配上一个很简单的更新按钮。这个创意就导致了后来大家所熟悉的状态更新这样一种信息呈现方式。 多西2006年3月21日发了一条推文,这是全世界第一条“推”:“我刚刚建立了我的Twttr”(那时还不叫Twitter)。从这条推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所有状态更新的基础元素设计都在里面了。 我看到这条推文的时候产生一个联想:在1876年3月10日,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第一次成功地用电话传输了语音,传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他对他的助手说:“沃森,到这儿来,我想见你。”可以发现这两条信息之间的惊人相似,一个简单的电话信息和我们知道的状态更新是非常相似的,而其革命意义也相似。 在《孵化Twitter》里讲到整个Twitter的成型。杰克说到,一条状态信息如果更新的话,之前的状态就应该被更新的状态所取代。另外一个核心创始人是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他说状态更新应该像博客一样按时间顺序展示,就是最新的在最上面。 第三个创始人非常悲惨,最后在整个Twitter故事当中出局了,他说我们要给每一个更新加一个时间标签,让人们知道每条状态更新的具体时间。最后杰克提出了令Twitter成功的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限制推文的长度为140个字符。由于这些人共同的智慧,导致Twitter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状态更新 当你用这样的方式将个人生活进行某种状态更新的时候,马上会遇到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你用这样的状态更新来干什么?你是用它来分享你个人的状态,还是用它来分享新闻?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两个不同的问题,分别叫“你在干什么”和“刚刚发生了什么”。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两个问题有多么不同。我们要延伸阐释的话,实际上它等于要你选择,是更多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还是讲述他人的故事。 最初Twitter的几个核心人物都认为,这个服务就是为了分享个人状态的,就像我们看到的杰克所写的第一条推,没有多大的意义,也就像贝尔打的第一通电话一样,没有多大意义。它对个人来讲有意义,对社会来讲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Twitter的想法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初认为该服务会被用来分享个人的状态,但实际上它慢慢地变成了24小时的新闻服务。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Twitter上的上述两个路径,慢慢地开始并存。 Twitter第一次把它的口号由原来的“你在干什么”变成了新的口号的时候,我在2009年7月28日写了一条推文,指出“Twitter今日变脸,意义十分重大,未来头号媒体格局初现”。所谓的“变脸”,是指Twitter把What are you doing的口号变成了Share and discover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anywhere in the world,即要去分享和发现你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要把这些事情告诉全世界。这个变化体现出Twitter整个的演进过程中理念的挣扎。 回过头来,如果Twitter是一个24小时报告信息的媒体,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究竟有谁会在乎我一天24小时都在干什么?如果你发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鸡毛蒜皮,别人为什么要在乎? 实际上,有很多理由导致大家对这样的服务一旦用上以后就欲罢不能。一个理由是“它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感受到朋友们生活的韵律”,这跟扎克伯格所开发的News Feed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就是想了解你的朋友在干什么,Twitter能为线上带来更多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同时,这跟我们生活的后现代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每个人都在流动,每个人都处在焦虑中,这个时候你会寻找一种通过电子媒介让自己不再那么孤独的方式和方法。 当然这也一定会被更大的社会因素所利用,比如说我们由此产生了外包式的新闻,进一步发现,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可以用来进行社会组织和发起社会行动。 时间线 整个媒体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人类在媒体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发展,这个发展叫作时间线(Time Line),它完全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等级制系统,我们都很熟悉的文档和图表,也不同于90年代中期的万维网模式(代表性应用是搜索引擎)。时间线的呈现方式,跟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信息呈现方式,有一个天差地别的颠覆。 举个例子来讲,我曾经是Google Reader的深度用户,可是Google Reader虽然有这么多人喜欢它,但最后还是关闭了。因为它不是时间线的方式,大家会觉得它非常落伍、非常不方便。我把依靠时间线作为呈现信息的基准方式而形成的媒体,统一称之为“生活流媒体”。生活流媒体是组织数字化内容的一种方法,这些内容可以是图片、文字、链接、邮件、视频、音频、网络行为……所有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由一条时间线串起来,既延伸到过去又指向未来,但核心的问题是现在,因为互联网最关心的是当下,将当下的饥渴深深嵌入社交媒体的架构和商业模式中。Twitter和Facebook对我们五年前在做什么或想什么不感兴趣;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或在想什么。 这些平台有充分的理由对当下产生偏好,因为这大大增强了它们向广告商推销我们的在线生活的能力。毕竟,很多时候我们想的都是满足我们的需求,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我们的需求越早被阐明,并与我们各自的人口群体相匹配,我们就越有可能被诱惑或胁迫在网上买东西。 建立在生活流基础上的媒体,或者商业方式,最后会统治互联网,因此世界上所有的数据最后会展现为我称之为“世界流”的东西。这个世界流在很多地方是公有的,但是在相当多的地方是专有的,只对特定的被批准的用户开放。 网络浏览器会被生活流浏览器所替代,用户将会习惯于我们的信息以一种“流”的方式出现在面前,而不再是从文件系统中读取文件。生活流会变成用户生活故事的展开的一种镜像。随着视频的进展,这个生活流一定是可视化的。 “生活流”与“世界流” 这个生活流具有可自我决定性,用户能够完全决定出现在他面前的东西,如果你不给用户这种选择的可能性,那么用户就会觉得这个“流”的出现或者它的呈现方式是有问题的。我们可能都处于不同的子流当中,但是我一旦想了解某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状态,就可以屏蔽掉跟此人无关的所有其他人的生活,而只看到这一个人的“流”。用同样的方式,其他人也可能只看到我这一个人的“流”,我把这种选择叫作“流”的可自我决定性。 这样的一个“流”的可自我决定性,最终跟人的个体故事相关。我们为什么使用时间线?通过这条线,最终可以讲述人生的整个故事。Facebook介绍时间线的广告就直接说,你可以告诉别人你的人生故事,并且这个人生故事是从开头到中间一直到现在。所以你在Facebook的时间流中可以看到所有你关注的人的故事,用一种信息流的方式,最后完整地呈现出来。 想象一下,你浏览的某些信息可能只是一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但是如果他从小的时候,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在Facebook上呈现,那么整体来看,这就是他非常完整的个体人生故事。 移动互联网大潮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核心就是自从苹果发明了触控技术以后,你会习惯于只要你在手机上做一下滑屏下拉的动作,更新的信息必须出现。如果下拉某个应用时它静止不动,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媒体,它也不构成生活流,它是无用的废物。 我们从儿童的使用体验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小孩三四岁的时候,看到任何一个屏他一定要去碰一下,碰了以后发现这个屏是不动的,他对这个屏马上就丧失了兴趣。所以只要是你有一个下拉的动作,就应该有新的信息呈现,我把这背后的逻辑叫作“时间现在成为媒体的组织原则”,最新的信息永远在最上面,这个可能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比如说,最新的东西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东西,然而时间线的流会导致新的东西是有霸权的,新的东西永远盖过旧的东西。这也就是杰克·多西设计的状态更新,只要有新的状态,旧的状态就会被覆盖。最新的东西永远在最上面,导致每一个时刻的重要性大大增强了。(所以腾讯朋友圈的英文叫作moment。)当你使用生活流媒体的时候,每一时刻的重要性大大地高于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每一个十年、每一个百年的重要性,时刻的重要性压倒一切。 社交媒体,同记者和其他“争上头条”的注意力召集者(attention-conveners)一样,重视新奇超过一切。 侵入性技术 由于重要性是以时刻来划分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媒介叫作侵入性技术,它对你的生活构成非常强烈的侵入。每个人在用微信的时候都有焦虑,你要消灭那些小红点。当时间成为媒体的组织原则的时候,就会滋生侵入性。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称之为时间现在成为媒体的表现形式,这个表现形式当然有很多种,比如说Twitter的字符数限制,它实际上是一个时间限制。你现在看到所有的短视频,从Instagram到腾讯的微视,在未来都可以使每个人成名8秒钟或者12秒钟,这就是典型的时间成为媒体的表现形式。 我们的碎片化的表达,甚至我们的语言现在越来越趋向于简短和缩略,都与这一点有关。甚至当你看YouTube视频的时候,你会去想一段YouTube视频有多长,这个时间的长度会影响到你观影的体会。你看到在Medium这样的媒体当中,它在一篇帖子的一开头就会告诉你,读完这篇帖子大约需要几分钟。它告诉你预计需要消耗这么多时间,这个信息是重要的,因为时间现在成为媒体的表现形式。 这样的变化会造成很多有意思的结果,有的是好的,有的可能不是那么好。它会造成一切东西都被压缩,压缩带来了效率、带来了生产的轻易性,使我们的知识采集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它造成生产者的无穷增多,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现在都有麦克风了,因为媒体的生产者现在可以无限供应;它也造成了那些谣言、误传以及有意传播的假信息,在社会中飞速地流传,让我们完全回归到部落时代的“口传社会”,我们重新部落化了;它也造成一个困惑,如何在140字之内表现思想?这几乎成为一个哲学问题。 没有慷慨就没有互联网 我们接下来可以沿着这个线索思考更多的问题: 当我们的商业和社会沟通以时间为组织原则,对于内容的创造与消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生活流媒体对于个人、组织、政府、媒体和整个社会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 社交媒体引发的时间压缩是增强了知识的宽度还是改变了知识的混合方式?比如我们可以用短内容指向长而深的内容。 这样有意思的问题,大概还可以列出很多。 最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语。第一,Twitter开始的时候有两条路线的挣扎,后来我们发现两条路线是并存的:它既记录你在干什么,同时也记录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所以我们说,对于个人来讲,你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刷你的存在感,但是与此同时,你也要让别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你需要具有分享的情怀,整个互联网都是建立在慷慨的基础之上,没有慷慨就没有互联网。 第二,任何一个好的媒体,应该成为拥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人可以交流的地方,它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空间,不应该是一个一元化的空间。 在过去,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历史由每个人书写。胜利者是谁呢?胜利者无非就是看你是不是拥有最洪亮的声音,是不是最会讲故事,导致你的故事的版本比其他人的故事版本更令人信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这样的媒体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性。 当互联网蓬勃兴起,大众媒体这颗明星如陨石般坠落。 今天如何看待新闻?在众声喧哗的年代,它何去何从? 今天如何看待媒介?是平等对话的空间,还是乌托邦? 数字化研究先驱、2018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大管理思想家”(Thinkers50)雷达榜单入选者 胡泳 | 既站在互联网潮头,又从业于大众媒体,深刻透视数字时代下的媒介与社会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