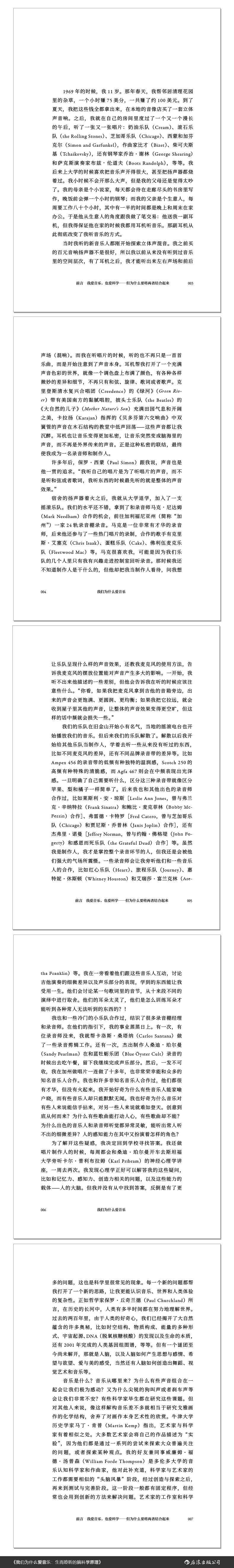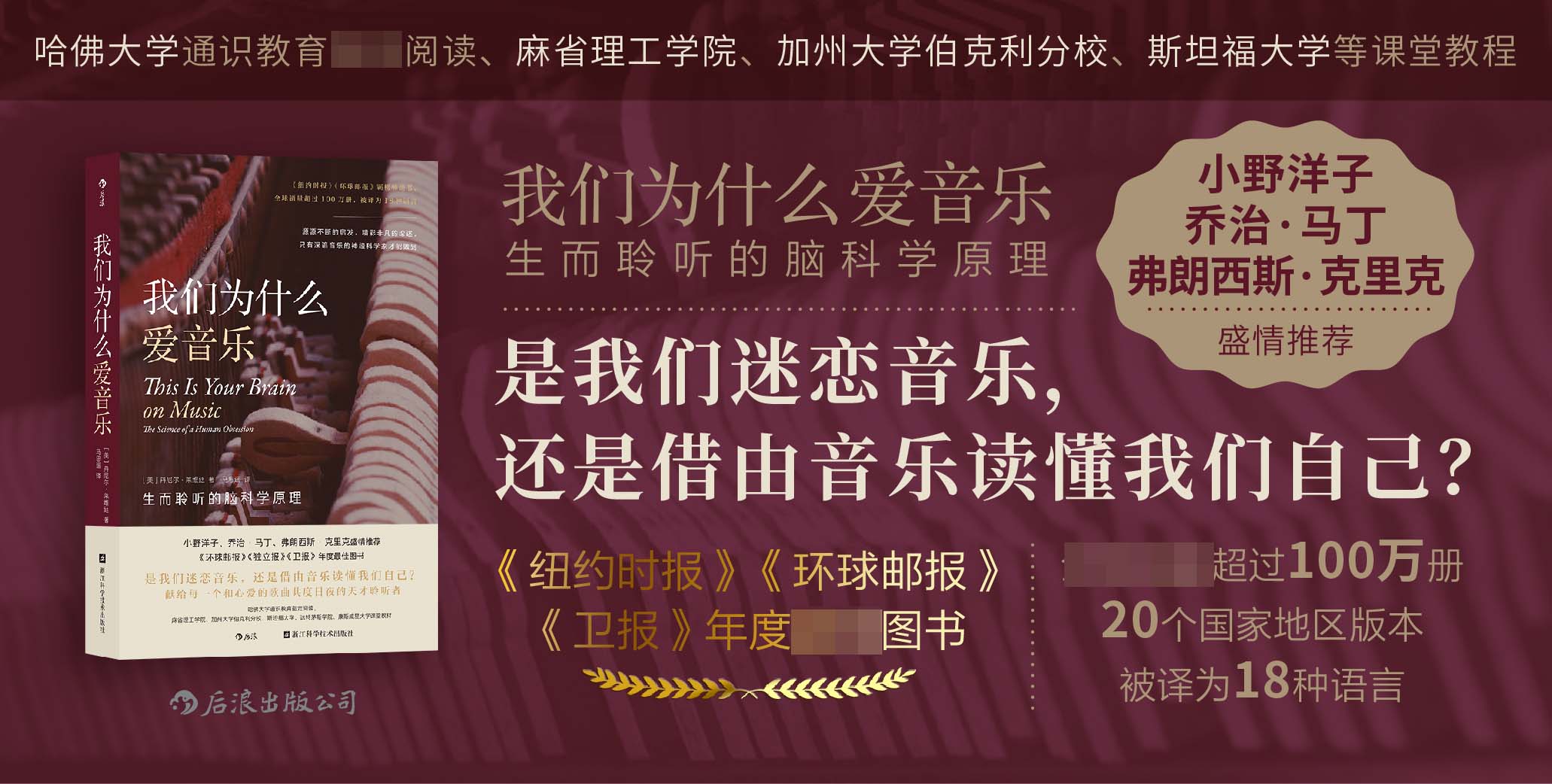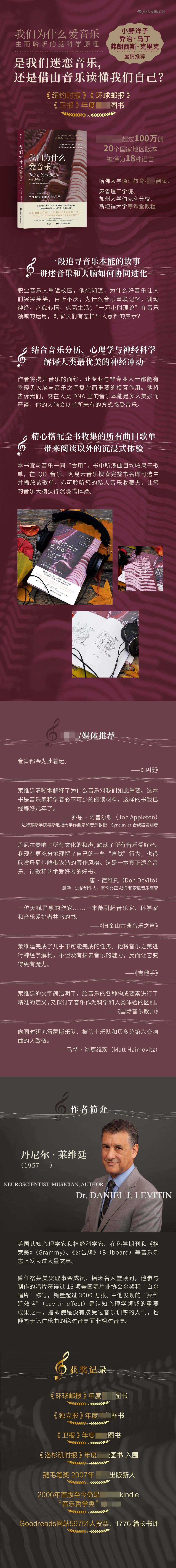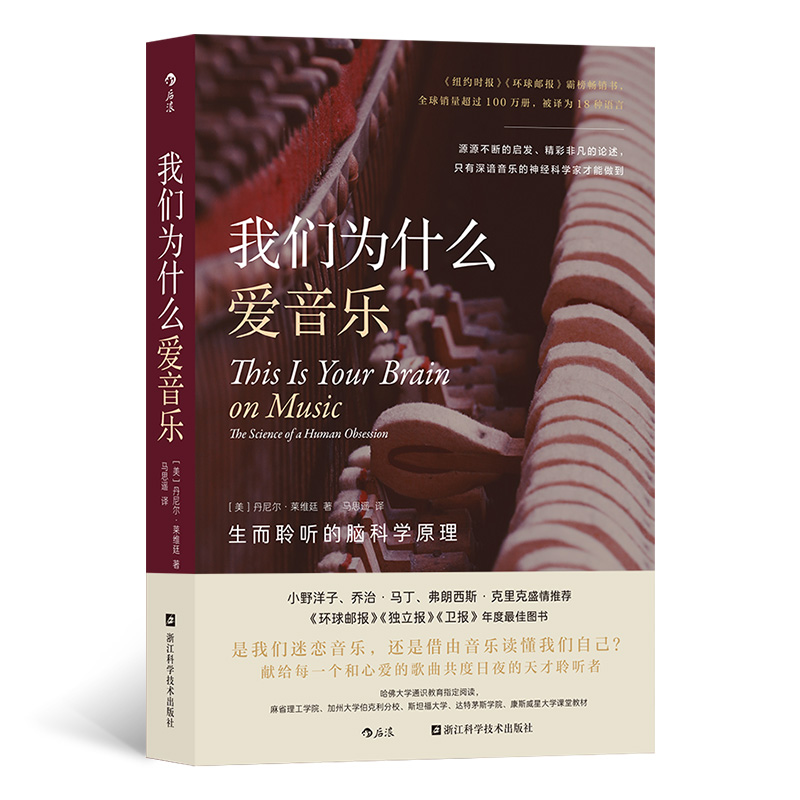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科技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80
折扣购买: 我们为什么爱音乐:生而聆听的脑科学原理
ISBN: 9787573902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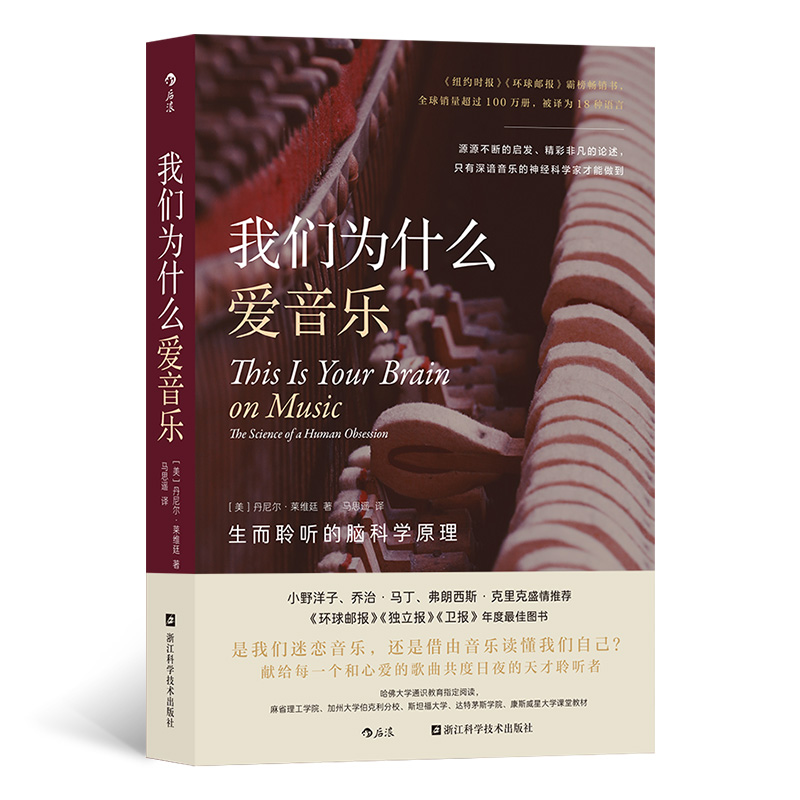
作者 丹尼尔·莱维廷(Daniel J. Levitin,1957—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曾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心理学系、科学史系和音乐系任教。现任麦吉尔大学音乐感知、认知和专业技术实验室主任,电子传播心理学詹姆斯·麦吉尔讲席教授,贝尔讲席教授,在科学期刊和《格莱美》(Grammy)、《公告牌》(Billboard)等音乐杂志上发表过大量文章。 在从事神经科学研究前,莱维廷是一名自由音乐人、录音师和唱片制作人,合作过的知名音乐人有史提夫·汪达、蓝牡蛎乐队等,曾任格莱美奖理事会成员、摇滚名人堂顾问,他参与制作的唱片获得过16项美国唱片业协会金奖和“白金唱片”称号,销量超过3000万张。他还为美国海军、飞利浦电子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提供水下声源分离方面的咨询。 由他发现的“莱维廷效应”(Levitin effect)是认知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指即使是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人们,也倾向于记住乐曲的绝对音高而非相对音高。 译者 马思遥,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琵琶、钢琴演奏者。
前言 我爱音乐,也爱科学——但为什么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1969 年的时候,我11 岁。那年春天,我帮邻居清理花园里的杂草,一个小时赚75 美分,一共赚了约100 美元。到了夏天,我把这些钱全都拿出来,在本地的音像店买了一套立体声音响。之后,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午后,听了一张又一张唱片:奶油乐队(Cream)、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芝加哥乐队(Chicago)、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 and Garfunkel),作曲家比才(Bizet)、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还有钢琴家乔治·谢林(George Shearing)和萨克斯演奏家布兹·伦道夫(Boots Randolph),等等。我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喜欢把音乐声开得很大,甚至把扬声器都烧着过。我小时候不会开那么大声,但是我的父母还是觉得太吵了。我的母亲是个小说家,每天都会待在走廊尽头的书房里写作,晚饭前会弹一个小时的钢琴;而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每周要工作八十个小时,其中有一半的时间都是晚上和周末在家办公。于是他从生意人的角度跟我做了笔交易:他送我一副耳机,但我得保证他在家的时候我都用耳机听音乐。那副耳机从此彻底改变了我听音乐的方式。 当时我听的新音乐人都刚开始探索立体声混音。我之前买的百元音响扬声器不是很好,所以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音乐里的空间层次,有了耳机之后,我才能听出来左右声场和前后声场(混响)。而我在听唱片的时候,听的也不再只是一首首乐曲,而是开始注意到了声音本身。耳机帮我打开了一个充满声音色彩的世界,就像一个调色盘上布满了颜色,有各种各样微妙的差异和细节,不再只有和弦、旋律、歌词或者歌声。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Creedence)的《绿河》(Green River)带有美国南方的黏腻唱腔,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大自然的儿子》(Mother Nature’s Son)充满田园气息和开阔之美,卡拉扬(Karajan)指挥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中双簧管的声音在木石结构的教堂中低声回荡——这些声音都让我沉醉。耳机也让音乐变得更加私密,让音乐突然变成脑海里的声音,而不再是外界传来的声音。正是这种私密的联结,最终使我成为一名录音师和制作人。 许多年后,保罗让乐队呈现什么样的声音效果,还教我麦克风的使用方法,告诉我麦克风的摆放位置能对声音产生多大的影响。一开始,我听不出来他描述的一些差别,但他会告诉我在听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你看,如果我把麦克风拿到吉他的音箱旁边,出来的声音会更饱满、更圆润、更均衡;如果我把它拉远,就会收到屋子里其他的声音,让整体的声音效果变得更空旷,但这样的话中频就会损失一些。” 我们的乐队在旧金山开始小有名气,当地的摇滚电台也开始播放我们的音乐。但后来我们的乐队解散了。解散以后我开始给其他乐队当制作人,学着去听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比如不同麦克风的差异,还有不同品牌录音带的差异等。比如Ampex 456 的录音带的低频有种独特的温润感,Scotch 250 的高频有种特殊的清脆感,而Agfa 467 则会在中频表现出光泽感。一旦明确了自己需要听什么,区分这三种录音带就像区分苹果、梨和橘子一样简单了。后来我也和其他出色的录音师合作过,比如莱斯利·安·琼斯[Leslie Ann Jones,曾与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和鲍比·麦克菲林(Bobby Mc-Ferrin)合作]、弗雷德·卡特罗[Fred Catero,曾与芝加哥乐队(Chicago)和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合作],还有杰弗里·诺曼[Jeffrey Norman,曾与约翰·佛格堤(John Fogerty)和感恩而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合作]等。虽然我是制作人,我才是掌控整个录音环节的人,但我还是会被他们强大的气场所震慑。一些录音师会让我旁听他们和一些音乐人的合作,比如红心乐队(Heart)、旅程乐队(Journey)、惠特妮·休斯顿(Whitney Houston)和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等。我在一旁看着他们跟这些音乐人互动,讨论吉他演奏的细微差异以及声乐部分的表现,学到的东西能让我受用一生。他们会讨论某一句歌词里的音节,从十来段不同的演绎中进行取舍。他们的耳朵太灵了,他们是怎么训练耳朵才能听到各种常人无法听到的东西的?! 我也和一些冷门的小乐队合作过,结识了很多录音棚经理和录音师。在他们的指引下,我的事业蒸蒸日上。有一次,有位录音师没来,我就帮卡洛斯·桑塔纳(Carlos Santana)做了一些录音剪辑工作。还有一次,杰出制作人桑迪·珀尔曼(Sandy Pearlman)在和蓝牡蛎乐团录音的时候出去吃午餐,留下我继续完成声乐部分。然后,一发不可收,我在加州做唱片一连做了十多年,也非常荣幸能和众多的知名音乐人合作。我也和许多非知名音乐人合作过,他们都很有才华,但没有火起来。我开始好奇为什么有些音乐人能家喻户晓,而有些音乐人却只能默默无闻。我也好奇为什么音乐对有些人来说能信手拈来,对另一些人来说就难如登天。创意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歌曲能打动人心,有些歌曲却不能?为什么出色的音乐人和录音师听觉都异常灵敏,能听出常人听不出的细微差异?人的感知能力在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为了解开这些疑惑,我决定回到学校寻找答案。我还做唱片制作人的时候,每周都会和桑迪·珀尔曼开车去斯坦福大学旁听卡尔·普利布拉姆(Karl Pribram)的神经心理学讲座,一周去两次。我发现心理学正好可以解答我的这些疑问,比如和记忆力、感知力、创造力相关的问题,以及这些能力的载体——人的大脑。但我并没有从中找到答案,反倒是有了更多的问题,这也是科学里很常见的现象。每一个新的问题都帮我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让我更能认识音乐、世界和人类体验的复杂性。正如哲学家保罗·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所言,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有多半时间都在努力地理解世界。过去的两百年里,由于人类的好奇心,我们已经揭开了大自然蕴含的许多奥秘,比如时空结构、物质构成、能量的多种形式、宇宙起源、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以及生命的本质,还有2001 年完成的人类基因组图谱,等等。但有一个谜团至今尚未解开,那就是人脑,以及人脑如何产生思想与感情、希望与欲望、爱与美的感受,当然还有人脑如何创造出舞蹈、视觉艺术和音乐等。 音乐是什么?音乐从哪里来?为什么有些声音组合在一起会让我们极为感动?又为什么尖锐的狗叫声或者刹车声等会让我们非常不安?有些科学家毕生都在研究这些课题。但对其他人来说,像这样解构音乐差不多就相当于研究戈雅画作的化学结构,舍弃了对画作本身艺术性的欣赏。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马丁· 肯普(Martin Kemp) 指出, 艺术家与科学家有着相似之处。大多数艺术家会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实验”,因为他们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尝试来探索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或者探索某种观点。我的好友兼同事威廉姆· 福德· 汤普森(William Forde Thompson) 是多伦多大学的音乐认知科学家和作曲家,他对此补充道,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工作都需要相似的“头脑风暴”阶段,经过创造与探索之后,再来到测试与完善阶段。这一阶段一般都有固定程序,但经常也会用到创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艺术家的工作室和科学家的实验室也有相似之处,比如里面都会同时存在大量正在进行的项目,每个项目的进展各不相同,而且工作室和实验室都需要配备专业设备。但实验的最后并不会得到像吊桥建造方案或者银行资金结算一样的结论性内容,而是会给出开放性的结果供大家自行解读,所以也就需要艺术家和科学家具备一种共同的能力——接受自己实验的结果供大家诠释与再诠释。这两种实验归根结底都是对真理的追求,但艺术家和科学家都明白真理的本质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而且真理取决于每个人的观察角度。今天的真理在明天可能就会变成谬误或者被人遗忘。皮亚杰、弗洛伊德和斯金纳的例子都能够说明,曾经风靡一时的理论也会让后人推翻(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论的正确性大打折扣)。在音乐方面,有些乐队早早地就得到了足以流芳百世的赞誉,后来却销声匿迹:廉价把戏乐队(Cheap Trick)曾被誉为新一代的披头士,滚石出版的《摇滚百科全书》(Rolling Stone Encyclopedia of Rock& Roll) 曾经给亚当与蚂蚁乐队(Adam and the Ants) 留足了笔墨,在版面上甚至与当年的U2 不相上下。曾经有段时间, 人们根本无法想象以后会有一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保罗· 史图基(Paul Stookey), 也不知道克里斯多夫· 克罗斯(Christopher Cross) 或者玛丽· 福特(Mary Ford)。对于艺术家来说,绘画或音乐作品并不是为了反映不折不扣的事实,而是为了表达普遍的真理,即使环境、社会和文化都发生改变,成功的作品依然能够继续触动人心。科学家们研究理论则是为了“当下的真理”,是为了推翻旧真理,而当下的新真理有一天也会被更新的“真理”取代,而这就是科学进步的方式。 音乐历史悠久,而且无处不在,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有史以来,任何一种人类文化都有音乐的存在。在原始人类文明的发掘地点,最古老的一批文物里有些就是乐器,比如骨笛和用树枝撑起动物皮鼓等。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原因,只要是有人类聚集的地方,就有音乐。无论是婚礼还是葬礼,无论是毕业还是从军,抑或体育赛事、小镇之夜、祈祷求福、浪漫晚餐、母亲哄宝宝入睡、大学生一起学习等,都会有音乐的陪伴。与现代西方社会相比,非工业文化中的音乐甚至更加丰富。从过去到现在,音乐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最近五百年左右,我们的社会中才出现了音乐表演者和音乐聆听者两种不同的角色分工。纵观世界各地和人类历史,音乐创作就像呼吸和走路一样自然,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而像音乐厅这样专门用于音乐表演的场所,直到近几百年才刚刚出现。 吉姆·弗格森(Jim Ferguson)是我从高中时候就认识的朋友,他现在是一名人类学教授,也是我认识的最幽默、最聪明的人。但他性格腼腆,我都想象不出这么腼腆的他是怎么讲课的。他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去被南非包围的“国中国”莱索托进行了实地考察。吉姆在当地做研究,和村民交流,逐渐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后来有一天,村民们邀请他来一起唱歌。听到当地索托人的邀请,吉姆像往常一样柔声答道:“我不会唱歌。”这么说确实没错,高中时候我们一起组乐队,他双簧管吹得很好,唱歌却有点走调。村民们听到他这么说十分惊讶,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在他们眼里,唱歌就是一种普通的日常活动,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会唱歌,唱歌并不是某些人专属的活动。 在我们的文化, 甚至我们的语言中, 我们会单独把亚瑟· 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艾拉· 费兹杰拉(EllaFitzgerald)、保罗·麦卡特尼( Paul McCartney)这样的人归为专业的音乐表演者,其他人则单纯就是听众。听众会付钱去欣赏专业音乐家的表演。吉姆觉得自己唱歌跳舞不是很在行,对他来说,在别人面前唱歌跳舞就像在告诉大家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一样。但村民们盯着吉姆,问他:“你说你不会唱歌是什么意思?!可是你会说话啊!”后来吉姆跟我说:“他们觉得很奇怪,就像我明明两条腿都很健全,却告诉他们我不会走路或者不会跳舞一样。”唱歌和跳舞是索托人生活里非常自然的行为,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大家也可以天衣无缝地合作。在塞索托语里,表示“唱歌”的动词(ho bina)同样表示“跳舞”,这种表达方法在其他很多语言里也都有体现,因为唱歌本身就包含身体的律动。 在几代人以前,电视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很多家庭都会坐在一起玩音乐,自娱自乐。而现在人们则非常重视技术与技巧,会判断某位音乐家是否达到了为他人演奏的“标准”。在我们的文化中,玩音乐已经成了一件较为专业的活动,其他非专业人士只负责听。音乐产业是美国最大的产业之一,从业人员高达数十万人。以2005 年为例,美国的专辑销售额可达三百亿美元,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演唱会门票、每周五北美各地乐队在酒吧的演出,以及三百亿首通过点对点文件共享免费下载的歌曲。美国人花在音乐上的钱比花在性和处方药上的钱还多。既然消费额如此巨大,那我可以说大多数美国人都有资格成为专业的音乐听众,能听出错音、找到喜欢的音乐、记住数百段旋律,也能随着音乐用脚打拍子。单是打拍子就涉及非常复杂的节奏判断过程,这种复杂程度大多数计算机都无法完成。所以,我们为什么听音乐?我们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听音乐?两张音乐会门票的价格完全抵得上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一张CD 的价格大概相当于一件衣服、八个面包或者一个月的电话费。所以,我们为什么喜欢音乐?是什么吸引着我们去喜欢音乐?了解这两个问题,就相当于开启了我们了解人性本质的一扇窗。 问及人类普遍而基本的能力,就相当于间接问及进化(演化)方面的问题。动物为了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会进化出相应的身体结构,其中在求偶方面有优势的特征会通过基因遗传给下一代。 达尔文的理论中有一点非常高明:无论是植物、病毒还是动物,活的有机体都与外部世界协同进化。换言之,在所有的生物随着外部世界进化的同时,外部世界也会随着生物的进化而进化。如果某个物种发展出了某种防御机制来躲避捕食者,那么为了应对生存压力,捕食者也会进化出破解这种防御机制的结构或方或另寻其他的食物来源。自然选择可以说是一场生理形态上的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 当前出现了一个相对较新的科学领域,叫“进化心理学(演化心理学)”,这门学科将进化理论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心理学范畴。我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认知心理学家罗杰· 谢泼德(Roger Shepard) 指出, 我们的身体和思维都是进化了数百万年的产物。我们的思维模式、解决问题时习惯选用的方法和感知系统都是由进化产生的,比如我们能够看到颜色(并且能够识别特定的颜色)等。谢泼德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思维与自然世界的进化是同步的,是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谢泼德有三名学生都是这一领域的前沿人物: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John Tooby),以及新墨西哥大学的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该领域的研究人员认为,通过研究思维的进化,我们可以了解更多人类行为方面的知识。那么在人类进化和发展的过程中,音乐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当然,五万或十万年前的音乐和后来的古典乐、摇滚乐、说唱音乐肯定大不相同。随着大脑的进化,我们创造出来的音乐和我们想要听到的音乐也在随之进化。那么,我们的大脑中会有特定的区域和路径专门为了做音乐或者听音乐发生变化吗? 过去人们简单地认为,大脑右半球负责处理音乐与艺术,大脑左半球负责处理语言和数学。但现在,我和同事的研究结果显示,处理音乐的区域遍布大脑的各个部位。通过研究脑损伤患者,我们发现,有些患者虽然丧失了阅读报纸的能力,但他们仍然能够读懂乐谱;有些人无法协调地系上扣子,但他们仍然能够演奏钢琴。聆听音乐、音乐表演和创作乐曲几乎涉及我们迄今为止所知的每个大脑区域,也几乎涉及每一个神经子系统。那么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说听音乐能够锻炼我们的其他思维吗?每天听二十分钟莫扎特的音乐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吗? 音乐能够调动人的情绪,广告商、电影工作者、军队指挥官和母亲都能够熟练运用这一点。广告商用音乐让自己的饮料、啤酒、跑鞋或者汽车看起来强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电影工作者用音乐让观众明确感受到画面想要表达的情绪,或者在特别戏剧化的情节中加强观众的感受。可以试想一个动作片中经典的追逐场景,或者女主角孤身一人在漆黑的老宅子里爬楼梯的场景。这些场景都会用音乐来影响我们的情绪,虽然这些音乐不一定会带给我们快乐,但我们会接受音乐的力量,也乐于让音乐带给我们不同的体验。早在我们无法想象的远古时代,全世界的母亲就都已开始用轻柔的歌声哄孩子入睡,或者在孩子哭的时候用歌声帮他们转移注意力。 很多音乐爱好者都说自己对音乐一无所知。我有很多同事研究非常复杂的课题,比如神经化学或者精神药理学等,可是我发现他们对音乐神经科学的研究却束手无策。但怎么能怪他们呢,因为音乐理论家有自己的一套神秘莫测的术语和规则,就像数学里最深奥的领域一样晦涩难懂。在外行人看来,纸上那些墨水的印记跟数学集合论的符号差不多,但内行人却管它叫“乐谱”。谈到音调、节拍、转调和移调,则更容易让人一头雾水。 虽然我的每一位同事都会被这些术语吓倒,但是他们都能跟我说出自己喜欢的音乐。我的朋友诺曼·怀特(Norman White)是一位世界级的权威人物,他主要研究鼠类的海马体以及鼠类如何记住自己去过的不同地点。他还是个爵士迷,对自己喜欢的爵士乐手如数家珍,能凭声音区分出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和贝西伯爵(Count Basie)两位爵士乐手,甚至能听出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早晚期的区别。可是诺曼在技术层面却对音乐一无所知,他能说出自己喜欢哪首歌,却说不出和弦的名字,不过他非常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诺曼当然不是个例,我们很多人都通过日常实践对自己喜爱的事物有所了解,我们不需要真正的专业理论知识就能表达自己的喜好。比如说,如果要买巧克力蛋糕的话,我会选择去自己经常光顾的那个餐馆,我不是很喜欢我家附近的咖啡馆卖的蛋糕。只有厨师才能对蛋糕进行专业的分析,将味觉上的体验拆分成各个元素,描述出口味、起酥油或者巧克力的区别。 很多人都被音乐家、音乐理论家或认知科学家的术语吓倒了,真的很可惜。其实每个研究领域都有专门的术语(试试自己能不能完全理解医生给出的血液分析报告),但就音乐而言,音乐领域的专家和科学家可以再努力一点,让大家更了解他们的工作,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现在不仅是音乐表演与音乐欣赏之间本不该有的鸿沟在不断扩大,那些热爱音乐(也喜欢聊音乐)的人和研究音乐原理的人之间的鸿沟也已经迎头赶上了。 我的学生经常跟我倾诉,说自己热爱生活,也热爱生活中的种种奥秘,但他们担心懂的东西太多会剥夺生活中很多简单的乐趣。罗伯特·萨波斯(Robert Sapolsky)的学生可能跟他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我自己在1979 年搬到波士顿读伯克利音乐学院(Berkee College of Music)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焦虑。如果我用学术的方法来研究音乐,在分析音乐的过程中揭开了音乐的神秘面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一旦我对音乐了如指掌,我从音乐中无法获得乐趣了,又该怎么办?然而我仍然非常享受音乐,跟曾经戴着耳机听廉价高保真录音带的我别无二致。我对音乐和科学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它们迷人,也越欣赏真正擅长这两个领域的人。多年实践经验证明,音乐和科学一样是一种探险,每次都会有不同的体验,这种探险会源源不断地带给我惊喜和满足。最终结果就是,我发现科学和音乐的融合其实还不错呢。 这本书打算从认知神经科学(一门结合了心理学和神经学的学科)的角度谈谈音乐的科学。我会在书中提到我和其他研究人员的一些最新研究,内容包括音乐、音乐的意义和音乐带给人的乐趣等。这些研究为一些深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比如,如果我们听到的音乐都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有些作品能够打动那么多人,比如韩德尔(Handel)的《弥赛亚》(Messiah)或者唐·麦克莱恩(Don McLean)的《文森特》[Vincent(Starry Starry Night)]?而反过来,如果我们听到的音乐是一样的,那又该如何解释每个人对音乐的偏好大不相同?为什么有的人喜欢莫扎特,有的人喜欢麦当娜? 最近几年,神经科学突飞猛进,心理学也探索出了新方法,包括新的大脑成像技术、能够影响多巴胺(dopamine)和血清素(serotonin) 等神经递质分泌的药物,再加上朴素的科学追求,人们的思维也随之开启。但有一项进展并不太为人所知,那就是我们在神经元网络建模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持续发展,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理解我们头脑中的计算系统。语言现在看起来其实像是大脑中的硬件连接起来的,甚至意识本身也不再是团团迷雾,而是在大脑实体中呈现出来的东西。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所有这些新的研究结合起来,并用结合起来的成果解释人类最痴迷也是最美丽的事物——音乐。了解大脑对音乐的反应是通往人类本质最深层奥秘的一条道路,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因为这本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而非面向内行人士,所以我会尽量简化主题,但不会让内容过于简单。书中提到的所有研究都已经过同行评议,并已在业界认可的期刊中刊登。详细资料请见本书末尾的参考文献。 一旦进一步理解了音乐是什么以及音乐从哪里来,我们也许就能够进一步理解自己的动机、恐惧、欲望、记忆,甚至广义上的交流。听音乐给人的感觉跟其他哪种感觉更相似?是像饿的时候吃饭一样满足需求?还是像看到美丽的夕阳或者做背部按摩一样触发大脑中的感官愉悦系统?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听音乐的品味似乎固定了,不愿再去尝试新的音乐?这就牵涉到了大脑和音乐如何协同进化的问题——音乐可以教我们如何认识大脑,大脑可以教我们如何理解音乐,而音乐和大脑的结合又会教我们如何更加了解自己。 《纽约时报》《环球邮报》霸榜畅销书, 全球销量超过100万册,被译为18种语言 源源不断的启发、精彩非凡的论述, 只有深谙音乐的神经科学家才能做到 ○ 一段追寻音乐本能的故事,讲述音乐和大脑如何协同进化 一名前途无限的职业音乐人,凭借对人类音乐痴迷的强烈好奇心重返校园,在认知科学领域取得突破。他想知道,为什么好音乐让人们哭哭笑笑,百听不厌;为什么音乐串联记忆,调动神经,疗愈心情,点亮生活;“一万小时理论”在音乐领域的运用,对家长们有怎样出人意料的启示? 音乐在人类史上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进步,答案开始变得清晰。 ○ 结合音乐分析、心理学与神经科学,解译人类最优美的神经冲动 如果音乐是文化的声音,那么莱维廷既是了解音乐的学者,也是研究文化的科学家。莱维廷的书揭开了音乐的面纱,让专业与非专业人士都能有幸窥见大脑与音乐之间复杂而重要的相互作用……这本书就像一块瑰宝,蕴藏着解读音乐的独特文字。 他将告诉我们,刻在人类DNA里的音乐本能是多么美妙而严谨。在读过莱维廷的作品之后,你的大脑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感受音乐。 ○ 是我们迷恋音乐,还是借由音乐读懂我们自己? 本书宜与音乐一同“食用”,书中所涉曲目均收录于歌单,在QQ音乐、网易云音乐搜索完整书名即可选中并播放该歌单,亦可聆听您的私人音乐收藏夹,让您的音乐大脑获得沉浸式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