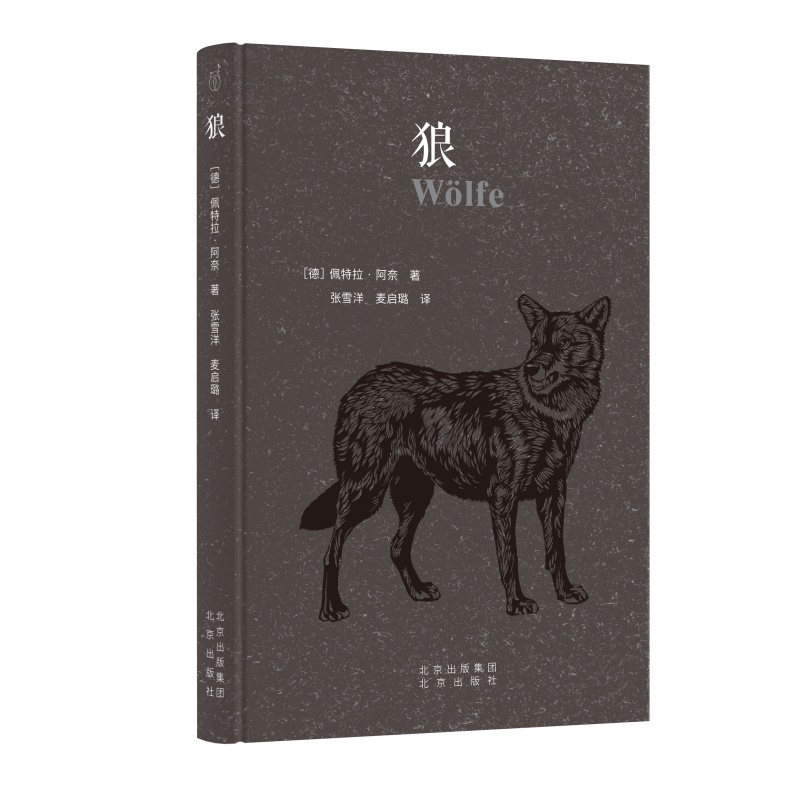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5.29
折扣购买: 动物肖像 狼(精)
ISBN: 9787200136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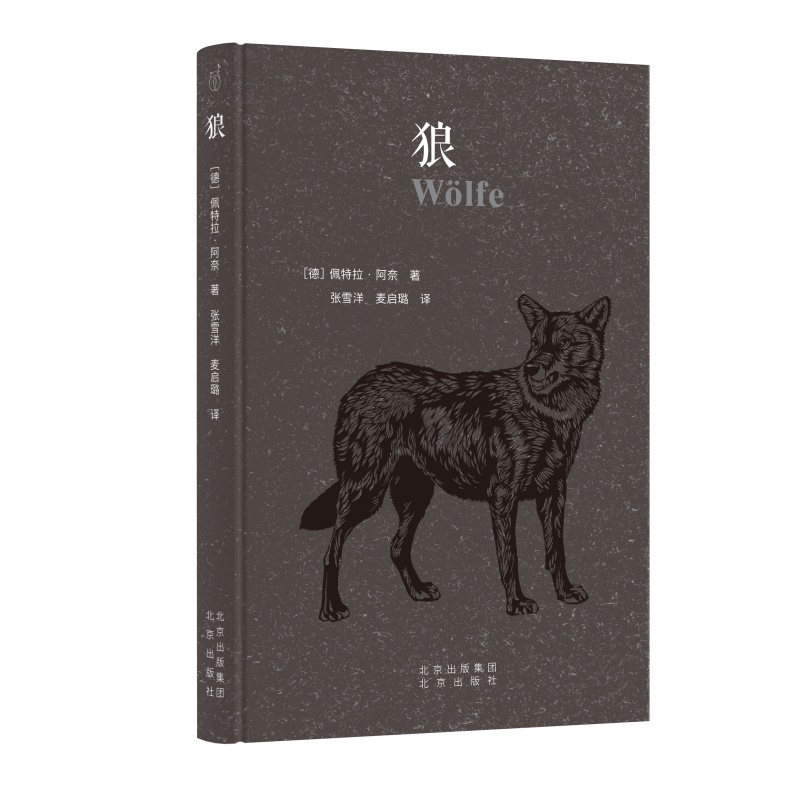
作者:佩特拉·阿奈(Petra Ahne),1971年生于慕尼黑,曾在柏林和伦敦学习比较文学、艺术史和新闻学,现任《柏林日报》编辑。 译者:张雪洋,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就职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德文化、科技与医学交流。 麦启璐,毕业于德国耶拿大学,现就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狗和狼是相爱相杀的一对:在文学上、科学上、犬类驯养上以及意识形态上它们一直而且以后也将一直携手出现。狗是一种游走在边缘的生物:它在人类走向定居生活、建立文明的道路上一直相伴而行,在此过程中它们又恰好被派作猎犬或看家狗,负责守卫在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界限上。在同一种动物身上总是有不同的特质出现—就看是从希望还是威胁的前景来看了。 如果狗和狼在一起,首先会出现什么呢?这两种动物可以通婚并产下后代,这是人们很久之前已经知道了的,16世纪时,康拉德·格斯纳在其《动物史》中可以说充满柔情地写道:“狗和狼有时也会进行交配……这样会生出非常勇敢又漂亮的小狗。” 杰克·伦敦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野性的呼唤》出版几年以后他写了一只这样勇敢的狗,小说英文名为《白牙》(White Fang),德语名字叫《狼之血》(Wolfs blut)。创作部小说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想法,他在这本小说里重复了他的成名作,只是这个故事是掉转过来的:小说的主人公“狼血”是一只公狼和一只母狼狗混种的孩子,它在爱的感化下从一只野性难驯的动物最终变得温柔和顺。当这只在严寒的阿拉斯加荒野出生的幼狼被印第安人捕捉到以后,它开始了它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它需要用到继承自它混血母亲那与生俱来的狗性。自然和文化的边界在这里又开始了摇摆:不久,它自身的天性被打败了,它必须尊人类为“神”,即使之前拥有“狼血”的那个人就是个暴君。主人公成为了一只让人惧怕的斗犬,这让它的主人挣了很多钱,直到在一个极其引起怜悯的情节下,一个充满爱心的新主人出现了,“狼血”有一种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那是全心全意的爱,而不是单纯的服从。 小说的最后一幕是人和兽处在安宁祥和的图景中:“狼血”尚未从一场战斗的伤患中恢复过来—在这场战斗中,它救了它主人的父亲。它在现在居住的农场花园中注视它的幼狼们玩耍。狼狗的野性与文明得以和谐统一,因为它完完全全在为人类提供服务—从这个意义上它却又随时可以被激活。这是完美的人狗关系。当杰克·伦敦的小说在德国发行时,在很多人家书架上还放着一套沉重的多卷册书籍,这套书跟杰克·伦敦的书一样表面上并不是以人为中心,但其核心又确实是人本主义的,而且还以自然科学家的名义发声。直到今天,在阿尔弗雷德·爱德蒙·布雷姆的《动物生活》问世150年后,这本书还散发着叙述的魅力,而人们越是细究这深棕色的、密密麻麻排满了德文尖角体文字的书页,他们就越能明白,为什么布雷姆在生前就被尊称为“动物之父”:在这里说话的是一名大家长,他用权威的姿态批评着好的或坏的家庭成员。 狼位于这本书第一卷的末尾,布雷姆为这种食肉动物写了19页纸,众望所归地,它被归到了坏动物的一边,这仅从视觉上就能判断出来:它们有着“高大而瘦削的狗的样子”,它的腿简直就是“骨瘦如柴”。布雷姆极其钟爱的狗是其参考系。然而狼是“有害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极其卑鄙”,它们和狗却又明白无误是沾亲带故的—至于两者关系有多紧密,那时人们还不清楚。为了走出这两难的境地,布雷姆采取了跟杰克·伦敦一样的处理方式。他在两种动物之间划定了一条灵活的边界线,把一些好的,在布雷姆眼中就是那些像狗的特点,从狗推导到狼身上:“狼拥有狗的所有天赋和特点:同样的力量和耐力,同样的感官敏锐和同样的理解能力。但与狗相比,狼更加片面,而且看起来远不如狗高贵,毫无疑问,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没经过人的调教。”在一定程度上狼被要求合理使用它们所拥有的智力,也就是说,它们要理解到,人类拥有更多的智慧。布雷姆在叙述中承认,“狗也是肉食性动物,它也习惯于征服其他生物,但即便如此,出于相当理智的原因,它们的理解力让它们非常愿意选择臣服于更高级的人类精神”。“把自己交给人类”是值得的,这是前提。 那些布雷姆引用的,关于家养狼的报告,毕竟是足以让狼拯救自己的荣誉的:“狼是可以被教化的,也可以被驯养,也就是说,跟没有偏见的人相处并非是不体面的。谁要是跟它相互理解,就可以从狼身上塑造出一种和家犬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动物。”对狼而言,还有希望。这种希望来自于成为一条狗。在布雷姆接下来描述的很多狗的品种当中,能感觉到对他而言,牧羊犬是一个榜样。他引用自然学者阿道夫·穆勒1872年在杂志《园圃小屋》里的说法并对其表示赞同:“如果一种狗因其人性获益,就是说得到承认和爱的感觉,那这种狗一定是聪明、忠诚、警觉又不知疲倦的牧羊犬。”牧羊犬不是一个统一的品种,许多不同大小和种类的狗都能归入这个实用犬类别,人们通常能在农场里找到它们。 狗和狼的相似性在布雷姆看来是明显的—这句话的真正意义却直到1899年年轻的骑兵上尉马克斯·冯·史蒂芬尼茨建立德国牧羊犬俱乐部才得以显现。他认为他的狗霍兰德·冯·格拉夫斯、玛丽·冯·格拉夫斯和施瓦本玛德勒·冯·格拉夫斯属于一个新的犬种。在俱乐部成立两年之后,冯·史蒂芬尼茨出版了厚厚的一本名为《图文解说德国牧羊犬》的著作,书中详细介绍了一种思潮,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牧羊犬在20世纪初会在定义民族和国家身份中发挥作用,这种关联很对纳粹的胃口。狼在这本著作中多次作为参考物出现,并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牧羊犬的正面形象:“狼显示了……我们牧羊犬有力修长的身材。它的背部线条优异,四肢弯曲程度……卓越无比。” 纳粹分子对德国牧羊犬异常钟爱,这得益于冯·史蒂芬尼茨在他的著作中把它视为一种展现法西斯国家的理想型动物—它们如此忠诚而具有奉献精神,就像社会对个人的要求那样。另外还有骁勇善战—在那些对纳粹事业费尽心力,野心勃勃而喜好战争的人看起来,他们和狼是如此相近:“就像狼冲进了羊圈,我们来了!”约瑟夫·戈培尔在约1928年的《人民观察家报》中这么写道。狼英雄般的,也就是社会上所说的那种好战的形象从此就被维护起来了,纳粹在德国牧羊犬身上明显地看到了这种特质。阿道夫·希特勒在早期的写作中使用的笔名就是“狼先生”,他给自己第一条德国牧羊犬起名叫狼,而在掩体里陪他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两条牧羊犬之一也叫这个名字。 如果不考虑外观,马克思·冯·史蒂芬尼茨也在致力于区分狼和德国牧羊犬。不能过分渲染狼这种“凶悍的食肉动物”的性格,而且他警告说,不能无底线地尝试通过杂交使更多的狼变成狗。而狼和牧羊犬的混种是“胡说八道”,他在书里放了一张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想象图。“这个头的构造不漂亮,给人不高贵的、在暗中窥伺的感觉。在这个情境中,这种外表也代表了本质。”这种“杂种”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表现在狼和德国牧羊犬的例子中就是“不可靠、本性不稳定、畏缩不前、阴险狡诈”。 关于这种混种性格特征的独到见解,冯·史蒂芬尼茨的解读绝对是有道理的。在20世纪30年代,萨尔路斯猎狼犬的饲养员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种犬是德国牧羊犬和雌狼杂交所得。这种犬没有长成想象中温顺、可靠的工作犬,相反它们变得羞怯。即便如此,萨尔路斯猎狼犬还是被繁育下去了,与此相同的还有捷克狼犬。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承认,这种德国牧羊犬和在喀尔巴阡山的狼杂交的品种其实并不是希冀中好斗的圈地犬,而是内向的,遇事会迅速逃跑的犬种,数年之后,这种犬种的粉丝又使得它的繁育重新兴盛起来。 当科学家们开始自问到底该如何区分狼和狗的时候,人类还培育了一个犬种—人们看这狗一眼便会觉得震惊。20世纪60年代,在基尔宠物研究所里,两只年幼的大型贵宾犬被送入一个母狼的狼圈里。其中一只不幸被母狼咬死了,而另一只却成为了母狼的伴侣。9周之后能是世界上第一只贵宾犬狼(Puwo)出生了。正如科学家们自负相信的那样,狼和大型贵宾犬的杂交品种恰好就是漫画里疯狂的宠物狗理发师剪出来的模样。实际上大型贵宾犬可以,却不是必须去理毛的,一定的蓬乱随意感让它光彩照人,它没有什么特定的特征,全面发展,从比例上来说跟狼也不无相似。埃里克·茨曼在博士阶段被委托研究贵宾犬狼,他自己似乎对其导师沃尔夫·黑尔为何偏偏选择大型贵宾犬作为研究对象感到惊讶,黑尔曾借助测量狗、狼、亚洲胡狼以及郊狼脑的重量证明所有犬种都起源于狼。或许这仅仅是黑尔的个人趣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还曾用大型贵宾犬做过其他的繁育试验。 茨曼需要找出狼和狗的行为有何区别以及这种区别是如何遗传到后代去的。1967年他和妻子带着15条幼狼搬到基尔以南一片森林中,在一座空置的守林人小屋里,他们给第一、二代幼狼、贵宾犬和贵宾犬狼盖起了许多狗舍。不久之后,茨曼发现,他们的计划比想象中更有野心,这最集中体现在第二代贵宾犬和狼的混血中。在它们身上能非常明显地看到,区分幼狼和幼犬的特征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延续下去:幼狼身上面对人类想要逃离的欲望本是它们为了生存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一点很明显遗传下去了。但狗身上对人的亲近与爱慕在隔代的孩子里又显现出来,只是兽与兽之间有些不同。茨曼这样看待这种相当复杂的性格特征:幼狼是既羞怯又亲近人类的,它相当温顺,却不再对人类产生兴趣。为了得到所有行为的组合和分级,茨曼不仅要观察4只贵宾犬狼二代的混血幼兽,其他的11只动物也要每3小时喂养一次。他认为,在研究它们的混血后代以前,人们必须先对狼和狗进行基础性研究。于是他把贵宾犬狼都送回了基尔。 茨曼跟贵宾犬和狼在树林里继续生活了两年,并发表了一个扎根于科学基础,关于野生和驯化动物至今还非常具有争议性的理论。他的中心思想在于:狗是狼的低配版,它们为了玩乐而存在。它们本质上做着一样的事情,只是狗有的时候似乎已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了。有一个无意中出现却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有一次,当一只狼和一只贵宾犬扑向一只活鸡的时候—其实茨曼是想用这只鸡做另一个实验的—人工饲养的狼杀死了鸡并撕咬起来,贵宾犬把鸡拖来拖去,却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许多犬种已经不能打猎了,狗寻找着狼只有在幼狼时期才会寻觅的社交亲密度,狗的表情和肢体语言都没有狼这么明确和强烈了,狗的发情期也更加频繁,茨曼把这些现象归结为狗作为一只宠物的“适应性”。狗已经戒掉了许多人类不再需要它们拥有的习性,因为它们能从人那里得到食物。人们也能允许它们一年产两次崽,而不是像狼那样,一年只能生一次。 茨曼通过对驯化的理性解释,致力于打破以往实验中的规则限制,那些实验服务于一种可疑的文明批判。在他的著作《狗:起源、行为、人与狗》里他总结了自己对狗和狼的研究的成果,他在书中引用了他的同事和榜样康拉德·洛伦兹的一篇文章,对此他只是简单地说明是这位行为学研究者“1940年的老文章”。而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根据他的想法,进行了过度文明化的大城市居民和高度驯化的宠物之间的比较,并发出“人类……由于面对驯化下的衰亡征兆没有选择……终将灭亡”的感叹。当然为了阻止这件事,“我们政体里的种族思考”至少已经“承担了……非常多”2,这本80页的《由驯化引起的某种行为障碍》是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最有政治意味的文章之一,其纳粹思想在其中表露无遗。茨曼所引用的部分是关于想象的“过度”,也就是对于家养动物一些特定行为方式的过度强调,对于另一些行为则完全消失,这一部分内容看起来还是比较客观的。 狗一定程度上是狼的低配版,它们把自己改造成更适合人类生活的样子—奥地利的狼科学中心(WSC)也持有这样的看法,这个研究中心在茨曼的狼狗同居实验后将近五十年再次进行这项工作。在维也纳周边的一个森林里,目之所及有着从头到尾大约三千年的驯养史,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相互之间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在通往科学中心小路右边的驯养区里居住着5只狼,左边则是一对狗。在它们的圈养区那巨大的林地以外发生了什么,除非有员工现身,否则它们并不关心。而当有员工出现时,它们的表现在人类的范畴里会这样表述:一边是有着从容镇定的好奇心,而另一边上蹿下跳表现得很激动以博取注意力。此时狼会无声地潜行到篱笆处,等待着,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来访者;而狗则在围栏处上蹿下跳,吠叫不止,摇着尾巴,表现出一种焦急。此时,人们只会想起库尔特·图霍夫斯基和他一针见血充满讽刺的作品《关于狗的论文》:“狗最讨厌狼了,因为狼会让它想起自己的背叛,想起自己已经委身于人类。” 这本《狼》是由德国引进的“动物肖像”系列中的一本,原版书系曾获德国最美图书奖。这套书是各种动物的文化史,从动物的角度,深刻剖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所谓人类的历史即动物进入人类生活的历史。《狼》以人类对狼的认识和与狼的关系为叙述主题,视角新颖,既普及生物学知识,又讲述这种动物的文化故事,解读狼的形象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与有趣的故事。书中有大量精美的图片,包括珍贵画作、手绘、老照片等。这本中译本复刻了德文原版的精美装帧,给阅读带来更加全方位的预约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