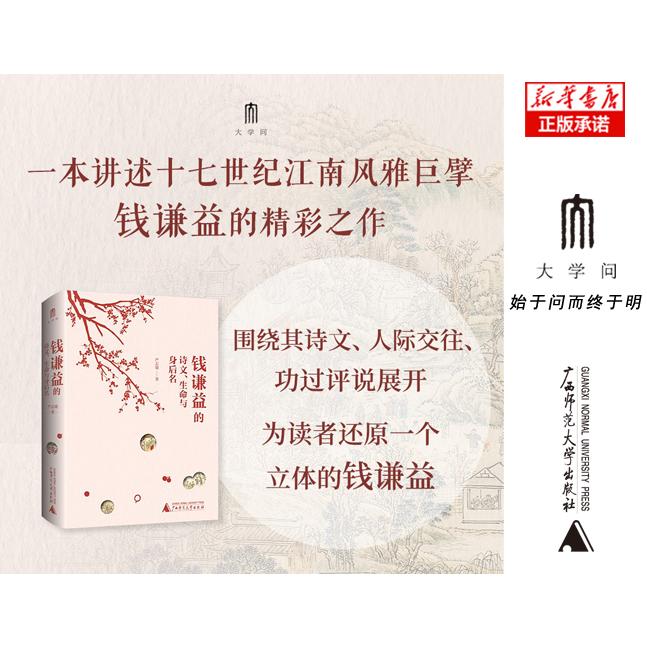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58.80
折扣购买: 钱谦益的诗文、生命与身后名
ISBN: 9787559871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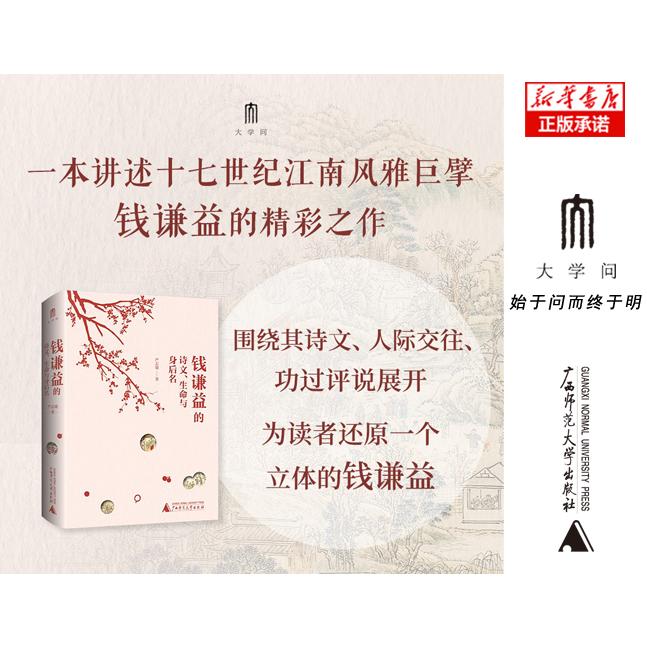
严志雄(Lawrence Yim),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合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文学文化、岭南文学等。专著有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秋柳的世界——王士禛与清初诗坛侧议》、《牧斋初论集——诗文、生命、身后名》等;编有《千山诗集》、《落木菴诗集辑笺》、《瞿式耜未刊书牍》等。 (简要介绍:严志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文学文化、岭南文学等。)
情欲的诗学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仲冬,柳如是(1618—1664)访钱谦益(牧斋,1582—1664)于江苏常熟虞山半野堂。半年之后,钱、柳结褵于茸城舟中。柳随钱返常熟,钱为筑绛云楼于半野堂后,柳乃称柳夫人。嫁入钱门,柳氏结束将近十年的漂泊生涯。 前此,柳如是漂泊无定,迁转在吴越之间,直至虞山钱谦益之访,始寻得一生之归宿。其时,柳如是乃远近闻名的一代才妓,“从良”前在一艘画舫上不断移徙,目的,是寻觅一个可托付终身的男人。看来,柳如是较诸当时别的女性(如名媛闺秀),似乎拥有较多的自由,可以选择往来的方向、托身的对象。究其实,这自由与特权,却是丧失了正常社会身份地位始能获得的——柳如是是一妓女,寄身、活动于正常社会、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缝隙中。而且这一艘画舫,是无法自给自足的,每隔一段日子,它必须靠岸——靠近、进入男性主宰的世界——始能获得赖以存活的资源与补给。这船,不事生产,它与世界交易的,是欲望(desire),这欲望就是柳如是。这艘画舫,几乎可以视作柳如是的隐喻(metaphor)。而它在水中漂移时,是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谓男性观看中的“景观”(a sight)吗?若然,它的身份构成,来自它己身的“观察者”(surveyor),而这“观察者”,又是一个“被观察者”(surveyed)。伯格说:“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作对象——而且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在这样的理论导引下,我们会看到,西方裸体画中,裸女惯常以温顺或诱惑的目光睇视着画框外的观者(画像可能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买家)。这个看法,或可为我们提供思考柳如是现象的一个起点,但柳如是牵动的欲望纠结、权力运作,实则远远超过这种稍嫌简略的“观看之道”。 柳如是可以裸露身体,向观者投以温顺或诱惑的秋波,但这屈从的行为同时也为她攫取得操弄男性欲望的权力。柳如是是一个有情无情似真似假的颠覆。她偶尔“着男子服”,无视传统礼教对女性“性别”服饰的规范要求(而且还习武,有侠义之气)。除了姿容绝世,柳氏“词翰倾一时”,擅长诗词书画,富学识,精音律,通禅理。她与当时江南各地著名文不妨说,在当时构成一个文士身份的种种条件,柳几乎都具备。后来钱谦益有时称柳为“柳儒士”(柳如是的谐音),戏谑而外,不无道理,柳氏拥有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确实不亚于(甚或多于)男性文士。就某一意义而言,当时众多才人学士之所以倾慕于柳氏,是因为在柳氏身上看出某种自己,是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的结果;而柳氏所拥有的,甚或多于自己,于是他们出于对己身“匮乏”的焦虑,更渴望着柳如是。柳如是是一个“景观”,又大于、逸出于一个“景观”。欲望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是无穷尽的,难以餍足,方死方生,连圣人都只能以“节”“寡”规训,知道不能“绝”。 我们回到庚辰十一月,柳如是拜谒钱谦益那一天的现场吧。据钱氏门人顾苓(1609—1682后)的记载: 庚辰冬,(柳)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 在这描述中,柳如是乘的是“扁舟”,小船,意味着柳如是离开了她的画舫、她掌控的资产、仆从、熟悉的环境,果毅地、神情潇洒地趋赴半野堂。(历史学家却可能会败兴地告诉我们,城里的水道,一艘画舫无法通过。此待考。)柳如是向钱谦益献上一首诗,目的,是奉承、诱惑他。此后半年,《东山酬和集》刊刻行世,集内收入钱、柳及钱之友人、门人唱和之诗文。《东山酬和集》是钱、柳的爱情结晶,也是一本欲望之书,镌刻着钱、柳环绕着爱欲的相互建构(intersubjective constitution),也见证着诗歌的语言、书写行为在这段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中所扮演的意味深长的角色。 节选自严志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与身后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08月 钱谦益为十七世纪江南风雅巨擘,其诗文曾因政治原因遭到禁毁,其人亦被清高宗乾隆列入《贰臣传》,职是之故,其人、诗、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下流传,近乎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晚清民国以降文禁稍松,钱谦益诗文通过刻印开始广为流传,然而诗文虽渐流传,解人却少,这与钱谦益博通文史、旁涉梵道,为文作诗又词雅意深、今典古典并用等不无关系,学问渊博如陈寅恪,曩昔作《柳如是别传》时尚且感叹“岂意匪独钱谦益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可见理解钱谦益绝非一件容易事。 文本永远是我们进入“作者”最主要的凭借,其产生既有赖于“作者”的创造,也深受“作者”所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我们能从什么角度认识钱谦益呢?肤泛的道德批评并不能让我们增进一丝一毫有益的了解,最为稳妥、且最具备可操作性的应当是严志雄教授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雨身后名》,既从文本细读入手,深入探寻诗文中“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同时注重还原文本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看见”钱谦益生前身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