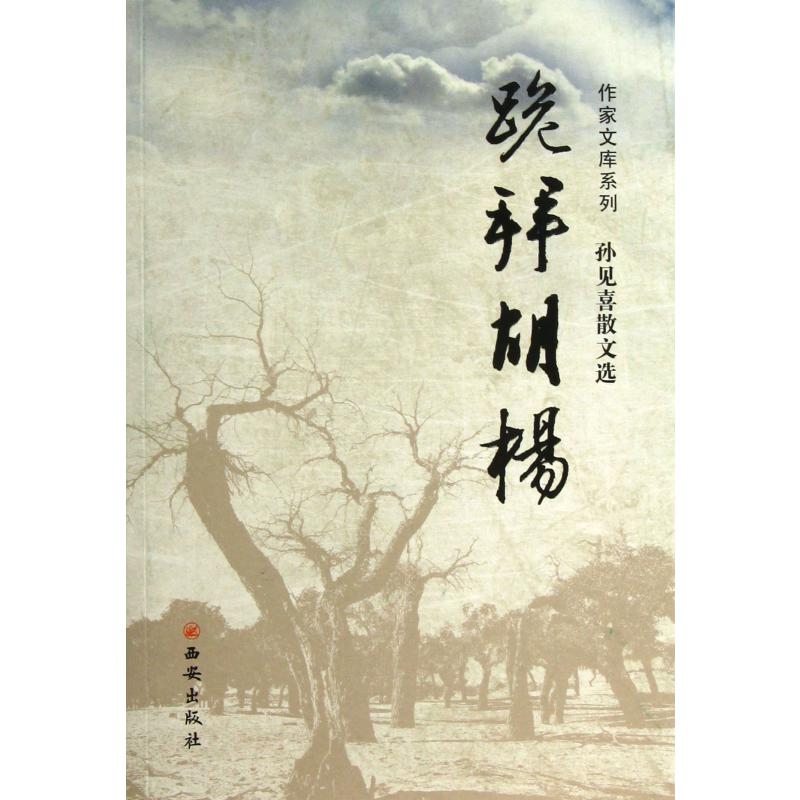
出版社: 西安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16.60
折扣购买: 跪拜胡杨(孙见喜散文选)/作家文库系列
ISBN: 9787554100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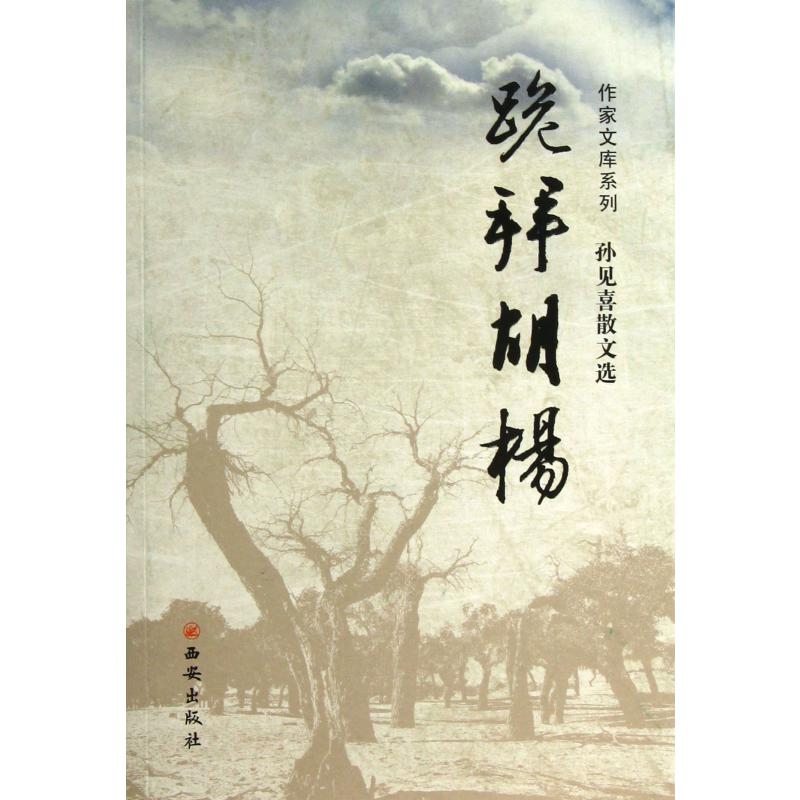
孙见喜,陕西商州人。1946年生,1969年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1970年分配到豫西“三线厂”当工人、助理工程师,业余创作小说。1981年调西安某军工所任工程师,1984年调省出版社做编辑至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家协会理事。作品曾获省市及报刊文学奖二十余次。 作品目录:《贾平凹前传(三卷)》/花城出版社,2001;《中国文坛大地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浔阳夜月》/N安旅游出版社,2000;《(浮躁)评点本扩/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亵渎偶像》/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孙见喜散文精选》/台湾金安出版社,1998;《鬼才贾平凹(一二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小河涨水》/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望月婆罗门》/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贾平凹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
雾村 是一个饱满而绵柔的长鸣,白色的,虚软有弹性;是一个生命在清晨颤 动,带着金属的硬度和质感。这便是晨雾中的牛声。 那只是一个虚淡的影子,刚劲的犄角和颈下的裙皮全被融解了,生动的 唯有一条尾巴,悠然荡动如浪中摇桨;于是,空气的粉色颗粒就起了旋涡。 天刚刚麻白,村人尚在死睡中。 那棵小槐树就被勾下来,带嫩刺的枝叶在牛尾的飘扬中滑进了胃囊。铁 缰绳拖在地上,那些残破的链环曾经结实过。晨雾把小山村锈死,隐映中屋 顶上残缺的脊兽很是尴尬。这些空膛的陶器五十年前就失去了装饰价值。几 株老榆固执在那里,一任流雾把它断成几截;扭斜的枝干把雷电的暴虐横陈 天际,有旧鸟巢在那里霉着。 踢踏踢踏,是惶惑又迟疑的步子。脚那么大,中间却要裂一条缝,走路 总是夹一绺黄泥的草根,这影响了它行进的速度,生物分类学上却美其名日 “偶蹄目”。有蛮实的力气,要么发泄于同类的角斗,要么服役于皮鞭的驱 使。给它一点随便,它却只知勾食路边的树叶,或者舌头一歪,揽几棵青苗 的茎蔓。若是雄性,早在英年就被骟匠挑去了睾筋;若是雌性,产儿之后不 及天伦之乐就有无尽容器来抽取奶水…… 牛之所以还算生物,其蓬勃欢跃全在犊儿时期。是惠日和风,是小河流 清,绿草上有黄蝶飞舞,沙地上有天鹅啄羽,小犊子就在那里奔跑,后腿蹬 起来,弹到高空打闪;前蹄忽而弹起,沙地上就刨出一个坑儿。蓦然一声奶 音,生命的青鲜嫩亮和母爱的万千柔情就一齐给搅活了,搅活了…… 之后,血在调教中凝固。生命在凝固中衰老。上颌的门齿没有了,胃分 为四室,唯有的作用是草食反刍。于是,不得不被役使。 东天仍然苍茫,雾还在嚣涨,听得见咔嚓嚓的搓动声。于是,青瓦的庙 堂和茅草的农舍一齐消解,横斜的弯榆和冲天的白杨一齐虚化,依稀是几千 年之后,这晨村沉人海底,唯余一片灰沉沉的朦胧。 突然就有了辘轳声,吱呜儿吱呜儿诉说,是谁家的妇人第一个踏破黎明 ,将小山村的实际存在告白天下。接着,有了鸡啼,有了鸟喧,有了三三两 两的开门声,有了小妈妈打骂独生子的恶喊:“叫你尿床!叫你尿床!” 东天泼射出水银的晕圈,雾向树梢滑去,世事清高起来。那条铁链子又 响了,是拖在沙石地上的搓磨,嚓啦嚓啦直割人耳朵。 是牛回来了,望着无以勾食的光杆枝丫,又发一声绵长的呜叫。金黄的 皮毛叫露水打湿了,如帚的尾巴湿重地下垂着。它惶然无所作为。 吱咛一声,提着大裆裤的汉子开门出来,一惊,说:“黑来咋忘了关牛 栏呢!” 屋里有妇人回声:“放开缰绳它也跑不到哪里去。” 苟村 一只白狗跑出来了,一只黑狗跑出来了。那油菜花的大色块里,就有了 一团黑白翻滚的毛球,就有了放蜂人的掷打和呵斥。 炫目的油菜花,浑蓝的苜蓿,满瓮的蜜浆,一位过路的文人到花地里撒 尿,眼目一时迷醉,连嗅觉也木木然愚钝。有女人在远处观赏,就作叹在野 地解手竟能充作风景,心想自己或许就是一只伢狗或一株静木了。 那狗又跑了回去。是村子,三户五户的人家,粉墙青瓦趔趄在苜蓿地的 那边。有鹅黄黄的柳丝儿,有白嘟嘟的槐花,有一种什么隆重的气息和清俏 的味道儿勾引着他,做文人的就束了腰带,忍不住往村子里去。文人的毛病 就是喜欢探究。 先是一把老榆钱,轻风里就地旋转;再是几棵刺芥芽,膨胀着从田埂的 板结中伸出头颈。天色正好,红日头下艳艳着几尾村姑,她们走过田埂,影 脚里一地芳菲。文人鼻腔里痒得舒服,认定这里有一种浓如草药的气息。这 气息渗润五脏六腑,就有了那种咝咝的消融和软化,心想,肝肠里有痞块的 人到这里来,心包里有硬化的人到这里来,脑血管有栓塞的人到这里来,一 切的肌体零件都会清洗然后重新装配,包括灵魂。走出去了,就焕然一颗新 生命。 然后是一种甜。一种柳叶子榆叶子槐叶子的联合提纯,清鲜又喷薰,尖 锐又漫延,顺着腰椎往上,整个儿脊柱就熟透了,没有了节疤和筋丝,没有 了气郁和烦忧。突然,轰地一响,大椎穴开窍,脑子就换成了爱因斯坦的, 或李白的,至少是郭沫若早期的。由不得就放胆追索。心理上的趋寻已不重 要,四肢的敏捷、七窍的灵光引他直奔源头。文人迷醉了也常常鲁莽。 撞倒一个老妇人,花花的围裙里掉下几块焦黑的红薯,笑说是送到老汉 子播粪的地头去。文人就惊怪,闻不到星点的焦糊味儿,连老妇的小脚边也 绕着两只花蝴蝶。 原是一株巨大的泡桐,花正飞谢,满地的紫色小喇叭,空气中饱和着药 药的软软的尖锐味道,是那种柳叶子、榆叶子、槐叶子的联合提纯。庞大的 树冠正被一咕嘟一咕嘟的绿叶缝合,胖嫩的萌芽喘着壮汉的粗气,阔大的叶 子已在阳面一手遮天。人或如昆虫,即便总统站到这里也依旧猥琐。 这就是赏心悦目的源头了。文人弯腰捡拾桐花,一滑脚踩在了牛粪上。 新鲜的牛粪。甚至还袅袅地冒出热气。有一种酸酸地味道。旁边就是羊圈, 褐色的尿液积成小潭,圆圆的羊屎蛋儿在小潭里软散开来,毛毛的纤维绒绒 着,又是一种药药的味道儿。 还有鸡粪,半流质的排泄物里有不能消化的石头。最大观的是那一方化 粪池,赫然洞陈在大桐树的阴凉里。主人勤快,秋天的落叶还沤在里头,柳 叶子、榆叶子、槐叶子,对,是那种尖锐的味道,是那种经过联合提纯的味 道。 文人严肃地注意到一个问题:卫生! 他在省城的街道上走,马路干净,店铺干净,连厕所里也闻不到臭气。 艳味儿当然有,人造的紫罗兰,法国的奥丽斯,机关一按“哧”一声香雾。 尽管j分钟之后,狐臭患者依然难逃众人侧目。 文人就捡起一朵桐花,活活地罩在鼻尖上,香味儿就沁得深刻。想这满 地落英,刮一层地皮到省城去也能当香料卖。又作想,倘没有那鸡屎牛粪, 没有那污浊的化粪池,岂不是彻底的七宝福地? 白狗又来了,黑狗又来了,一个在桐树根上撒尿,一个用鼻尖触那热牛 粪。文人就忽然明白:是什么东西支持着菜花的黄、苜蓿的蓝,和这桐花、 槐花、榆钱的雅香和清鲜? 城市人最可卑的性格是只要结果不要过程。 文人捶骂了自己,要记住这个村子的名字。那两只狗就引来了一群狗。 一群狗在他心里汪汪。就想:叫它狗村吧! 在油菜地边,问放蜂人,答说:“不叫狗村,叫苟村。早年的写法是草 头下一个勾子。” 又补充说:“是勾引的勾。” 文人自觉尴尬,就笑笑地说:“我是去看一棵桐树。” 放蜂人说:“桐树下住着什么人你当然知道!” 根据这口气,文人可以想得出,那里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或者一个贤惠 的小寡妇。但他仍然说:“那棵桐树很香。”放蜂人怪怪儿一笑,摆手说: “走吧走吧!” 文人走了。贼溜溜的真如一个品行糟糕的男人。他想:探索是需要付出 代价的,但若真要以品行为代价,行吗? 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