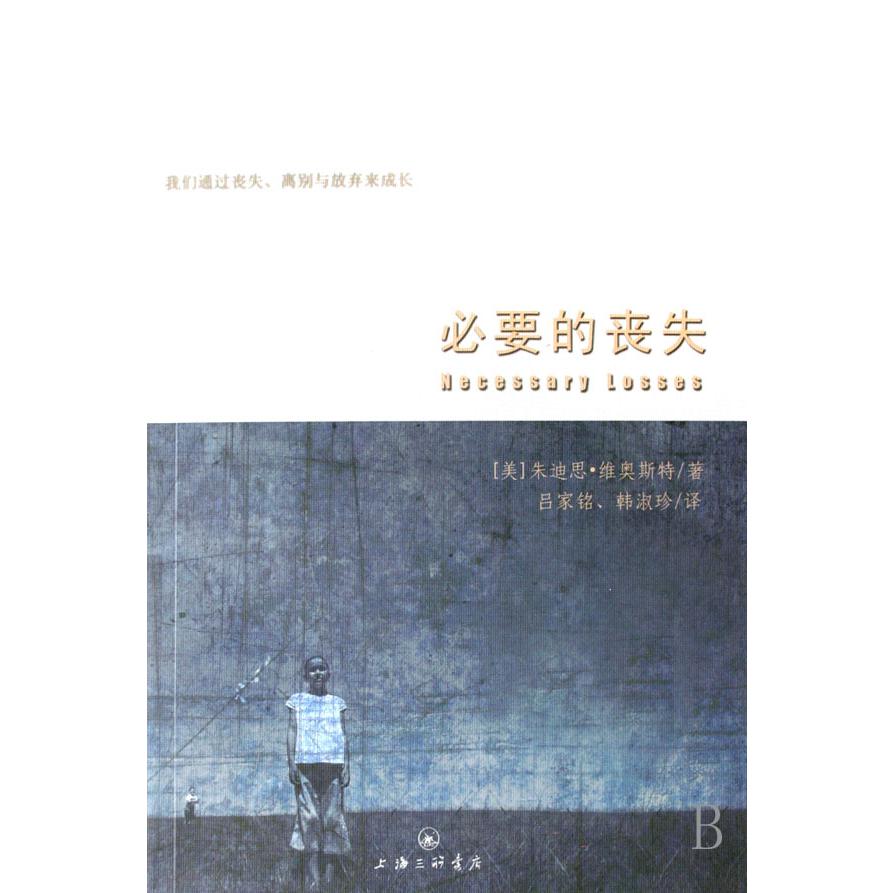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三联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22.60
折扣购买: 必要的丧失
ISBN: 9787542625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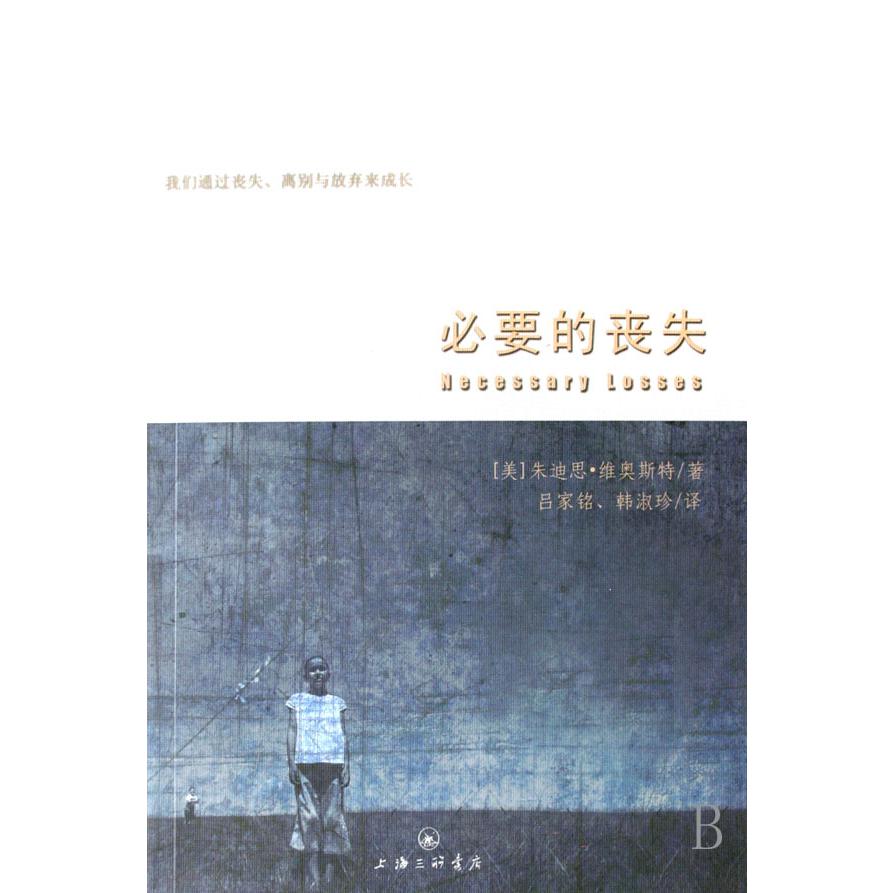
华盛顿精神分析学院的研究员,从事了将近二十年的儿童与成年人内心世界的写作。
只有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即瑟莲娜出生后的这些年月里,我们才把注意 力集中于丧失母亲的高昂代价上;集中于哪怕是短暂性分离所造成的随即而 来的创痛和未来的长久后果。一个与母亲分离的孩子会表现出对分离的反应 ,而这种反应可能会在母子相聚后依然长时间地持续着。这些反应包括饮食 与睡眠上的问题、尿床和大便失禁,甚至是用词量的减少,更有甚者,在年 仅六个月大的时候就可能变得哭闹不停和悲伤,并且还会十分忧郁。与上面 所说的反应有密切关联的,是所谓的“分离焦虑”的痛苦感觉。它包括了孩 子当母亲不在时独自碰上危险的恐惧,以及当母亲在吋害怕再次失去她的恐 惧。 我非常熟悉这些症状和恐惧,它们在我四岁住院的三个月里就接踵而来 。由于当时的医院严格限制探病的时间,我度过了三个月好像没有母亲的日 子。等到我病愈出院后的好几年,我竟然还承受着住院的负面影响,我转移 忧虑的其中一个显著症状,便是那新养成的梦游习惯。梦游的习惯一直持续 到我十五六岁为止。 举个例子:在我六岁时的一个温和的秋夜,父母整晚都不在家,我感到 非常苦恼。我在没有醒来的状态下爬下了床,轻声地走过了正在打盹儿的保 姆,打开大门走到家的外头。我在熟睡的情况下穿过了繁忙的十字路口,最 后终于来到了我梦游行程的目的地——消防局。 “小姑娘,你要做什么?”一个惊讶的消防员温和地问道,以免把我惊 醒。 据说,我在沉睡的状态下,毫不犹豫地以清晰洪亮的嗓音答道:“我要 消防员们找我妈妈。” 一个六岁大的孩子竟然极度渴望他的母亲。 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孩也极度渴望母亲在他的身边。 因为孩子到了六个月大左右,即使母亲不在,他也能在脑海里勾勒出她 的形象。他记得母亲并且特别需要她,而母亲不在他身边的这一事实让他感 到痛苦。由于他有着只有他的母亲一一他不见了的母亲——才能满足的急切 需要,所以他感到莫大的无助和失落。 一旦孩子与母亲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他年纪越小,察觉母亲的丧失是永 久的丧失所需要的时间就越短。尽管他人的亲切关怀能够帮助他忍受每日的 分离,但是孩子至少要到三岁,才会渐渐明白不在身边的母亲仍安然无恙地 在别的地方活着,并且会回到他的身边。 只是,等待母亲的归来或许会感到是无限期的——或许会感到要永远等 下去的。 因为我们得记住,时间随着年月增长而加速,过去我们衡量时间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从前的一小时是一天,一天是一个月,而一个月肯定就是无尽 头的了。这也难怪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会为不在身边的母亲而感到悲伤, 像成年人哀悼过世的人一样。这也难怪当一个孩子被带离他母亲的时候,“ 那急躁和思念会使他伤心得发疯”。 分离使人心绪缭乱,而并非更加好受。 事实上,分离会造成一系列普遍的反应:抗议、沮丧再到最后的疏离。 把一个孩子从他母亲身边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同陌生人一块儿相处,他无 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安排,便会尖叫、哭闹、胡打乱踢;他会急切地、不顾一 切地寻找他的母亲;他会抗议因为他仍心存希望.但是过了不久,当母亲还 没有来……还没有来时,抗议便会转化为失望,一个充满无法形容的悲痛, 无言且低沉的思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三岁两个月大的帕特里克被送到英国的汉普 斯特德幼儿园。让我们看看安娜。弗洛伊德对他所作的观察: 他满怀信心地安慰自己和向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保证他母亲一定会来接他 。他母亲会为他披上外套,然后再次带他一同回家…… 之后,那记录着母亲会为他穿上服饰的单子继续增加:“妈妈会帮我披 上外套,穿上毛线裤,她会帮我拉好拉链,再带上那小小的帽子……” 当这个顺序被没完没了地反复重述,变得乏味无聊的时候,有人问他是 否能别再重复了……他虽然不再大声说出来,但那不停在动的嘴唇表示他仍 然在对自己重复着相同的话。与此同时,他也用手势来替代语言,摆出帽子 的位置,假装披上外套,拉上拉链等等……当其他孩子忙着玩玩具、嬉戏、 做音乐等等,小帕特里克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会满脸悲痛地站在某个角落, 不停掰弄手指,自言自语。 由于对母亲的需要是非常强烈的,多数的孩子会从绝望中脱离出来,寻 找母亲的替代者。而就是因为这个需要,我们能合理地假定当那失散已久的 母亲回到孩子身边时,他会喜出望外地投入母亲的怀抱中。 事实却不是这样。 令人意外的是,许多孩子——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孩子——会对归来的母 亲表现得非常冷淡,同她保持一段距离,一脸茫然,好像是在说,“我从来 没见过这位女士”。这样的反应叫做疏离——一种爱之情感的终止——并且 它通过诸种方式来处理丧失,例如:它惩罚离开的人。它也是隐蔽愤怒的一 种表现,因为激烈极端的怨恨是被抛弃的主要反应之一。它可能也是一种防 卫——可能会持续数小时、数日甚至是一辈子——一种避免承受重新爱过但 又再次失去的痛楚的防卫。 分离使人心寒意冷,而并非使情感更深。 而如果这分离实际上是同家长的分离;如果童年经历一系列这样的分离 ,那会怎样? 精神分析学家塞尔玛·费雷博格描述一个16岁的男孩在阿 拉梅达郡提出一项诉讼:以在16年内,自己被寄养于16个不同的家庭为由, 要求得到50万美金的赔偿。那又怎么样,确切地说,他控告的伤害是什么呢 ?他回答:“它就像是心灵上的一道伤痕。”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