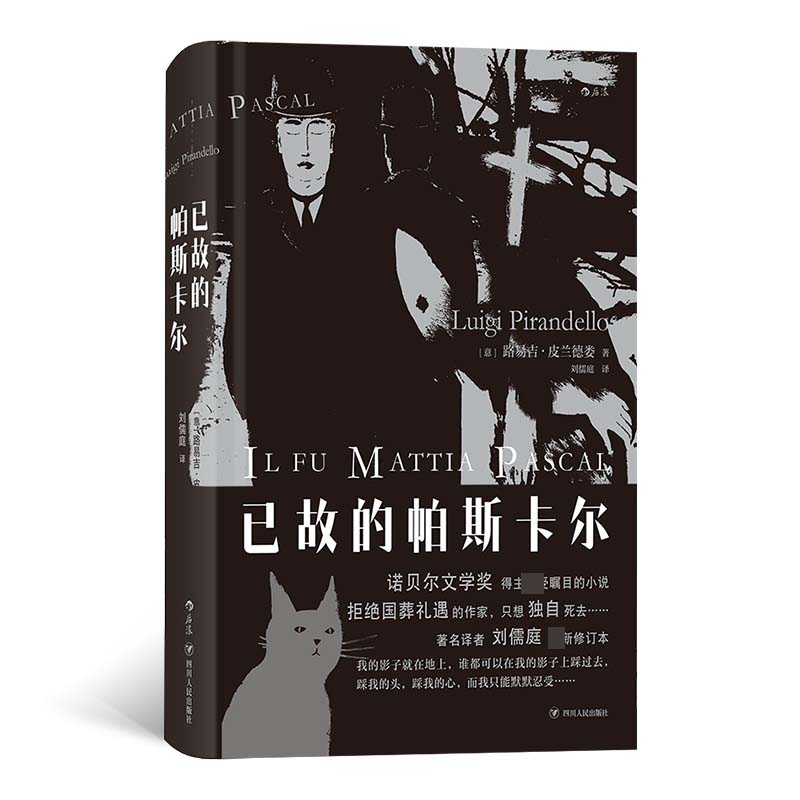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已故的帕斯卡尔(精)
ISBN: 97872201147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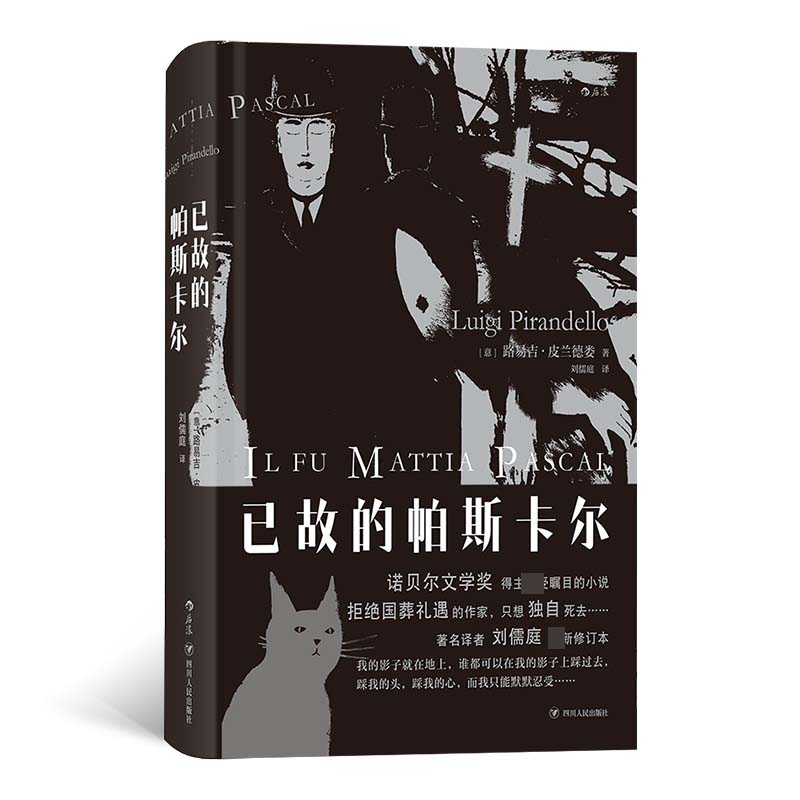
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有三百余篇短篇小说、七部长篇小说、七卷诗集、四十多个剧本以及两本文艺论著。1934年因“无畏而智巧地复兴了戏剧和舞台艺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初期作品《被抛弃的女人》《没有爱情的爱情》等大多以西西里为背景,具有真实主义风格。从第二部长篇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1904)开始主题发生重大变化,着力刻画不可知的外部世界与不确定的内心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变化大概与其身世相关:破产、妻子发疯、儿子沦为战俘、家境濒临崩溃,他甚至一度想了却生命……一个初冬,皮兰德娄受寒患肺炎,医治无效身亡。遵照其生前遗愿,他的葬礼极其朴素:赤身裸体仅裹一条床单,用一辆最简陋的马车载送,除了车夫、马匹,无任何送葬者,不发讣告、不要鲜花、不点蜡烛。 译者简介 刘儒庭,1941年生,河北人。译审,意大利仁惠之星骑士。曾任新华社罗马分社首席记者,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译作有理论著作《开放的作品》《影子的门槛》,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基督不到的地方》《为时已晚》《鞑靼人沙漠》《相爱一场》,电影剧本《甜蜜的生活》《红色沙漠》及诗歌《青春诗》等。
一 开场白 我生来知识贫乏,所知甚少,我所掌握的全部知识中的一点,不,不是其中的一点,而是唯一的一点是,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我常常利用这一点点知识。有时,我的朋友或认识的熟人有什么事搞不清,只得跑来征求我的建议或意见,每当这种时候我就耸耸肩膀,挤挤眼,回答他们说: “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 “谢谢,亲爱的,这我知道。” “怎么,你认为这还不够?” 这还不够,说实话,连我也觉得确实太少。但是,我真不知道,对一个连这一点都不懂、连更多的回答都不能够做出的人,他还有什么想说的呢?也就是说,像我之前经常做的那样,只在必要时说: “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 有人可能会对我表示同情(这分文不值),想象着如何对一个极为不幸的人表达一番深切的哀悼之情,想马上弄清楚这个不幸的人……可弄清楚什么呢?是的,一句话就够了,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既不知道他过去如何,也不知道他过去并非如何。有的人也可能会对风俗的败坏、世风日下和悲惨境况极为愤慨(这也分文不值),这些可能就是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弄到这步田地的主要原因。 好吧,那就随便你们怎么想吧。可是,我不能不说一句,事情恰恰并非如此。我真的可以写出我的家谱,可以说明我这个家族的渊源和它的兴衰史,还可以证明,我不仅知道我的父母是什么人,而且还知道我的先祖和他们的活动。当然,祖辈相传,他们的活动并非都是真的值得赞扬的。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我的情况非常怪诞,非常特殊,正因稀奇古怪,世间少有,所以才值得我从头道来。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待在一个图书馆里,不知道自己是个抓老鼠的,还是个图书管理员。那个图书馆是博卡马扎主教在1803 年临死前赠送给镇政府的。显然,这位主教对他同乡的脾气秉性所知甚少;要么就是,他希望他的这份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点燃同乡们学习的热情,更何况在图书馆学习又是那么方便。迄今为止,这种学习的爱火没有被点燃,这我可以做证。我这样说也是对我同乡的赞扬。对于这份遗赠,镇政府并不喜欢,甚至不愿为博卡马扎立一尊半身雕像,尽管应该这样做,那些书也被扔进一个又潮湿又无人问津的库房,一扔就是好多年。后来,这些书倒是从那个库房里被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那些书都成了什么样子,移送到偏远的圣玛丽亚自由教堂去了。那座教堂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被改为俗用了。在这座教堂,镇政府又不假思索地把这些书委托给一个无事可干的人负责,他倒真像个不担任教化工作的有俸神职人员,一天赚两个里拉a。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看守这些书,或者说看守都没有必要,只不过是在那里忍受好几个小时的霉臭味道。 后来,这样的命运也轮到我头上。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不喜欢这些书,不管它们是印刷的还是手稿(像我们图书馆的那些非常古老的手稿)。正像前面讲的,我的情况怪诞特殊,要不是这样,我才不会去写什么手稿哩,永远不会去写。由于我的情况怪诞特殊,写下来之后,也许有那么一天能使某个好奇心强的读者获得教益,或许也能使博卡马扎主教的良好愿望最终有一天得以实现。这样一个读者或许有一天会来到这座图书馆,我的这部手稿就是留给我的这位读者的。不过,他必须服从一个条件:在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最终死亡后五十年之内,任何人不许打开这一手稿阅读。 眼下,我已经死了(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悲伤),确实,我已经死了,而且死了两次,第一次是因错而死,第二次是因……且听我慢慢道来。 二 辩白式的第二篇(哲学的)开场白 写这部书的想法,或者说写这部书的建议,是我可敬的朋友唐·埃利焦·佩莱格里诺托向我提出的。他现在在看管博卡马扎的那些书。我的书一写完我就把手稿交给他,只要能够写完。 我就在这座不再是圣地的小教堂里写作,借助的光线就来自头顶圆穹的吊灯。这是后殿为图书管理员留出的一块地方,周围是柱式木质矮围栏。在我写作的时候,唐·埃利焦也在忙他的,他勇敢地承担了整理这些乱堆乱放的书的任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担心,他恐怕永远也弄不出个头绪来。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浏览一眼书脊,至少大致弄清这位主教送给镇政府的都是些什么书。人们以为,所有的书无非都是些有关宗教的书,或者差不多都是这类书。现在,佩莱格里诺托发现,这位主教的书涉及的面很广,这让佩莱格里诺托感到极为欣慰。由于这些书都是随手乱堆在那里的,所以乱得简直无法形容。有些书除去外表华丽之外还十分亲密地粘连在一起。例如,唐·埃利焦·佩莱格里诺托对我说,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三卷本的内容淫秽的《爱女人的艺术》同另一本书剥离开,这套三卷本是安东·穆齐奥·波罗写的,1571 年出版。剥离出来的那本书名为《福斯蒂诺·马特鲁 奇的生与死——有人称之为在天先知的波利罗内本笃会修士的马特鲁奇》,是1625 年在曼托瓦出版的一部传记作品。由于库房潮湿,这两套书已紧紧粘在一起。他还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清,那套三卷本的第二卷除去那些淫秽的内容之外还详细地描述了修道士的生活和风流韵事。 唐·埃利焦·佩莱格里诺托整天在一架点路灯的人用的那种梯子上爬上爬下,在书架上挑来选去,选出很多内容有趣读了让人高兴的书。每找到一本好书,他就站在梯子顶端,以优美的姿势将书扔到房间正中那张大桌上,小小的教堂就会发出隆隆的响声,一大团尘土随之扬起,两三只蜘蛛从那团尘土中飞快逃离。这时,我就穿过栅栏,从后殿跑过来,先用这本被扔下来的书把蜘蛛从满是尘土的桌上赶跑,然后打开书开始阅读。 就这样,我渐渐培养起了阅读的兴趣。现在,唐·埃利焦对我说,我的书应该以他从这座图书馆里挖掘出来的这些书为范本来写,也就是说,应该具有这些书的特殊味道。我耸耸肩,对他说,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然后我就去考虑别的事去了。 唐·埃利焦满头大汗,浑身是土,从梯子上爬下来,到小园子里呼吸新鲜空气。那个小园子就在后殿外边,是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树枝和带刺的东西好不容易才围成的。 “啊,我那可尊敬的朋友,”我坐在矮墙上,手杖支着下巴对唐·埃利焦说,这时他在专心观察他的莴笋,“看来我是写不出这本书了,写书可不是闹着玩的。看来搞文学创作也同其他任何 事一样,我不得不翻来覆去地重复我那些陈年旧事。该死的哥白尼!” “嘿,同哥白尼有什么关系!”唐·埃利焦直起腰,满脸通红,在那顶破草帽的映衬下他的脸显得格外红。 “有关系,我的唐·埃利焦,因为在地球不转的时候……” “怎么可能呢!地球总是在转!” “不是这么回事!过去,人们不知道地球在旋转,因此,可以说,地球好像不转。现在,好多人就觉得地球也不转。有一天,我对一个老农民这样说,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那倒是醉鬼的好说辞。另外,对不起,还有您,您也不能怀疑,约书亚让太阳停在当空。这些暂且不去说它了,我要说的是,在地球没有转的时候,人们——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是那么道貌岸然,是那么自豪,以至对自己的尊严感到心满意足。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一种细腻的、充满冗繁细节描写的作品是会受到欢迎的。从昆提利安的作品中人们是读到还是读不到——就像您教导我的——历史应当用于叙述而不是用来让人们去验证的?” “这一点我不否认。”唐·埃利焦回答说,“但是,不应该否认的是,世界上绝对没有写得这么详细的书,甚至把那些隐秘的细节都统统写进去了。因此,就像您说的那样,也就让地球转起来了。” “好极了! 你听,‘伯爵准时起床, 每天八点半, 分秒不差……伯爵夫人穿上一件藕荷色衣服,衣服滚着花边,一直到下巴……特雷西娜因饥饿而死……卢克雷齐娅忍受着爱情的折磨……’啊呀呀,我的上帝,您觉得这与我何干?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小陀螺上?太阳的光线就像一根鞭子,抽着这只陀螺在旋转,像一粒沙粒一样在疯狂地转啊转的,转个不停,既不知道为什么而转,也不去预想未来的命运,好像是要向我们证明,这样旋转就是它的乐趣,好像是为了让我们有时感到暖和,有时又感到寒冷,好像是为了让我们转了五六十圈之后再死去。那时,死者常常会发现自己一生有那么多小小的愚蠢行为。我的唐·埃利焦啊,哥白尼,哥白尼他可是毁掉了人类,无可弥补地毁掉了人类。现在,对于‘我们人类是无限渺小的’这样的新观念,对于‘我们人类在宇宙中无足轻重’这样的想法,尽管我们有这样的发明、那样的发现,对于这些观念和想法,我们大家已经逐步适应了。那么,您还想使那些消息——我指的不是关于我们无限渺小的消息,而是像全球性灾难这类消息——具有什么价值?我们的历史不过就是小小的爬虫的历史。你读过有关大安的列斯群岛的小小的灾难的报道没有?没有。可怜的地球转得不耐烦了,正像那位波兰伟人说的那样,它是无目的地在旋转的,不耐烦了就稍微停一下,它本来有好多大裂口,这时,其中一个裂口就喷出火焰来。有谁能说得出,是什么东西使它如此暴怒?也许是一些人的荒唐使它大发雷霆,这些人空前厌倦才做出了一些荒唐事。不管怎么说,总之是成千上万的小小爬虫被火焰烤死了。我们依然活着,有谁还去谈死的人?” 可是,唐·埃利焦却让我仔细想一想,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头去毁灭、粉碎大自然为了我们好而在我们心中树起的理想,但我们总是难以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人类轻易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一点确实不错。比如,我们这座城市就规定,有那么几天夜里不许点灯,所以我们经常只得忍受一片漆黑,特别是乌云密布之夜。 说到底,这意味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相信,月挂中天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在夜里给我们照明,就像太阳在白天给我们带来光明一样,星星也是为了给我们现出满天星斗的美景而存在。确实如此。我们常常有意忘记,在互相尊重和看重方面,我们都是那么小气,我们倒是能为了一小块土地而大打出手,或者为了一点儿什么事而互相怨恨,如果我们真能搞清我们作为人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为了那么一点儿小事而互相怨恨实在太不值得。 好了,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偶然的发现,再加上我的情况怪诞特殊,所以我才要谈谈我自己。当然,我要尽量简短,也就是说,只谈那些值得一谈的事。 当然,其中自然有些事不会使我很有面子,然而,我现在处于一种特殊境地,这使我可以认为自己已经不在人世,所以也就没有任何避讳和顾忌了。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 皮兰德娄193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赖声川倾情推荐的一代戏剧大师,尤内斯库、奥尼尔、萨洛特、品特、萨拉克鲁、季洛杜、贝克特等都深受其影响。为精准传达其复杂的哲思,皮兰德娄在剧本构思和舞台艺术方面展开许多革新和实验,使戏剧的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统一,其中《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亨利四世》《给赤身裸体者穿上衣服》《寻找自我》已成为戏剧史上的传奇。为纪念皮兰德娄,第12369号小星星被命名为“皮兰德娄星”。 * 《已故的帕斯卡尔》是一本“幽默里透着悲凉,怪诞中蕴含哲理”的小说,主人公两次抛弃“自我”,制造自己的“死亡”:重获新生后会怎样?——“拥有无边无际的自由。”无边无际的自由意味着什么?——“成为永生永世的局外人。”人到底该如何存在?——“没有目的地,没有目标,像是走向一片虚无缥缈之中……一个死去的人的影子,这就是我的生活。”作者企图用“想象的真实”来对抗“生活的荒诞不经”,面对不可知的外部世界与不确定的内心世界,展现人们对“自我”身份丧失的焦虑与恐惧。 * 由马塞尔·莱尔比埃执导,伊万·莫兹尤辛、鲁伊·莫兰和米歇尔·西蒙主演的法国印象派默片《已故的帕斯卡尔》(1926年)改编自本书;由喜剧大师马里奥·莫尼切利执导,马塞洛·马斯楚安尼、森塔·贝格尔、弗拉维奥·布奇、劳拉·莫兰特和劳拉·德尔·索尔主演的意大利电影《马蒂亚·帕斯卡尔的双面人生》(1985年)改编自本书,在第3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提名金棕榈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