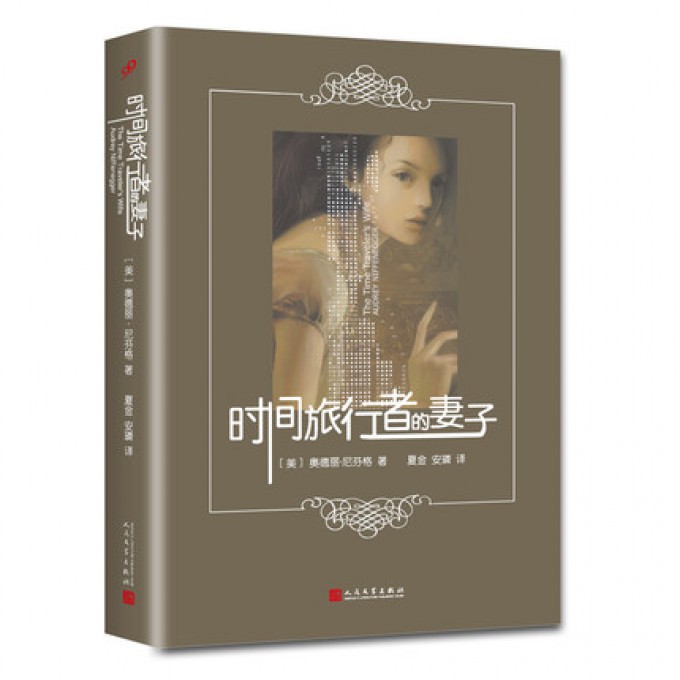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4.40
折扣购买: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ISBN: 97870201200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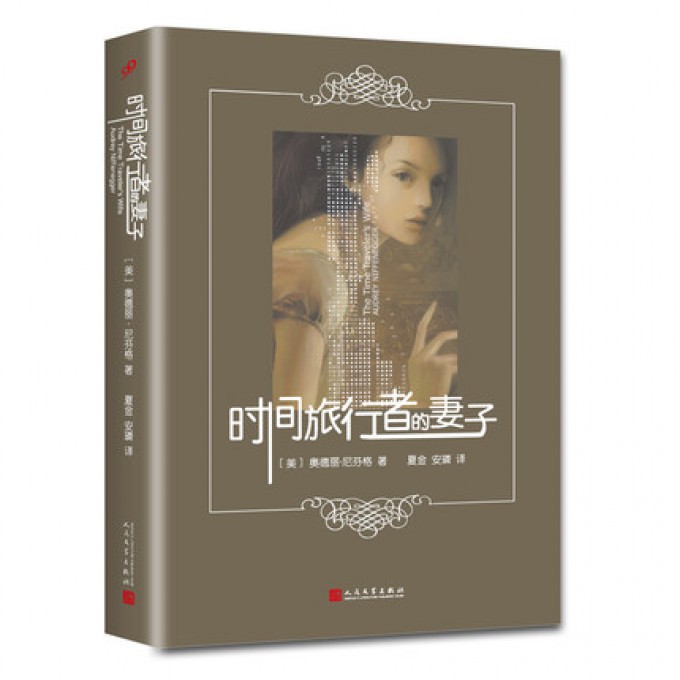
奥德丽·尼芬格(Audrey Niffenegger),视觉艺术家,也是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书籍与纸艺中心的教授,她负责教导写作、凸版印刷以及精**书籍的制作。曾在芝加哥印花社画廊展出个人艺术作品。二〇〇三年,尼芬格出版了**部小说《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引起轰动,售出四十多国版权,三年多时间里始终列于美国***排行榜前一百位,被英国《卫报》评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百本书之一,成为**畅销书,其同名电影于二〇〇九年在美国上映。二〇〇九年,尼芬格第二部小说《她的镜像幽灵》以**的伦敦海格特墓园为背景,借由两代双生子的奇特纠结,再一次讲述了一段深情不弃的爱情故事,其文辞婉转细腻,令人难以释卷。
克莱尔:被丢下的感觉真艰难。我等着亨利,不知道他在哪儿,不知道他一切可好。做等待的一方,真艰难。 我尽量让自己充实。那样时间会过得快一些。 我独自一人入睡,独自一人醒来。我经常走动。我工作到精疲力竭。我注视被一整个冬天的积雪覆盖的垃圾,随风飞舞。除非你停下来想这件事情,否则一切都依旧单纯。为何缺席总让爱意*浓? 很久以前,男人们出海,女人们为之守候,伫立海边,搜寻天际的轻舟。现在,我等着亨利。没有任何预兆,他就这么不情愿地消失了。等待的每分每秒,都仿佛经年累月般漫长。每个微小的时刻,如同玻璃沙漏里的细沙,缓慢而透明,每个微小的时刻,我都能看见,它们无穷无尽,汇聚成漫长的等待。但为何他的离去,我总无法相随? 亨利:感觉如何?感觉如何? 有时,像是瞬间的走神,接下来,你突然意识到捧在手中的书、红色棉布格子衬衫和上面的白色纽扣;意识到挚爱的黑色牛仔裤、栗色的就要磨破的袜跟;意识到起居室、厨房里即将鸣笛的水壶:所有的一切瞬间幻灭了。只剩下你像只**的松鸦,独自兀立在乡间无名沟渠的齐踝的冰水中。你等了一分钟,或许还能突然重返书边,重返你的家之类的地方,经过大约五分钟的咒骂、颤抖和想让自己立即消失的*望,你开始漫无目的地前行,而*后总会遇见一座农舍,那时,你可以选择偷窃或选择解释。偷窃有时会让你被捕,解释则*加冗长无味,因为解释免不了说谎,有时同样会锒铛入狱。天下还有*倒霉的事么? 就算躺在*上半梦半醒,有时也感到自己猝然站立,你听见血液涌进大脑,体验**时晕眩般的刺激,犹如芒刺在背,随即,手脚也没了知觉,你又一次不知身在何处了。即使稍纵即逝,你觉得应该有时机抓住些什么,你的手臂也曾用力挥舞过(结果往往伤了自己,或损坏了房间里的贵重器物),然后你就滑到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星期一清晨四点十六分,滑到俄亥俄州雅典市第六汽车旅馆那铺着深绿色地毯的走廊上。你的头一下子撞到某扇房门,于是里面的客人——一位来自费城的蒂娜·舒曼女士,开门后一阵尖叫,因为一个**男人正晕倒在她的脚下。你终于被一阵吵闹搅醒,却发现自己躺在郡立医院的病房里,门外一名警察正用他破旧的、充满杂音的晶体管收音机,收听费城人队的棒球赛事。老天开眼,你又被抛回无意识中,数小时后再度醒来,回到了自己的*上。妻子正探身看着你,眼神中充满焦虑。 有时,你满心欣喜,身边的一切都庄严壮观,金光笼罩,而转眼间,你又**恶心 初次约会(上)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星期六(亨利二十八 岁,克莱尔二十岁) 克莱尔:虽然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大理石,可是这 个阴冷的图书馆,闻上去怎么有股地毯吸尘器的味道 ?我在访客登记簿上签下“克莱尔·阿布希尔,一九 九一年十月二十六*十一点十五分,于特藏书库”的 字样。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纽贝雷图书馆,现在我穿 过这条幽暗的、略有些阴森的入口过道,一下子兴奋 起来,仿佛刚刚梦醒在圣诞节的早晨,整个图书馆就 像只装满美丽书籍的大礼盒。电梯缓缓上升,不是很 亮,几乎没有声响。到了三楼,我填写了阅览卡申请 表,然后走到楼上的特藏书库里,我的皮靴后跟在木 质地板上啪嗒作响。房间里安静,拥挤,满是坚固沉 重的大书桌,桌上是成堆的书,桌边围坐着读书的人 们。高耸的窗子,透进芝加哥秋天早晨明亮的阳光。 我走到服务台边,取了一叠空白的索书单。我正在写 一篇艺术史课的论文,我的研究课题是:克姆斯歌特 版的《乔叟》。我抬头看了看这本书,填了一张索书 单,同时,我也想了解克姆斯歌特出版社的造纸方法 。书籍编目很杂乱,于是我走回服务台,请求帮助。 正当我向那位女士解释我需要什么时,她的目光掠过 我的肩头,落在正从我身后走过的一个人身上,说: “或许德坦布尔先生可以帮您。” 我转过身来,正准备再次解释一下我的需求,刹 那间,我的脸和亨利的脸相对。 我哑口无言了。这就是亨利,镇静,穿着齐整, 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年轻。亨利在纽贝雷图书馆 工作,此时此刻,他就站立在我面前。我欣喜若狂。 他很有耐心地看着我,稍显诧异,但很有礼貌。 他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么?” “亨利!”我只能压抑着抱住他的冲动。很显然 ,他这辈子从未见过我。 “我们见过面么?对不起,我不……”亨利环顾 四周,生怕读者或同事注意到我们俩,他迅速搜寻记 忆,然后意识到,某个未来的他早已经提前认识了现 在的我,这位站在他眼前喜形于色的女孩。而我*后 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坪上吮我的脚趾。 我试着解释:“我是克莱尔·阿布希尔。我小时 候就认识你了……”我有一种茫然,眼前我深爱着的 男人,居然对我**没有印象。因为对他而言,一切 都还在未来。整个古怪的过程让我直想发笑。多年来 ,我对亨利积累的了解,此刻如洪水泛滥般涌上心头 ,而他却疑惑、畏惧地打量着我。亨利穿着我父亲的 旧渔裤,耐心地考我乘法口诀、法文动词、美国各州 的首府;在*坪上,亨利边笑边注视着我七岁时带来 的特别午餐;我十八岁生*时,亨利身穿无尾礼服, 紧张地解开衬衫和饰扣。此地!此时!“来呀,我们 去喝咖啡,去吃晚饭去别的什么吧……”他一定会答 应,在过去和在未来都爱着我的同一个亨利,通过类 ,突然离去。你被抛在郊外的天竺葵地里,或是你父亲的网球鞋上,或是三天前卫生间的地板上,或是一九〇三年前后伊利诺伊州橡树公园里铺满木板的小道上,或是一九五几年某个晴朗秋天的网球场上,或是在各种可能的时间和地点里你自己**的双脚上。 感觉如何呢? 它像极了一个梦:你突然想要**去参加一场你从没有修过的学科考试,而当你出门时,钱包却忘在家里了。 一旦我去了那儿,就立即被扭曲成一个*望的自我。我成为一个窃贼、流浪汉,成为一只终*奔跑躲藏的动物。老太太被我吓倒,孩子们惊讶不已,我是一个恶作剧,我是**幻影,我难以想象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 是否存在一种逻辑,一种规则,掌控着我所有的来去往复、所有的时空挪移呢?是否存在一种方法,能够让我原地不动,让每个细胞都拥抱这当下的时刻?我不知道。也有一些线索,正如所有的疾病存在各种类型和各种可能:过度劳累、嘈杂声音、压力、突然的起立、泛光灯——任何一件都有可能诱发下一场故事。可是,我也许正在我们的大*上翻阅周**的《芝加哥太阳报》,手握咖啡杯,一旁的克莱尔偎依在我身上打盹,突然,我来到了一九七六年,目睹十三岁的自己在祖父的*坪上锄*。这样的情节,有的只能维持片刻,那情形如同在汽车里收听广播时,费力地搜寻锁定某个频道。有时,我发觉自己被抛进人群里面、观众之间、暴民当中;同样有时,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落在田野里、房间里,出现在车上、海滩上,还有深*半夜的中学教室里。我害怕发现自己出没在监狱、异常拥挤的电梯和高速公路,我莫名其妙地来临,我**着身体,叫我如何解释得清楚。我从来带不上任何东西,没有衣服,没有钱,没有身份证。时空逗留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寻找遮羞的衣物,东躲**。幸运的是,我不戴眼镜。 令人啼笑皆非,是的,我所有的爱好都是居家的:舒适的扶手躺椅、平静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激动。我需要的一切都只是卑微的快乐:枕畔的一本探险小说、克莱尔金红色秀发沐浴后湿湿的幽香、朋友度假中寄来的明信片、融化进咖啡里的奶油、克莱尔乳峰下那抹娇嫩的肌肤、厨房桌子上对称的两个等待被拆的食品袋,我爱等到阅览者们全部回家后,信步走在图书馆的书堆之间,轻手划过列列书脊。当我被时间随意摆布,我对它们的思念犹如针尖一样刺骨。 克莱尔,总是克莱尔,清晨克莱尔睡眼惺忪、面容紧皱;工作时克莱尔把双臂伸进纸浆大桶里,拉出模具,这样那样地搅动,搓揉着造纸纤维;看书时克莱尔的长似蝙蝠次声波般的神秘时间感应,现在也一定会爱我 !我松了口气,他果然立即答应了,我们约好今晚在 附近一家泰国餐厅见面。图书馆服务台后面的女士目 瞪口呆地看完了我们整个交谈过程,离开时,我已完 全忘记了克姆斯歌特和乔叟。我轻盈地走下大理石台 阶,穿过大厅,来到芝加哥十月的阳光中,然后小跑 着穿过公园,我一路微喘个不停,幼犬和松鼠都远远 地避开我。 亨利:这是十月普通的**,秋高气爽。在纽贝 雷图书馆四楼,那间装有湿度控制系统却没有窗子的 小房间里,我正在分类整理一套刚捐来的大理石纹纸 。这些纸很美,但分类工作枯燥,乏味,甚至让人有 些自怨自艾。事实上,我感觉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一 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痛饮昂贵的伏特加直到半夜, *望地想要挽留住英格里德·卡米切尔施舍的爱,这 种滋味有谁能懂?彻夜,我们俩都在争执,现在,我 甚至都记不得当时究竟吵了些什么。我大脑里的血管 突突直跳,我需要咖啡。我把那些大理石纹纸稍稍理 了一下,任由它们以一种乱中有序的方式四处散落。 我离开了这个小房间,径直走向办公室,当我经过服 务台的时候,听到伊沙贝拉的声音:“或许德坦布尔 先生可以帮您。”我不由停下脚步,她的意思其实是 说:“亨利,你这个神出鬼没的家伙,这会儿又想去 哪啊?”然后就是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女孩一下子回 过头来,琥珀色的头发,高挑的身材,猛地攫住了我 的眼睛,仿佛我就是上帝专门给她派来的救星。我的 胃一阵痉挛。显然她认识我,可我真的不认识她。天 晓得我曾对这个光芒四射的美人说过、做过或者承诺 过什么,因此我只能用图书管理员***的语调说: “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么?”而这个姑娘轻吐出我的 名字“亨利”!她如此唤醒了我,让我不得不相信在 某段时间里,我们曾一起神仙眷侣般地生活。一切* 加混乱了,我确实对她一无所知,甚至都不知道她的 名字。我问她:“我们见过面么?”伊沙贝拉此时给 我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你这个大傻帽。”可是 那个女孩却说:“我是克莱尔·阿布希尔。我小时候 就认识你了……”接下来她请我出去吃晚饭,震惊之 余,我还是接*了邀请。尽管我没刮胡子,一副宿醉 没醒的糟糕模样,可她看我的目光依旧灼热。我们约 好当晚在泰国情郎共进晚餐。得到我的允诺后,这位 克莱尔小姐便云一般轻巧地飘出了阅览室。我晕眩着 进入电梯厢,终于意识到,一张有关我的未来、金额 巨大的彩票,此刻已经找上门来了,我笑出了声。我 穿过大厅,跃下层层台阶走上大街,猛然看见克莱尔 正小跑着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看她兴高采烈、蹦蹦 跳跳的样子,我突然不知为何想哭。 P7-9 发披散在椅子靠背上;临睡前克莱尔用精油“噼噼啪啪”地按揉摩擦。克莱尔低柔的声音总在我耳畔萦绕。 我不想呆在没有她的时空里。但我总是不停地离去,而她却不能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