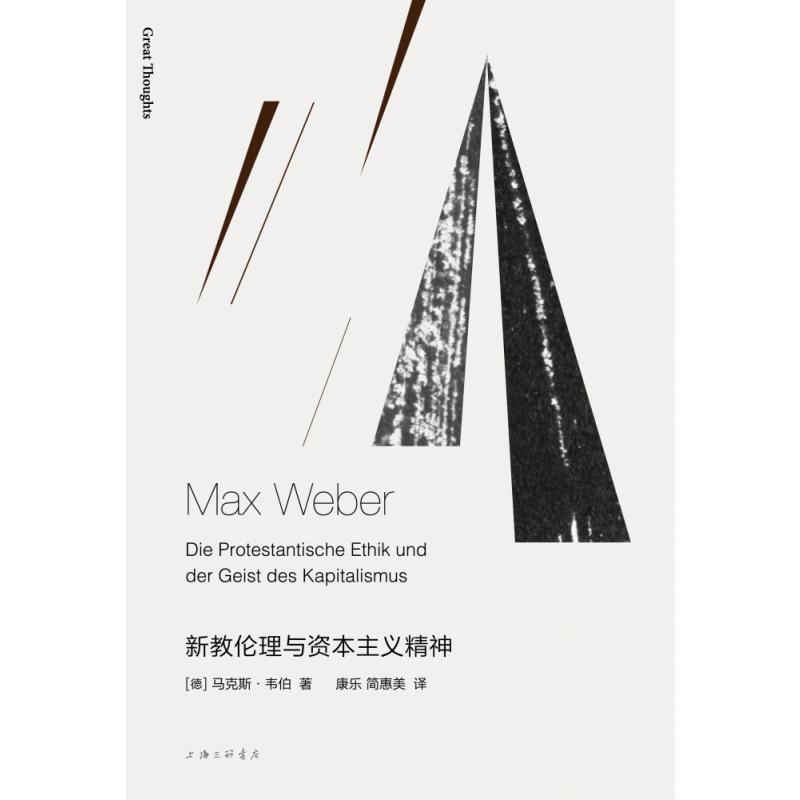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3.50
折扣购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ISBN: 9787542664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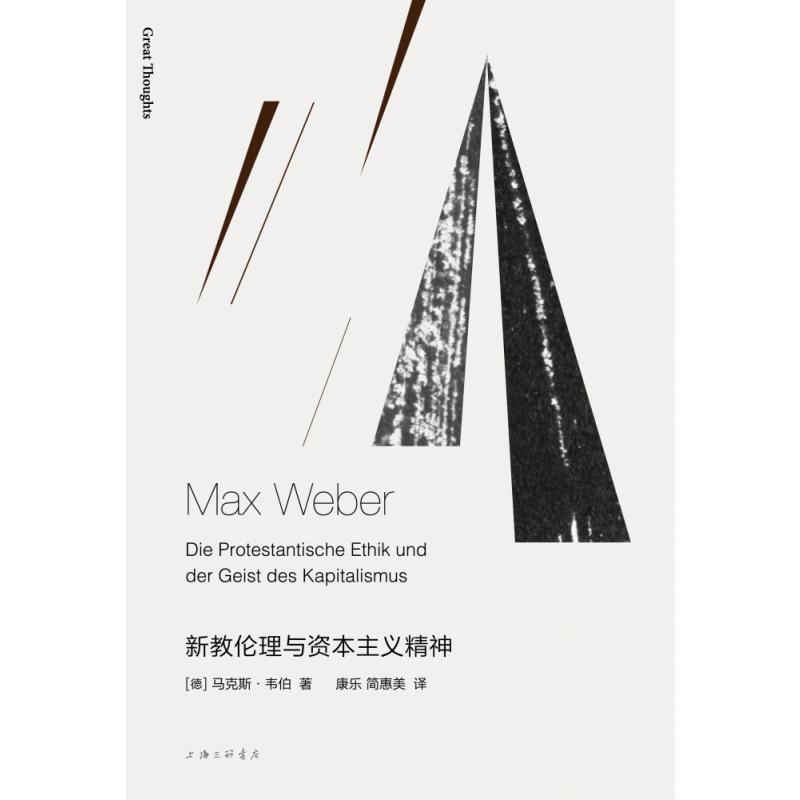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4.21—1920.6.14),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小城埃尔福特。1882年,开始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92年起,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逝。 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和爱米尔·涂尔干三人,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在对现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中,马克斯·韦伯的地位至今仍然无可质疑,其思想体系始终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他一生著述甚多,其中以《学术与政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举凡清教人生观的力量所及之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有助于市民的、经济上理性的生活样式的倾向——这比单是促进资本形成自然是重要得多。清教的人生观实为此种生活样式之最根本的尤其是唯一首尾一贯的担纲者,守护着近代“经济人”的摇篮。当然,此种清教的人生理想,在面对那连清教徒自己都十分熟稔的财富的“诱惑”如此巨大的考验下,也会有动摇的时刻。我们经常发现,清教精神最为纯正的信奉者是属于正在兴起中的小市民与农民阶层,而“富裕的人”(beati possidentes),即使是教友派信徒,却倾向背弃昔日的理想3。正如入世禁欲的先驱者中世纪修道院里的禁欲所一再遭遇的命运一样:在生活规律严格且节制消费的中世纪修院里,理性的经济营运一旦充分发挥其效用时,所获取的财富不是直接——像教会分裂之前那样——朝着贵族化的方向堕落,就是使修道院的纪律濒临崩溃的危机,以致必须着手那一再反复的“宗教改革”。事实上,修院纪律的整部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与财富世俗化的问题相抗争的循环史。清教的入世禁欲亦是如此,而规模更大。十八世纪末英国工业兴盛前夕,卫理公会强大的“信仰复兴”足可与此种修院改革相比拟。此处我们或可引一段卫斯理自己的文章,来为以上我们所说的林林总总做个结尾。因为这段文章显示,禁欲运动的领袖本身是如此充分了解本文所述看似相当矛盾的关联,并且完全是以本文所铺陈的意义来加以了解2。他写道: “我觉得,举凡财富增加之处,宗教素质即等比例地减少。所以,按道理,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使真正的宗教复兴长长久久。因为宗教必然产生勤劳与节俭,而这两者无疑又产生财富。但财富一增加,傲慢、激情和各形各色的现世爱执也随之增加。那么, 卫理公会这个心灵的宗教,尽管现在有如青翠的月桂树欣欣向荣, 但如何才能使它长保此态呢?由于卫理公会信徒在各处都是既勤奋又节俭,所以财富也增加了。相应的,他们的傲慢、激情、肉欲、眼色和生活的志得意满也随之高涨。如此一来,宗教的形式是保持住了,但精神却迅速消失。难道没法防止吗——纯正宗教的这种持续沉沦?我们是不该阻止人们勤奋与节俭;我们必须勉励所有基督徒赚取一切他们所能赚取的,节省一切他们所能节省的;也就是说,事实上,变成富有。”(他接着劝告,凡是“赚取一切他们所能赚取的,节省一切他们所能节省的”人,也应该“给予一切他们所能给予的”,如此才能添加神的恩宠并累积天上的财富。)——我们看到,他将我们此处所要阐明的关联,巨细靡遗地表达了出来。 那些强而有力的宗教运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首要在于其禁欲的教育作用——全面展现出经济上的影响力,正如卫斯理此处所说的,通常是在纯正宗教热潮已经过了巅峰之时,也就是追求天国的奋斗开始慢慢消解成冷静的职业道德,宗教的根基逐渐枯萎并且被功利的现世执著所取代之时。换言之,套句道登的话, 就是在民众的想象中,班扬所描绘的那个内心孤独、匆匆穿过“虚荣之市”、奋力赶往天国的“朝圣者”,已被《鲁滨孙漂流记》 里兼任传道工作的孤独的经济人所取代。后来,当“兼顾两个世界”(to make the best of both worlds)的原则胜出时,结果必然亦如道登所指出的,纯善的良心就只能变成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一种手段,正如“纯善的良心是柔软的枕头”这句德国俗谚所巧妙传达出的意思。然而,充满宗教气息的十七世纪所遗留给下一个功利世代的,最重要莫过于在营利上的惊人的纯良之心——我们很可以说,一种法利赛式的 纯正良心——只要一切都是出之以合法形式的话。“总非上帝所喜”那样的想法,消失得无影无踪。独特的市民职业风格(bürgliches Berufsethos)业已形成。市民阶级的企业家,只要守住形式正当的范畴、道德行为没有瑕疵、财富的使用无可非议,那么他就能以充满神的恩宠受到神明显可见的祝福之意识来从事其营利的追求,而且也应该这么做。 不只如此,宗教的禁欲力量又将冷静、有良心、工作能力强、坚信劳动乃神所喜的人生目的的劳动者交在他的手中。这力量让他安然确信,现世财货的分配不均乃神之具有特殊用意的安排,借着此种差别,正如通过特殊的恩宠,神有他奥秘的、非人所能了解的目的要完成。加尔文有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民众”,亦即劳动者与手工匠大众,只有在贫穷中才会继续顺服于神。荷兰人(彼得·库尔及其他一些人)将这句话“世俗化”为:人民大众唯有受迫于贫困时才肯劳动;而资本主义经济主要调性之一的这番定式化,后来便汇入到低工资的“生产性”这个理论的洪流里。在此,正如我们一再观察到的发展模式, 当思想的宗教根基枯死之后,功利的倾向不知不觉地潜入称雄。中世纪的伦理何止是容忍乞讨,根本就是对托钵僧团的乞讨行为大加赞赏。即使俗世的乞丐,也因为他们给了有产者借慈善而积善功的机会,所以经常被当作是一种“身份”来对待。连斯图亚特王朝时英国国教会的社会伦理,在精神上也非常接近这种态度。直到清教徒的禁欲参与使那苛刻的英国济贫法成立时,才让这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之所以如此,不外乎是因为基督新教诸教派与严格的清教诸教团内部当中,事实上根本就不知乞讨为何物。 另一方面,从劳动者这一侧来看,例如虔敬派的钦岑朵夫宗派,就赞美不求利得而忠于职业的劳动者,认为他们是以使徒为人生的榜样,亦即具有耶稣门徒的卡理斯玛。再洗礼派早期也盛行同样的想法,只是更为激烈。当然,基督教几乎所有宗派的整体禁欲著作,全都弥漫着这样的观点:生活上并无其他机会的人, 即使工资低也仍旧忠实地劳动,这是最为神所喜的。在这点上, 基督新教的禁欲并未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虽然如此,它不仅最强而有力地深化了此一观点,而且为此思想规范创造出使其影响力得以发挥出来的、最具关键性的一股力量,亦即借着认定此种劳动为天职、为确证恩宠状态最好的——最终往往变成唯一的——手段的这种想法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心理的驱动力(Antrieb)。 另一方面,基督新教的禁欲又视企业家的营利为“天职”,从而正当化了这种特殊劳动意欲的剥削利用。因视履行劳动义务为天职而唯独天国是求的努力,以及教会纪律自然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的严格禁欲,必然多么强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意义下的劳动“生产性”,是很明显的。近代劳动者视劳动为“天职”的这种特色,正如同企业家视营利为天职的相应特质。像佩蒂爵士这样一位英国国教派的敏锐观察者,便对这个在当时仍属新闻的事实做了描述:他认为十七世纪荷兰的经济力量应归功于该国“非国教派”(加尔文派与洗礼派)的特多,那些人视“劳动与产业为他们对神的义务”。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英国国教派所采纳的特别是劳德2的观念里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带有国库—垄断色彩的“有机的”社会体制,是清教所反对的;清教徒起而抵制这种立基于基督教—社会党下层结构的国家、教会与“独占业者”的同盟,并且标榜个人主义的驱动力, 亦即凭借自己的能力与创意来从事理性与合法的营利,所以其代表人物彻彻底底是这种基于国家特权的商人—批发业—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激烈反对者。在英国,虽然基于国家特权的独占产业不久即再度全军覆没,但清教的这种心理驱动力却对产业的建立——不依赖官方权力,部分而言反而抵抗这种权力来建立产业——起了决定性的协力作用1。清教徒(普林与帕克)认为那些具有大资本家特征的“廷臣与筹划者”是个道德可虞的阶级,所以一概拒绝与他们合作往来,另外又以自己优越的市民营业道德为荣,这才是引来那个圈子的人对他们施加迫害的真正原因。笛福亦曾提议,以联合抵制银行票据和撤回存款来对抗对于非国教徒的迫害。这两种资本主义作风的对立,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与宗教上的对立形影相随的。非国教派的仇敌甚至到了十八世纪都还一再嘲笑他们是“市侩气”的担纲者,并认为他们是老英格兰理想的扼杀者而加以迫害。此处也明摆着清教徒的经济风格与犹太人的经济风格的对立,而当时人(普林)业已明白,前者而非后者才是市民的经济风格(bürgerliche Wirtschaftsethos)。 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不只如此,还有近代的文化,本质上的一个构成要素——立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而这就是本文所要加以证明的。我们只要再读一下本文开头所引的富兰克林的那段小文,便可看出那儿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心态,在本质的要素上实与稍前所究明的清教的职业禁欲的内容并无二致;只是前者的宗教根基,即使是在富兰克林那儿,也业已枯萎衰亡。近代的职业劳动具有一种禁欲的性格,这想法本身并不是件新鲜事。断绝浮士德式的个人全方位完美发展的念头,而专心致力于一门工作,是现今世界里任何有价值的行动所必备的前提。因此,“事功”与“断念”如今注定是互为表里不可切割。市民的生活格式——若要成为格式而非不成个样子的话——所具有的这种禁欲的基本格调,也是歌德在作品《漫游时代》 及给予浮士德的一生之结局中,以其高度的人生智能所想要教导我们的。对他而言,这样的认知等于是向一个完美人性的时代断念诀别;这样的时代,在我们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已无法重演,犹如古雅典文化的全盛时期已一去不返。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Berufsmensch)——而我们则必须成为职业人。 ★本书是马克斯·韦伯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著作,发表之际即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激烈争论,一百年过去,它仍旧被反复讨论。书中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独特见解,在大陆学界影响巨大,是一代代学人的必读书目。关于本书有诸多解读甚至误解,但无论如何,在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中,它是一本绕不开的著作。 ★译本特色: ?余英时、苏国勋联袂推荐——本书是由专业学者基于研究之上的严谨迻译。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外,亦收录有姊妹篇《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由年轻学者王楠撰写导读,《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他以新一代学者的眼光重新解读韦伯以及韦伯之于今天的意义:直面现代人被缚于“资本主义”牢笼的处境,探寻重建社会伦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