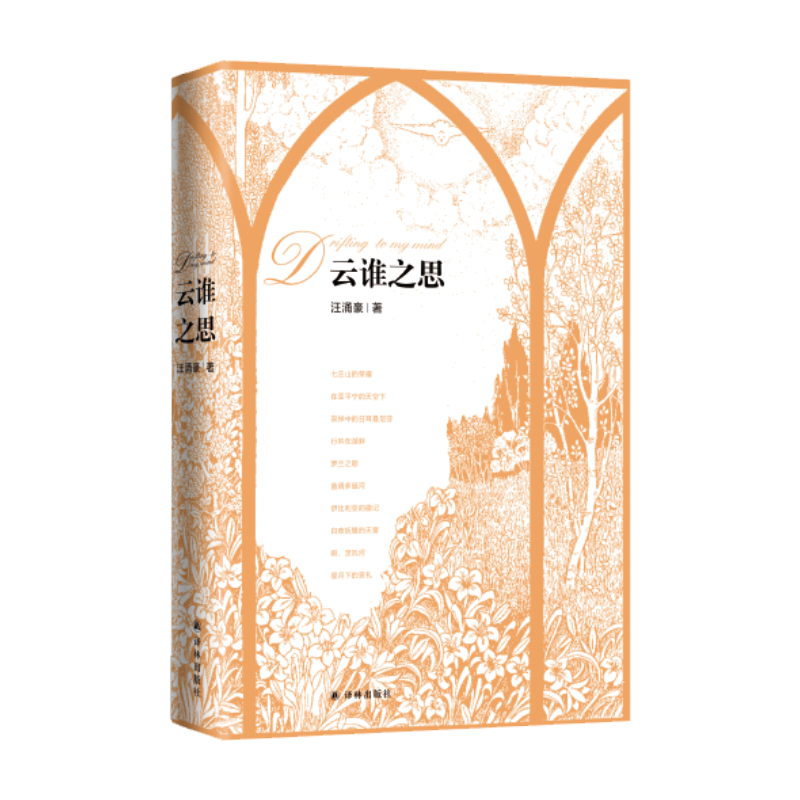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2.20
折扣购买: 云谁之思(精)
ISBN: 9787544764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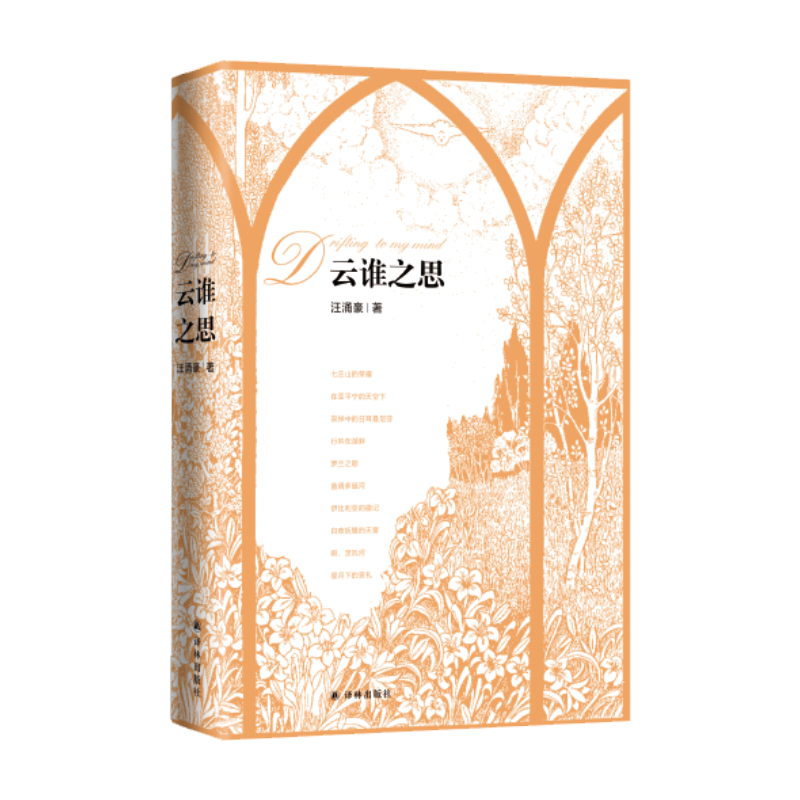
汪涌豪,***“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为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神户大学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美学与文论研究,兼及古代哲学、史学与当代文化批评。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中国游侠史论》《中国游仙文化》《言说的立场》《汪涌豪人文演讲集》等十七种。
我不能在柏林说 古巴比伦, 幼发拉底河畔神的城, 你忧伤的目光 发散成坦直的大道, 似要代苏美尔和亚述兄弟 行过西亚细亚,正朝向 自然与丰收**伊什塔尔的门。 很快有狮与牛 及一切兽的吼声 汇集成浩荡琉璃的仪仗, 来攀佩加蒙 *精致而繁富的祭坛。 有环绕着美索不达米亚的 靛蓝的市声 透过阿勒颇房间的窗户, 撞向波斯地毯上的那些金银陶罐, 和由藤蔓缠绕着的 倭马亚王朝残存的宫墙。 然后,古罗马米勒特斯集市的大门 被推开来了, 一群满地找眼睛的人 等来了以后无穷的世纪, 和满屋子的惊呼声。 我本来已经得救 面对将要到来的受浸, 他涨红着脸, 奋力啼号在四周缄默的神像前。 他蓝色的眼睛 照头上的玻璃穹顶, 与施洗者胡须上的烛光一样 一刻都不消停地等 颂祷声起, 和有人替他默颂福音。 他只得收住哭闹, 眼里似自带着信德的考较 逼视每个观礼者的初心。 他们应该都听到过罗斯元年 第聂伯河畔那个希腊牧师的布道, 那人性复苏的意味 为什么还是让许多人 明明耽溺于肉身, 仍奢望于天堂别样的风景? 这样想着, 他重新开始啼哭, 想从这样的世界中分别出自己。 他感到因为受洗, 自己是有了罪与死的初体验, 但自己被收容的生命 是否算有了信仰的根基, 实在是一个 太难回答的问题。 很快过尽了骚动的七月, 很快他也做了父亲。 他臂弯中也有了一双眼睛 闪亮着,看向穹顶。 这使他不敢欣喜, 只有悲悯。 从未属于过你的温德米尔湖 你需要迈开腿, 换一副属灵的眼睛, 才能渡越坎伯里山脉, 让自己的狂喜 贴着大朗戴尔峡谷飞翔, 再折返,喘息, 以便能仿效那些自在的羊, 轻轻地落在丛生着 芜菁与苜蓿的 田畴。 然而转出山谷的湍流 飞快地冲过桥屋, 才汇合了断崖下的瀑布, 就不再听你的央恳, 并不在意你急着想为耳朵 换一层膜, 以便能听清每一颗沙粒中的 宇宙,是否还留有 诗人略显憔悴的 歌喉。 终于,靠黄水仙的指引, 你看到了这些优雅地 吸攒阳光的湖,如三色堇, 正大度地任每一朵镶边的云 投在自己的波心。 有时它们还温柔地升腾自己, 以便复活被晒褪了原色的万物, 且没觉得这是在代神付出, 而纯然是一种 享受。 只可惜你已不敢要求它 为你滋润干涸的唇, 去说出正困惑着你的 眼耳鼻舌身的焦虑。 你任欲望在心里伸展带刺的枝条, 不同于授粉后的花能等待, 以便能理解它对高地上雪的守候, 是正照见你这样自毁生命, 早过了能投身于它的 时候。 我坚决地相信每一朵花 ——致朴素生活与高尚思考中的华兹华斯 我坚决地相信每一朵花, 都能在斯科费尔山峰下 尽情地舒展,开放。 在被湖水沾湿了的阳光下, 和丛生的竺葵一起 沿干草车碾出的辙迹, 朝向每一条藤蔓去到的方向。 然后再告诉风小声些, 说它们每次从骨朵撑开的声音, 其实都值得安静地倾听。 我不止一次地央告, 以我垂死的生命, 所有的花都请放慢开的节奏, 以便在布谷鸟与画眉的叫声中, 让一种浩荡的慈悲 启众生,葬万物, 让匆忙无主的人们 能像*了解自己的昆虫, 谦虚地听土地的教诲 和大自然温暖的声音。 我是温德米尔的孩子, 阿尔斯沃特湖上 *柔和的一抹靛蓝; 是赫尔维林山下佝偻的老朽, 和斯托克吉尔瀑布 每一次飞溅出的精灵。 然而,我终究不能像罗瑟河一样 归入它的怀抱。 只好先让我的朵拉, 安葬在圣奥斯瓦尔德教堂底下。 湍濑的源头,山岚的归踪, 草之光鲜与花的芳香, 紫杉和黄水仙的提示是 此地系上帝遗落在下界的天堂。 然而因缺少它那样的干净, 我至今仍孤独地飘浮在天上。 我能问我的后人吗, 到底谁是它遗落在人间的天使, 谁又会在意 那天使吟哦的声音? 你的许多是我的** 有许多痛苦 让人背负各自的罪责, 认识到人生的归路 和真地狱的风景, 是尽一季白夜都无法履行的 与上帝达成的约定。 有许多遗憾 不让人终于知道真相, 用洒向坟墓的泪 去洗死屋中思忖的痛苦。 它所自带的崇高, 不经意就能在忍耐与驯从中 战胜所有通俗廉价的幸福。 有许多罪与罚 从谢苗诺夫校场出走, 居然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 杀人路线,站上了 科库什金的桥头,回望。 虽冷静是这运河上冻结的波纹, 怎么就一条条地刻上了 他劫余刑后的额头。 有许多镀金的邪恶 鬼附在诲淫者和虐待狂的身上, 正看着**了解苦难的他 走向涅夫斯基修道院。 尽管他怜恤游荡在街上的众人的沮丧, 但他们会在意他吗, 他凋落在麦地里的种子 究竟会与什么福音一起 唱颂终获果实的希望? 可叹你们有那么多的许多, 我只有一颗感知忧伤的头颅。 我潜意识里的每一刻 都不停地在《荷马史诗》中搏斗, 伴着复调实验,才想回视莎翁, 已被颓废的人们奉为前驱, 并即使卡夫卡的血亲说也不再是 **的确认, 为我曾经冲冒的风寒和预先知道的*望, 是许多人终将在自虐与分裂中疯狂。 再追悼一下这个许多吧, 包括许多鄂木斯克无法独处的时光, 和压在轮盘赌上的 许多再也无法追回的健康, 是何其微弱的向许多人的生之布道。 回思痛苦独独是他的气质, 以及终未获得自由的他的死亡。 他已让许多人的血和他一样 瀑布般地奔泻,所谓以苦难净化的是人的灵魂, 所以就不必再去卡皮托利丘加冕, 以躲避许多雕像都有的雕鸮们的轻狂。 后记 就个人来说,写诗不过是近三年的事,但喜欢诗却远不止三十年。 这三十年中,读过许多书,但记住的不是很多。留下可以记住并相信的,多半是诗,或与诗有关。所以有时会说自己与诗有缘,原非过甚其词。对此,别人也许不怎么觉得的,自己也懒得说明。是为痴。 间有一二故人动了好奇心,来问发生了什么。其实能发生什么呢,不过是随时间推移,渐渐了解了自己;又随人之将去,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多断弃。但这样的解释似乎仍没什么说服力,因为在常人眼里,诗是这样的东西,它只会使真实变得不真实,乃或在生活中不能真实,人才会去写诗。总之,如果人生果真是一趟忧伤的行历,那么它的先锋通常是诗,但拣尽寒枝后它的殿军,通常另有其人或事。 不能说持这种认识的人一定错了,连弗罗斯特都没法说服人不将诗视为装饰,一如丁香必定有它自己,但还是难逃被人用以调味食物的命运。至于想出版诗集,固无不可,希望它能被关注,就纯属马尔克斯所说的丢一瓣玫瑰花入山谷,然后指望能听到它的回声了。不过饶是如此,个人仍觉得上述的认识不真。一个人偏好用诗来安顿自己,一定是切切实实地体认到诗是人心*大的真实的。此所以阿诺德称诗是“人心的精髓”,赫兹利特认为诗是“生活中*精细的部分”。 可用为佐证的照例是诗。如华莱士·史蒂文斯就曾有这样的诗句:“秋叶落尽之后,我们回归 / 一份事物的直感。”正因为诗须依赖直感,并只专注于或*擅长写直感,注定了它比其他文体都*努力地以裸出真实为职志,并*能让写诗或读诗的人借此不惮面对真实的世界,乃至真实的自己,既足证自己有自信,因为他根本不以自己的拙于应世为意,他坚持按自己的意思活,并当生活给的不是他想要的,仍因为有诗而相信,能安静;又足证自己够诚意,因为他认定“诗是抗拒不**现实的一种方式,亦为创造替代现实的一种尝试”,一如布罗茨基所说,这让他在心里祛除一切功利的计较,全不算计与人沟通的成本,是*执意地要将倾诉进行到底,并当别人不能理解,决不强求同情;万一对方懂得,也不必然会有望外之喜,只是*确知诗的力量而已。 此外,诗的无可替代就都在它有恰如其分地传递人心精髓和生活的精细的形式了。即它能假一种特殊的语言,造成动人的韵律和节奏,来传达人内心的情感,进而调用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段,凝合成可移合、嵌接和转换的意象,多角度表达这种情感的力度与速度。正是这种特殊而强烈的“内指性”,使诗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成为如薄伽丘所说的一种“精致的讲话”。由此带出的魔力,足以让人面对生活中任何言说的寒俭和表达的苍白,宁可选择沉默,也不愿哓哓不休,进而认为有些话是不说与说一样真,*有些话一旦说出来就必须浃髓沦肌,直达人的心底。 在这方面, 几个世纪以来的中西诗人和诗论家们都有过精彩的论述,也留下了许多可称经典的诗作。直到一百年前西诗传入,在中国人的抒情与西方诗的浪漫的颉颃中,尤其在传统与当下的交互激荡中,面对着一边是认定唯诸夏**的俪文律诗,才可与外域文学一较高下,一边是坚持唯文废骈、诗废律才是进步,才有出路,一些新文化阵营中的人在响应胡适倡导的“自然音节”同时,已不时“勒马回缰写旧诗”。至于那些持文体本位的新诗作者与诗译者,基于汉语的特性,体认着悠长的中国古典的传统,*留心梁启超提出的“新意境”、“新语句”和“以古人风格入之”的作诗三原则,希望通过“敛才就法”的修炼,来成就“诗界哥伦布”的伟业。他们孜孜矻矻,比勘中西声律之异同,追求诗与音乐的联通,由此讲字节和顿数,衡音尺和音组,并经上世纪五十年代往下直贯到**,对如何守正开新,在脱弃旧体诗束缚的同时,造成节有定行、行有定拍,并换韵有序的新体格律,仍多有艰苦的探索,*抱有*大的热忱。 个人的趣味与这种主张*接近一些,并觉得经由意象派的译介,中西诗可共通的一面已大体为人所知。当,其间的差异也*加显而易见。及至二十世纪以后,西方诗歌和诗学理论被不断引入中国,有的诗人还亲来中国与读者分享自己的经验,这导致了新诗体式的多样化已日渐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其中不重字而*重句与语段的锤炼,不重段式均齐、章法互应而*多放任诗意流散和诗行出入,*是成为风气。其下焉者,*挟“日常写作”的诉求而沦为“口语诗”“废话诗”。但正如不论在前现代还是后现代的语境下,西人作诗论诗都好讲意象,中国古人也一直很重视意象的营建;不论古代还是现代的中国人,作诗论诗都好用典故,西方诗人和诗论家也同样每常出入希腊罗马,像哈罗德 · 布鲁姆《读诗的艺术》在讨论讽喻、提喻、转喻和隐喻的同时,就特别谈到用典。至于因语言不同,中西诗人追求诗歌警策的方式固然有所不同,但在诸如从整体上追求诗的陌生化方面,宋明以来诗家通过处置诗歌中的闲言助字,来求得诗品诗格的不同凡俗的讨论,与欧美结构主义学派和形式主义批评中有些论述,其实并无二致。要之,一个是诗与乐从其发端到流变从来联系密切,是为诗乐一体;一个是抒情诗在词根上就与乐器有关,决定了其自由抒写必定不离节奏,并只有赖富有形式感的整赡节奏才能真正实现。 所以就诗歌内蕴的营造而言, 个人*在意的是前已述及的写出自己直接感知到的心底的真实,并因为有意赋予这种真实以*广大的指向,而不免常以诗人所谓“此时此刻我在说一件事情,而在表达时我所说的也许又有些超出那件事情”为极诣。而在形式上,如果说新诗的确存在自由体和格律体的大致分野,那么自己*愿左右采获,务求综合其所长,尤其希望能打通古今与中西的界域,*充分地开显创作背后所隐蓄的中国文化的底色。 这个说起来容易,要做好很难。好在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一百四十首诗,都是写个人在欧洲的行历。欧洲的历史与文化同样悠久而复杂,许多此前根本不了解,有的虽略知一二,一旦身临其境,仍不免惊诧莫名。由此产生的心灵震撼,不作诗真不知如何消解。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似天然地就在写作之初,要求自己*多地投入,化身为客观而不偏狭的异文化的观察者。与此同时,提醒不要忘了比量从来的传统,检视自己的内心,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这是自己所见到的欧洲,又因为是在诗中,它可能并未这样发生,甚至并未真实展开过,只是被自己的“误读”,唤出了它将要到来的可能。这样的幽窈惝恍,本身就**诗歌。 现在,再看这些旅途中草成的歌吟,回忆十年间行过的每一处川原和山峦,它诞育于大地的灿烂文明,自带光环,是那样富有诗意甚至神性地根扎在欧罗巴厚实的土壤,和每一块不可思议的岩石的缝隙,而它精神的枝条,仍借着这块土地上伟大人物的不朽创造,既通过文物制度,也每借助色彩和音符,在阳光下向我招摇。这当中,自然不会少诗人,譬如在塞特和蒙彼利埃的瓦雷里,他的故居、博物馆和滨海墓地,直接引动了我郁勃的诗兴。故除收入集中的墓前吟唱外,我另口占了一首七律,贴在早已空无一物的他故居的门前:“簇锦篱花照眼青,萧森柏树属云停。曾传孤耿欣神助,还剩清衷赖鬼听。目想日迟能去海,魂招风软不来庭。问随心事归何处,分与浮生到杳冥。” 在我快写完这篇后记时,亚平宁半岛的太阳想必已经升起,莱芒湖的鹅也开始从温暖的翅膀中探出它们的头,等着下一个十年,还会去履踪未及的每一个地方的我,应该还会被许多的风景和人感动。这样的情景,太像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丁尼生《尤利西斯》所写的:“尚未游历的世界在门外闪光,而随着我们一步一步去前行,它的边界也不断向后退让”,“尽管已达到的多,未知的也多啊”,“几次生命堆积起来尚嫌太少,何况我**的生命已余年无多”。 汪涌豪 二〇一九年春分 ◆行走在欧洲文明中,捕捉历史的回声 诗人踏遍欧洲,探寻旖旎的自然风光,走访诸多人文景观,但这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因为有诗为证。无论是帕特农神庙的历史荣耀、佛罗伦萨的艺术殿堂,还是如调色盘一般浓烈的巴黎,诗歌记录下欧洲土地上伟大君主的起起落落,记录下永恒的艺术家们不灭的作品,也记录下某个想象的瞬间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阅读这部诗集,读者仿佛跟随诗人一道,重回历史现场,重温人类文明的高光时刻。 ◆打破古今与中西诗歌的界限 千百年来,诗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是语言的精华。诗包含了动人的韵律与节奏、丰富的修辞与意象、多重情感张力,因此能直达读者心底。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诗人在摆脱旧体诗束缚的同时,吸取外域文学之所长,形成一套新诗格律。诗人在这部诗集中,继承前人定下的新诗传统,也努力不落入新诗随意松散的窠臼,采自由体与格律体之所长,力图打破古今与中西的诗歌界限,充分显示创作背后的中国文化底色。 ◆呈现不一样的学院派诗人 公众与媒体眼中的汪涌豪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著称,在这部诗集中,他展现出对于欧洲文明的**学养,熟稔各种典故与渊源。但这些诗作并非是意象堆砌和文字炫技,每首诗歌背后浸润着诗人对人类文明的敬意,对真实与美好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