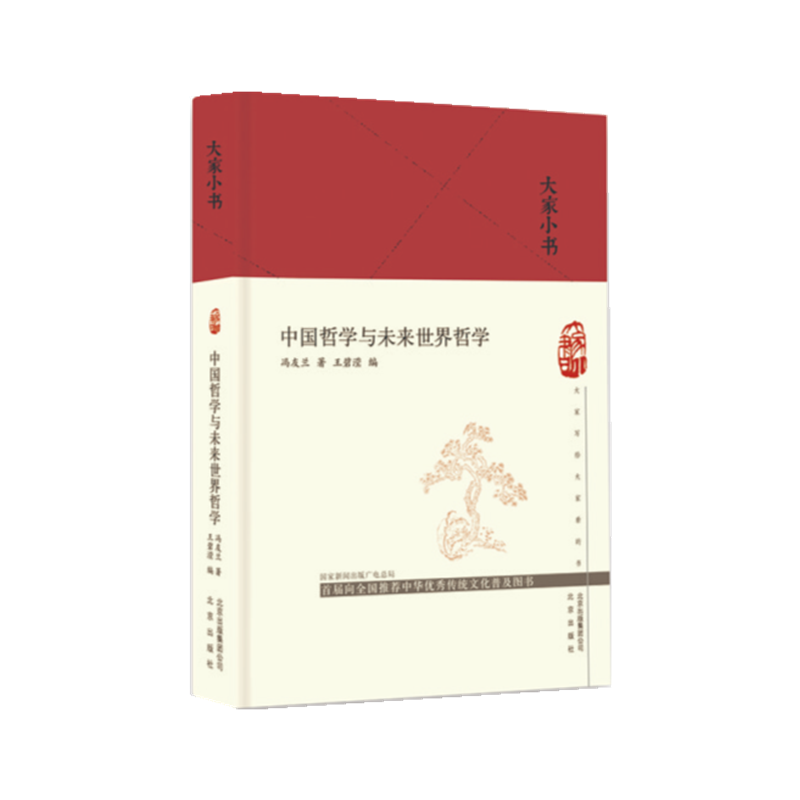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8.40
折扣购买: 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精)
ISBN: 9787200150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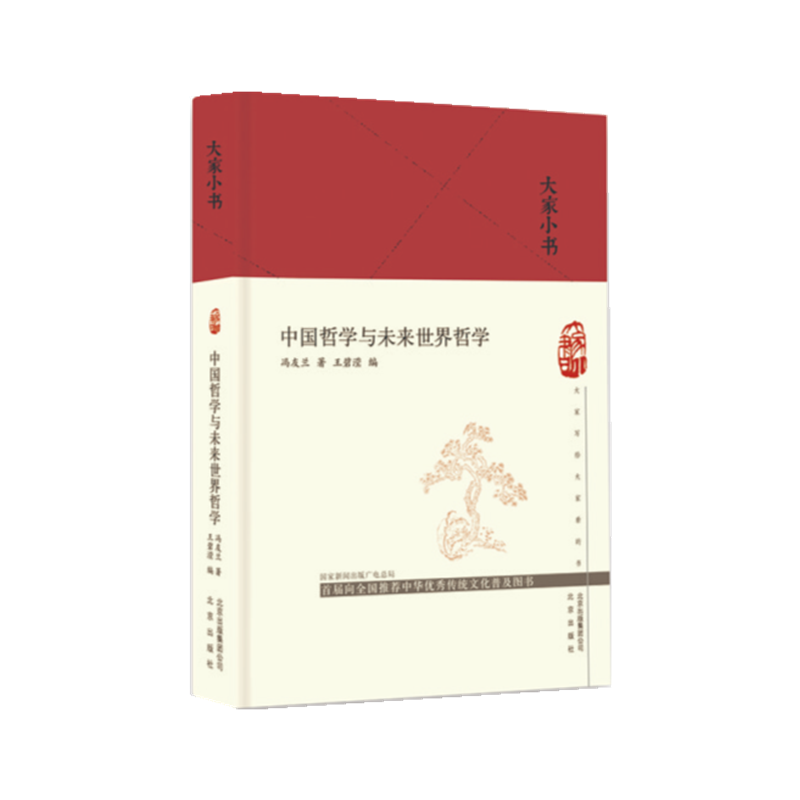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曾就学于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52 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是近代以来能够建立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其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影响深远。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局面尽管看来混乱,可是中国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哲学思维,却有了伟大的进步。这并不出人意外。中国的混乱,是中国社会性质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方面。在这场转变中,造成了新旧生活方式之间的真空,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古老废弃,新的生活方式仍然有待于接受。这样的真空,十分不便于实际日常生活,但是很有利于哲学,哲学总是繁荣于没有教条或成规约束的人类精神自由运动的时代。 在转变时期,过去的一切观念、理想,都要重新审查,重新估价,在这点上一律平等,哪个也不能要求比别个具有更大的权威。进行重新审查、重新估价的人是哲学家,他由此达到的观点,要比自限于单一思路的人高得多。 在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变中,哲学家们特别幸运,因为自本世纪初以来,他们重新审查、估价的对象,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过去的观念、理想,而且有西方的过去和现在的观念、理想。欧洲、亚洲各个伟大的心灵所曾提出的体系,现在都从新的角度,在新的光辉照耀下,加以观察和理解。随着哲学中新兴趣的兴起,老兴趣也复兴了。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当代中国思想竟无伟大的变革,倒是非常可怪了。 变革已经发生,速度很快。许多观点已经表达出来了,只是又被后来的观点取而代之,后来的观点则是更多地研究和理解西方哲学的结果。我自己的观点也会被取而代之,虽然如此,我还是把它表达出来,说明中西哲学如何可以互相补充,以及在这种互相补充中,中国思想如何对未来世界哲学可以有所贡献。我只讲两点:一点是哲学使用的方法,一点是由哲学达到的理想人生。 中西哲学必有某种根本的相似之点,否则就没有理由把它们都叫作哲学。分析它们的相似之点时,我基本上限于它们的形上学学说,或限于有形上涵义的认识论学说,因为只有在这里最容易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在西方哲学中我提出两个主要传统,柏拉图传统和康德传统,以供讨论,并与中国哲学中两个主要传统,儒家传统和道家传统,进行比较。柏拉图传统和儒家传统,代表着形上学中可以称为本体论的路子;而康德传统和道家传统,就其形上学或其哲学的形上学涵义而论,代表着可以称为认识论的路子。有一点强烈地吸引着我,就是,尽管形上学的目的是对经验做理智的分析,可是这些路子全都各自达到“某物”,这“某物”在逻辑上不是理智的对象,因而理智不能对它做分析。这不是因为理智无能,而是因为“某物”是这样的东西:对它做理智的分析就陷入逻辑的矛盾。 本体论的路子,开始于区别事物的性质与事物的存在。正如柏拉图学说的当代解释者乔治·桑塔耶纳所说:“像公理一样自明的是:事物若没有性质就没有存在;只有有某种性质的事物才能存在。但是存在就有变化,或有变化之虞;事物能够变形,或换句话说,事物可以丢掉一个本质而拾起另一个本质。”[鲁尼斯(D.D.Runes)编:《二十世纪的哲学》,第315页]这个路子展现出关于本质的逻辑同一性和永恒性,这些当然都是理智的对象。但是,拾起本质、丢掉本质的那个“存在”又是什么?理智在分析某一事物时,将其性质一一抽去,抽至无可再抽,只觉得总还剩下“某物”,它没有任何性质,但是具有任何性质的事物都靠它才存在。 这个“某物”,在柏拉图学说中叫作“买特”(matter);柏拉图说它“能接受一切形式”,所以“不可以有形式”(柏拉图:《蒂迈欧》)。“买特”不可分析,不是因为理智无能,而是因为凡是可以分析者一定具有某种性质。凡是具有性质者就不是叫作“买特”的“某物”了。 有些哲学家不喜欢柏拉图这个“买特”概念,想说“事件”或“物质”,在作为“材料”的意义上,才是宇宙最后的存在。但是这样的想法不是严格的理智分析。我得说,这些哲学家是错在把某些代表实际科学知识的实证观念,当成最后的了,这些实证的观念不是逻辑分析得出的形式的观念。“事件”或“材料”不过是另一类的事物,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即使接受“事件”的说法,可是一个事件或一块材料又得分解为无性质的“某物”加上某性质。 中国哲学中的儒家,从它最初之日起,就尊重“名”,认为名代表人类行为的原则或德性的本质。儒家学说这一方面的形上学涵义,在朱熹的体系中发挥至极。朱熹体系成为中国正统的国家哲学,是从13世纪起,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将帝制连同国家哲学一起推翻为止。若将朱熹的形上学体系与柏拉图的形上学体系加以比较,就会对这两位伟大哲学家的相似之处有很深的印象。不过朱熹并不认为实际世界只是理(Ideas)的不完全的摹本,而无宁是理的具体实现。在这方面,朱熹是沿着柏拉图的伟大门徒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活动的[参阅冯友兰:《朱熹哲学》,布德(Derk Bodde)英译,载《哈佛亚细亚研究学报》1942年第七期,第1~51页(中文原文载《清华学报》第七卷第二期)]。 正像本体论的路子开始于区分事物的形式和质料,认识论的路子区分知识的形式和质料。后者正是康德所做的事。照康德说,知识的形式,如时间、空间,以及传统逻辑讨论的诸范畴,都是人的认识能力中固有的。靠这种能力人能够有知识。但是人的知识所包括的仅仅是其形式之内的东西,因而与形式混合在一起,不能分开。在理想中与这些形式有区别的东西可以叫作知识的质料,但是它究竟是什么,人不得而知。这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或“本相”(noumenon),人不能知道它,人只能知道“现相”(phenomenon)。人不能知道“自在之物”,并非因为人的智力不足,而只是因为,如果叫作“自在之物”的东西当真可知,它就必然也只是另一个现相,而不是“自在之物”。 因此康德主张,有个“界线”存在于知与未知之间——未知的意思不是尚未知,而是不可知。康德说,界线“看来就是占满的空间(即经验)与空虚的空间(我们对它毫无所知,即本相)的接触点”[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卡勒斯(Paul Cams)英译本,第125页]。他继续说,“不过,既然界线本身是一个肯定的东西,它既属于在它里边所包含的东西,又属于存在于既定的总和以外的天地,因此它也仍然是一个实在的肯定认识,理性只有把它自身扩展到这个界线时才能得到这种认识,但不要打算越过这个界线”[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卡勒斯(Paul Carus)英译本,第133页]。 就一个方面说,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与康德之说相同。道家也区分可知与不可知。儒家以为,名代表原则或本质,原则或本质是实际世界中事物的标准;道家则以为,名代表主观的区别,主观的区别是人类智力造成的。“名言”这个名词是道家常用的。“言”是语言,用“名言”这个名词,道家将“名”归结为语言的事,这就必然与知识相联。人的知识只能通过名言。但是名言背后、名言之外,是什么呢?那就是“某物”,它在原则上,根据定义,是不可知的。用康德的术语说,那个某物在界线的彼岸,可以描述为“虚”(void)。这恰好就是道家用来描述界线彼岸的词。道家惯于将界线彼岸描述为“无”,意思是not-being,为“虚”,意思是void。 我只说在一个方面道家与康德相同,在另一方面道家则与康德不同。在伦理学,或康德称为道德形上学方面,他十分吻合儒家,特别是他的“无上命令”之说及其形上学基础,更为吻合。但是专就区分可知与不可知而论,康德与道家十分吻合。 但是,即使在这一方面,他们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康德似乎看出,靠纯粹理性的帮助,没有越过界线的道路。在他的体系中,不论纯粹理性做出多大努力去越过界线,它也总是留在界线的此岸。这种努力有些像道家说的“形与影竞走”。但是看来道家却用纯粹理性真的越过界线走到彼岸了。道家的越过并非康德所说的辩证使用理性的结果,实际上这完全不是越过,而无宁是否定理性。否定理性,本身也是理性活动,正如自杀的人用他自己的一个活动杀他自己。 由否定理性,得到道家所说的“浑沌之地”。若问:由否定理性,是否真正越过了界线?此问没有意义。因为照康德与道家所说,这个界线是理性自己所设。随着理性的否定,也就不再有要越过的界线了。在事实上,越过界线就是取消界线。若问:越过或取消界线之后,有何发现?此问亦没有意义。因为照康德与道家所说,辨认一物不过是理性的功能。随着理性的否定,也就无所谓辨认了。 在道家看来,康德常用的“自在之物”这个名词,是一个十足误人的名词,因为它有肯定的意义,给人以错误的印象,好比说,我面前这张桌子只是一个假象,真正的桌子却在它的背后,那才是“自在之物”。当然,越过界线的东西不能用像“桌子”这样的词来描述,但是也不能用像“真正的”这样的术语来指称。它只能用否定的名词来表示。最后,连这个否定的符号也必须自身否定之。因此,谁若对道家有正确的理解,谁就会看出,到了最后就无可言说,只有静默。在静默中也就越过界线达到彼岸。这就是我所谓的形上学的负的方法,道家使用得最多。禅宗也使用它。禅宗是在道家影响之下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佛教的一个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