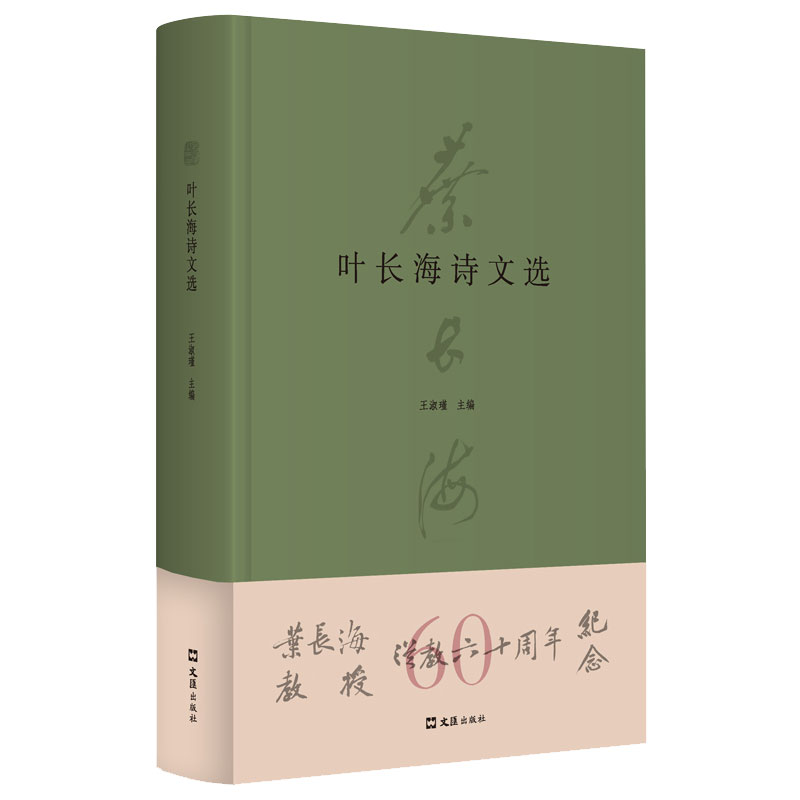
出版社: 文汇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3.70
折扣购买: 叶长海诗文选
ISBN: 9787549639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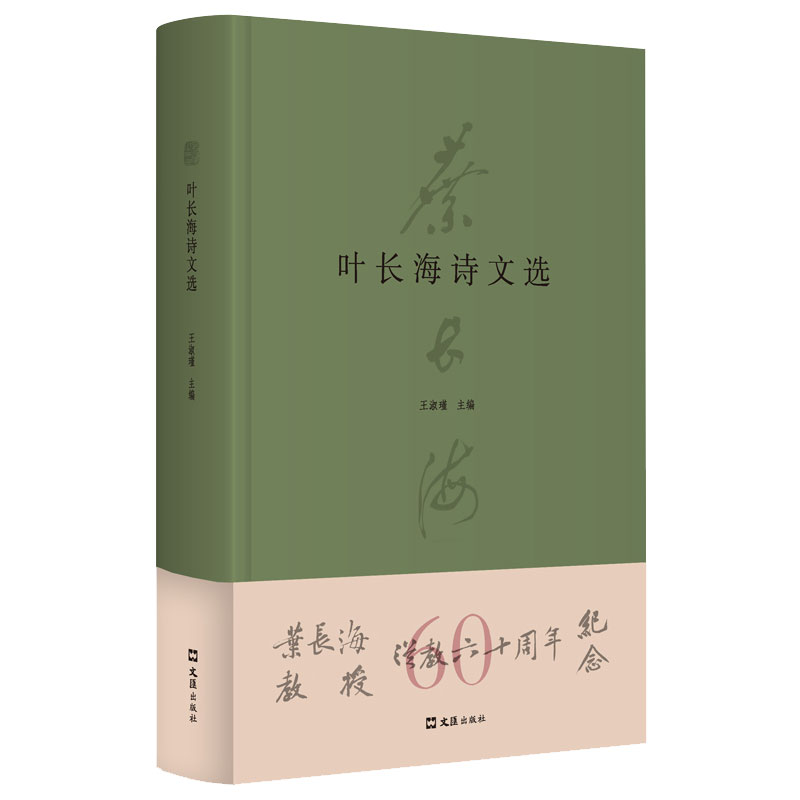
王淑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研究方向为中国戏曲史,获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学位,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并出版有散文集。历任上海译文出版社《ELLE》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新发现》主编、《周末画报》华东区主编、一条视频总编辑。创办一条艺术。
沉潜于艺术的学者 王淑瑾 自学成才,半路出家 浙江永嘉是中国南戏的故乡,宋代以来,永嘉地区人杰地灵,戏剧英才辈出。一九四四年五月,叶长海先生浸润着艺术精神出生于斯地。 谈起人生经历,叶长海老师总是说:“我作学术研究是半路出家,从事教育才是少年功夫。”这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一段颠沛的历史中所遭逢的特殊际遇。他会笑着告诉学生,除了学龄前的孩子,他这一生的教授对象从小学生、中学生到博士生、博士后,真正是桃李满天下。 时间回到一九六二年。十八岁的叶长海从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在故乡的小学、中学开始最初的教师生涯。工作没多久,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有一段时间几乎是“停课闹革命”。叶长海老师曾经做过有七十五个中学生的班级班主任,并担任两个班共一百五十人的语文课老师。当时他年纪轻,劲头足,工作出色,不久被调去温州市中心的中学任教。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叶老师的二十二到三十二岁,他做过中学历史老师、音乐老师和语文老师。真正的青春年华都被“文革”占据了,大学梦难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叶老师和他的同龄人却读了一部最深刻的“历史剧”甚至亲历其中。当看到了身边的权力更替、人事沉浮,再回过头来读中国历史理解就和以往完全不同了。但当时,叶老师对于自己的前途非常担忧,他不知道哪年哪月“文革”会结束。不过,他与几位朋友坚信,若干年后,国家将缺乏各种实在的人才,因而他们在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如饥似渴地读书。求知就是他的精神信仰。 叶长海老师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在读书,文史哲不分。他觉得人生就是这么吊诡,要是当初进了他朝思暮想的大学中文系,学术基础和视野可能反而会受到限制。后来,他在一九七九年上海戏剧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表现出广博的文史阅读量,就是这段自学经历的最好注解。他说:什么东西都要自己琢磨,知识结构慢慢形成,这实际上是锻炼了自学的能力。他说的这种“自学”能力,实际上包括能自寻老师,“转益多师”的能力。 大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文革”后期,有人给他介绍了温州的郑西村先生。郑先生是戏曲专家,对古典音乐也有独到见解。于是,叶老师经常去老先生家里,聊音乐史和戏曲史,得余闲时则吟诗填词。一时间曾下苦功研究宋词音乐,对姜白石十七首词的旁谱,尝试着搞出一个新体系,并请人弹琵琶演唱。至今,他还保留着那时的录音。 事实正是如此。在“文革”结束后全国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中,相当大比例的人是没有念过大学的,有很多读过大学的考生在这些人面前反而落败了。叶老师感慨地说:“这说明当时靠自学获得的知识还是比较全面的。不论在什么环境里,人们都有可能自己设计自己,摸索出一套自学前进的方法。” 读万卷书,“两翼”齐飞 一九七九年秋天,叶老师正式成为“文革”后上海戏剧学院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师从昆曲专家陈古虞教授和戏曲理论家陈多教授。那一届共有四位同学,学的分别是中国戏曲史、外国戏剧史、中国话剧史和戏剧创作理论,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戏剧界非常有造诣的专家。同一个宿舍里,学中外古今的都有了,这对于每位同学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安排”,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聊戏剧。关于那段经历,叶老师还写过一篇散文,叫作《小屋的回忆》。 叶老师至今都很清晰地记得戏剧学院那些各具特色的老师,说起他们的故事如数家珍。陈古虞教授很有个性,他原是北大西语系出身,专攻英语及莎士比亚戏剧,课余却迷恋着昆曲,唱演俱佳,尤以研究北昆著名。另一位导师陈多教授,博学多才,学术个性强,富于论辩。陈多老师曾经在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古剧考略》,他认为《诗经》里有一些篇目是当时歌舞剧演出的唱词。其实这个观点是由闻一多先生的观点发展而来的。闻一多认为《九歌》就是一部古代的歌舞剧。但这些新见解很少有人赞同。叶老师却认为闻一多讲得不错,他说:“我觉得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读书结果。有人把戏曲当诗来读,有人则在诗中读出了戏剧。前者往往是文学家,而后者往往是艺术家。”陈多教授的理论创新精神和做事认真的特点,也在日后深深影响了叶老师。 硕士学位论文,叶老师写了十二万字的《王骥德〈曲律〉研究》,在答辩会上,七位委员老师一致予以佳评。王骥德在戏曲理论史上的重要性现今已是众所周知,但在叶老师之前,还没有人如此系统、深入地研究过这位晚明曲家。叶老师从现存很少的资料中考述了王骥德的生平、行实、著作以及《曲律》一书的写作过程,阐述家庭、师友、社会等因素对其文艺观念、人生态度的影响,其中对万历年间戏曲创作流派的分析更显示出独到的学术眼光。后来论文出版,答辩委员会主任赵景深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篇近年难得看到的、高质量的论文。”现在,我们只有了解一九八一年前后中国研究界在沉寂多年后取得的卓然成绩以及赵先生评骘学问的严格态度,才能体会这句话的分量。次年,论文即获得“首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叶老师的学术丰收期。那时,在艺术领域中,学科意识普遍比较薄弱。经过长期的思索,叶老师在《中国古代戏剧学绪说》中率先提出“中国戏剧学”这一概念,并从理论上阐明其内涵和外延。在研究中国戏剧历史的时候,他试图从建立学科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以学科史的方法来进行写作。这个观念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一九八六年,凝结着他心血的五十万字的《中国戏剧学史稿》面世。此书和以往介绍戏剧史的书不同,一般戏剧史论述的是戏剧的历史,而此书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是从世界性的视野论述了中国戏剧学的基本内容及学科的形成历史。同时,它与理论批评史也是不同的。理论批评史主要是梳理理论著作,而从戏剧学的角度来说,有些材料性、技术性的东西也要给予整理与考释。从戏剧学的角度即学科的角度来看,同戏剧有关的知识、材料、理论,都有必要做一个全面的考察。所以,此书是戏剧学观念的实证,也是中国戏剧学在实践上的真正创见,它的问世引起当时戏剧界与学术界的瞩目,并成为少见的学术畅销书。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早就希冀有一部属于中国自己的戏剧学研究著作问世,从而早日改变以往在本学科研究中多照搬西方,唯独缺少自我的不正常现象。无日地等待,不如自己先摸索着干起来。本书正是这种探求的产物。”这本著作后来分别荣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首届文化部直属艺术院校优秀专业教材奖,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为中国戏剧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叶老师研究的领域中,同戏剧学非常相近的,就是曲学。曲学属于中国传统的学科概念,文学史上有诗、词、曲,因而也就有了诗学、词学和曲学。诗词曲作为“韵文”,本身包蕴着文学性和音乐性两个方面,有人称之为“音乐文学”,其中的“曲”,尤其是戏曲部分,除了文学性和音乐性之外,还会牵涉到表演和剧场,也就是与演出艺术的结合。所以在叶老师看来,“曲学”有狭义曲学、广义曲学的不同概念,应当把它们区分开。他创办《曲学》杂志,也是试图将曲学研究放在学科的框架中来思考,这既是对狭义曲学研究的深入,同时又是对广义曲学研究的空间拓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叶老师的学术研究主要就是上述的“戏剧学”与“曲学”,当时一些论文也是关于这方面的。在他出版的论文集《曲学与戏剧学》的自序中,他界定了“曲学”与“戏剧学”这两个分别源于东西方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戏剧学”除研究戏剧的艺术问题外,还要研究剧场演出活动中一些非艺术问题,如舞台建筑、剧场管理等;而中国“曲学”着力甚多的是唱腔音律问题。两者“实则有着相对应而又相交叉的关系”。他对中国戏剧学和曲学理论的精深阐发充分显示了他的研究个性与学术成就,为中国文学史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 近年来,叶老师主编着两种刊物,一种名为《曲学》,另一种名为《戏剧学》,两者正从学科高度勾勒着这位大学者毕生的研究领域。 行万里路,开辟新领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叶老师的学术研究在一些领域有新的开拓。他有一个心愿是为中国艺术学的建设作出努力。其时,他开始研读中国古代书画论。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写成了《石涛画语录心解》,同期写成的还有《中国艺术虚实论》。当时他是想将画论作为研究的突破口,从画论、乐论、曲论三方面着手,梳理出艺术学的概念。 但由于身在戏剧学院,其主要工作任务是为戏剧艺术事业教书育人,因而叶老师对中国戏曲现状的关注及对曲学、戏剧学的理论思考不能间断。十年间,他相继出版了《戏剧:发生与生态》(1990)、《当代戏剧启示录》(1991)、《曲律与曲学》(1993)、《中国艺术虚实论》(1997)、《曲学与戏剧学》(1999)等著作,并参与主持了《元曲鉴赏辞典》(1990)、《中国曲学大辞典》(1997)、《中国京剧》(1999)等重要工具书与大型画册的编撰工作。 自从“戏剧戏曲学”申请到了上海市的重点学科后,经过数年努力,该学科又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十多年里,国家一直在大力支持,希望这门学科发展壮大。作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叶老师始终在考虑如何将这门学科打造成全国一流的、有世界对话意义的学科,或者以后能把它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学科。学科建设的工作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 在这门学科里,他特别加强对一些薄弱环节的研究,比如对中国戏曲剧种、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的调查研究等。同时,他也专注于世界民族戏剧的研究,他认为不能只知道希腊戏剧,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戏剧都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近期他的一个重要设想是推动对中国同周边国家戏剧的互相影响交融的研究,这也是相当大的课题,其所涉及的有西部(丝绸之路)、西南部(印度文化)、东部跨海,等等。而研究该课题比较有利的做法是从汉文字圈入手。“汉文字圈”其实就是古代中国以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中国文化对东亚这些国家的影响当然很大,其中也包括戏剧,而且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也不可忽视。经过比较分析,叶老师发现,研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已有不少成果,而研究最薄弱的就是琉球。于是他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研究思考琉球演剧历史,以及它和古代中国的戏剧交流。他在上戏成立了研究小组,两度奔赴冲绳考察。在他的书房里,关于琉球的研究资料都放在最显眼处。历史上,琉球作为独立王国于明朝初年同中国建立了宗藩关系。当他们的新国王登基时,中国朝廷会派遣册封团渡海为之册封加冕。明清两朝一共二十多次派团赴琉,册封过程中包含大量的戏剧演出,这正是最宝贵的研究资料。所以叶老师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中国文献,尤其是从册封使的记录中寻找中国与琉球的演剧交流,另外就是从日语文献中考察,从这两方面寻找琉球戏剧演出的历史。在中国学人与日本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已有一批学术成果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叶老师撰写的《琉球演艺初识》及《明清册封使记录的琉球演剧》已先后完成。这些成果,为东方戏剧的研究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进入新世纪,叶老师陆续担任上海戏剧学院诸多重要职务,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他在学校里匆忙的身影。他仍以充沛的精力关注着“戏剧学”学科的新发展,并带领青年学人在学术领域不断开拓。在学校,所有同学提及叶老师,都感佩于他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教书育人的奉献精神。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上戏“戏剧学”学科建设的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其前景是很宏大的。 有一次在扬州大学参加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该校的研究生请叶老师谈谈他个人的学术经历,他半开玩笑地说:“‘文革’之后的二十年,八十年代,读万卷书;九十年代,行万里路,学术的脉络基本是这样的。” 以乐载情,以诗言志 谈及个人兴趣爱好,叶老师最津津乐道的是音乐和诗词。 他秉性聪颖,凡事喜欢自学,笛子、二胡、钢琴、小提琴都曾有过自学的经历。他的二胡演奏甚至达到相当专业的水准。由于爱好音乐的缘故,他在“文革”后期同几位师友相与调查温州永嘉昆曲,让老艺人们唱曲,为他们作记录。这对他后来的戏曲研究大有裨益。戏曲是一种总体性的艺术,里面有大量关于音乐的内容。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曲律》,这里就牵涉到很多音乐史的问题。 叶老师曾写过许多关于故乡的诗文,其中有一首得意之作,那就是为温州地标景点江心屿写的歌词。自一千六百年前谢灵运写下《登江中孤屿》一诗,瓯江的江心屿便被称为“诗岛”。叶老师青少年时期就住在瓯江边,对江心屿很有感情,他写了一首浓缩他们那代年轻人真情实感的《情系江心屿》,由他的好朋友潘悟霖作了曲。“每当清风吹拂的月夜,涛声送人怡然入梦。为什么久久地萦怀,那满江闪烁的灯影?噢,故人的才情故园的魂,在人间化作新的生命……”他至今还能唱起这首感情深挚的歌曲。这首歌还曾在一次浙江省的歌曲比赛中获奖。 无论在怎样的学术境遇中,叶老师始终坚持旧体诗词写作,这也是他寄托情感的最佳方式。他认为诗词凝聚了一个人的人生感悟,也结晶了一个人的时空情怀。在最近创作的七律《人生七十》中,他写道: 尘世喧阗岁月催,闲吟难得翰为媒。 园边已老东坡竹,座上初停北海杯。 逝水岂从今夕尽,新株犹待别时栽。 年来疏问纷繁事,唯有家山常梦回。 朝去暮来,叶老师从“半路出家”从事戏剧学术研究,至今已经整整四十个年头,度过了极其艰辛而硕果累累的岁月。他为中国戏剧学和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艺术教育付出了毕生心力,做出了丰伟的贡献。虽然已到古稀之年, 但其壮心未已,正如他在这首诗中所吟唱的:“逝水岂从今夕尽, 新株犹待别时栽。” 二〇一九年七月 回 首 叶长海 检点从来百事疏, 身随世运自乘除。 青春逐梦路千里, 白首还家酒一壶。 未尽文章磨岁月, 尚多生趣付江湖。 平居孰道东风老, 更有秋怀在客途。 朝去暮来,叶老师从“半路出家”从事戏剧学术研究,至今已经整整六十个年头,度过了极其艰辛而硕果累累的岁月。他为中国戏剧学和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艺术教育付出了毕生心力,做出了丰伟的贡献。虽然已到古稀之年, 但其壮心未已,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吟唱的:“逝水岂从今夕尽, 新株犹待别时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