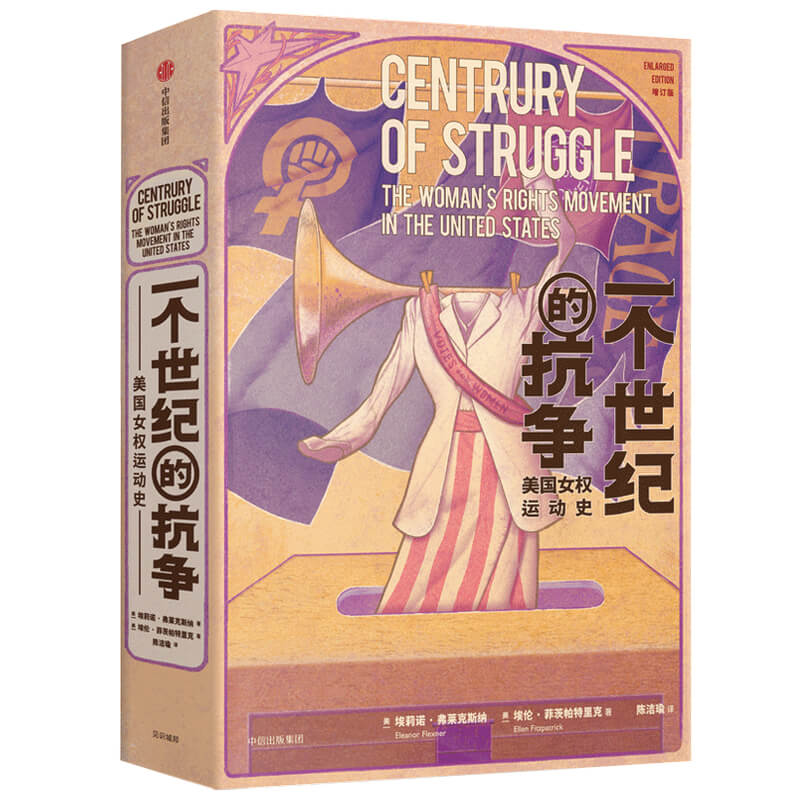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6.40
折扣购买: 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增订版)(精)
ISBN: 9787521708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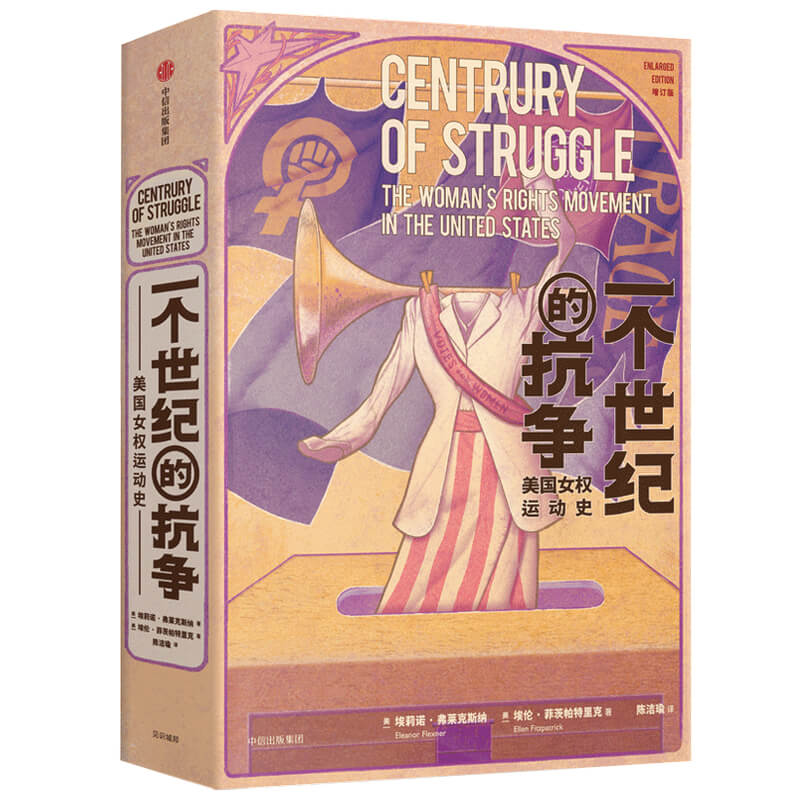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生于肯塔基州的乔治敦,是美国杰出的独立学者,妇女研究领域的先驱。她从小就显露出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后,她继续在牛津大学深造。弗莱克斯纳于1936年加入共产党,从事社会和政治工作,这激发了她对女性议题的关注。整个40年代,弗莱克斯纳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工作和组织活动填满。这些事让她越来越了解工人的艰辛斗争,越发意识到性别歧视的严重性,也让她看到了社会运动的艰巨性。50年代初,弗莱克斯纳的想法从写一本关于女性历史的书,逐渐细化为写一本关于妇女参政权运动的书。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种激情,找到了贯穿参政权运动的矢志不渝的决心、令人心碎的挫折感,以及无与伦比的兴奋之情。《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妇女权利斗争细致而精彩的叙述,而且呈现了从殖民时代开始的妇女历史经历的全景图。;.;艾伦?菲茨帕特里克,拥有布兰代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是专攻美国现代政治和思想史的教授和学者、新罕布什尔大学历史学教授,曾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任教,著有《致杰基的信:悲痛国家的哀悼》(Letters to Jackie: Condolences from a Grieving Nation)《最gao的玻璃天花板:距离美国总统最近的女人》(The Highest Glass Ceiling: Women's Quest for the American Presidency)等。
前言 您手中的这本书,讲述的是美国历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争取女性参政权的斗争,可谓一场持续时间最长、最成功的斗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美国政治选举体系所发起的最激进的挑战。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数百万人为争取妇女的参政权,矢志不渝地斗争着。许多倡导妇女参政的先驱从未在有生之年品尝过自己奋斗的果实。另外一些人虽然看到了成功,但却注定要面对这场艰难的胜利所带来的某些让人沮丧的后果。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女性因为习俗、惯例和法律等因素,无法拥有正式的政治权利和责任,这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而正是这种权利和责任,支撑并维持着美国当时还年轻的民主制度。然而,妇女无权正式参与大多数政治选举这一事实,却持续了一百多年。妇女参政权论者深知,投票权不仅仅意味着能够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投票,它还会唤起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将不再会因为性别而被区分对待,每个人都会平等地享受公民待遇,每个人也都肩负着维持社会有序运转以及创造共和国未来的责任。不仅如此,投票权也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敲门砖。在家庭之外的广袤世界里,有着财富的汇聚和观点的交锋。只有参与公共事务中去,才有可能把控未来。这些,仅凭旁观政策制定和被动地寻找对应的策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很长一个时期,妇女都无法拥有参政权。这不单单是因为当时主流观点认为妇女的身份和能力不足以参与选举,也是因为某些人精心策划阴谋、公然阻碍妇女行使民主权利。而在许多方面,相比反对势力的阴谋,关于男性和女性特质和责任的固有观念更加难以颠覆。事实上,妇女参政论者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障碍,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成见。女性从小就受到这种观念的灌输,她们认为自己应该待在家中,自己的首要职责是照顾和维系家庭。挑战甚至颠覆这些约束妇女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观念,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视野的。 有些女性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质疑甚至抛弃了主流道德标准。但如果她们想要改变社会,就必须更进一步。她们需要创造一种方法,让世人看到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桎梏,同时她们又必须防止自己的抗争被世人视为一种病态的表现,或是被嗤为不服从社会规范的人的无端妄想。这对参政论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宗教领袖,特别是在19世纪出现的所谓的“科学家”,不断地在为女性天性被动和从属于家庭的特质提供长篇大论的理论支撑。也许,参政论权者最艰巨的任务,是在公开场合明确反抗不公——公开演讲本身就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质的挑战。她们必须说服那些盲目接受陈规陋习的人,让他们重新审视当时的价值观和习俗,尽管这些东西看上去无可指摘、无懈可击,也从未受到公共政策的约束。 重任在身,数以百万名男人和女人投入漫长的争取参政权的运动之中。还有更多的人在热切关注着这场运动的进程,他们为参政论者们争取女性平等政治权利的决心而鼓掌喝彩。他们的支持维系着这场运动,让它走过风雨,迎来彩虹。1920年8月,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正式把女性参政权纳入国家政策。对好几代参政论者来说,这意味着一场胜利,虽然它曾经看上去那么遥不可及。 在近代美国政治史上,参政权运动的戏剧性是其他历史事件所不能企及的。然而,大部分美国历史学家很少关注妇女争取参政权的故事。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决定撰写这本书时,才有所改变。尽管历史学家似乎觉得有必要记录赋予妇女参政权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获得批准的情况,但是很少有人会去探究带来这一重大变革的漫长社会运动以及这场运动背后的力量。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她本人就是一名积极的参政论者。她的丈夫查尔斯?比尔德虽然没有她积极,但也深受参政权论的影响,两人有时还会合作著书。在《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一书中,比尔德夫妇阐述了妇女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玛丽?比尔德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做了许多关于妇女和政治的工作,堪称此领域的先驱。 然而,在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百年抗争》问世之前,许多关于女性参政权的历史著作都是由那些本身参与过参政权斗争的女权主义者所撰写的。弗莱克斯纳在参考文献中写道,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苏珊?安东尼(Susan Anthony)以及玛蒂尔达?凯奇(Mathilda Cage)曾在1881—1886年编纂过《女性参政史》(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的前三卷,她们为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三卷书发表于女权主义者取得胜利之前。第四卷发表于1902年,由苏珊?安东尼和艾达?哈珀(Ida Harper)共同编纂。第五卷和第六卷均发表于1922年,由艾达?哈珀独立编纂。弗莱克斯纳指出,后三卷书都存在着历史分析不充分的问题,而且在描绘历史事件时,过于强调记录人名、日期、事件和区域性胜利。当然,她们对构建参政权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努力是不可抹杀的,她们也为弗莱克斯纳以及之后的历史学家进行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但是,可以想见的是,早期编年史家所描绘的妇女参政权运动缺乏“客观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参政权运动的参与者。 虽然当时有一些零星的历史记录,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提笔撰写《百年抗争》时,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话题。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是什么促使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把视线集中到妇女参政权运动上的呢?个中原因很复杂。尽管弗莱克斯纳本人并未承认过,但她的家庭经历无疑对她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她父母的人生,本身就折射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塑造女性主义的多股力量。埃莉诺的母亲安妮?克劳福德?弗莱克斯纳(Anne Crawford Flexner)对《百年抗争》的写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5年,安妮从瓦萨学院毕业,当时美国的女大学毕业生还为数不多。毕业后,安妮成了一名颇有声望的剧作家。她对民间故事《卷心菜屯的威格斯夫人》 的戏剧改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让她从此生活富足。正因为安妮为埃莉诺留下了足够的财产,埃莉诺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本书的研究和创作。 弗莱克斯纳的父母都是女性参政权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并肩参加了1915年夏天在纽约举行的妇女争取参政权的大游行。晚年的弗莱克斯纳对这桩童年往事依然记忆犹新:“那个夏天,小儿麻痹症流行,而我得了风湿热。我父母从外面回来,穿着白色的衣服,他们得把衣服全换了,才敢进我的房间。”弗莱克斯纳的父亲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他在社会和公共事务方面的进步观点远近闻名。此外,他还是一位著作颇丰的作家。1910年,他发表了关于美国医学教育的报告,影响深远。他的著作还涉及包括教育在内的广泛社会议题。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而言,有如此成功的父母有时像是一种负担。她后来回忆说,“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亚伯?弗莱克斯纳的女儿”,这让她感到厌倦。“每当有人介绍我的时候,就会有人问,到底是弗莱克斯纳家的哪个?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让我的名字不依赖于父母而独立存在。” 除了父母的影响之外,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从小就显露出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她就读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ague),主修历史和英语,还参与了一个强调小班教学的创新荣誉课程。她本科论文的主题是玛丽?都铎(Mary Tudor),这篇论文为她赢得了奖学金,可以去牛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深造。1930年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后,埃莉诺就去了牛津。在那里,她继续学习历史。但遗憾的是,因为她之前接受了多年的新式教育,所以她的拉丁文并不能达到获得牛津大学学位的要求。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历史学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准备论文写作的研究过程中,她需要阅读大量一手文献,而埃莉诺对整个过程甘之如饴。 相比家庭影响、学术兴趣和学术训练,对本书的写作影响最大的,还是20世纪30年代这一历史时刻。当时,弗莱克斯纳从英国回到美国,大萧条刚刚开始。美国因经济崩溃而风雨飘摇,凄惨的景象随处可见。仅在纽约市,失业率急速上升,申请救济的人数不断增长,这些都是苦难的明证。弗莱克斯纳回忆:“我回来的时候,萧条已经很严重了。不过,因为我父母双方的收入都是固定且有保障的,我们家得以奇迹般地免收苦难……我觉得我有必要去感受一下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恰巧,弗莱克斯纳的一个表亲把她介绍给了福利委员会。福利委员会下设许多志愿救济机构。当时罗斯福还未当选总统,赈济失业者和贫困者的努力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弗莱克斯纳在委员会期刊上写道:“经济危机的广度令人不寒而栗。同时,我也像很多人一样被罪恶感吞噬。我得以幸免于难,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多有能耐。” 不久之后,弗莱克斯纳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世人听到她内心的社会良知。弗莱克斯纳这种对戏剧的热爱,和她的母亲一样。30年代初,她加入了一个纽约的戏剧社。虽然这个戏剧社最终因缺乏资金而停止运营,但弗莱克斯纳已经把戏剧当成了表达自己情感和思维的途径。她作品的关注点,是社会经济动荡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她的一部作品讲述了1934—1935年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反对当地专制政权的故事,这部话剧所关注的,正是法西斯主义兴起这一话题。1934年,弗莱克斯纳开始为好莱坞出版商海伦?多伊奇(Helen Deutsch)工作。弗莱克斯纳生平的第一份工资即来源于此。多伊奇人脉很广,当时她所负责的剧作还包括马克斯韦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的《冬景》(Winterset),这部作品取材于臭名昭著的萨科和万泽蒂案 。 随后,弗莱克斯纳去《新戏剧杂志》工作。在政治上,她越发向左派组织靠拢,试图调动人们对社会和政局的不满情绪,从而组织激进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戏剧艺术委员会(Theatre Arts Committee)。1936年,尽管时局艰难,戏剧艺术委员会依然为当时深陷内战的西班牙共和派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援。当时的弗莱克斯纳是委员会通讯TAC的负责人,这让她深入戏剧界的激进主义工作中,也让她异常繁忙。1937年,弗莱克斯纳开始撰写《1918—1938年的美国剧作家:远离现实的戏剧》(American Playwrights, 1918—1938: The Theatre Retreats from Reality)。在这本书中,弗莱克斯纳赋予了剧作家们针砭时弊的责任:“只有那些坚持关注社会现实的、激进的戏剧,才是精彩的。一旦戏剧创作瞄准了奢侈的生活,或仅仅是为了好莱坞而创作,那么这些作品本身就少了些生动性,效果也没那么好了。” 那时候,弗莱克斯纳已经和美国共产党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虽然弗莱克斯纳最终认为自己“太过于自我和独立”,以至于缺乏“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素养”,但在30年代的时候,她还是为共产党的工作付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直到40年代,她依然与左派激进组织和活动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她与左派的密切关系、组织劳工运动的经验以及她所参与的政治活动都对《百年抗争》的写作和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弗莱克斯纳后来回忆:“老实说,30年代的激进运动激发了我对女性的关注和热情。就像许多和我情况相似的人一样,我当时的境遇比我所知的大多数人都要好得多。后者遭遇各种波折,并为之苦苦挣扎,而我从未经历过这些。为此,我有着很深的负罪感。我曾说过,任何还有点良知的人都加入了左派运动,或者至少和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为左派运动是唯一在尝试改变美国所深陷的经济困境的社会运动。” 左派运动对弗莱克斯纳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她甚至认为,正是左派运动让人们开始关注美国的黑人和女性。这一论断肯定了30年代历史工作的重要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20世纪初其他历史事件和思潮对黑人和女性所产生的影响。80年代初,弗莱克斯纳解释说:“我想强调的是,共产党,以及像《新大众》(New Masses)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激发了白人对黑人历史、思想与文学的兴趣。当时,几乎没有白人会对这些感兴趣。此后,它们又引发了对女性权利和女性意识形态的关注。” 弗莱克斯纳很清楚,是加入共产党的经历让她下定决心要写一本关于女性历史的书籍。她说:“很多人把《百年抗争》称为经典,把它看作一部‘扛鼎之作’(其实我不这么看,但它确实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但要论这本书的起源,那就不得不提到我当时结交的几位共产党人,比如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和克劳迪娅?琼斯(Claudia Jones)。尤其是后者,当时白人对她知之甚少。” 弗莱克斯纳是通过玛丽安?巴克拉克(Marian Bachrach)认识这些人的。巴克拉克是美国共产党内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弗莱克斯纳极为敬重的好友。在弗莱克斯纳的印象中,巴克拉克“善于变通,但并不是那种只有煽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充满智慧、有同理心、光彩照人的女性,像她这样的人并不多。”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弗莱克斯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是这场运动中为数不多和我有相似知识背景的人,而且她和我一样阅读面广泛。”弗莱克斯纳回忆说,“当时的共产党人大多在为生计挣扎,无法接受真正广泛的教育。”弗莱克斯纳和巴克拉克都来自富裕的家庭,这也让她们二人和左派团体中许多工人阶级参与者截然不同。随着《史密斯法案》的施行,加入或拥护任何致力于用武力或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都变成了违法行为。即便如此,巴克拉克依然通过自己的记者工作,推进着共产党的各项目标。她确实也因此遭到了起诉,但因为当时她已经身患癌症,病情严重,所以她从未因为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而受到审判。1957年,巴克拉克去世。这对弗莱克斯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1982年,在巴克拉克去世25年后,弗莱克斯纳依然为此深感悲痛:“我每天都希望她还和我们在一起。” 巴克拉克曾建议弗莱克斯纳去参加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在纽约的一个演讲。这件事大约发生在40年代。弗林是一个爱尔兰后裔,是一个被称为“叛乱女孩”的脾气火爆的劳工运动组织者。在她的努力下,激进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诞生了。1937年,她已然成为美国共产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弗莱克斯纳回忆道:“伊丽莎白?格利?弗林的演讲让我第一次听说了洛厄尔磨坊女工 ,以及其他妇女工人运动领袖。受弗林那些生动的故事的感召,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搜寻这方面的书籍。弗林是那种老派的演说家,充满了似火的激情和力量。从那天起,我开始对她演讲中所描述的人和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弗莱克斯纳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她失望地发现,弗林在演讲中所描绘的女工们栩栩如生的英雄事迹,在其他历史书中却鲜有提及。共产党一向非常支持妇女关注马克思主义。弗莱克斯纳认为,美国历史中的那些事件,足够让她写成一个精彩的故事。“我就是这么开始的。因为没有其他书可读,于是我决定自己写一本。” 如果说弗林激发了弗莱克斯纳记录女性历史的热情,那么弗莱克斯纳的政治活动则塑造了弗里恩对女权运动的理解。不管是在书写哪一个历史阶段,作者自始至终都关注着工人阶级妇女所承担的经济负担,这一特点是非同寻常的。同时,鉴于美国黑人妇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的状况,这本书也用了很大篇幅去记录她们。弗莱克斯纳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关注这些主题了。 “二战”期间,在参加工业组织议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所组织的团结工人阶级的运动后,这些就成了她重点关注的主题。 “二战”期间,弗莱克斯纳把大量精力放在了组织小职员和秘书们参加社会工作,那些人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银行、出版业等。在这些所谓的“粉领” 岗位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这一现象也让弗莱克斯纳越发意识到性别歧视的严重性——后来许多左派中的男性和工会领袖表现出的家长作风和男性至上主义更让她加深了这种感觉。弗莱克斯纳曾负责过某一办公室职员工会的人事安排工作,这个工会就特别强调为女性和美国黑人创造就业岗位。弗莱克斯纳认为,女性参与工作对美国战时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促使民权活动家对联邦政府在保障平等就业权方面的工作形成了压力,这些都为社会变革创造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她在反思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在美国工人阶级黑人妇女的生活中交错的问题时说,“这两条线交织到了一起”。 40年代末,弗莱克斯纳意识到,自己急需一份能够为自己提供经济保障的工作。但是,她的政治活动是无法提供经济保障的。当时,她在经济上依然依赖于父母,这也让她备感压力。为了找到能发挥自己才能又契合自己政治诉求的工作,弗莱克斯纳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1946—1948年,她担任了中左政治联盟美国妇女议会(Congress of American Women)的秘书长。这一组织深受美国共产党的影响,鼓励妇女争取“四个自由和其他一切能争取的,包括公平的工资、工作、住房等等”。在此期间,她结识了克劳迪娅?琼斯,两人也成了朋友。琼斯是一个祖籍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女性,也是共产党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员。琼斯批判了当时党内对妇女议题的忽视,并用这个议题成功地吸引了弗莱克斯纳。尽管这让弗莱克斯纳非常兴奋,但当时妇女议会的财务非常不稳定,在东部城市中组织发展分支机构也面临许多困境。这些都让她备感沮丧。 重新回到战时供职的工会机构后,弗莱克斯纳决定要“给自己找一份工作,而不是再给别人安排工作”。工会派她去了外交政策联合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FPA)。弗莱克斯纳早先曾帮助该联合会调整人员安排。该联合会的使命之一,就是尽力说服美国政府支持国际机构进行维护和平的工作,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及其前身国际联盟。弗莱克斯纳回忆道:“外交政策联合会这样的机构对于民主的发展真是太好了。它们都开始雇用黑人秘书了,这简直振奋人心。这些事震动了整个外交政策联合会,但并没有震动我们。我们当时都想得到那个位置,但他们很迅速地雇了一个既迷人又称职的黑人秘书。”当时,弗莱克斯纳是外交政策联合会发言人办公室主任的助理,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女性,她们之后都活跃于妇女参政权运动。一时间,联合会成了那些致力于参政权和维护和平的女性主义者的聚集地。 在外交政策联合会工作期间,弗莱克斯纳结识了海伦?特丽(Helen Terry)。不久,两人就结成了人生伴侣,这一关系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特丽去世。用弗莱克斯纳的话说,两人相遇一两年之后,就已经“开始同居”了。她们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在政治理念上。她们都积极参与了40年代末期发动和组织劳工和房客的运动。当时,弗莱克斯纳的住所离史岱文森城只有两个街区。这是一个由大都会生活公司开发的位于曼哈顿的住宅区。为了让这一住宅区接纳黑人,她不仅参加了静坐示威,还努力让“尽可能多的共产主义者进入该住宅区,这样也能对其他房客施加压力,让他们接受黑人。最终我们成功让一些黑人家庭住进了史岱文森城,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整个40年代,弗莱克斯纳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工作和组织活动填满。这些事让她越来越清楚工人的艰辛斗争,也让她看到了社会运动的艰巨性和令人振奋的可能性,这些也构成了参与社会运动最重要的经历。她找到了“为黑人妇女和黑人劳动妇女争取权益的组织”,这些组织让弗莱克斯纳为之着迷。“二战”后,她还曾在全国有色人种毕业护士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Graduate Nurses)工作过,负责公共关系。这是让她非常满意的工作之一。在美国南部各州,许多黑人护士是无法加入美国护士联盟(American Nursing Association)的。由于美国护士联盟当时在为提高其成员工资待遇和职业地位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游说,无法进入护士联盟,对黑人护士来说,这就意味着无法获得经济上的保障。 和黑人护士共同工作的经历,加深了弗莱克斯纳对“黑人妇女的历史和困境”的兴趣。同时,她也更加坚信,在她对美国女性运动的历史研究中,黑人妇女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她开始在杰斐逊社会科学学院开设关于美国女性的历史的课程。杰斐逊社会科学学院是在美国共产党支持下设立的,为劳动人民提供在职培训课程。在备课的过程中,弗莱克斯纳关于“妇女权益斗争的历史进程的看法逐渐成型”。此时,斗争的概念已经贯穿于弗莱克斯纳对历史、工人运动,以及女工和美国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的理解。 50年代初,弗莱克斯纳的想法从写一本关于女性历史的书,逐渐细化成写一本妇女参政权运动的书。她决心把注意力放在女性为赢得投票权的斗争上面。她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在1950年读了《生而平等》(Created Equal)这本书。这本书出版于1940年,是阿尔玛?卢茨(Alma Lutz)为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所写的传记。弗莱克斯纳也开始查阅其他关于女性权力斗争的文献,但在当时,这方面的文献并不多。弗莱克斯纳发现,许多文献对黑人女性和女工都“只字未提”,其中包括伊内兹?欧文(Inez Irwin)关于女性参政权运动史的著作《天使和亚马孙女战士》(Angels and Amazons)。这让她备感失望。尽管如此,她依然坚信,参政权运动史是一个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虽然很少被提起,但充满了可能性。她把写作《百年抗争》的想法告诉了玛丽安?巴克拉克,巴克拉克对此非常支持。她仔细阅读了长达19卷的《美国女工和童工状况报告》。这份由美国国会在20世纪初委托撰写的报告让弗莱克斯纳坚信,工人阶级妇女是妇女历史的一部分。接下来,弗莱克斯纳所要面对的一项艰巨工作,就是寻找第一手史料。她需要寻找关于个人、组织、各个州妇女运动的史料,以及能让自己的故事更加丰满的想法和思路。 弗莱克斯纳决心编纂一系列题材广泛的史料,从细节上刻画美国妇女历史。她的这一决定是受共产主义历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的启发。阿普特克曾热心地致力于美国黑人历史档案的发掘工作。“我没听说过任何关注妇女的档案馆,也没听说过任何其他历史学家对妇女感兴趣。虽然有人说当时有一个伯克郡女性历史学家联合会(Berkshire Conference for Women Historians),但我对她们一无所知,也没有和她们取得过联系。”在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弗莱克斯纳为了寻找黑人女性的史料,还联系到了W.E.B.杜波依斯。但杜波依斯对弗莱克斯纳的书和想要达成的目标都没什么兴趣,随随便便就把她打发走了。他的这一反应让弗莱克斯纳大失所望。不过,也有人对弗莱克斯纳施以援手,比如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一个档案馆员。他建议她去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Sophia Smith Collection)看看。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金矿。弗莱克斯纳在这里找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历史点滴、证据和无价的历史细节资料。“我就像充上了电,”弗莱克斯纳解释道,“之后的一切都变得顺利了。” 在史密斯学院,藏书馆员向弗莱克斯纳提供了“无数的文献和报刊剪辑资料……从这些资料里随便找出一个名字,就可以深入发掘出更多的故事。”虽然弗莱克斯纳在杜波依斯那里遭到了冷遇,但她并没有放弃,依然希望把黑人女性放到参政权运动史中。“之前那些研究参政权运动的所谓的历史学家,对黑人女性连半个字都不会提。”弗莱克斯纳反感地总结道。(在她看来,工人阶级妇女其实并没有比黑人女性好多少。)在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多萝西?波特(Dorothy Porter)正在努力筹建斯平加恩藏书馆(Spingarn Collection),这个藏书馆重点收藏的是关于美国黑人历史的书籍,这也意味着它将成为一个新的知识宝库。同时,琼?布莱克韦尔?赫特森(Jean Blackwell Hutson)也在做着相似的事情,她正在位于哈勒姆(Harlem)区的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分管筹建朔姆堡藏书馆(Schomburg Collection)。这两位女性不懈努力的目标,是让黑人女性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有一席之地。波特和赫特森都非常欢迎弗莱克斯纳,并毫无保留地为她提供相关联系人资料和建议。在米丽娅姆?霍尔登(Miriam Holden)夫人那里,弗莱克斯纳又发现了另外一个无与伦比的私人图书馆。“她邀请我去她位于纽约的家中。其他图书馆里有的,她那里都应有尽有。在别的图书馆,这些书都是珍稀馆藏,只能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图书馆内查阅,还有图书馆员盯着。而在这里,我想拿多少回家就拿多少回家。” 在翻阅成堆的历史资料后,弗莱克斯纳逐渐找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斗争”。这个选择反映了她对历史进程的看法,也反映了她的政治观点和对美国妇女历史意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妇女有组织的努力和斗争,以及所有和这些有直接联系的事件……都将被囊括到这本书中。与这些不相关的,我都不会写。”(但事实上,《百年抗争》所囊括的主题远远超过了这一范围。)对弗莱克斯纳来说,“斗争”的主题“是这本书的基石。这本书的题目也来源于此……我觉得这是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东西”。 也许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斗争”这个主题让历史变得更加生动起来,也让那些不时浮现于美国近代史中的、看似最不可能发生任何变革的黑暗时刻,有了意义。试图改变美国社会历史意味着什么?在写作《百年抗争》时,弗莱克斯纳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理解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她找到了一种激情,去形容那些她相信是贯穿于参政权运动中的矢志不渝的决心,令人心碎的挫折感,以及无与伦比的兴奋之情。“我知道那种感觉,”她后来说道,“那种并不完全是被人从楼梯上推下去,而是被人在面前摔门的感觉。这种情况在我为工会拉票的时候出现过很多次,不管是为哪个工会拉票,这都会发生。”她回忆道: 我知道组织竞选活动或是工会活动需要投入多少精力,这些我都经历过。那种大家同心协力努力工作,并为之做出牺牲,胜利时欢欣鼓舞,失败时深呼一口气从头开始的激情,在我身上从未消退过……我知道腰酸腿疼是什么感受,也知道心碎是什么感受。 1955年,弗莱克斯纳开始全职写作《百年抗争》。那一年,她的母亲过世,给她留下了一笔足够让她衣食无忧的遗产。这时,弗莱克斯纳已经快50岁了。这时的她,不仅找到了写作的灵感和对历史的想象力,也更加能够接受30年代这段渐渐远去的记忆。那时,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憎恶、极权主义政权的可怖罪行(早在弗莱克斯纳离开共产党之前,这些就已经广为人知了)、四处蔓延的冷战、对左派的压迫,以及50年代劳工组织的溃败,似乎都在嘲笑着激进的梦想和理念。《百年抗争》的写作,让弗莱克斯纳觉得“自己之前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浪费。否则,我会说:‘好吧,我把时间花在了那件事上,但却一无所成,这真是太糟了。’”战后的那几年里,似乎很少有什么能存留下来,至少弗莱克斯纳是这么认为的。“工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认识的那些激进分子也不见了。他们比那些备受尊敬的人更加激进,更加左倾。在某种意义上,《百年抗争》几乎是我之前活动的产物,它让我早期的工作没有被浪费。” 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有谁会对女性参政权的历史感兴趣。弗莱克斯纳回忆道:“过去,很少有人会对这个国家的女性历史感兴趣,也没有人会去书写这段历史。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没有人会愿意读这本书,更不用说出版了。”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妇女历史的早期倡导者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一直非常支持弗莱克斯纳的工作。他认为弗莱克斯纳的研究对美国历史有重大意义。弗莱克斯纳曾经问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我应该写这本书吗?”“无疑问。” 施莱辛格回答。但是,弗莱克斯纳又担心自己并不是一名博士。“没有关系,” 施莱辛格回答道,“你识字就行。”他让弗莱克斯纳去联系执教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历史学家珍妮特?詹姆斯(Janet James)。她不仅在为创办女性历史专业做准备,也在撰写《著名美国女性》这本传记体的鸿篇巨著。这本书的出版,将对女性历史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尽管有人对女性历史有着和弗莱克斯纳同样的热情,但当弗莱克斯纳把书稿的前150页给父亲一位当编辑的朋友看时,她收到的反馈却不那么让人高兴。出版商告诉她,这本书要想卖得出去,那么关于黑人女性的部分就必须全部删掉,因为没有人会对黑人女性有任何兴趣。虽然弗莱克斯纳完全不同意这点,但她一直困扰于到底会不会有人对这本书感兴趣。不过,这些都没有动摇她把黑人女性带入她所写的历史的信念。书稿完成后,一位出版商认为她这本书太沉重了。还有一些人甚至都不愿意读一下书稿。正因为这些冷遇,当历史学家阿瑟?曼(Arthur Mann)的妻子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妇女选民联盟会议(League of Women Voter’s Meeting)上(真是世道不同了!)建议她去和自己的丈夫谈谈,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百年抗争》的时候,弗莱克斯纳还颇为怀疑。“他们肯定不会出这本书的!”弗莱克斯纳当时回应道。 事实是,阿瑟?曼和他的妻子一样,坚信这本书正是那种哈佛大学出版社热切期待可以出版的书。曼当时是北安普顿史密斯学院的教授,弗莱克斯纳正好也住在那里。在给施莱辛格的一封信中,弗莱克斯纳写道:“很明显,我接触过的出版商都对这本书没有兴趣。这本书将改变美国历史叙述中性别失衡的现状,我希望它可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施莱辛格无疑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他和同事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一道,为哈佛大学出版社评审了这本书的手稿,并热切地推荐出版这本书。施莱辛格在给出版社的推荐语中写道:“在我看来,弗莱克斯纳这本书填补了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之前也有关于妇女权益的历史书,但是它们在这个主题的处理上,视角更为狭窄,作品中也难免流露出对女权斗士的个人感情。而弗莱克斯纳小姐将这段历史列为美国民主发展进程中一个了不起的篇章。她对历史的处理是客观的,但毫无疑问,读者很容易就可以知道她站在哪一边。” 施莱辛格对《百年抗争》提了一个重大的建议。在书稿中,弗莱克斯纳用整个第2章的篇幅记述了“奴隶制下的黑人妇女”。施莱辛格认为这部分不仅“从编年史角度看完全放错了地方,还打断了这本书的叙事”。他认为,把这部分缩写一下,融入第3章会更加合适。相反,汉德林则盛赞了弗莱克斯纳在书中记录黑人历史这一不同寻常的做法。他写道:“把黑人女性作为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加以关注,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汉德林是当时顶尖的美国移民史学家。所以,他自然关注了另外一个方面。他劝说弗莱克斯纳在《百年抗争》中加入女性移民的内容。弗莱克斯纳同意缩短关于美国奴隶制的内容,尽管部分内容依然出现在了第一章中。在本书所描绘的人物中,弗莱克斯纳囊括了许多参与过参政权运动的境外出生的女性以及移民子女,所以她认为她对移民的描写是充分的。出版社并没有让弗莱克斯纳进行大的改动。1959年,这本书出版了。 几年后,随着妇女运动的复苏,一些美国女性开始追寻自己的历史。《百年抗争》因此也变得与她们密切相关。造就了《百年抗争》的历史洪流,再一次通过与三四十年代极具渊源的政治活动和学术兴趣,为这本书找到了自己的读者。正如历史学家芭芭拉?所罗门(Barbara Solomon)所注意到的,这本书成了六七十年代许多对妇女历史有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起点”。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也极力推荐此书。她在《女性的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的脚注中写道,《百年抗争》应该是每个美国女大学生的必读书。十年内,弗莱克斯纳就获得了女性历史领域先驱的殊荣。但很少人会意识到,这本书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者在三四十年代所参与的激进运动,以及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莱克斯纳掩盖了这一来源。 历史的洪流把《百年抗争》塑造成了一部历史著作,但这本书本身却是超越时间的。也许,这就是一部著作对历史领域做出了不朽贡献的标志之一。了解塑造《百年抗争》的希望与梦想、失望与悔恨,可以让我们了解塑造这段历史的各种复杂因素。不过,即使我们对作者一无所知,即使她在读者心中是隐形的,对那些想要了解世纪之交妇女争取参政权这段历史的人来说,《百年抗争》依然非常有价值。 《百年抗争》还有一个杰出历史著作都有的标志,那就是它不仅仅是一部研究深入而透彻的作品,同时它为历史研究不断扩大视野、扎实基础做出了贡献。在很大程度上,《百年抗争》预言了定义当代女性历史学学科的主题。当代女性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主题,绝大多数都在《百年抗争》这部鸿篇巨制中有所涉及,有些甚至得到了详尽的叙述。弗莱克斯纳之所以能做到这样,部分原因是她没有也不能将争取投票权的斗争从塑造妇女权益斗争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抽离,否则所有她所坚信的决定历史轨迹的一切都将遭到否定。正因为这样,《百年抗争》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妇女权益斗争的细致而精彩的叙述,还为他们呈现了从殖民时代开始的妇女历史经历的全景图。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发现那些在后世女性历史研究中成为焦点的话题和思想。其中,殖民时期妇女工作的重要性和妇女经历的多样性、作为美国革命时期重要部分的妇女抗争、美国奴隶制度对妇女的无情剥削、南北战争时期工厂女工的劳工运动、女权运动在废奴运动的进程中的成熟化领悟(体现在她们的政治艺术和掌握的公共演讲和请愿技巧)、农村妇女对民粹运动的参与、高等教育对改革和女权主义的严峻考验,以及20世纪初黑人女性俱乐部 运动的独特使命,都是这本书中最吸引人也是最重要的思想。这些,还有弗莱克斯纳在本书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最终也无疑成为后世女性历史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 在弗莱克斯纳看来,《百年抗争》尽管成就斐然,但也是有遗憾的。她认为,书中应该有更多关于女性与美国劳工运动的史料。“我所做的,就好比是竖一根旗杆,然后说‘这里躺着某个人’ ‘这里是谁谁谁’,仅此而已”。但事实上,在书写的过程中,弗莱克斯纳已然为美国女性历史领域设定了主题。《百年抗争》不仅是一部详尽的关于妇女参政权的历史,也为历史研究描绘出一幅蕴含着无限机遇的未来图景。它让历史得以完美衔接: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反复回顾历史,以获得对历史的理解,并从过去寻找可以为当代社会所借鉴的意义。弗莱克斯纳本人似乎也对这种能让历史学家和他们的研究紧密联结的力量深有体会。“我认为《百年抗争》是一本好书,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原因之一就是它和我过去的许多经历都是有关联的。”通过《百年抗争》的写作,弗莱克斯纳让人们看到了妇女经历在美国社会中的意义,同时,她也发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埃伦?菲茨帕特里克 大师之笔,忠实呈现美国女权运动史,对其他国家处理女权问题提供有益参照 ?知名学者、媒体联合推荐 国内知名女权研究者陈亚亚、资深媒体人侯虹斌、美国当代女权活动家贝蒂·弗里丹,知名媒体《纽约时报书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联合推荐。这是所有人都应该阅读的一本书。它将帮助我们在多年抗争结束之际,保持对自己更清醒的认知。 ---- ?忠实呈现美国女权运动史,为其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角色申明 作者从19世纪初叶的女性权利行动开始,叙述了此后100多年中美国女性通过宣传、抗争、牺牲和与体制的种种互动,终基本实现权利平等的历史。女性为获参政权所做的斗争作为美国历史进步的根基,而非一段式微的插曲,在这里得以展现。本书内容价值高,是国内鲜有的珍贵文本。 ---- ? 具社会意义,对其他国家处理女权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纵观历史,美国在女权问题上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其实在今天,性别歧视仍是全球性的重要问题。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关于美国女权问题简明而有价值的论述,对其他国家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 ? 大师之笔,语言平实真切,可读性强 两位作者虽是科班出身的学者,但语言生动平实,娓娓道来。她们深刻的洞见及创新的思路引人入胜,讲述了女性用勇气、坚韧和决心书写的充满希望的故事。这将引起读者对女权这一话题产生全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