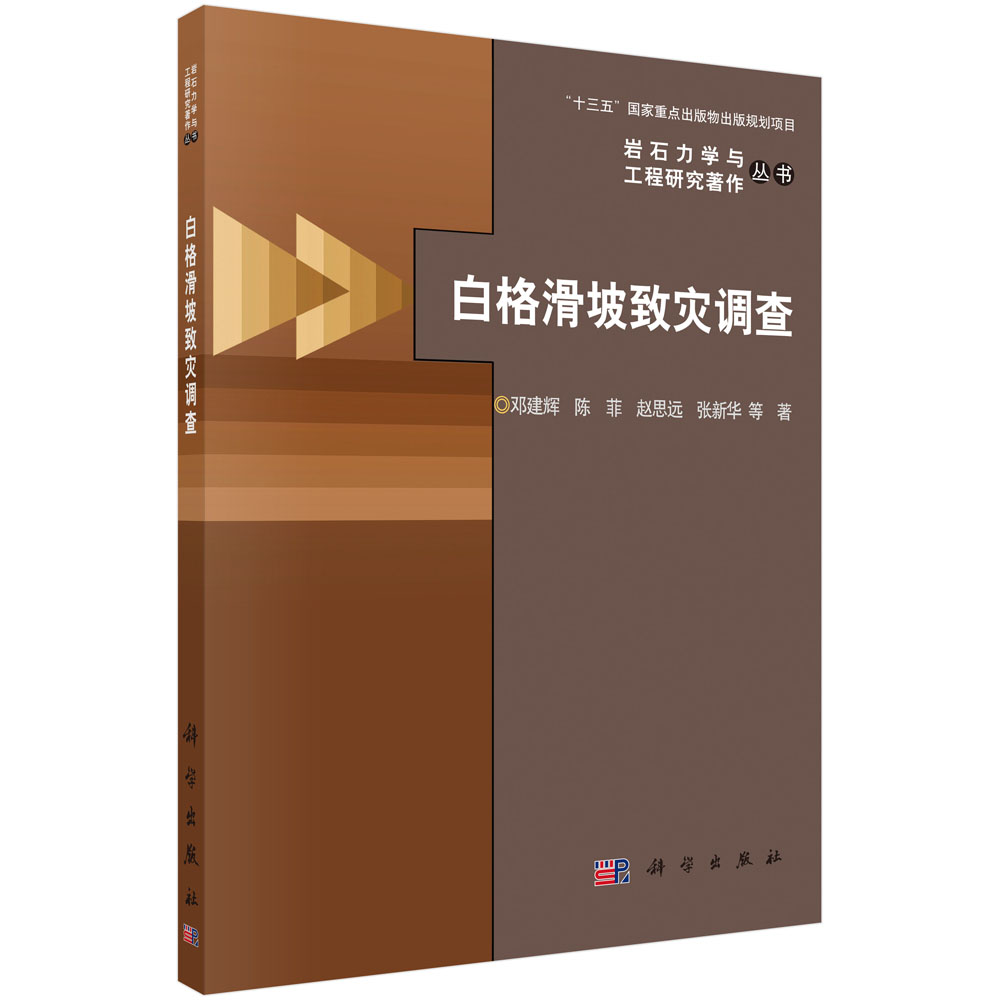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159.00
折扣价: 125.70
折扣购买: 白格滑坡致灾调查
ISBN: 9787030682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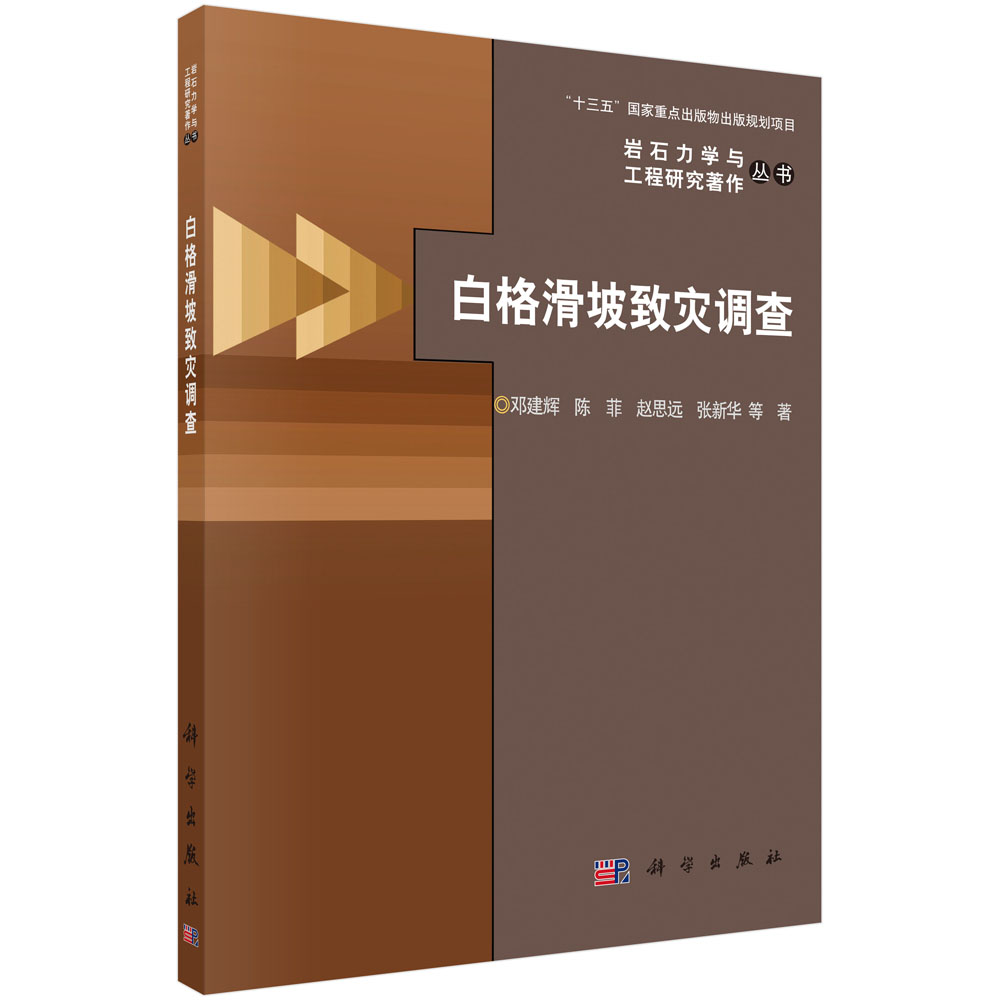
第1章 绪论
1.1 川西滑坡堵江事件概述
四川西部简称川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该区在青藏高原的构造隆升与流水下切作用下,自西至东发育有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四条主要河流。作为河谷地貌自然演变的典型剥蚀、沉积形式,堵江滑坡在这四条河流中的河谷地带十分发育。
几起影响较大的堵江滑坡事件按时间顺序简述如下。
(1)金沙江马湖地震滑坡[1,2]。马湖地震的时间是1216年3月17日,震级7级,距今已经超过800年,可能是四川最早有历史记录的滑坡堵江事件。据《宋史 宁宗纪》载[1]:“嘉定九年二月辛亥,东西四川地大震,三月乙卯又震;甲子又震;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1]上述历史记录描述的是金沙江下游四川省雷波县马湖段的滑坡堵江情况,向家坝水库蓄水前谷米乡上游关村滑坡对岸尚有部分遗迹(图1.1),只是尚未经证实是否与此次地震相关。马湖是滑坡堵江形成的堰塞湖,崔玉龙等曾详细调查过马湖滑坡[2],发现滑坡坝主要物质为二叠系栖霞组和茅口组灰岩与峨眉山组玄武岩,范围上自马湖北岸,高程约1150m,下至现代金沙江河床,高程约320m。该滑坡坝是多期滑坡的产物,最早一期年代为(46390±2570)a BP(36CL测年),最晚一期年代为(935±30)a BP(14C测年),与马湖地震相当,即现代马湖最终成型于1216年。
图1.1 马湖地震滑坡堵江遗迹
下部为三叠系飞仙关组砂岩,上部为胶结良好的二叠系栖霞组与茅口组灰岩碎屑,为左岸过江物质
(2)大渡河摩岗岭滑坡[3-6]。由康定地震诱发形成,时间是1786年6月1日(清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戊申),滑坡区地震烈度达Ⅸ度。滑坡区地层为澄江期—晋宁期康定杂岩,岩性主要为花岗岩、闪长岩,局部发育辉绿岩脉。这次地震灾情十分严重,康定城几乎完全摧毁,滑坡堰塞大渡河达9日之久,滑坡坝溃决导致洪水在下游酿成巨大水患,至湖北宜昌才渐渐平息,下游沿岸人员伤亡达10万之众[6]。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溃决洪水伤亡事件。据我们考证,滑坡地点在泸定县得妥镇大渡河大桥上游约1.3km处、大渡河右岸。得妥镇发现的“铁庄庙碑”(图1.2)记载了这起滑坡堵江事件,“乾隆伍(五)十一年,大限(陷)地动,山崩石立(裂),作山一皮(匹),今(金)洞子节(截)水九日,五月十四,鸡明(鸣)出水”,括号中的字为江在雄先生的解读[4]。
图1.2 铁庄庙碑
现收藏于泸定县地震办公室
(3)金沙江石膏地滑坡。源区位于金沙江右岸、云南省巧家县城南约8km,左岸的四川省会东县大崇乡小田村仍保留有滑坡堆积残体,岩性主要为二叠系栖霞组与茅口组灰岩。该滑坡在清光绪《东川府志》和民国《巧家县志》均有记载,“光绪六年三月初九(1880年4月17日),巧家厅石膏地山崩,先是于更尽后,忽吼声如雷,夜半山顶劈开,崩于对岸四川界小田坝,平地起坵,压毙村民数十人。金江断流,逆溢百余里,三日始行冲开,乃归故道”。小田村观音庙的“滇山崩倒”碑也有类似记载[7]。该滑坡与地震无关。会东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1日将其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立有“大崇镇滇山入川遗址”碑。
(4)岷江上游的叠溪地震滑坡群[8-10]。由叠溪7.5级大地震产生,时间为1933年8月25日15:50:30,震中烈度达到Ⅹ度,岩性主要为志留系和泥盆系石英片岩、云母片岩。地震诱发的滑坡群形成了十余个堰塞湖(海子),其中在岷江干流的3个“海子”规模最大,从北到南依次是大海子、小海子和叠溪海子。地震后第45天(1933年10月9日)叠溪海子溃决,洪水汹涌而下,形成严重的次生水灾,又造成至少2500人死亡。此次地震灾害共造成6865人死亡,1925人受伤,房屋倒塌5180间。大海子和小海子至今遗存,滑坡区小海子现已开发为装机容量达180MW的水电站。
(5)白泥洞滑坡[11]。位于金沙江左岸,会理县新发乡铜厂村(图1.3),滑坡发生时间是1935年12月22日中午12时左右。滑坡形成的高速碎屑流造成其下游的沙坝沟和上、下沙坝三个村的30余户村民被埋,金沙江断流3天,碎屑流形成的尘土飞扬达几公里,黄家村一带屋顶瓦面积灰厚约10cm。滑坡后缘高程约2360m,前缘高程880m,宽约885m,估算残余方量大于1×108m3。滑坡基岩为前震旦系天宝山组千枚岩、板岩等。
图1.3 白泥洞滑坡
(6)雅砻江唐古栋滑坡[12-15]。滑坡地点发生于雅江县孜河乡雨日村,时间是1967年6月8日早晨8:00,失稳方量约6800×104m3。滑坡区地层岩性为上三叠统侏倭组变质砂岩与印支期—燕山期侵入的花岗伟晶岩脉,逆向坡。表层卸荷岩体发生滑动后,堰塞雅砻江,形成一高度为175m(右岸)至335m(左岸)的滑坡坝。雅砻江堰塞达9昼夜,堰塞湖壅高水位高程达2585m,回水53km,库容6.74×108m3。1967年6月17日8:00漫顶溃决,8:30溃口宽约数米泄流,12:00后溃决加快,14:00~15:00过水量最大,溃口宽达150m左右,14:30最大溃坝流量57000m3/s,至20:00下降到1900m3/s,溃坝过程基本结束。整个溃坝历时12小时,溃坝洪水总量6.57×108m3。坝下游洪水位陡涨到50.4m。溃坝洪水影响延伸至1730km的重庆寸滩水文站,水位上涨1.54m。
上述滑坡事件在四条河流地貌演变产生的滑坡堵江事件中仅仅是沧海一粟。一方面四条河流均位于边远地区,人口稀疏,历史滑坡记录不全;另一方面还存在史前滑坡堵江事件。
朱明先[16]列举了石膏地滑坡以来金沙江的8次断流事件,其中就包括鲁车渡一带的白泥洞滑坡,据此将白泥洞滑坡时间界定为1935年12月22日。朱明先提到的一次历时较长的金沙江断流事件,目前尚未找到对应的滑坡堵江地点。文中写道,1877年,《绥江县志 卷一》以《金沙江之涸》的标题记述:“清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江水陡落数丈。次日更落,河面仅如小溪,浅处可涉。河底现出泥沙,埋没金、银、铜、铁各器物甚伙。三月初九日晨,洪涛骤至,超过迹数丈,泛若龙潭,如夏季水势。沿江拾财物者奔避不及,多被水漂没。事后遍访上流阻滞原因与地点,云、川两境俱不得详,然皆同时涨落。疑山崩水阻必在西陲荒远之地矣。”
近20年来随着四条河流水电开发,史前滑坡堵江遗迹在四条河流中均有发现[17-32]。与前述案例不同的是,很多遗迹显示堵江滑坡规模巨大、溃决洪水严重,或者河流堰塞历史悠久。据论证[32],金沙江虎跳峡下游大具盆地沉积的厚度可达100~200m的碎屑堆积是滑坡堰塞湖溃决洪水堆积。而湖相沉积物测年结果表明,金沙江下游的白马口滑坡堰塞湖存在年限接近4600年(7500~12100a BP)[30]。
总之,川西四条河流的滑坡堵江事件具有数量多、灾害链效应突出等特点。
1.2 滑坡堵江事件研究进展
纵观国内外滑坡堵江事件研究成果,案例研究仍然是主旋律,具体包括滑坡堵江案例的辨识、滑坡与滑坡坝的形成机制、滑坡坝溃决机制与溃坝洪水演进过程分析、滑坡坝应急处置与利用等。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统计分析方法在案例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国内外大量学者试图通过历史案例资料的统计分析,找出滑坡堵江事件的一般规律。
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USGS)的Costa和Schuster[33,34]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滑坡堵江事件研究工作,80年代开始收集全球案例,至1991年共编录全球463起有历史记录的滑坡堵江事件,其中中国案例为48起。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卢螽槱[35]在国内较早开展了滑坡堵江事件研究,收录案例13起,并界定了研究涉及的相关基本概念。柴贺军等[36-41]将案例拓展到147起,系统地分析了滑坡堵江事件的类型、形成条件与分布特征等。相关概念引述如下。
(1)滑坡堵江事件:凡斜坡或边坡岩土体因崩塌、滑坡及其转化为泥石流而造成江河堵塞和回水的现象,包括完全堵江与不完全堵江两类。所谓完全堵江是指滑坡堵断江河水体,使下游断流,上游积水成湖;不完全堵江则是失稳坡体进入河床或导致河床上拱,使过流断面的宽度或深度明显变小,上游形成壅水。
(2)堵江历时:滑坡坝从形成到溃决,或江河水流挟带固体物质将堰塞湖淤满的这段时间,包括短暂堵江和长期堵江两类。短暂堵江的历时小于1年,否则就叫长期堵江。前述的马湖地震和叠溪大海子、小海子就属于长期堵江,而摩岗岭、石膏地、白泥洞等滑坡形成的堰塞湖则属于短暂堵江。
(3)滑坡堵江事件的环境效应:由滑坡堵江造成的不良地质环境,滑坡运动造成的破坏,入江时形成的涌浪、滩险,堰塞湖的淹没及水位升降变化引起的岸坡变形破坏,天然堆石坝突然溃决导致的次生洪灾,冲刷、淤积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柴贺军等[36]统计的中国147起堵江事件基本上有历史记录,绝大部分存续时间不超过一个水文年。上述数字可以说仅仅是沧海一粟,仅2008年的汶川地震诱发形成的滑坡坝,崔鹏等[42]给出的数量是257座,而范宣梅等[43]遥感识别的数量是828座。这些滑坡坝及其灾情,特别是造成广泛社会影响的汶川地震唐家山滑坡[44]和2014年鲁甸地震红石岩滑坡[45]堵江事件及其环境效应,客观上推动了针对滑坡堵江问题的研究。滑坡坝及其溃坝问题研究备受政府与学术界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均列有滑坡坝(堰塞湖)专项科研课题。2009年发布了两部堰塞湖应急处置行业规范,即《堰塞湖风险等级划分标准》(SL450—2009)和《堰塞湖应急处置技术导则》(SL 451—2009)。近年来国内已有多部专著出版[46-49],特别是刘宁等撰写的专著《堰塞湖及其风险控制》内容全面,不完全局限于滑坡堰塞湖,基本上概括了堰塞湖理论研究与防灾减灾实践的最新进展。
年廷凯等[50]系统总结了滑坡坝稳定性评价方法及灾害链效应,包括滑坡坝形成、稳定和溃决等涉及的方方面面,并以历史数据为基础,基于1328个案例,建立了考虑坝长、坝宽和堰塞湖库容的滑坡坝稳定性快速评价经验公式。该公式主要利用几何参数对滑坡坝的长期稳定性评估进行了探索,而若用于应急评估,滑坡坝结构特征是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滑坡坝类似土石坝,但是性质极不均匀,同时没有防渗和泄洪设施,极易出现漫坝、管涌或坝坡失稳等形式的破坏,这是绝大部分滑坡坝存续时间很难超过一个水文年的原因所在。溃坝洪水次生灾害产生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也往往最为严重,1786年的大渡河摩岗岭滑坡坝溃决和1933年的叠溪海子溃决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致使溃决洪水估算成为早期滑坡坝研究最为关注的重点。
近年的研究与实践进展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1)研究案例的积累,提高了滑坡堵江事件及其灾害的认识深度。
(2)数值模拟技术进步很快、应用广泛。包括滑坡运动、涌浪与堵江过程模拟,溃口演变与洪水演进模拟等,这些模拟均涉及多相耦合问题。
(3)勘测技术、应急响应与处置技术进步很快。无人机航测、遥感解译、变形监测、应急通信保障和应急组织协调是进步较快的几个方面。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至2018年的白格滑坡,这些技术进步十分突出。
滑坡堵江灾害问题涉及滑坡形成-堵江筑坝-溃坝洪水-级联效应等多个环节,是一个连续过程。从灾害防控角度,研究还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1)灾害源早期识别技术与地质研究。无人机航测和各种遥感技术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在各种气象与遮挡条件下可实现灾害源的遥感判识,在高山峡谷区灾害源早期识别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未来需要在几何分析的基础上与各类物探技术结合实现灾害源物性参数与地下结构特征的判识工作,为地质分析提供参数。地质研究需要解决的难题包括地质参数的快速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