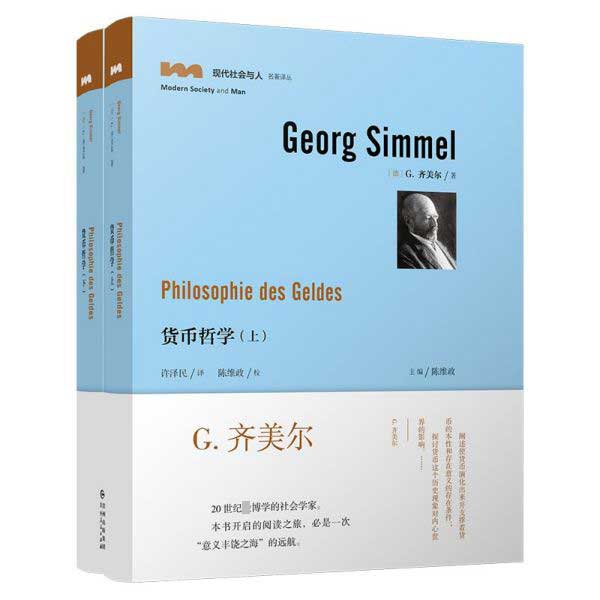
出版社: 贵州人民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55.90
折扣购买: 货币哲学(上下)/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ISBN: 9787221155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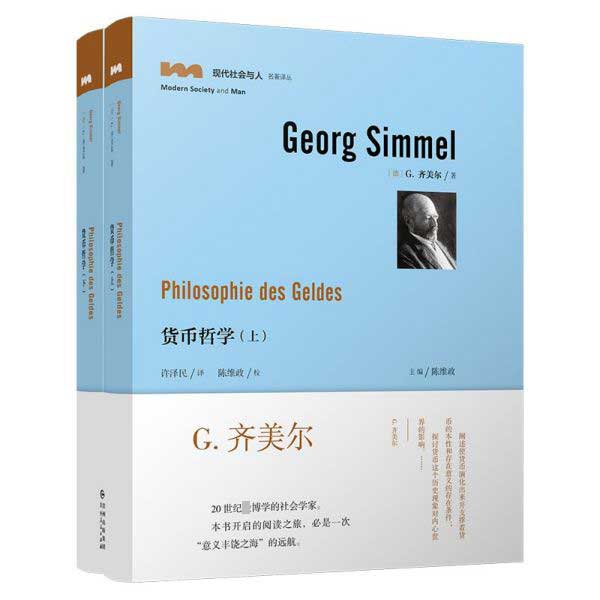
G.齐美尔,20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其在社会学方面的影响被公认仅次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
在灵魂的救赎被觉得是终极目的的地方,贫困也被许多学说阐释为一种全然积极的、绝对必要的手段,然后,这一手段又被提升到其手段的地位之上而俨然成为一种具有内在意义和效力的价值。这种情形可以在目的链的不同环节上发生,也可以出于不同动机。首先,对一切世俗享受和世俗兴趣单纯避而远之就可以引发这种情况。往最高处奋斗的灵魂,就仿佛这一负担自行脱落了一样从其中解脱了出来,不再需要专门针对它的意志了。最早期的基督徒可能是经常这样做的:他们并不直接对花花世界的物质享受采取敌对或者攻击性的态度,而只是简单地缺了跟物质享受的关系,仿如我们觉察不到某些事物,是因为我们缺了这样的器官那样。因此,极其零星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尝试,跟现代共产主义追求在最深刻的本质上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前者起源于对世俗利益的冷漠,而后者则恰恰起源于对世俗利益最大限度的重视。在这两种思潮出现的间隔时期,也曾出现过这两者的混合形式:中世纪末期发生的种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虽然具有绝对贪婪的本性,但它们还是部分地得到过全面践行俭朴理想的苦行主义思潮的哺养。当然,就金钱而言,苦行主义必须从远离物质利益的仙界回到凡间,并采取更加果断而切实的形态,因为人们在追求基本必需品的道路上会不断地跟金钱相遭遇,也因为取得金钱要比作为其结果的取得生存资料本身,需要意志更多的关注和辛劳。无论谁都可以像那位把油脂当黄油吃而茫然不觉的教父那样对这一利益麻木不仁,然而,如果他终究要在货币交易的时代生存下去,他就不能在谋取金钱的时候,让自己的意识以这种方式受到丝毫分散。因此,如果对待任何外部事物在原则上都是只有冷漠占上风,那么,这种态度在面对金钱330时,很容易就在事实上转而化为仇恨。其次,金钱的诱惑性在这一方面的影响更加明显。由于金钱可以在任何时刻供人使用,所以,金钱是薄弱时刻最危险的陷阱。由于金钱是供任何人筹措的东西,因此,金钱会把其当时最迷人的地方展现在灵魂面前;而只要金钱实际上仅仅作为钱掌握在我们手里,它就是世界上最超脱、最清白的东西。这时,所有这些诱惑的危险性就更大了。因此,对于苦行的感觉方式而言,金钱是魔鬼的真正象征。它戴着与人为善、毫无偏袒的面具向我们频频招手,使我们既防魔鬼又防金钱的唯一保障,就是彻底跟它保持距离,不跟它发生任何关系,无论它看起来可能多么无害。这种心态在早期的佛教社团中得到了原则的表达。一旦加入了佛教社团,僧人就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财产,放弃了家庭关系和妻子。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况,僧人不得拥有日常必需的小物品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甚至在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作为施舍物得来的时候,他也不得拥有。佛教这种戒律的基本重要性,透过僧人们为他们自己所起的名字“托钵僧社团”得到了说明。当他们每天都为自己当天所需的东西而化缘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出声求恳,而是默默地等待着施舍——他们跟任何财产的关系,也就在其终究可能的程度上被化去了。正如某些阿拉伯游牧部落通过法令禁止种植庄稼、建造房屋以及类似的东西,以免人们受到引诱而安居下来并背弃部落的生活方式,佛教也同样为僧人们制订了修身养性的戒律。佛僧们把自己比作鸟,无论飞到哪里,身上除了翅膀以外别无所有。他们不得接受可耕地、牲畜、奴隶等施舍331物。不过,佛教对金银财宝持戒最严。金钱是不能向佛僧布施的,施主必须先把金钱交给手艺人或者商贩,然后,后者再用金钱买来实物交给佛僧。倘若哪位佛僧收下了金银,他就必须在僧众面前忏悔。如果在附近找到有缘的凡俗人,那些金银就交给他,让他帮助购买生活资料;佛僧不得亲自购买东西。假如附近没有凡俗人,那么,那些金银就交给一位佛僧,让他把它们扔掉,而且,这位佛僧还要“无欲、无嗔、无痴”,以确保他真正把金银扔掉。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变成了恐惧和厌恶的对象——尽管这种心态犹如灵魂在奇特的贫血衰竭之中僵化地形成的一种观念——而贫困则变成了被嫉妒地看护着的财产,变成了游离于世界的全部多样性和趣味之外的生存之价值目录表当中的一个珍贵条目。价值是统一用货币支付的;拒绝货币就是拒绝世界的全部多样性。 20世纪最博学的社会学家。阐述使货币演化出来并支撑着货币的本性和存在意义的存在条件;探讨货币这个历史现象对内心世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