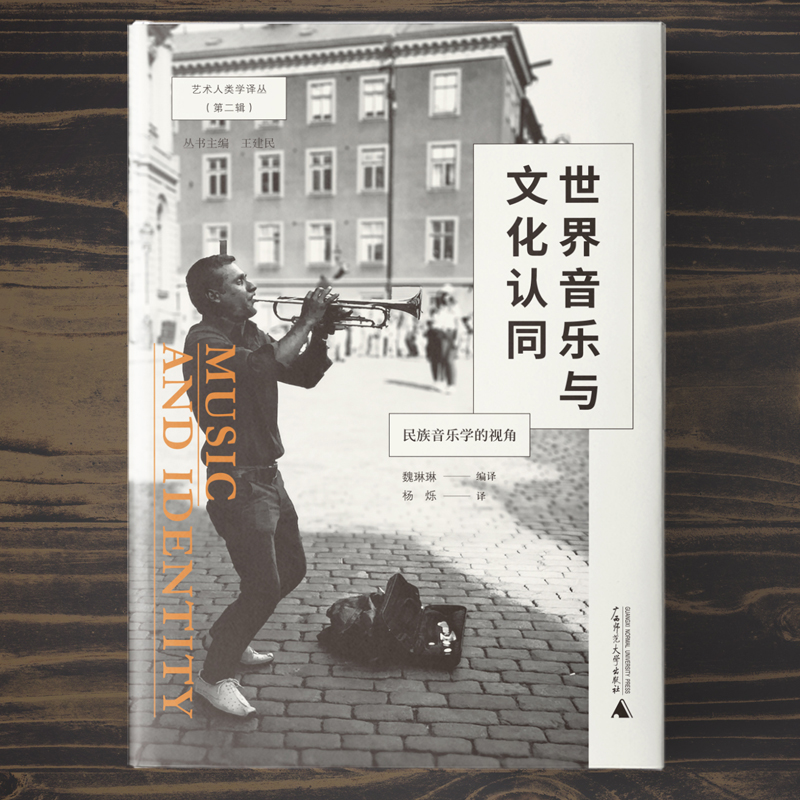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108.00
折扣价: 64.80
折扣购买: 艺术人类学译丛(第二辑) 世界音乐与文化认同:民族音乐学的视角
ISBN: 9787559867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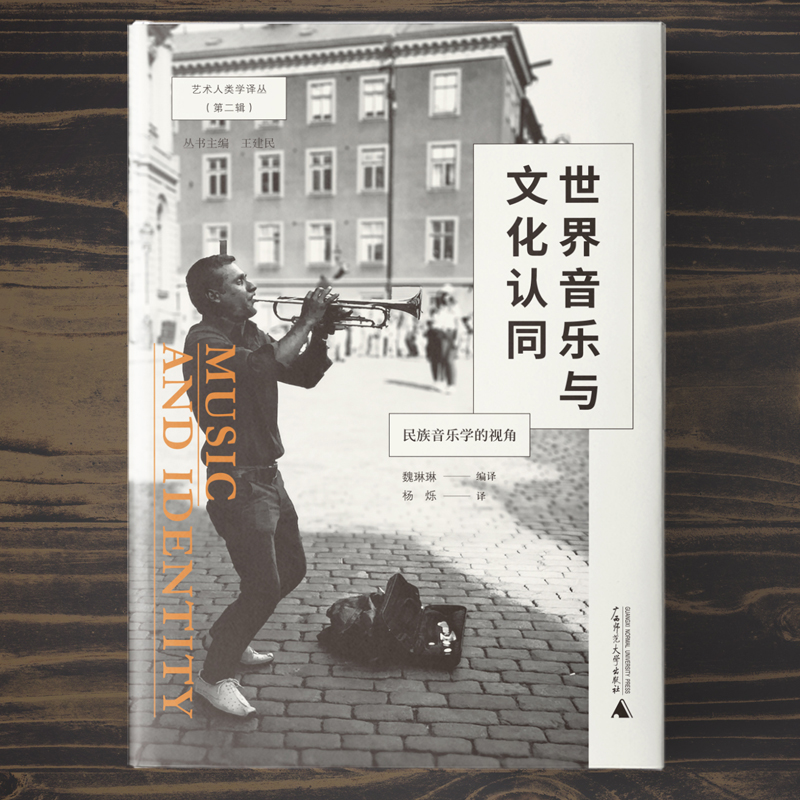
魏琳琳,1980年生,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艺术人类学博士后,扬州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有音乐学学术专著1种,先后在《音乐研究》《民族艺术》上发表论文及译文40余篇,编有《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
认同从何而来? 社会认同来源于哪里?这个问题有过两个回答,一个“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回答和一个“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的回答。本质主义主要的关注点,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身份政治,一方面是由民族、种族、阶级和性别界定的底层阶层对权力阶层进行反抗的这类身份政治实践。本质主义立场对认同的理解基于族群的品质和特点亘古不变这一认识,而音乐和这些坚固认同的关系,通常会被解释为反思、符号化、同源性和表述等的过程。建构主义则认为认同的形成基于群体在某个时间段可获得的文化资源,也就是说,认同是偶然的、脆弱的、不稳定的、多变的,而不是持久的、稳定的。若持第二种观点,关于认同的议题变为:音乐创作和聆听等实践是否参与、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以及如何参与建构新兴的、不断变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认同。虽然后者在近来文化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的著述中占了上风,但它不得不与一直持续的本质主义抗衡,比如美国的身份政治和有关后社会主义东欧和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讨论。相关主题的大多数文章都在处理两种主义的矛盾:由于各种政治及社会原因,新的身份认同正在产生,但个体、某社会群体或某些政府仍普遍固着于持久、本质主义的认同。 诸多讨论音乐与认同主题的作者像念经一样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音乐有助于建构社会认同。但是,在这种语境中,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往往又退回到对既有社会认同的讨论中,结果就是,他们认为,音乐在认同实践中的作用主要是对既有社会认同进行符号化、或反思、或给予其表演性的生命。例如,劳拉·艾伦(Lara Allen)研究一种于20世纪50年代在南非黑人城镇发展起来的新融合音乐,叫作“人声摇摆乐”(vocal jive)。在此研究中,反思或建构哪个更关键并不清晰。关于反思,我们了解到,作为产业化的流行音乐,它采用“当地旋律、当下城镇中的俚语和时事话题”为创作素材来“表达一种根植于当地”的身份认同,并可以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它通过一种国际化的、以流行爵士蓝调为基础的音乐来完成地方性表达,所以从中也可看到一种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混合性认同。后来,作者谈到音乐有助于“建构”一种身份认同:“人声摇摆乐在音乐上的兼容并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将西方与非洲的元素进行混合,形成一种非部落的、国际化的非洲城市文化身份认同,而这与英国殖民者以及南非白人移民颁布并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得以巩固的种族隔离政策是相悖的(……)即便是在十分压抑的政治语境下,商业流行文化还是可以以一种具有煽动性的方式起作用。”她认为,“政府想否认城镇居民的存在,而人声摇摆乐这样的混合风格使城镇居民城市化、非部落化、特别是西方化的体验与身份认同得以表达。(……)通过培育一种表达了政府所排斥的身份认同的混合音乐风格,并允许意见不同的歌词存在于其中,唱片产业也为大多数普通城镇居民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去进行文化抗争,无论这些抗争是明显的,还是像大多数情况一样通过一种隐蔽、模糊、偶然并具有变动性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似乎被摆在首位,音乐自身标志性的混合形式反映了该认同(部分非洲、部分城市、部分西化)的混合性。当然,一种在非洲城市中新出现的混合性认同并不符合大多数本质主义观点强调的、可追溯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持久不变的民族或族群认同。但这个实例还是说明了建构主义的论证很难不退回到本质主义的论述中去。 在变化中,在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就认同问题展开博弈的情况下,被建构的认同就成了一个问题。有些作者认为音乐确实参与了建构新的或想象的认同,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申辩。例如,彼得·曼努埃尔(Peter Manuel)指出,弗拉门戈(flamenco)与西班牙社会三个受压迫的社会群体相联系:那些住在安达卢西亚的人、吉卜赛人和较低阶层的人。他认为,音乐“不仅仅是一个使之成形的广泛社会文化现象的被动反映”,而且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的程度上,表现、帮助塑造现代安达卢西亚的认同”。弗拉门戈表演者们似乎通过创造新音乐类型而建构起一种新的族群意义上的自我理解,开启了使传统“崇高化”(dignification)和专业化的新进程。这些变化“提升了安达卢西亚和那里的吉卜赛人的形象”,从而形成“一个对他们(更崇高)的身份认同来说特别重要的标志”。这似乎是一个建构主义的课题,目的是表达一个新的自我认识,向其他人呈现一个可以领会的新形象。除了对传统弗拉门戈进行的崇高化,两个新的流派也参与着认同的形成或建构。 其中之一是阿拉伯风格弗拉门戈(flamenco arabe),将阿拉伯歌曲置入弗拉门戈旋律结构(flamenco cantes)。“通过颂扬与摩尔人的联系,阿拉伯风格弗拉门戈呈现出对安达卢西亚独特文化遗产的重申。同时,它被看作是一种与马德里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统治的有意脱离。”另一个流派是流行弗拉门戈(flamenco pop),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工人的城市化以及他们向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迁移。这个流派是包括摇滚和古巴流行音乐在内各种影响下的混合物,音乐的文本“赞美吉卜赛人的自由价值观和对权威的敌意”,并且参与到“新的城市形象认同的形成过程中”。这个流派已经“成为新城市安达卢西亚人意识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融合性(……)服务于影响和表达现代城市社会认同的不同方面。”在这里,有一点似乎很清晰,带有新的社会身份认同的新型社会群体还没有形成。迫在眉睫的是建构一种新的自我认识,这种对新的自我认识的需求是由长期存在的不满和新的经济社会环境激发的,这些新环境使生活变得比以前更糟糕。曼努埃尔的研究认为,当身份认同需要改变或正经历改变时,通过音乐建构自我认识和身份认同也就得以成就。音乐通过发生改变来促成上述过程,或者最好是音乐家通过改变音乐参与到建构新认同(自我认识)的过程中,通过改变音乐来改变关于自我认识的符号性表述或再表述,从而使他人对这一族群的认识也随之改变。 “认同”这个词,是我初接触社会学理论时感到十分费解的一个术语。它对应的英文是“identity”,是名词,但为何译为中文却看起来像一个动词?为什么不能翻译为更容易理解的“身份”?为什么“身份”竟然是一个问题?那么身份认同问题就是与之相关的那些历史问题吗?……编辑《世界音乐与文化认同:民族音乐学的视角》的过程,也是我重新理解“identity”(身份、认同)的过程。如果全景式地去看,通过赖斯教授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综述和追问,以及其他学者对赖斯的回应,可以看到,书中收录的这些普通美国学者的文章勾勒出了学术界的另一个侧面,与中国学者笔下的问题意识、学术脉络、学术交流、学术传统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比如书中有几篇文章研究宗教活动中的音乐应用,研究者有活动组织者、也有“参与式研究者”,从他们的角度可以看到,在一些我们以为极纯粹、永远静止的活动中,其实一直混杂着很多世俗的元素,这些世俗的元素是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而且推动着神圣元素发生变化。另外有几篇研究流行音乐的文章,以及美国学者研究上海街坊的江南丝竹社团的文章,则带来通过陌生的目光重新理解熟悉事物的启发。还有一些在我们非常不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的研究,比如基于玻利维亚高地歌唱活动的研究和用符号学理论研究音乐接受问题的研究,因为作者写得清晰细致,也会在某些时刻感同身受。所以,这本书做完,环抱“identity”一词的迷雾也散去一些:首先,通过认识他者的学术圈,我更客观地理解了自己身处的学术环境;其次,通过细读他人的认同过程,我重新审视自己那些身份认同发生和起效的瞬间;最后,这本五百多页的文集,也在学理层面梳理了身份认同这一术语的内涵、理论脉络及其与音乐活动的互动,案例丰富、角度多样,对于进一步理解“认同”究竟是动词还是名词,以及要在这个领域深耕的学者来说也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