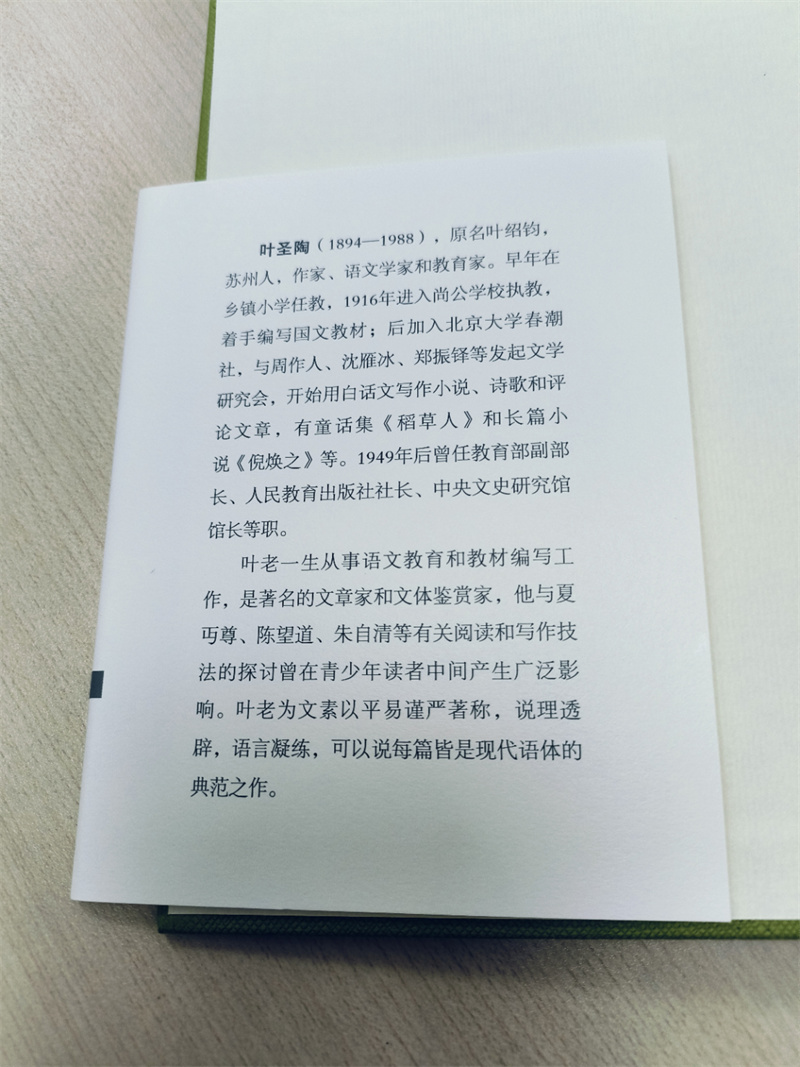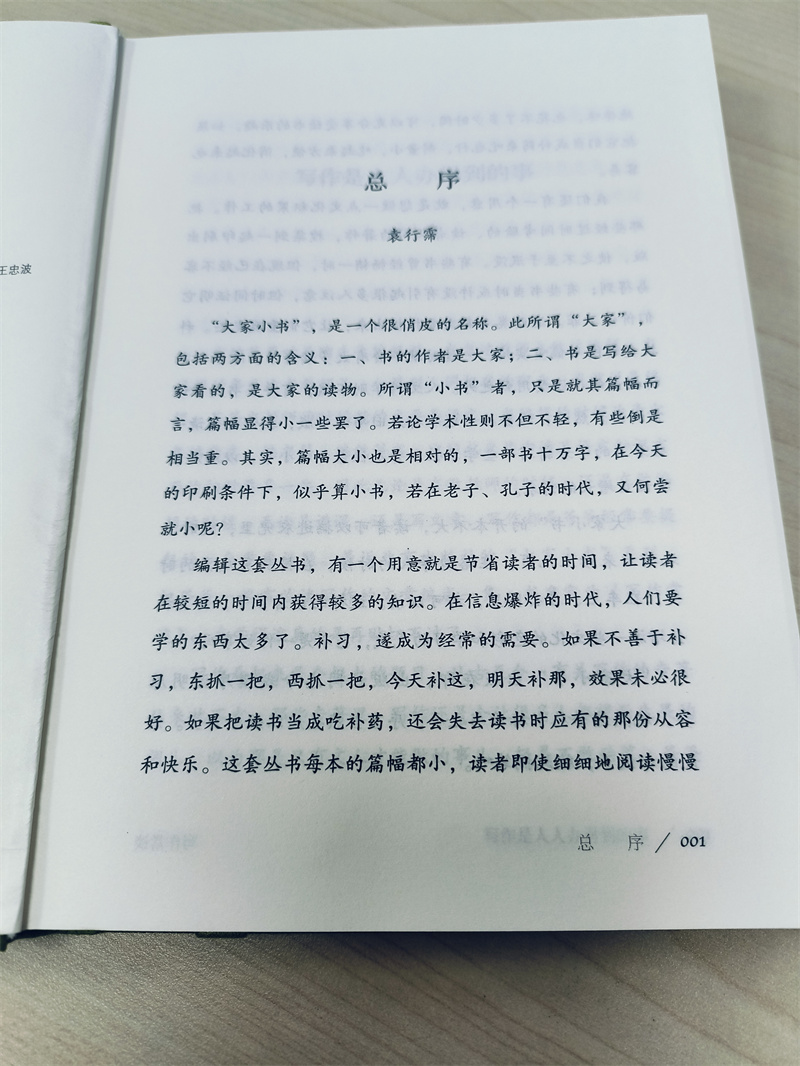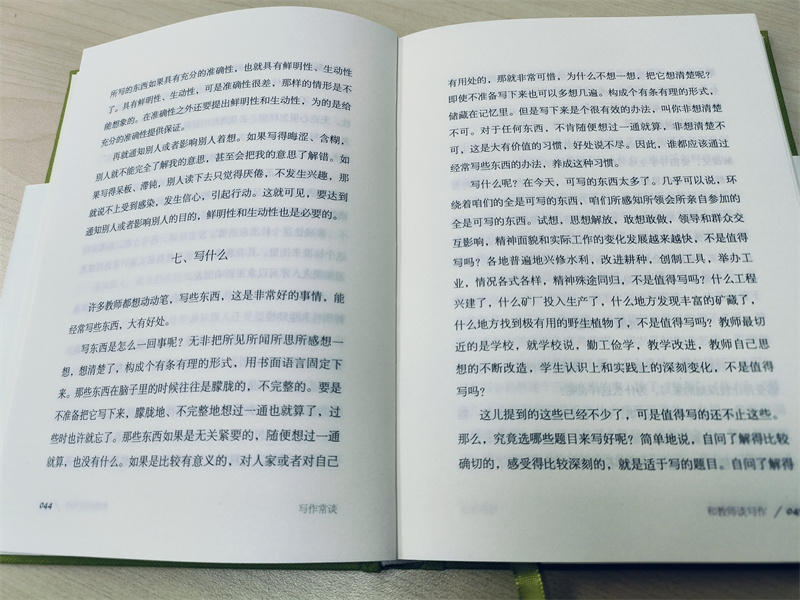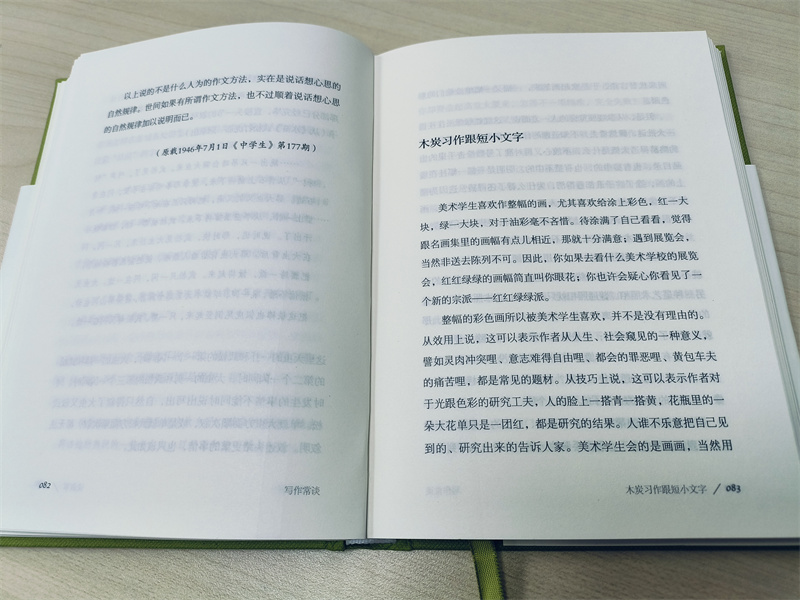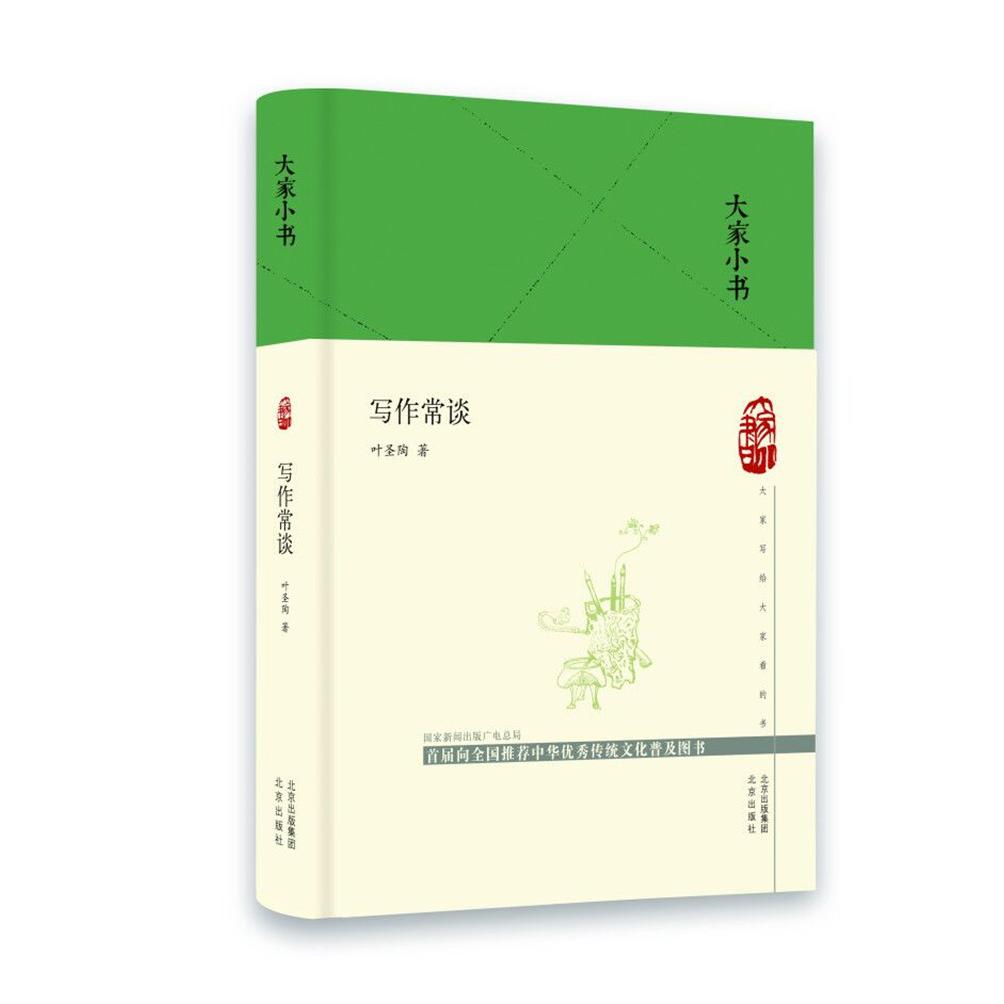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4.90
折扣购买: 写作常谈(精)/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56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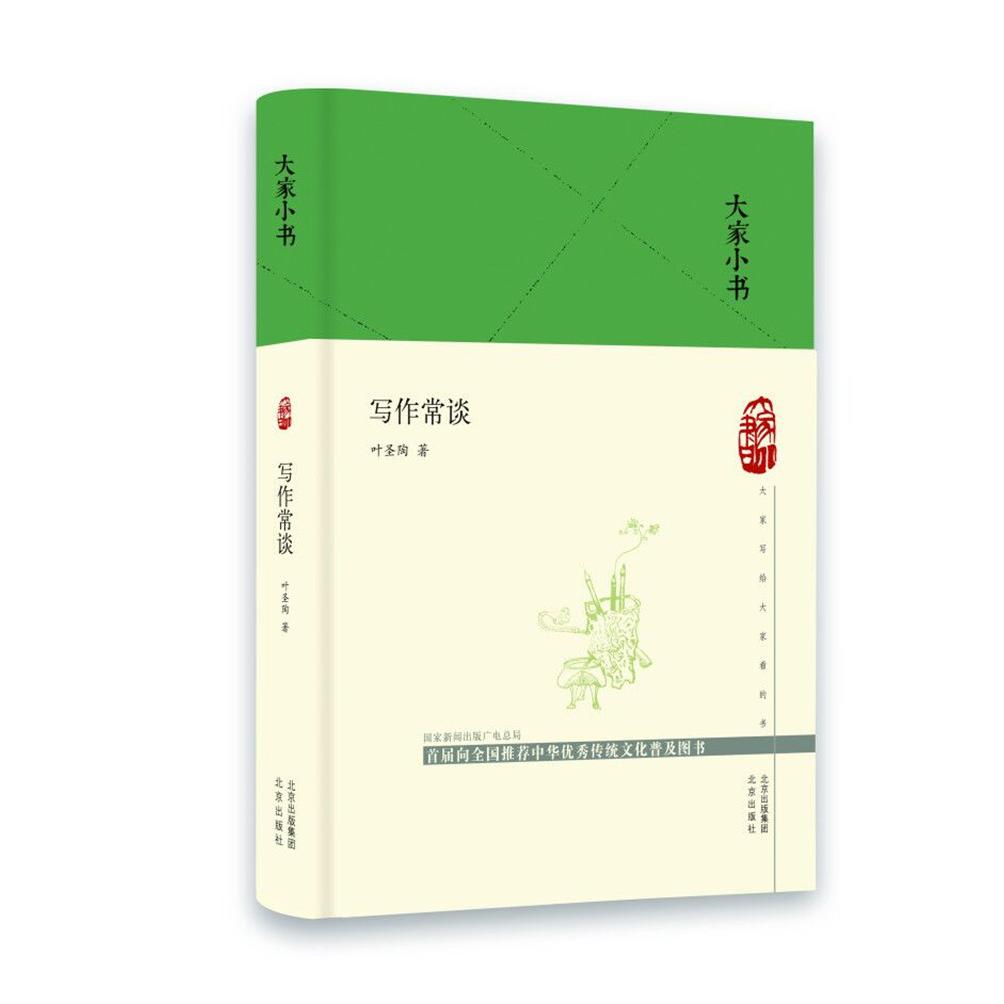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苏州人,作家、语文学家和教育家。早年在乡镇小学任教,1916年进入尚公学校执教,着手编写国文教材;后加入北京大学春潮社,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文学研究会,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小说、诗歌和评论文章,有童话《稻草人》和长篇小说《倪焕之》等。1949年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叶老一生从事语文教育和教材编写工作,是著名的文章家和文体鉴赏家,他与夏丏尊、陈望道、朱自清等有关阅读和写作技法的探讨曾在青少年读者中间产生广泛影响。叶老为文素以平易谨严著称,说理透辟,语言凝练,可以说每篇皆是现代语体的典范之作。
“作文”,现在有的语文老师改称“写话”。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 其实,三十年前,大家放弃文言改写白话文,目标就在写话。不过当时没有经过好好讨论,大家在实践上又没有多多注意,以致三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写话。 写话是为了求浅近,求通俗吗? 如果说写话是为了求浅近,那就必须承认咱们说的话只能表达一些浅近的意思,而高深的意思得用另外一套语言来表达,例如文言。实际上随你怎样高深的意思都可以用话说出来,只要你想得清楚,说得明白。所以写话跟意思的浅近高深没有关系,好比写文言跟意思的浅近高深没有关系一样。 至于通俗,那是当然的效果。你写的是大家说惯听惯的话,就读者的范围说,当然比较广。 那么写话是为什么呢? 写话是要用现代的活的语言写文章,不用古代的书面的语言写文章——是要用一套更好使的、更有效的语言。用现代的活的语言,只要会写字,能说就能写。写出来又最亲切。 写话是要写成的文章句句上口,在纸面上是一篇文章,照着念出来就是一番话。上口,这是个必要条件。上不得口,还能算话吗?通篇上口的文章不但可以念,而且可以听,听起来跟看起来念起来一样清楚明白,不发生误会。 有人说,话是话,文章是文章,难道一点距离也没有?距离是有的。话不免啰嗦,文章可要干净。话说错了只好重说,文章写错了可以修改。说话可以靠身势跟面部表情的帮助,文章可以没有这种帮助。这些都是话跟文章的距离。假如有一个人,说话一向很精,又干净又不说错,也不用靠身势跟面部表情的帮助,单凭说话就能够通情达意,那么照他的话记下来就是文章,他的话跟文章没有距离。不如他的人呢,就有距离,写文章就得努力消除这种距离。可是距离消除之后,并不是写成另外一套语言,他的文章还是话,不过是比平常说得更精的话。 又有人说,什么语言都上得来口,只要你去念,辞赋体的语言像《离骚》,人工制造的语言像骈文,不是都念得出来吗?这样问的人显然误会了。所谓上口,并不是说照文章逐字逐句念出来,是说念出来跟咱们平常说话没有什么差别,非常顺,叫听的人听起来没有什么障碍,好像听平常说话一样。这得就两项来检查:一项是语言的材料——语汇,一项是语言的组织形式——语法。这两项跟现代的活的语言一致,就上口,不然就不上口。我随便翻看一本小册子,看见这样的语句,是讲美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支配的几种刊物的:“……在不重要的地方,大资产阶级让他们发点牢骚,点缀点‘民主’风光,在重要的地方,则用不登广告……的办法,使他们就范。”不说旁的,单说一个“则”,就不是现代语言的语汇,是上不得口,说不来的。就在那本小册子里,又看见这样的语句,是讲美国司法界的黑暗的:“有好多人,未等到释放,便冤死狱中。”不说旁的,单说按照现代语言的组织形式,“冤死”跟“狱中”中间得加个“在”,说成“冤死狱中”是文言的组织形式,不是现代语言的组织形式,是上不得口,说不来的。 或许有人想,这样说未免太机械了,语言是发展的,在现代的语言里来个“则”,来个“冤死狱中”,只要大家通用,约定俗成,正是语言的发展。我想所谓语言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实际生活里有那样一种需要,可是现代的语言里没有那样一种说法,只好向古代的语言讨救兵,这就来了个“咱们得好好酝酿一下”,来了个“以某某为首”。“酝酿”本来是个古代语言里的语汇,“以……为……”本来是文言的组织形式,现在参加到现代的语言里来了,说起来也顺,听起来也清。这是一种发展情形。“则”跟“冤死狱中”可不能够同这个相提并论。现在在文章里用“则”的人很多,但是说话谁也不说“则”,可见这个“则”上不得口,又可见非“则”不可的情形是没有的。“冤死狱中”如果可以承认它是现代的语言组织形式,那么咱们也得承认“养病医院里”“被压迫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是现代的语言组织形式,但是谁也知道“养病”跟“被压迫”底下非加个“在”不可,不然就不成话。 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想。既然“则”可以用,那么该说“了”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矣”吗?该说“所以”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是故”吗?诸如此类,不用现代语言的语汇也可以写话了。既然“冤死狱中”可以用,那么该说“没有知道这回事”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未可知”吗?该说“难道是这样吗”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岂其然乎”吗?诸如此类,不照现代的语言组织形式也可以写话了。如果这样漫无限制,咱们就会发现自己回到三十年以前去了,咱们写的原来是文言。所以限制是不能没有的,哪一些是现代语言的词汇跟组织形式,哪一些不是,是不能不辨的。不然,写成的文章上不得口,不像现代的语言,那是当然的事。咱们看《镜花缘》,看到淑士国里那些人物的对话觉得滑稽,忍不住要笑,就因为他们硬把上不得口的语言当话说。咱们既要写话,不该竭力避免做淑士国的人物吗? 不愿意做淑士国的人物,最有效的办法是养成好的语言习惯。语言习惯好,写起文章来也错不到哪儿去,只要你不做作,不把写文章看成稀奇古怪的另外一套。 把写成的文章念一遍是个好办法,可以检查是不是通篇上口。不要把它当文章念,要把它当话说,看说下去有没有不上口的地方,有没有违反现代语言规律的地方,如果它不是写在纸面的文章,是你口头说的话,是不是也那样说。 还可以换个立场,站在听话的人的立场,你自己听听,那样一番话是不是句句听得清,是不是没有一点儿障碍,是不是不发生看了淑士国里那些人物的对话那样的感觉。 还有个检查的办法。你不防想一想,你那篇文章如果不用汉字写,用拼音文字写,成不成。有人说,咱们还在用汉字,还没有用拼音文字,所以做不到真正的写话。这个话也有道理。但是,为了检查写话,就把汉字当拼音文字用,也不见得不可以。一个语词有一个或者几个音,尽可以按着音写上适当的汉字。这样把汉字当拼音文字用,你对语言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你会发觉有些话绝对不应该那样说,有些话只能够写在纸面,不能够放到口里。经过这样的检查,再加上修正,距离真正的写话就不远了。 (原载1951年1月10日《新观察》第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