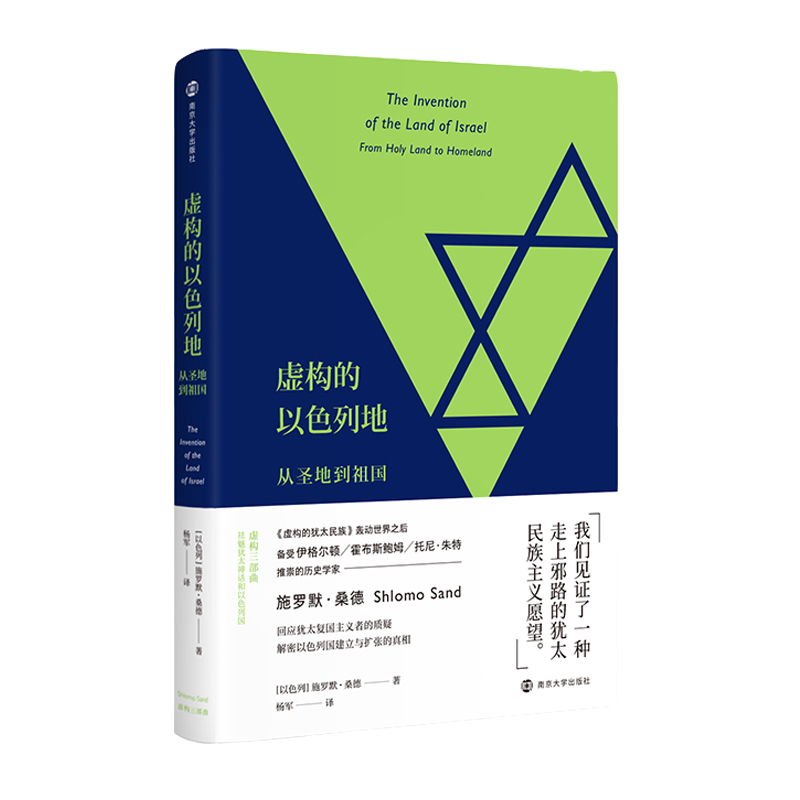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1.50
折扣购买: 虚构的以色列地(从圣地到祖国)(精)
ISBN: 9787305217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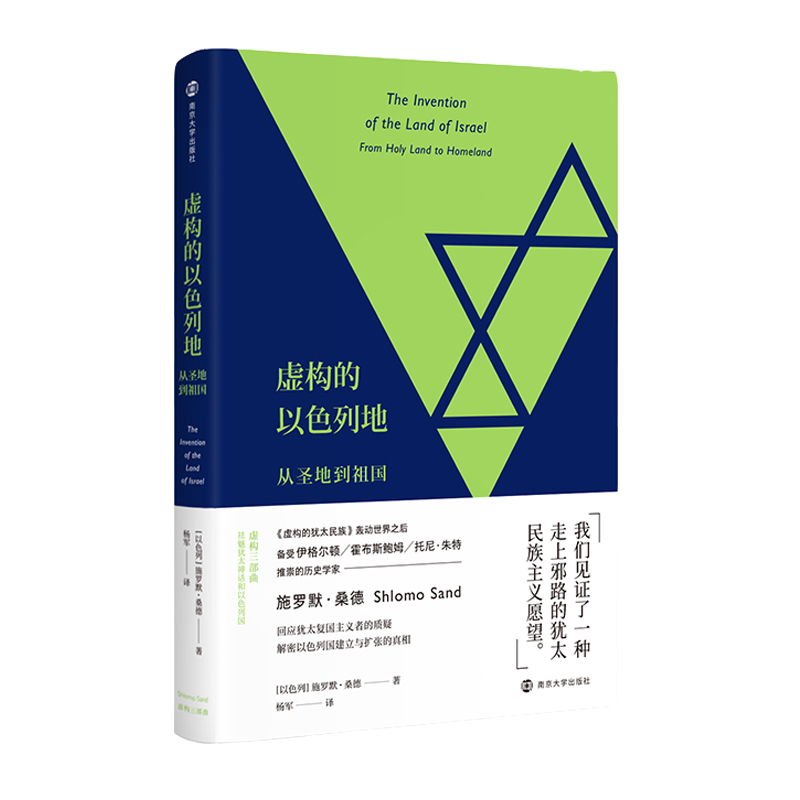
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46年出生于奥地利林茨,是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裔犹太人的后代,幼年时生活在难民收容所,1948年举家迁往雅法。1982年获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致力于民族与民族主义、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电影史等研究领域。其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虚构的以色列地》《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被称为“虚构三部曲”,在以色列和西方学界引起轰动与争议。 另著有《知识分子、真相和权力:从德雷福斯事件到海湾战争》(Intellectuals, Truth and Power: 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the Gulf War)、《词语和土地:以色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神话》(The Words and the Land: Israeli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alist Myth)等。
导言 平庸的凶手与地名学 先辈土地的名称 本书的目标之一是回答,作为应由“犹太人民”统治的、一个变动着的领土空间,“以色列地”是如何被虚构出来的?同样,我曾在别处长篇大论,在这里简短论及,“犹太人民”也是经由意识形态建构后发明的。这块土地对西方来说极具魅力,不过,在进入其神秘深处的理论旅程之前,我必须先提请读者注意它所在的概念体系。如在其他民族语言中常见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例也包含着自己的语义学操控,充满了令任何批评话语都头痛的时代误植。 …… 地区和国家的名称会随着时间而变,有时候,用后来的历史所给予的名字指称古代地域是常见的。不过,只是在所说的地方没有已知的或已被接受的名字的情况下,人们才采纳这一语言学惯例。例如我们都知道,汉谟拉比统治的是巴比伦而不是永恒的伊拉克地,尤利乌斯?恺撒征服的是高卢而不是伟大的法兰西地。然而,很少有以色列人意识到,杰西的儿子大卫和约西亚王统治的地区是迦南或犹大,马萨达的群体自杀不是发生在以色列地。 不过,以色列学者若无其事、毫不犹豫地重复着这种语言上的时代错误,不受其问题多多的语义学上的“过去”的困扰。耶胡达?埃利茨乌(Yehuda Elitzur)是巴尔伊兰大学的《圣经》与历史地理学资深学者,他以罕见的坦率总结了那些以色列学人的民族主义科学立场: 按照我们的观念,我们与以色列地的关系不应简单等同于其他民族与祖国的关系,其中的区别不难觉察。我们还未进入这块土地时,以色列就已经是以色列了。进入流散期许多个世代之后,以色列还是以色列。甚至在一片荒芜的时候,这块土地依然是以色列地。别的民族不是这样的。人们之所以是英国人,凭依的是他们生活在英国的事实;英国之所以是英国,原因是那里住着英国人。在一代或两代人以后,离开这个国家的英国人就不再是英国人了。如果英国没有了英国人,它也不再是英国了。所有民族都是这样的。 正如“犹太人民”被看作永恒的“民族”,“以色列地”也成为实体,像它的名字一样不会改变。在所有关于《圣经》和“第二圣殿时期”文献的上述书籍的解读中,以色列地被描述为一块确定的、稳固的、受到认可的领土。 下面的例子将证明这一点。2004年,《马加比二书》的一部高质量希伯来语新译本出版了,在其导言和脚注中,“以色列地”出现了156次。哈斯蒙尼人自己可不知道,他们是在叫着那个名字的地方领导的起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做了类似的跨越,他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名为“哈斯蒙尼文献中作为政治概念的以色列地”,虽然其所说的时期并不存在那个概念。近些年里,这一地理政治神话极其盛行,以至于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作品的编辑们大胆地将术语“以色列地”用在了所译的文本之中。事实上,作为指称这个地区的许多名字之一其中一些同样为犹太传统所接受,如圣地、迦南地、锡安地、瞪羚之地等“以色列地”一词是后来的基督徒和犹太拉比发明的,原意是神学而非政治的。我愿谨慎地指出,它首次出现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显然,如果这个基督教文本作于1世纪末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术语“以色列地”的使用的确可以看作是突破性的:“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马太福音》2:19—21) 这里,用“以色列地”一词指称耶路撒冷周边的用法是孤立的、一次性的。它很不寻常,因为《新约》的绝大多数地方用的是“犹大地”。新术语的出现或许源于第一批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看作以色列之子,而不是犹太人。此外,我们也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它是在很久之后才被塞入这个古老文本中的。 术语“以色列地”扎根犹太教是在圣殿被毁后,当时,由于三次反异教徒起义的失败,在整个地中海地带,犹太一神教显示出衰落的迹象。只是在公元2世纪,当犹大地按照罗马的命令成为巴勒斯坦后,当彼时的一个重要阶层皈依基督教后,在《密西拿》和《塔木德》中,我们才看到术语“以色列地”首次犹疑不定的出现。而且,这个名词的采用还可能由于一种深切的担忧:担心巴比伦的犹太人中心不断增长的力量,担心它对犹太知识分子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不过,如上面提到的,尽管基督教和拉比使用了这个术语,它与民族主义时期犹太人与这个地区相关联的那个词含义仍不尽相同。古代和中世纪有一些概念,如“以色列人民”“特选子民(人民)”“基督教子民(人民)”“上帝子民(人民)”等,它们与今天在说“现代人民”时的含义大相径庭;类似的,在犹太和基督教传统中,“应许之地”“圣地”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祖国”也不一样。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上帝许诺的土地包括了半个中东,而在《塔木德》的以色列地中,宗教的和有限的边界区分出的总是一些不连续的小地块,并被赋予不同的神圣级别。犹太人的思想传统漫长且多样化,但是,这些分界从未被设想为政治主权的边界。 只是到了20世纪初,在新教的熔炉出现多年之后,神学概念“以色列地”才最终转变和提炼为明确的地理民族概念。从拉比传统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取代“巴勒斯坦”一词,主张移民开拓的犹太复国主义借用了这个术语。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时候巴勒斯坦一词不仅在整个欧洲广泛使用,第一代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也都使用它。而在移民者的新语言中,以色列地成为指称这个地区的唯一名字。这一语言学工程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记忆建构的一部分,这种记忆建构后来涉及地区、地段、街道、山脉、河床名字的希伯来化。它让犹太民族主义记忆后退了惊人的一步,略过了这个地区漫长的非犹太人历史。不过,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一个事实:这一地域的命名既不包括也不涉及当地的大批人口,因此这一命名更容易将他们看作承租人的聚合或暂时的住户。术语“以色列地”帮助塑造了一种广为接受的空地意象“没有人民的土地”永远是为“没有土地的人民”准备的。这个虚假意象流传很广,但其实是福音派基督徒发明的;对它的批判性审查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1948年战争期间难民问题的形成,理解1967年战争后开拓定居的复兴。 之所以写这本书,我主要是想解构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历史权利”概念,解构相关的民族主义叙事,它们的唯一目的是构建领土攫取的道德正当性。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努力想要批判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体制的官方史学,并在此过程中,追踪逐渐萎缩的犹太教内犹太复国主义重大范式革命的后果。从一开始,犹太民族主义对犹太宗教的反抗就牵涉对后者词汇、价值、象征、节日、仪式等的稳步增长的工具化。世俗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事业从一开始,就需要一件正式的宗教服饰,既用来维持和加强“民族”的边界,也用以定位和认同其“先辈土地”的边界。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梦想的消失一道,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使得这件正式服饰更显重要。到20世纪末,在政府和军队中,它支撑着以色列民族宗教的意识形态体制的地位。 不过,我们不应被这一相对晚近的进程欺骗。揭开这块土地神秘面纱的不是上帝之死,而是上帝的民族化,它把土地变成了新犹太民族能随心所欲地践踏和建设的一片土壤。如果对犹太教来说,形而上的流亡的反面首要是弥赛亚救赎,是拥有与这块土地的精神联系,而不是对它提出实际的要求,那么对犹太复国主义来说,想象的流亡的反面已经得以显明,即通过创造一个地理的、实实在在的现代祖国,实现对土地的主动救赎。然而,由于缺乏永久的边界,这一祖国对其居民和邻居都很危险。 ◆本书作者施罗默?桑德是民族与民族主义领域的专家。本书是桑德享誉国际的“虚构三部曲”其中一部,三本书都致力于以颠覆性的方式论述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历史,破除各类迷思,解释中东当下的复杂现状,寻求可能的解答,因此“虚构三部曲”又可被称为“祛魅犹太神话与以色列国”三部曲。 ◆《虚构的以色列地》沿袭了作者严谨而坦率的著作风格。桑德的这本书将目光聚焦在以色列建国合法性和巴勒斯坦殖民化的问题上,修正了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撰写的以色列官方历史,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掌握和理解,作者试图涤清蒙在以色列和犹太群体之上的民族主义污垢。本书出版后,因延续前作《虚构的犹太民族》的争议性,又在西方世界掀起一番激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