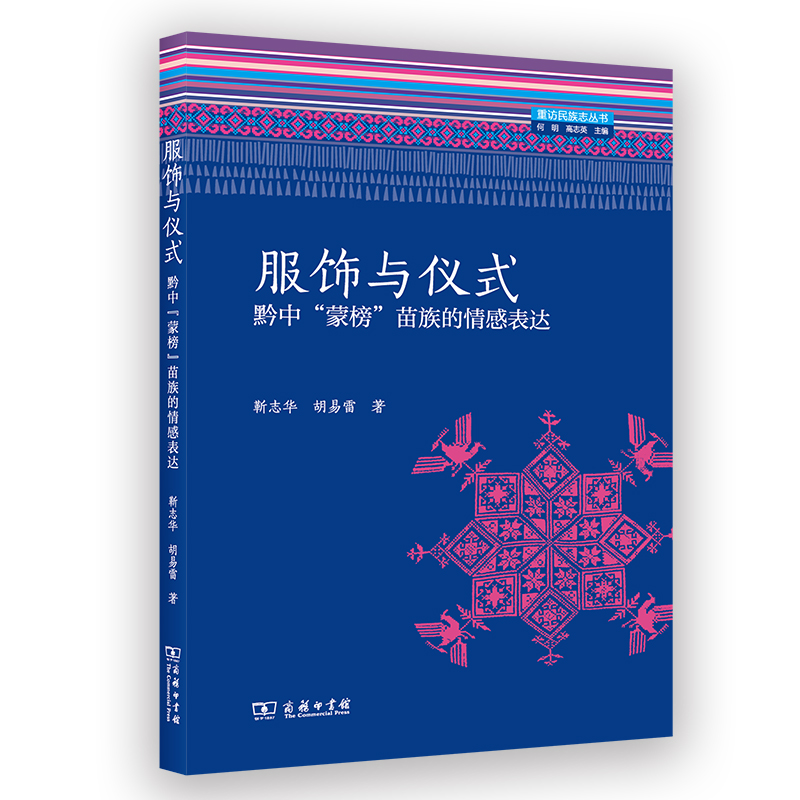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40.60
折扣购买: 服饰与仪式:黔中“蒙榜”苗族的情感表达/重访民族志丛书
ISBN: 9787100220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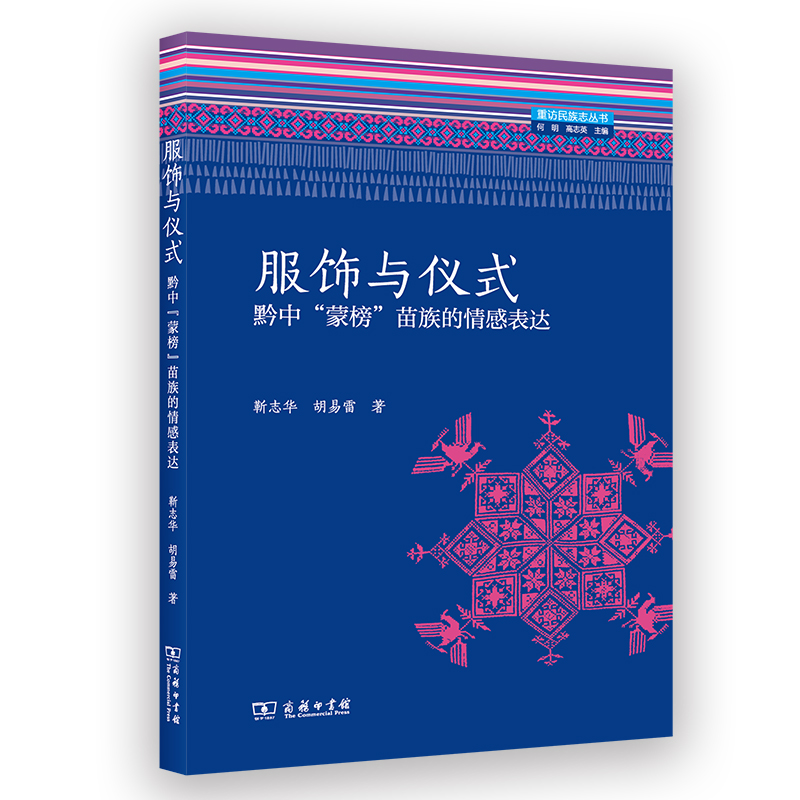
靳志华,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经济。先后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等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著作3部。 胡易雷,现工作于贵州黔南经济学院,主要从事民族文化,民族旅游研究。先后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等发表论文数篇。
导? 论 一、从鸟居龙藏到“蒙榜”苗族 1905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以下简称“鸟居”)游历中国西南诸省,走访调查生活于此的苗族、瑶族、彝族。归国后,鸟居以其观察所得,旁征古今中西图籍,著成《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书中记述了苗族的族源识别、体质特征、风俗习惯、语言等内容,成为贵州苗族研究乃至苗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专著,影响深远。 可以说,鸟居的《苗族调查报告》是一部介绍苗族群体的“游历式”记录文献,基本上沿着入黔交通线散点(重安江、青岩、惠水、安顺等地)调查记录,并没有选择固定的村寨对其诸如社会制度及运转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总体上是走马观花式的感官呈 现和记述。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囿于年代背景以及当时学科的主流研究倾向,鸟居沿袭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学人从心理学、体质学、人种学等学科角度对苗族族体进行划分,厘清了苗族族体的广义与狭义之别,界定了“纯苗”构成的五个支系——红苗、青苗、白苗、黑苗、花苗,仍有其开创之功。 书中,鸟居对苗族的服饰花纹及审美格外关注,从他对黔中一带苗人服饰的详述中可见一斑。尤其是他独辟专章介绍该地的绣布花纹,以采集的衣服,包括小儿背带、胸布、围裙等实物为例,描述其中的色彩搭配与造型织法,并将其与铜鼓花纹做比较,沉迷于苗人刺绣上的纹饰图案及其呈现的情感性格意象。他认为“彼等表现于刺绣上之意匠,为连续花纹,色彩为一种阴郁之表现,……彼等刺绣上所表现之性格,即为柔软阴郁,与表现于笙之音律之沉静、阴郁同一也”。继而以此推断出苗族的性格——“综合此种事实考之,苗族之性质实极阴郁”,“此不可谓非苗人之人种心理学上最应注目之事实也”。与此同时,鸟居将苗族服饰花纹造型与其族源迁徙(与汉人相比)、民族性格进行关联,也开启了民族服饰研究的新路径。 通观鸟居的《苗族调查报告》,书中通过对黔中一带苗人服饰花纹造型与色彩应用的记述得出苗族性格“柔软阴郁”的特质,值得追问与商榷。事实上,鸟居对苗族整体性性格的认识,忽视和混淆了苗族不同方言区群体性格的具体表达,同时也遮蔽了苗族性格的多重呈 现。苗族东、中、西部三个方言区群体,基于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各自群体行为有别。东部方言区(湘西、黔东南)是苗族聚居的大本营,也是最早与中央王朝接触的群体。尤其是?阳河和清水江一带的苗人,在与中原汉人交往的过程中,既有摩擦冲突,也有文化 上的交流与互动;既有硝烟弥漫的战事,也有热情欢快的歌舞。而中西部方言区就有所不同,特别是西部方言区苗族,他们的情感世界中“迁徙与游离”是主旋律,我们从悲怆的《亚鲁王》古歌,从呜咽的芦笙曲中就能感受一二。 他们也是逃避王朝统治,“游” 得最深、 “游”得最远(至东南亚、欧美)的群体。鸟居在调查报告中所接触的主要是中西部方言区的这部分群体,通过走访调查,从他们的服饰纹样及铜鼓芦笙乐调中得出苗族的“整体性”性格——柔软阴郁。由此看来,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迁徙,才有了现在我们对苗族的认识,但对苗族性格的界定,并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忽视内在的群体差异性和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表达。 对于情感,不同的学科亦有不同的理解与看法。在《心理学大辞典》中,情感被解释为“人对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美国心理学家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认为情绪和情感相比较,情绪着重于描述情绪过程的外部表现及其可测量的方面。历史学家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认为情感是人类集体意象的反映,通过人类行为得以表达,并将人类行为合理化。因此,情感是与特定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一种社会现象,情感既由特定社会文化所塑造,又反过来影响特定社会的文化面貌和文化进程。而在《情感社会学》一书中,特纳从社会学的视角认为情感包括以下成分:(1)关键的身体系统的生理激活;(2)社会建构的文化定义和限制,它规定了在具体情境中情感应如何体验和表达;(3)由文化提供的语言标签被应用于内部的感受;(4)外显的面部表情、声音和副语言表达;(5)对情境中客体或事件的知觉与评价。此外,由于受到人类学诸多理论影响,情感的研究基本遵循两大范式,或被视为人类普同的心理生理反应,或被视为人类社会文化塑造的产物。 情感与人的社会性需求相关,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稳定的生活体验,与家族及族群关系以及日常情理密切相关。在某些特定的文化场景中形成集体记忆,不受外界影响而内化于心,如在祭祀场景中的祖先崇拜、服饰纹样中的图腾崇拜等,深沉而久远,不会轻 易改变。同时,情感也是人社会能动性的体现,与自我表述相联系,主要受到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文化教养等影响和制约,如不同的人对认同感、羞耻感、剥夺感、责任感等的认知与理解不同。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认为情感是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实践主体在社会实践中自我表述时而产生的具有一定持续性的生理心理状态。情感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不同主体间的情感体验和感受要放置在特定社会文化时空的互动中去理解分析。这种情感既包括个体间情感如 父子、母女、姊妹、兄弟、恋人等之间的情感,又包括与之关联的家族、村寨,以及族群等集体情感。 黔中是贵州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自元代起,苗族黔中南支系就与朝廷有着较深的接触,汉族文人对这部分苗族的认识和了解也较为丰富。此外,对这一片区最早的记载始见于《安顺府志》,平坝县清道光年间的《安平县志》亦载:“世为蛮夷所居”,但是境内的 苗族来自何朝代,《安顺府志》和旧县志均未明确。旧县志《民生志》载:“苗族来自放逐者,有‘窜三苗’之文,苗族即‘三苗’因窜逐始南来,惟这一片区之苗族,确来自何年,则不可考。”并且,《元史·本纪》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丙午,从葛蛮军民安抚使宋子贤请,招谕未附平伐、大瓮眼、紫江、皮陵、潭溪、九堡等处诸洞猫蛮”。据前辈考证,这里的“猫蛮”,即是汉人称的“苗”。其中平伐在今贵定,紫江在龙里、贵定、开阳三县交界处,瓮眼在龙里,潭溪和九堡则在今天新添寨、乌当附近,而皮陵就在高坡。可见,在这些古籍中有一共同点,即皆粗略提及,并未详细记载这一地区苗族的迁徙史。 尽管如此, 在一些古籍碎片化的文字记载中仍能发现这一片区苗族称谓。《元史·本纪》记载:泰定二年(1325)二月,“丁亥,平伐苗酋的娘率其户十万来降,土官三百六十人请朝”。在元朝的文献中,这一片区的苗族已有称呼,叫作“平伐苗”。在明朝的文献中,也能看到对于高坡及其周边苗族的称呼和记载。《明史·英宗》记载:天顺三年(1460),“夏四月,己巳,南和侯方瑛克贵州苗”。《明史·方瑛传》记载:天顺二年(1459),“东苗干把猪等僭伪号,攻都匀诸卫,命瑛与巡抚白圭,合川、湖、云、贵军讨之,克六百余寨,边方悉定”。《明史·李震传》:“天顺中复以瑛平贵东苗干把猪。”《明史·白圭传》记载:“天顺二年,贵州东苗干把猪等僭号,攻劫都匀诸处,诏进右副都御使,赞南和侯方瑛往讨,圭以谷种诸夷为东苗羽翼,先剿破四百七十余寨……乘胜攻六美山,干把猪就擒,诸苗震詟。”可见,这一方言区的苗族被称作“贵州苗”或“东苗”。在清代的文献中,又把 平坝及其周边的苗族称为“白苗”,如《黔书》载:“白苗在龙里县,亦名东苗、西苗。服饰皆尚白,性戆而厉,转徙不恒。多为人雇役垦佃,往往负租而逃。男子科头赤足,妇女盘髻长簪。”《贵阳府志》又有:“白苗在府属者居中曹司高坡、石板诸寨,在龙里者居东苗坡、上中下三牌、大小谷朗诸寨,在贵定者居摆成、摆布、甲佑诸寨。” 万历末年成书的郭子章《黔记》中,引用了江进之吟诵黔中各族民风的组诗,才首次提到“花苗”这一名称。这个群体分布面积并不广,主要在原水西土司“水外六目的”的东南边缘,以及明代金筑司 辖境的东北角,今贵阳市花溪区辖境的西部。历史上,对黔中花溪、平坝这一片区苗族的称呼并不统一。据《安顺续修府志》《贵州通志》记载,这一片区的苗族以“苗”作为称谓最早见于宋代,如居住在平坝的苗族称为“西苗”,清代又将这一区域的苗族称为“坝苗”“水西苗”。而在清康熙初年陈鼎的《黔游记》中,叙述黔省“苗蛮”种类时,已提及“花苗”和“青苗”等。此外田雯的《黔书》对花苗、青苗的习俗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对花苗称谓的来源进行了记载:“花苗在新贵县广顺州。男女折败布缉条以织衣,无衿窍,而纳诸首,以青兰布裹头。少年缚楮皮于额,婚乃去之。妇人敛马鬃尾杂人发为髲,大如斗,笼以木梳,裳服先用蜡绘花于布,而后染之,既染,去蜡则花见。饰袖以锦,故曰‘花苗’。”陆次云《峒溪纤志》中描述:“苗人,盘瓠之种也……尽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衣各别以色,散处山谷而成寨。”李宗昉《黔记》中记载:“花苗,衣用败布缉条织成,青白相间,无领袖。” 事实上,“蒙榜”是黔中“花苗”的自称。“蒙榜”苗族女性尤 其擅长挑花刺绣,其盛装服饰颜色艳丽,且多为挑花图案,当地人俗称 “花衣服”。黔中“蒙榜”苗族现今主要分布在贵阳市的花溪区、南明区、云岩区、乌当区、白云区、清镇市、修文县,贵安新区以及黔南州的龙里县等地,其服饰、饮食、习俗和语言相同,是同一个方言区苗族群体的统称。整体而言,黔中“蒙榜”苗族相对其他支系的苗族,居住环境较好,多居住在土地肥沃的平坦之地,如贵安新区马场镇新寨、凯掌,云岩区高寨、乌当区石头寨等。本研究以黔中贵安新区为主要田野调查点,同时也兼顾贵阳花溪区及云岩区等地的“蒙榜”苗寨。 “蒙榜”苗族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现在以自由恋爱为主缔结婚约,在形式上要经过提亲、踩门、接亲、吃喜酒等环节。丧葬有送终、开天窗、开斋、升鼓、下银钱、诵亡者、开路、出殡、安葬、复山等仪式流程。 “蒙榜”苗族的传统节庆活动是“跳场”,有时也称“玩场”,是众人集会祭祀先祖以祈求风调雨顺的场合,也是结伴游玩、谈情说爱、联络情感的重要节日。此活动通常在农历一月至七月间举行,按照“蒙榜”苗族的说法,农历一月和二月的场叫跳场(或跳花),三 月至七月的场叫玩场。跳场和玩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场地内栽花竿(立竹竿)。一般来说,跳场必须要栽花竿,而玩场则不需要,但也有例外。相较而言,跳场通常比玩场更加隆重,更受人们重视。玩场或跳场的场地由各村各寨约定俗成,每个村寨都有属于自己的场, 届时不同村寨会以轮流“串场”的方式进行。此外还有四月八节,主要是为了纪念苗族的民族英雄,节时要吃彩色糯米饭。六月六节祈求风调雨顺、家族平安,当天会杀牛祭拜天神。总之,在“蒙榜”苗族传统节日中,以跳场和玩场最为隆重,六月六节最为热闹,四月八节 最具民族特色。 本书基于情感人类学的视角,对黔中花苗从出生、结婚到死亡等重要人生节点的仪式流程展开深描,全面呈现民族服饰在不同场景中传递的情感体验,深入诠释何为以物寄情,值得一读。★语言平实简练,大量当地图片,收获轻松阅读体验; ★一手资料翔实,众多案例的全面呈现有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回应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研究,既有本土视角,又有观点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