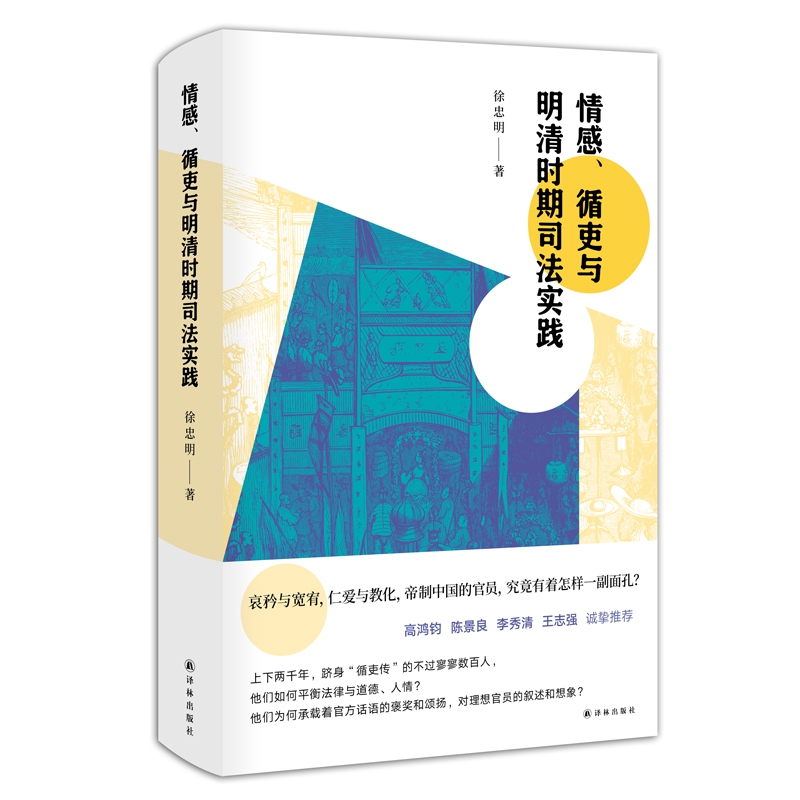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
ISBN: 97875447727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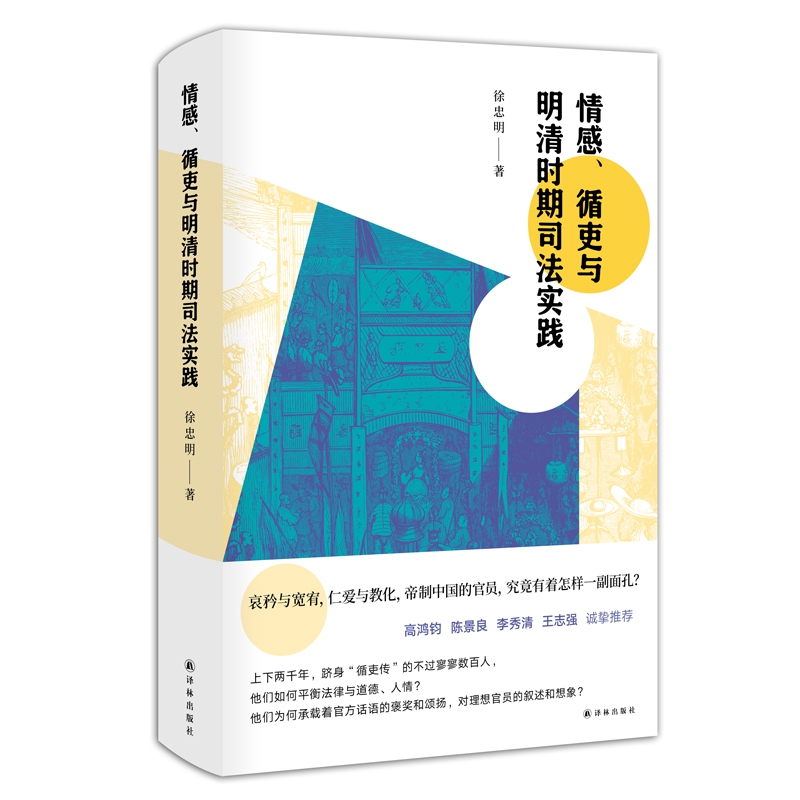
徐忠明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古典中国的法律与文学、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明清中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出版著作《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等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明清循吏的司法技艺:智谋与神判 在前面的讨论中,笔者已经涉及了明清时期循吏的司法技艺问题。因为归根结底,调处息讼与哀矜折狱属于司法技艺中的两个不同侧面。下面,我们将要继续探讨明清时期循吏的司法技艺的另一侧面——破案智慧与超验神判。前者关注的是人的司法智慧,后者凸显的是神的明察秋毫。与此同时,本书还将略微涉及明清时期循吏的法律知识与司法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期揭示司法官员的法律知识和经验能力之于司法实践的价值究竟何在。 倘若我们展读五代和凝父子编辑的《疑狱集》与宋代郑克扩增的《折狱龟鉴》之类传统中国破案断狱的资料汇编,就可以发现,司法官员洞察“人情”和“物理”的能力,乃是他们司法智慧和司法技艺的基础,而在“智慧与技艺”背后,则仍然蕴含着“仁恕哀矜”的道德情感。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人(尤其是儒家)眼里,与“智慧和技艺”相比,道德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和正当性;也就是说,他们对知识和技术进行了道德化的处理。就司法实践而言,司法的“智慧与技艺”同样必须在道德引领下,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述判断,我们来看《疑狱集·序》的相关阐述: 《易》曰:“先王以明罚敕法。”“君子以折狱致刑。”《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两造具备,师听王辞。”是知古之圣贤,慎兹狱讼。念一成而不变,审五听以求情。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俾无枉滥,以召和平。在上者既能尽心,居下者得以措手。其来尚矣,可略言焉。……足使愚夫增智,听讼而不敢因循;酷吏敛威,决狱而皆思平允。助国家之政理,为卿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溥。况当圣世,拒可 忽旃。……父作子述,诚有愧于下才;刑清狱平,冀少裨于大化。 这篇《序》的要旨有三:其一,扼要地阐述了远古圣贤和儒家经典关于“听讼折狱”的核心思想,无论“明罚敕法”抑或“折狱致刑”,关键在乎“惟刑之恤”。所谓“五听求情”,系指司法官员的知识和技术,即司法官员如何通过两造的五种不同(色、气、词、耳、目)的脸部表情和心理反应,来判断他们的“口供”的真实程度,属于“聪明”的智慧范畴——主要是指经验智慧;而“慎兹狱讼”和“致其忠爱”,则包括了司法官员的职业态度和道德情感的两个层面。两者结合起来,它们的最终目的,乃是达到“俾无枉滥,以召和平”的理想境界。其二,简洁地说明了作者编集《疑狱集》的旨趣,所谓“助国家之政理,为卿士之指南”者是也。具体来讲,系指“足使愚夫增智,听讼而不敢因循;酷吏敛威,决狱而皆思平允”。不消说,前者关乎司法的智慧和技艺,后者涉及司法的职业态度和道德情感。合而观之,乃是追求“决狱平允”或“刑清狱平”的司法境界。在作者看来,良好(酷吏敛威和平允无冤)的司法效果,有赖于司法官员的法律技艺和道德情感。其三,所谓“父作子述”一言,既交代了《疑狱集》的编撰情况,又隐含了作者重视司法实践的基本态度。 元代杜震在《疑狱集·序》中也有类似的意见: 狱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王制》曰:“凡听五刑之讼……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古之君子,其详慎用刑而不敢忽也如此。大抵鞫狱之吏,不患其处事之不当,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患其用心之不公,每患其立见之不明。苟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烛,刚足以断狱,无余憾矣。 这篇《序》所欲阐述的基本道理只有一点:唯有在“仁足以守,明足以烛”(道德与智慧兼容并包)的条件下,司法官员才能实现“足以断狱”之目的。总之,在中国古人看来,法律知识与司法技艺,只是听讼折狱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内容。换句话说,司法官员的道德情感(哀矜)与职业态度(审慎),乃是实现司法平允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对此,南宋景定年间的赵时藁在《折狱龟鉴·跋》中这样写道:“盖狱者民之命,折狱者贵其明而尤不敢轻用其明。龟鉴有书,所以推广其明而示人以慎重之意也。”在赵时藁看来,司法官员的折狱态度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司法官员必须要“明”,但却不能轻易用“明”,进而,即使具备了“明”,仍然要用“慎”来加以约束。无论“明”抑或“慎”,都要秉承一个基本前提,即是“惟良折狱”的古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惟良折狱,罔非在中”与“哀敬折狱,咸庶中正”的理想境界。归根结底,还是强调司法官员的道德操守,只是,赵时藁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法律知识和司法技艺之于听讼折狱的关键作用。 此外,清代道光年间的许梿在《折狱龟鉴·叙》中这样写道: 甲午岁冬,与天门熊君璧臣有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之刻,以为案者已成之狱,而深有感于哀敬折狱之旨。……或疑其(笔者按:系指《折狱龟鉴》)偏主于宽,未协中道,不知法有宽有猛,心有宽无猛,道德之弊,犹或流为申韩,刻核以立论,其不为《罗织经》者几希。……著其法于事,而存其心于论,不可谓非中道。……读是书者,知人罪之出入,务慎之于定案之先,其于哀敬之思,且油然生矣。 许梿在《叙》中明确指出:“哀敬”乃是折狱的核心价值。与此同时,针对有人批评《折狱龟鉴》偏于宽宥的论调,许梿认为:首先,司法官员应持“有宽无猛”的折狱态度,这显然是“哀矜”思想的另一表述。其次,竭力表彰《折狱龟鉴》能够贯彻“著其法于事,存其心于论”的“中道”精神—法律与情感之间的平衡,审慎与哀矜之间的平衡。 一句话,像《疑狱集》和《折狱龟鉴》以降的司法故事汇编,有着千年一贯的传统,它们旨在展现,在司法官员必须具备“审慎”的职业态度与“哀矜”的道德情感的前提条件的引领下,传统中国的司法智慧和司法技艺。反过来讲,它们也是传统中国司法经验的积淀与汇总。所以,把握其中的核心要义,对于我们理解传统中国的司法实践的意义,实在不可小觑。而这也是本书专门予以讨论的原因之所在。 这种思想观念、法律知识和司法技艺,在郑克所撰《折狱龟鉴》的“按语”中也有很好的体现,囿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下面,我们来看历代《循吏列传》中的记载。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皃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其中,所谓“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一句,可谓意蕴丰富。随着孝武皇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战国以降逐步形成的法制传统与“吏道”传统,如今渐次朝着“儒法结合”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以“通于世务”来概括的行政和司法的经验知识,与文本上的法律知识和经典知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融合的局面。由此,儒家倡导的“哀矜折狱”的司法理念,也得到了相应的落实。2这是循吏得以兴起—尽管他们早在文景时期就已出现,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兼顾“法律与道德”的意识形态背景。 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盛赞黄霸的司法能力,文曰: 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为丞,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 会宣帝即位,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 可见,黄霸兼具“明察内敏,又习文法,温良有让”的司法经验和道德情感。在司法实践中也能做到“持法平允”,从而赢得了“吏民爱敬”和皇帝的赏识。然而,这些都是一般意义上的评论,而没有涉及具体的决狱智慧。 在《南齐书·良政列传》中,则记载了傅琰决狱的著名故事: 故事一 太祖辅政,以山阴狱讼烦积,复以(傅)琰为山阴令。卖针卖糖老姥争团丝,来诣琰,琰不辨核,缚团丝于柱,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 故事二 二野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鸡得粟,罪言豆者。县内称神明,无敢复为偷盗。 从傅琰审理的两个案件中,我们看到了傅琰确实颇具司法的智慧和能力。然而,这种智慧和能力与法律知识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凸显傅琰的明察和经验。它们与传记“琰尤明察,又著能名”的评价吻合,主要表现在揭破真相和获取证据的能力上。就两个案件的取证而言,我们确实看到了傅琰观察“物理”的能力,但是必须承认,这种“观察”尚需一定的条件。这里,我们稍作抬杠。在“故事一”中,如果卖糖者足够机智,事前也来“敲打”团丝,那么傅琰的取证工作,就有可能受阻。在“故事二”中,倘若“言豆者”足够聪明,拖延一下时日,等到鸡胃中的食物排泄干净,再去衙门诉讼,那么傅琰的判断也会出错。当然,这些都是“马后炮”式的事后高明,甚至是无理取闹,并不符合案发当时的情境。况且是否即时提起诉讼,也非“言豆者”能够单方决定。不过这也告诉我们,揭破案件的事实真相,确实并非易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据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胡适要将包公式的司法官员视为“中国的歇洛克· 福尔摩斯”。根本原因,即是他们的案件侦破能力和获取证据能力,与法律知识和是否“依法裁决”无关。与此同时,这也告诉我们,一味以法律知识来考虑传统中国司法官员的决狱能力,可能有失偏颇。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在传统中国社会,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或许并非由于司法官员的法律知识不足,而是因为他们“兼负”的破案能力不够,再加“审限”制度的约束,一旦草率将事,难免出现冤假错案。 这类刻画司法官员“明察”的故事,在历代《循吏列传》中还有若干。现在,我们来看明清时期《循吏列传》的相关记载。先来解读《明史·循吏列传》中的故事: (张淳)授永康知县。……巨盗卢十八剽库金,十余年不获,御史以属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盗,而请御史月下数十檄。及檄累下,淳阳笑曰:“盗遁久矣,安从捕。”寝不行。吏某妇与十八通,吏颇为耳目,闻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令他役诈告吏负金,系吏狱。密召吏,责以通盗死罪,复教之请以妇代系,而己出营赀以偿。十八闻,亟往视妇,因醉而擒之。及报御史,仅两月耳。 一个“十余年不获”的巨盗卢十八,却在张淳手里仅仅费了“两月”即被缉获,充分展现出张淳侦破案件的超强能力。必须指出,张淳缉获巨盗的手段,属于“钩慝”之法。所谓“钩慝”之法,郑克在《折狱龟鉴》中曾有简要的解释:“按:贼逃匿者,谲使出焉,免于追捕之烦,其术固不可废。然人之逃匿,既可谲取之矣,则贼之隐匿,亦可谲取之也。擿奸钩慝,是谲取其情者也。”说白了,所谓“钩慝”,即是“诈术”。在侦破这起巨盗案件时,张淳设计了一个连环套。首先,他“请御史月下数十檄。及檄累下,淳阳笑曰:‘盗遁久矣,安从捕。’寝不行”。请求御史不断下檄,乃是为了迫使巨盗逃匿;张淳“寝不行”而佯装懈怠,则是为了麻痹巨盗,使其放松警惕。卢十八果然中了圈套,所谓“意自安”,即是此意。其次,张淳得知“吏某妇与十八通,吏颇为耳目,闻淳言以告十八”,随即采取将计就计的办法,“乃令他役诈告吏负金,系吏狱。密召吏,责以通盗死罪,复教之请以妇代系,而己出营赀以偿”。张淳利用“钩慝”之法,达到“引蛇出洞”之目的。果不其然,巨盗得知吏妇入狱,“亟往视妇”,却因醉而被张淳擒获。 顺便指出:其一,根据《大明律》卷十八“常人盗仓库钱粮”规定,得财价值八十贯,处以绞刑。据此,巨盗卢十八至少应判绞刑。另据卷二十七“知情藏匿罪人”规定:“若知官司追捕罪人,而漏泄其事,致令罪人得以逃避者,减罪人罪一等。”其二,按照卷一“加减罪例”规定:死罪减一等,应得流三千里。如果这样的话,某吏当得流三千里的刑罚。由此看来,张淳“责(某吏)以通盗死罪”的指控,恐怕与法律规定不合。其三,至于“复教之请以妇代系,而己出营赀以偿”的举措,更是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根据《大明律》卷二十八“囚应禁而不禁”规定:对于流罪囚犯应禁而不禁,相关的司法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笞责五十。所以,张淳让某吏“己出营赀以偿”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然而,在张淳看来,只要能够缉获罪犯,采取何种手段并无严格限制,在法律上是否得当也可以在所不问。实际上,这并不是张淳的个人风格,而是传统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现象。 描写张淳善于听讼和破案的评价和故事,在传记中还有记载。请看: 故事一 (在建康担任县令时)日夜阅案牍。讼者数千人,剖决如流,吏民大骇服,讼浸减。凡赴控者,淳即示审期,两造如期至,片晷分析无留滞。乡民裹饭一包即可毕讼,因呼为“张一包”,谓其敏断如包拯也。 故事二 民有睚眦嫌,辄以人命讼。淳验无实即坐之,自是无诬讼者。 故事三 岁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夺者死。有夺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杀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众旨慑服。 故事四 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车,顾其下曰:“某盗已来,去此数里,可为我缚来。”如言迹之,盗正濯足于河,系至,盗服辜。永人骇其事,谓有神告。淳曰:“此盗捕之急则遁,今闻吾去乃归耳。以理卜,何神之有。” 关于“故事一”,前面已经作过讨论,不再赘述。根据“故事二”所述,明清时期的民间百姓往往因“睚眦小忿”而“辄以人命”起诉,这种风气非常流行。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只要尚未造成致命后果,地方官员往往以“乡愚无知”为理由,采取网开一面的态度,或者以“讼简刑措”为借口,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很少按照“诬告反坐”的法律进行惩办,通常是杖责了事,以致诬告之风炽盛,成为难以根治的社会问题和司法顽症。有所不同的是,张淳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民众的诬告风气,不是采取“姑息养奸”的态度,而是依法予以惩罚,传记所谓“验无实即坐之,自是无诬讼者”。再加张淳“剖决如流”的干练敏断和勤于听讼,从而出现了“吏民服,讼浸减”的结果。事实上,这也是“仁恕爱民”和“钦恤罪犯”的表现。必须指出:民众诬告与地方官员消极懈怠、压抑诉讼、处置不当或审断不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地方官员的上述行为,才导致了民间百姓的诬告和缠讼的风气。在“故事三”中,张淳针对饥民公然劫掠的行为,一是“下令劫夺者死”,这仅仅是文本上的恐吓,未必有效。这是因为对于真正的“夺五斗米者”,张淳又不忍心根据自己所下的“劫夺者死”的命令处以死刑。换句话说,张淳的司法实践,仍然蕴含着“哀矜”饥民的道德情感。二是“佯取死囚杖杀之”,并且“榜其罪曰‘是劫米者’”。这当然是一种“杀鸡儆猴”的策略。不过两者相配,颇能给人一种“令行禁止”的感受。由此可见,张淳措置干练,应对灵活机变,以致取得了“众旨慑服”的积极效果。在“故事四”中,我们更能看出张淳的破案能力。就表面而言,很有一种“料事如神”的气派。但是,我们从张淳自谓“此盗捕之急则遁,今闻吾去乃归耳。以理卜,何神之有”一言可知,这是张淳“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而后取得的司法能力。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张淳的司法能力并非来自法律知识,而是来自先天智慧和后天经验。 我们再看《清史稿·循吏列传》中的其他故事: 故事一 (咸丰年间,李炳涛先后出任蒙城和亳州牧令,有机警,善断狱之誉。)在蒙城,营马为贼所劫。乃传谕,诘旦城但启一门。见有马奔出,有鞍而无辔,命羁之。俄一人手持一封,将出城,回顾者再,缚之。发其封,则辔与劫物皆在,其人伏罪。 故事二 在亳州,田父报子夜投井死,验无伤,井旁有汲水器。炳涛念夜非取水时,既原死,何暇持器。询其妇,无戚容。侦其平日与邻妇往来,拘邻妇鞫之,果得状。盖邻妇弟与妇通,欲害其夫。适其夫以事忤父,邻妇邀醉以酒而投之井。置汲器者,欲人信其取水投井也,于是皆伏法。 就“故事一”而言,李炳涛可谓“机警”,而其成功缉获盗马贼的根本原因,乃是洞察人情事理。首先,传谕“诘旦城但启一门”的理由,是因为李炳涛洞察盗马贼急需出城,逃避官府的追捕。可以想象,如果四处城门皆开,就会给缉捕盗马贼带来不必要的困难。其次,李炳涛下令只要“见马奔出,有鞍无辔,羁之”,是因为被盗之马有鞍无辔,这是缉捕盗马贼的重要线索,不能轻易放过。果不其然,捕快一举缉获了盗马贼。其中,尚有盗马贼“回顾者再”的细节,引起了捕快的注意,从而将盗马贼绑缚归案。从“故事二”来看,引起李炳涛特别注意的疑点有三:一是“夜非取水时”,二是“既原死,何暇持器”,三是“询其妇,无戚容”。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经验与人类情感的反映。试想:在通常情况下,谁会深更半夜去井边打水?一个想要自杀的人,难道还会带着汲水工具投井自杀?面对丈夫死于非命,妻子难道毫无悲切的情感流露?这些都是违反常识(常理和常情)的现象,因此引起了李炳涛的注意。可见,这是一起他杀案件。据此判断,李炳涛展开了调查,结果案件的真相得以大白天下——邻居“妇弟”与死者妻子私通,起意谋杀亲夫。案发现场乃是被告的伪造,以期制造自杀的假象。案件被李炳涛审问清楚,被告只得认罪服法。值得稍事探究的是,就“邻妇弟与妇通,欲害其夫。适其夫以事忤父,邻妇邀醉以酒而投之井”来看,其中有一法律问题值得追问:死者之妻是否与奸夫共谋?单就此言而论,死者之妻似乎并不知情,因为“欲害其夫。适其夫以事忤父,邻妇邀醉以酒而投之井”表明,是邻妇和兄弟密谋将死者投之于井的。而且从“拘邻妇鞫之,果得状”来看,结果也是如此。否则,何以李炳涛只字不提死者之妻的行为呢?倘若这样,那么,根据《大清律例》卷二十六“谋杀奸夫”规定:“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凌迟处死;奸夫处斩。监候。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绞。监候。”在本案中,邻妇也参与了谋杀亲夫的犯罪,按照同律卷二十六“谋杀人”规定:“凡谋杀人,造意者,斩,监候。从而加功者,绞,监候。”综上,奸夫当得斩监候,邻妇当得绞监候,奸妇也应该处以绞监候。当然,传记没有提到三人应该如何定罪量刑。 下面,我们接着分析《清史稿·循吏列传》的故事: 故事一 (乾隆年间,朱休度出任山西广灵知县)尤善决狱,刘杷子妻张,以夫出,饥欲死,易姓改嫁郭添保。疑郭为略卖,诘朝手刃所生子女二而自刭。休度诣验,妇犹未绝,目郭作声曰:“贩,贩!”察其无他情,谳定,杷子乃归。众曰: “汝欲知妇所由死,问朱爷。”休度语之状,并及其家某事某事。杷子泣曰:“我归愆期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 故事二 薛石头偕妹观剧,其友目送之。薛怒,刃伤其左乳,死。自承曰:“早欲杀之,死无恨。”越日,复诘之曰:“一刃何即死也?”薛曰:“刃时不料即死。”曰:“何不再刃?”薛曰:“见其血出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遂以误 杀论,减戍。 如欲审理这两起杀人案件,关键在于“明察”案件的事实真相。不过在“故事二”中,也涉及了法律适用问题,此乃后话,暂且不说。 我们先看“故事一”的描述。本案的事实比较简单,关键在于如何判断。传记写道:“休度诣验,妇犹未绝,目郭作声曰:‘贩,贩!’察其无他情,谳定。”根据这一描述,朱休度似乎完全相信刘氏临死之前的口供:“贩,贩!”意即,刘氏的新任丈夫郭添保贩卖人口。配合朱休度的现场勘验,得出“其无他情”的判断,确实有其道理。当然,本案死者刘氏的改嫁,倒是值得我们深思。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现实生活的压力可能要比礼教纲常的压力来得更加实实在在。换句话说,理学家标榜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语)的教条,对于社会底层的妇女来讲,实际影响或许并不是很大。换句话说,在生存压力下,民间妇女之改嫁,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令人感到羞耻。 在“故事二”中,核心问题有三:首先,被告自承:“早欲杀之,死无恨。”就此而言,被告似有杀人故意,从“欲”字可以看出。朱休度复诘:“一刃何即死也?”被告回答:“刃时不料即死。”实际上,这也可以用来说明,被告下手很重,以致一刀毙命;况且伤在“左乳”,很有可能刺中心脏,以致毙命。当然,我们不太清楚的是,这一刀究竟是“砍中左乳”还是“刺中左乳”。但是朱休度好像不信,因此又问:“何不再刃?”被告再答:“见其血出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这意味着被告没有再次下手杀人的决心与狠心。综上两点,朱休度认为:“一刃即死”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被告已有“不忍再刃”的意图。如果这样的话,恰好可以证明,死者毙命出乎被告的意外,因此不是谋杀或者故杀,而是误杀。这就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其次,我们来看朱休度作出“误杀”的判决是否得当。那么,什么是“误杀”呢?根据《大清律例》卷二十六“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规定:“因斗殴而误杀伤旁人者,各以斗杀伤论。(死者,并绞。)”据此,被告的行为与“误杀”根本不同。对此,清代著名律学家沈之奇作了很好的解释:“误中旁人,出于不意,然其心则欲以杀伤人之心也,虽未及于欲殴、欲杀之人,而旁人已被杀伤,则其殴与杀之事,已施于人矣。故由斗殴而误者,以斗杀伤论;由谋杀、故杀而误者,以故杀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者,死者与被告没有斗殴。当然,鉴于记载简单,我们难以判断两人是否相斗或相殴,不说也罢。二者,即使斗殴,被告并非误杀旁人。所以,朱休度的判决并不得当。依我看来,被告的行为更像是谋杀,而非故杀,更非误杀。因为被告声称“早欲杀之”和“一刀毙命”两个情节,已经足以证明被告的行为特征是谋杀。如果被告属于谋杀,那就应得斩刑。必须指出,与现代刑法及其理论不同,在传统中国法律里,谋杀与故杀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强调杀人的预谋,后者乃是临时起意的杀人。按照《大清律例》卷二十六“谋杀人”的解释,所谓“谋”,系“或谋诸心,或谋诸人”的意思。又据“斗殴及故杀人”的解释,所谓“故”,指“临时有意欲杀,非人所知”的意思。不过“临时有意欲杀”的语境,则是斗殴。再次,即使是“误杀”,根据“律注”解释,被告应得绞刑,而非“减戍”,意即流刑。当然,所谓“减戍”,也可以被解释成在绞刑上减一等,应得流三千里的刑罚。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减戍”无疑属于宽宥的处罚。复次,按照“斗殴及故杀人”所附条例规定:“凡审理命案,一人独殴人致死,无论致命不致命,皆拟抵偿。”可见,本案被告也应得死刑,而非流刑。总而言之,朱休度作出“减戍”的裁决,无疑是出于“哀矜”囚犯而“宽宥”其罪,减轻其刑。最后,笔者推测,朱休度之所以认定被告属于“误杀”,可能是因为被告仅仅砍了一刀,而且砍的地方也非致命的左乳,其友死亡出乎自己的意外,未能产生正确的结果,或者说产生了不正确的结果。在通常意义上,对“误”的这种理解,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就“误杀”的法律定义而言,则是错误的。那么,朱竟是因为法律知识不足而导致认识上的错误,抑或是为了开脱被告罪责而故意作出的错误理解?笔者更愿意接受后面一种解释。这是因为根据传记的记载,朱休度对于法律颇为精通,适用法律也很慎重,并有丰富的司法经验和司法能力。请看传记所谓:“休度尝曰:‘南方狱多法轻情重,北方狱多法重情轻,稍忽之,失其情矣。’待人以诚,人亦不忍欺。周知民情,诉曲直者,数语处分,民皆悦服。数年囹圄一空,举卓异。”如果他对于法律懵懂无知,那么传记作出这样的评价,显然是混淆视听。根据笔者上面的分析,传记这一评价颇为得当。但是就朱休度裁决的案件来看,依然不免超越法律的做法。据我看来,朱休度之所以如此裁决,是因为出于“哀矜”囚犯的考虑,而非司法能力与法律知识的不足。顺便一提,朱休度有关“地域文化与法律轻重”的概括,实际上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和“因风俗而形成礼教”的另一说法,并非什么新鲜的观点。程颐曾说:“南方人柔弱,所谓强者,是义理之强,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强悍,所谓强者,是血气之强,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气,须要理义胜之。”2所谓“血气强”,故而刑罚须重;所谓“义理强”,所以刑罚应轻。这与廖冀亨因吴人体质柔弱而不愿处以重罚的意思,刚好相同。因此,我觉得,如此理解朱休度的概括,也非不得要领。 在明清时期的《循吏列传》中,尚有其他描写循吏破案决狱的智慧与能力的故事,这里不再一一展开讨论。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几个比较特殊的破案决狱的故事。也就是说,当人的智慧和能力不足以完成侦破案件或决断狱讼的艰巨任务时,明清时期的循吏又是怎样借助神的明察秋毫之超验能力来破案决狱的呢?这个问题较少受到学者的关注,相关的学术成果也不是很多。这里从瞿同祖先生的讨论说起。他说: Robson说神判法是普遍的习惯,在世界上很少有一国家不曾使用这方法,唯一的可能的例外是中国,中国人中找不到神判的痕迹。(见W.A. Robson, Civil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Law, Macmillan, London, 1935, p.112, note 1)是慎重而较合于历史事实的论断。 中国有史以来就以刑讯来获得口供,早就不仰赖神判法了。但在使用刑讯以前,似也曾经过神判的阶段。 神判法在中国的历史时期虽已绝迹,但是我们只是说在规定的法律程序上不见有神判法而已。实际上神判法依然有其潜在的功能。官吏常因疑狱不决而求梦于神,这显然是求援于神的另一种方式。 细绎瞿同祖先生的观点,不外是说:由于上古中国的人文进化较早,因此自从有史(文明时代降临)以来,在国家的法典和法规中已经不见神判法的痕迹,而且在法律程序上也没有神判的遗迹。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官员如果遇到疑难案件,单凭人的理性智慧不能侦破解决,那么求助神的超验智慧也是时有所见的办法,它是神判的另一方式。近些年来,更有学者张大其事,认为传统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具有“鬼神化”的特征。这一判断颇有道理,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课题,即关于“民众法律意识”的课题。但是,审视其著作罗列的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谈论“民众法律意识”的内容,实际上与“官方法律意识”和“精英法律意识”仍有不少重叠部分。譬如,作者谈到“善书”中的法律意识,就不仅仅涉及民众的法律意识或法律信仰;再如,其中提到的“城隍信仰”,也非单单关乎民众的法律意识或法律信仰,因为“城隍信仰”属于国家祀奠的正式内容,而非纯然是民众的信仰。对此,英国人类学者王斯福指出:“城隍是民间崇拜与官方崇拜之间象征性对话的基点。这是比较妥帖的意见。据此,城隍崇拜是官方与民间共有的信仰。 必须指出的是,第一,就早期中国神判的发生学意义而言,瞿同祖先生已有非常敏锐的观察。他说:獬豸神兽的传说诞生的时代,正是上古中国“第一法官产生的时代,其巧合不是无因的。这种神兽后代虽然绝迹,但汉以来法官一直以獬豸为冠服。犹有其遗留,至少上古的人都相信此种传说。可能当初即普通的羊,后人不明了神判的意义,加上神话的渲染。亦可能当初以羊为判时即利用神的心理,使人易于信服。后来獬豸的绝迹与其说是神兽的绝迹,毋宁说是神判法的绝迹”。由此,我们可以将早期中国的神判传统与许慎所谓“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换句话说,许慎关于“灋”的含义的著名解释,与神判的历史遗迹有关。当然,从司法制度的角度来看,神判早已不是汉族政权的司法传统的特点,但神判的印迹倒是不绝如缕,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它的痕迹。第二,从“城隍崇拜”的历史脉络来看,作为城市守护神的城隍信仰的起源很早。据说,城隍之名,最早见于《易经》第十一卦“城复于隍,勿用师”的记载。在《礼记·郊特牲》中,则有“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祭坊与水庸事也”。后有“水庸居七,水则隍也,庸则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的注释。综上,城隍之祭,似乎与农业丰歉之报有关。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将城隍释作“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可见,城隍是指城市的城墙与沟壕,城是居住区,隍是防御沟或防御池。另外,尚有学者认为:城隍祭祀始于尧舜时代,因为“伊耆氏”即“尧也”。至少到了隋唐时期,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工商阶层的兴起,城隍信仰得以发展,从京师到全国各地的府县都普遍修建了城隍庙。洎乎明清,城隍信仰和城隍祀典有了空前的发展,城隍地位也被帝国政府抬高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城隍信仰的政治作用得到了凸显,与世俗社会官僚系统匹配的冥界官僚架构,也渐成系统。3姑且撇开城隍的各种具体功能不谈,作为世俗社会的司法实践之守护者和监督者的城隍,不但成为民众申冤雪枉的对象,而且司法官员遇到难以侦破和裁决的疑难案件,也会祝祷城隍。由此,城隍也就变成了传统中国的司法神。顺便指出,城隍神有时是那些深得民心的司法官员生前死后被晋封的,以期福佑一方平安。实际上,明清时期《循吏列传》记载的神判故事,基本上都是诉诸城隍的审判。 那么,城隍信仰的政治意义和司法意义究竟怎样呢?明初洪武二十六年“祭文”写道: 凡我一府境内人民,傥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轻则笞决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我等阖府官吏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蠹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照报。如此,则鬼神有鉴察之明,官府非谄谀之祭。尚享。 如果我们将“祭文”中的“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与朱元璋手书的《教民六谕》所谓“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相比,即可发现,两者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内容也大致相同。就此而言,国家倡导的礼法秩序和良好风俗,不仅仰赖世俗政权和民间社会的积极推动,而且要靠幽冥世界的神灵予以配合。另外,在明代洪武二十六年《告城隍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果有生为良善,误遭刑祸,死于无辜者,神当达于司,使之还生中国,永享太平之福。如有素为凶顽,身死刑宪,虽获善终,亦出侥幸者,神当达于所司,屏之四裔,善恶之报,神必无私。……神当钦承敕命,镇控坛场,鉴察善恶,无私昭报。 清代著名循吏汪辉祖曾经这样写道: 朝廷庙祀之神,无一不当敬礼,而城隍神尤为本境之主。余向就幕馆,次日必斋诚诣庙焚香,将不能不治刑名及恐有冤抑,不敢不洁己佐治之故,一一摅诚默祷,所馆之处,类皆宁谧。馆仁和,则钱塘多狱;馆钱塘,则仁和多狱。其后,馆乌程、归安,亦然。当事戏号余为福幕。自维庸人庸福,荷主人隆礼厚糈,所以蒙神佑者大矣。窃禄宁远,亦以素心誓之于神,凡四年,祈祷必应,审理命案,多叨神庇。而刘开扬一事,尤众著者。谨略书于左,以著城隍神之有益吏治云。 据此,如果我们从官方“神道设教”的角度来看,那么城隍信仰的政治意义与司法意义实在不可小觑。对此,著名学者杨庆堃也曾指出:“城隍通过支配人死后的灵魂,以其威慑力对人的道德良知产生了影响,正如世俗政府以法律的威慑力管理人的行为一样。”又说:“这足以证明城隍信仰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已经成为传统社会加强政治伦理秩序的重要手段。”这样一来,从人间世到幽冥界,从人法(王法)到神法,就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权力网络与惩戒体系,从而发挥了控制人们的行为和精神的功能。汪辉祖所谓“庸人稚妇,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诛,且畏土神甚于畏庙祀之神。神不自灵,灵于事神者之心,即其畏神之一念,司土者为之扩而充之,俾知迁善改过,讵非神道设教之意乎?” 正是鉴于城隍崇拜具有“神道设教”的重要作用,故而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员到任伊始的首要任务,即是告祭城隍。例如,黄六鸿在《入境》中说:“上任前一日或前三日,至城隍庙斋宿。”在《斋宿》中又讲:“斋宿例于城隍庙,如不便,就宿公馆,于行香时诣城隍庙亦可。”在《到衙门》中提到:“上任日照择定某时,穿吉服,诣城隍神前,行祭礼……”在《到任祭城隍文附》中我们可以读到祭祀的写作格式,核心内容不外乎是“善恶报应”的意思。 除了上书具有一般意义的关于城隍崇拜的政治、司法和教化功能的阐述之外,汪辉祖更是现身说法,特别介绍了自己利用城隍信仰破案决狱的好处。请看“敬城隍神”的记载: 刘开扬者,南乡土豪也。与同里成大鹏山址毗连。成之同族私售其山于刘氏,大鹏讼于县,且令子弟先伐木以耗其息。开扬虑讼负,会族弟刘开禄病垂死,属刘长洪等负之上山,激成族斗争,则委使殴毙,为制胜之计。比至山,而伐木者去,长洪等委开禄于地,开扬使其子闰喜击开禄额颅立毙,而以成族殴死具控。余当诘开扬,辞色可疑,絷焉。已而大鹏词诉辨未殴而已,终不知殴者主名,因并絷大鹏同至城隍庙。余先拈香叩祷,祷毕,命大鹏、开扬并叩首阶下。大鹏神气自若,而开扬四体战栗,色甚惧。余更疑凶手之不在成氏矣,然不敢有成见也。相验回时已丙夜,复祷神,鞫两造于内衙,讫未得实。忽大堂声嘈嘈起,询之,有醉者闯入,为门役所阻,故大哗。命之入,则闰喜也。开扬大愕,跪而前曰:“此子素不孝,请立予杖毙!”余令引开扬去,研鞫闰喜,遂将听从父命击开禄至死颠末,一一吐实;质之开扬,信然。长洪等皆俯首画供,烛犹未跋也。次日覆鞫闰喜投县之故,则垂泣对曰:“昨欲窜匿广西,正饮酒,与妻诀,有款扉者,呼曰:‘速避去,县役至矣!’启扉出,一颀而黑者导以前。迨至县门,若向后推拥者,是以哗。”夫闰喜下手,正凶也,牍无名,而其父开扬方为尸亲,脱俟长洪等供吐拘提,已越境飏去安能即成信谳。款扉之呼,其为鬼摄无疑也。杀人者死,国法固然,懵昧如余,得不悬案滋疑,则神之所庇,不信赫赫乎! 这是一起不知杀人真凶的疑案。在这种情况下,汪辉祖利用民众崇拜和敬畏城隍的心理,将两造带到城隍庙进行审理,一番焚香祝祷之后,根据两造不同的心理反应和神情表现,初步判定凶手不是成大鹏。进而慑于城隍的威力,真凶刘闰喜发癫,供出真情。因此,汪辉祖才会说:“款扉之呼,其为鬼摄无疑也。杀人者死,国法固然,懵昧如余,得不悬案滋疑,则神之所庇,不信赫赫乎!”其自信和自得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这类故事,在《循吏列传》中也不乏记载。譬如,在《梁书·良吏列传》中记有何远修缮“城隍”的政绩。1第一例诉诸城隍的司法故事,见于《元史· 良吏列传》的记载: (田滋)大德二年,迁浙西廉访使。有县尹张彧者,被诬以赃,狱成,滋审之,但俯首泣而不语。滋以为疑,明日斋沐,诣城隍祠祷曰:“张彧坐事有冤状,愿神相滋,明其诬。”守庙道士进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状到祠焚祷,火未尽而去之,烬中得其遗稿,今藏于壁间,岂其人耶?”视之,果然,明日,诣宪司诘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状示之,皆惊愕伏辜,张彧得释。 当然,这起案件最终得以水落石出,并非由于城隍的显灵,而是道士提供的线索。但是,从罪犯祝祷城隍的行为来看,是祈求城隍神的福佑,以期逃脱司法的追究;反过来讲,就田滋行为而言,同样是希望得到城隍爷的帮助,从而查明疑案的事实真相。 我们转而来看《明史·循吏谢子襄列传》记载的城隍裁判的事例: 有盗窃官钞,(谢)子襄檄城隍神。盗方阅钞密室,忽疾风卷堕市中,盗即伏罪。 不消说,《明史》作者叙述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如何量刑,而是怎样缉获盗犯。我们可以设想,以当时的刑事侦察技术,如果盗犯没有留下犯罪线索的话,欲想逮捕盗犯,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官员利用人们普遍信仰的城隍的明察秋毫的超验能力来侦破案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但问题是,这个故事讲得有点离奇,也即谢子襄祝祷城隍,居然成为“忽疾风卷(钞)堕市中”的原因。据我看来,这种因果关系的建立,显然属于《明史》作者“想当然尔”的描写,而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不过作者之所以这样描写,一则可能是出于“神道设教”的目的而故神其事;二则可能是来自民间已经流传的故事而被作者所采纳,成为一个“真实”的故事;三则可能是谢子襄祝祷城隍与“忽疾风卷(钞)堕市中”恰好在时间上吻合,而给人一种逻辑上的关联。而其背后,或许正如汪辉祖所谓“神不自灵,灵于事神者之心”的信仰。 在《明史·循吏信中列传》中另有一个神判的故事: (乐清)盗杀一家三人,狱久不决。信中祷于神,得真盗,远近称之。 这里,如果我们将“狱久不决”与缉获“真盗”联系起来考虑,或许可以推测,当时可能已经缉获“假盗”,只是由于信中不敢轻率定谳,因而成为“狱久不决”的疑案。也因此,信中才会向神祝祷。此其一。信中之所以不敢轻率定谳,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是一起“盗杀一家三人”的重大案件,属于《大明律》中的“十恶不赦”的重罪,稍有不慎,极有可能铸成冤案。此其二。在这种情况下的神判,可以说是“哀矜折狱”的另一种表现。 另据《明史· 循吏李骥列传》的记载: (东安)有嫠妇子啮死,诉于(李)骥。骥祷城隍神,深自咎责。明旦,狼死于其所。 嫠妇因幼儿被啮死而到东安县衙向李骥告状,很有可能是不知道幼儿的死因。如果我们以现代的刑事侦察技术来判断,那么排除“谋杀”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倘若这样的话,那么寡妇告状之事可能纯属多余。然而,中国古人没有这样的技术,因而只得祝祷城隍以求破案。不过奇怪的是,李骥祝祷城隍的翌日早上,发现了一头狼死于寡妇的住所。由此,人们便建立了“凶手”(狼)与幼儿啮死之间的因果关系,案情的真相由此得以揭破。 在《清史稿·循吏姚柬之列传》中也有一例祝祷城隍而后破案的故事: (姚柬之出任)河南临漳知县,屡决疑狱。……常姚氏被杀,罪人不得。柬之察其时为县试招覆之前夜,所取第一名杨某不赴试,疑之。召至,神色惶惑,询其居,与常邻。乃夜至城隍庙,命妇人以血污面,与杨语,遂得图奸不从强杀状。 这起杀人案件的侦破,可谓人的经验智慧与神的明察秋毫的超验能力完美结合的结果。理由如下:首先,在“县试招覆”之时,考取第一名的杨某竟然不赴县学复试,这是科举时代不可想象的事情,从而引起了姚柬之的怀疑。可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怀疑。其次,为了证实这一怀疑,姚柬之特意将杨某召来,发现其“神色惶惑”,这就更加令人怀疑。进而,姚柬之“询其居”,杨某的答复是:与被害人常姚氏毗连而居。由此,怀疑也更进一层。但是出于慎刑上的考虑,姚柬之不敢遽然定谳。最后,姚柬之设计了一场神判,所谓“乃夜至城隍庙,命妇人以血污面,与杨语,遂得图奸不从强杀状”。一者基于“人间私语,神目如电”的信仰,一者是在“妇人以血污面,与杨语”的恐怖情境下,杨某终于心理崩溃,道出“图奸不从强杀”的真相。而“命妇人以血污面,与杨语”中的妇女,则显然是活人的扮演,其目的是套取杨某的口供。顺便一提,在《大清律例》中,强奸杀人,拟斩立决。也正因为强奸杀人的法定量刑很重,越发要求司法官员审慎将事,不可草率定谳。据此,姚柬之“诉诸城隍”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发现犯罪,而是为了进一步证明杨某强奸杀人的罪行。 必须指出的是:其一,在明清时期的司法实践中,神判的形式多种多样,而“诉诸城隍”则是其中比较常见、也比较重要的一种形式。而这显然与城隍崇拜在官方祀典系统中的崇高地位有关。其二,神判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乃是案件的事实真相。这也表明揭破案件真相,确实是传统中国司法官员的首要难题。其三,对于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来讲,虽然熟练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非常重要,但是,由于传统中国司法体制“集侦察与审判于一体”的独特构造,所以司法官员必须承担的首要任务乃是获取案件的事实真相,其次才是如何准确适用法律的问题。其四,从上述故事来看,司法官员之所以采取神判的手段,基本上是出于“慎刑”的缘故。就此而言,神判实际上是一种贯彻“哀矜折狱”精神的司法实践,而非纯粹的迷信。其五,神判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人们对于神的明察秋毫的超验能力极度敬畏。这也表明那句流传广泛的“人间私语,神目如电”的谚语,并非只是说说而已,其实际作用或许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其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法律知识和破案技术,撇开法律知识不说,在我看来,神判作为一种信仰,可以弥补破案技术的不足。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神判视为一种侦察案件的技术。也就是说,能否恰到好处地利用神判技术,直接关乎司法官员能否有效地缉捕罪犯,并且公正地适用法律。 在这一节中,笔者着重讨论了明清时期司法实践的另一面向:智谋与神判。经由这一考察,我们已经看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优秀的司法官员,不但必须具备法律知识,而且必须具备“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经验智慧,更要具备善于利用“神道设教”的能力,用以弥补人类智慧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司法审判的重。过就《循吏列传》记载的司法实践的诸多故事来看,作者关注的不是司法官员的法律知识,而是他们是否具备“哀矜折狱”的道德情感和缉获罪犯的实际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与民间广泛流传的包公之类的清官故事刻画的重点,倒是若合符节。那么,这种法律文化“表达”的特殊偏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值得我们深思。这也许意味着中国古人关注的司法实践的核心问题:第一,揭破案件的事实真相;第二,本着“哀矜宽宥”的道德情感作出公正的裁决。 以二十五史“循吏传”为素材,于寻常史料之中发掘新问题 在如今精彩纷繁的史学研究中,像二十五史“循吏传”这样的材料,实在太过寻常。因此,如何在寻常材料之中展开不寻常的思考,也就更考验功力。史料既无所谓新,也无所谓旧,史料的价值究竟怎样,不但要看学者据以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也端赖学者观察问题之视角,运用史料之技巧。正是在这些“土得掉渣”的史料中,本书发现了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问题:两千余年来被帝国官方历史编撰者反复赞誉的循吏群体,他们的司法实践究竟有何典范意义?或者说,哪些要素构成了明清中国州县官员司法的类型特征,他们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恒定性? 为帝制中国上下两千年的模范司法官员群体画像,展现法律文化史的独特魅力 人既是文化和制度的创造者,又是它们的产物,还是它们的运用者。如果国家、社会和文化是考察司法问题的宏观背景,司法制度是考察司法实践的程序架构,那么司法官员便是在宏观背景与具体制度中进行操作实践的特殊群体。唯有刻画司法官员的行为方式,才能获得司法实践的动态图像。通过司法官员群体这个中间视角,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宏观背景和制度架构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实践行为,而他们的实践行为又形成了怎样的司法风格,对司法制度产生了什么影响。 考证与想象力的完美结合,既富有学术性,又令人有悦读感 本书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与理念,不仅长于考证,也不缺少适度的想象,学术性与悦读感兼备。史料翔实,参考文献及资料引用广搏,就学术原创性而言,既是对“循吏传”的经验研究,也提出了具有规范意义的理论构想。在论述过程中,丰富的故事和案例,读来趣味盎然,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各类史料的深刻理解,对研究对象的透彻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