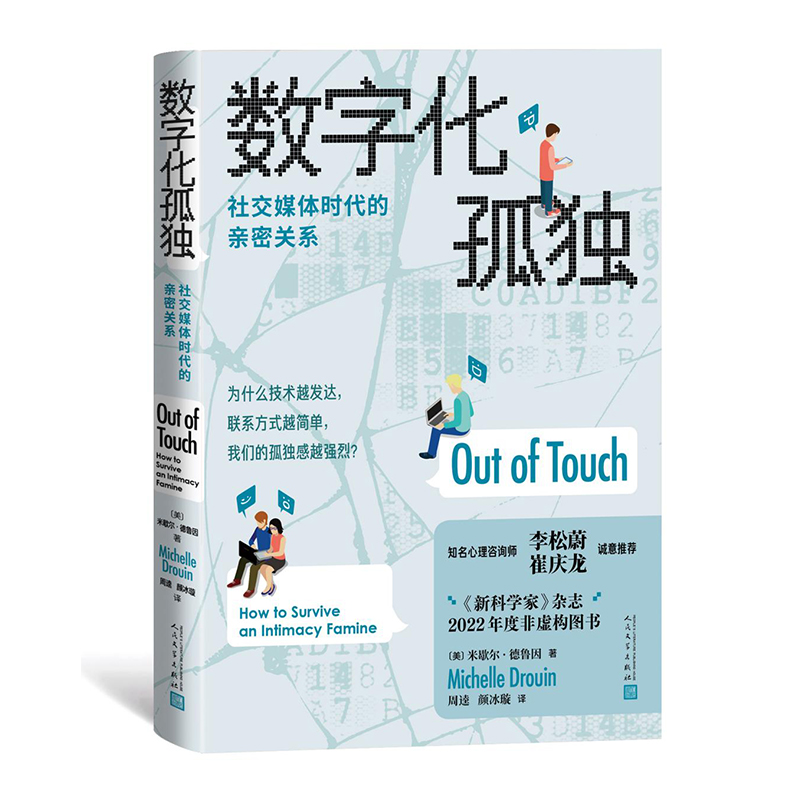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原售价: 62.00
折扣价: 39.70
折扣购买: 数字化孤独:社交媒体时代的亲密关系
ISBN: 9787020181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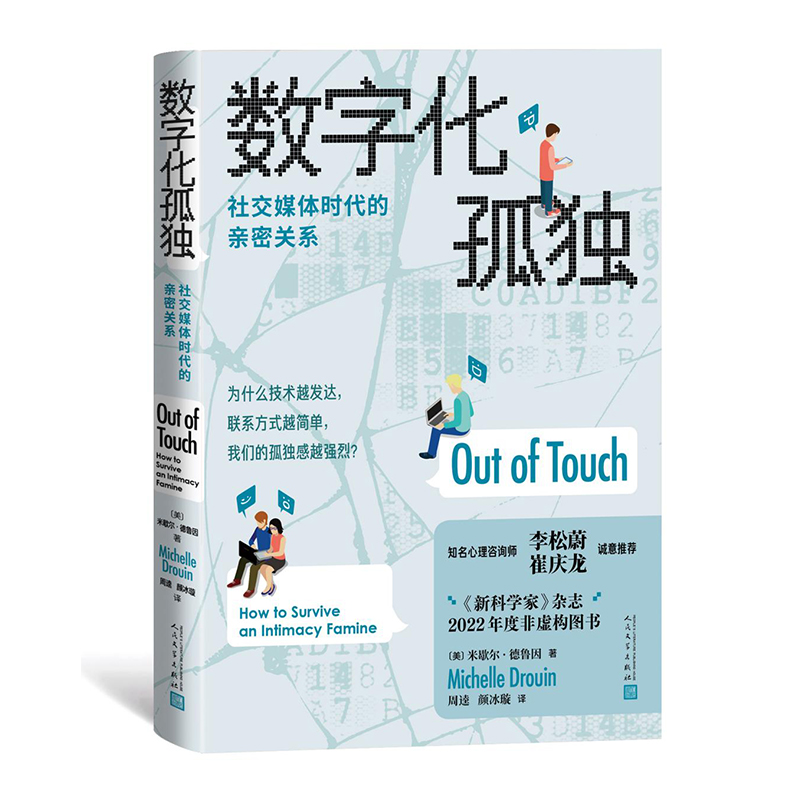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米歇尔·德鲁因(Michelle Drouin,1974— ),牛津大学博士,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维恩堡分校心理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两性关系、人际交往与技术发展,研究成果被《纽约时报》、CBS、CNN、NPR等媒体广泛报道并引用。 【译者简介】 周逵,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译著《群体性孤独》曾获第十届文津图书奖。 颜冰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译有《广场与高塔》。
第四章 手机生存指南 我们都成了手机的奴隶 这样看来,把自己的隐私资料交给互联网公司似乎是愚蠢而错误的行为。然而,就在我创作这一章时,至少拿起手机刷了不下一百次各种社交媒体账号:脸书、Instagram、推特、领英……为什么会这样?简单地说,我和世界53%的社交媒体成年用户都一致认为,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功能可供性,比我所付出的成本更有利。我与社交媒体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 谈论“我与社交媒体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论断,因为得出这种论断的前提是,我必须承认我与社交媒体处于一种关系之中。更进一步说,是我与手机的关系。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技术只是我们发展和维持人际关系的机制,人不可能与“技术”这种无定形的存在形成关系。然而在许多方面,我的手机已经扮演了核心角色,正如它在全球无数其他手机用户的生活中一样。这个角色到底有多关键?2016年,在线定性研究平台dscout的一项在线数据追踪研究显示,普通人(从10万人中随机抽取而来)每天要接触手机2617次,而重度手机用户(前10%)每天接触手机的次数更加惊人——5427次。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可能不会高于平均数据,但手机肯定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核心角色了。 手机利用灯光、声音和振动,向我发出了希望被关注的请求,而我也做出了回应。就像我对生活中其他发出这种要求的人(比如我的丈夫和孩子)的反应一样,我转向它、关注它,并努力解决问题。我的手机可能是当前世界中要求最多的“人”了。作为一名发展心理学家,我曾教导学生,及时给予回应是养育孩子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父母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可以做的最有影响的事情之一。这么说来,鉴于我对手机的回应,我也算是“养育”了它。但是巩固我和手机关系的不仅仅是回应:我小心翼翼地擦拭屏幕,去除污点(仿佛灵长类动物为对方梳毛);不论走到哪里我都带着它,把它放在钱包里、握在手上或放在口袋里(肌肤与屏幕密不可分);要是哪一刻它不见了,我会紧张万分(分离焦虑);我与手机似乎已经合二为一——我彻底沦陷了。 我身边的其他人也注意到了人与手机的微妙关系。我与家庭学家布兰登·麦克丹尼尔(BrandonMcDaniel)一起,一直在研究科技是如何利用一些小插曲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些小插曲被称为“科技干扰”(technoference,technology与interference两个词的结合)或“低头族”(phubbing,phone和snubbing两个词的结合)。自2016年以来,麦克丹尼尔和我以及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系列一致的趋势。人们有时会选择与手机互动,而不是与他们身边的人互动,这可能会导致夫妻、家庭和朋友关系产生冲突和嫉妒情绪。反之,这种冲突和嫉妒与较低的关系满意度有关,也损害了亲密关系。不幸的是,这种科技干扰几乎每天都在影响我们中的一些人。2019年,在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中,麦克丹尼尔和我采用了日记研究的方式,要求一对恩爱情侣在14天内每天记录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科技干扰和实际感受。研究结果显示:在两周的时间里,大多数情侣(72%) 在与伴侣的互动中出现了科技干扰。更重要的是,在实验参与者记录了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更多科技干扰的日子里,他们也同时记录了更多与技术相关的冲突次数,以及与伴侣面对面交流次数的减少、对亲密关系的消极情绪。这些结果甚至也出现在控制了与伴侣相处时长之后——这意味着,不仅仅是花在科技产品上的时间取代了与伴侣相处的时间(并导致了更多消极后果);另一方面,科技干扰本身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或者说,当人们放弃与身边的人互动、转而选择与手机互动的那一刻,负面影响就出现了。 当身边的伴侣或朋友拿起手机、而不是和我们互动,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一种被拒绝的感觉?根据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是带有信息(message)的,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确定自己在对方生活中的角色。当你对面的人在你和手机之间选择了手机——尤其是当你努力想与他交谈的时候——这种行为发出的信号是“手机比你更重要”。即使这只是一瞬间的感受,也会让人产生一种被拒绝的感觉。这一行为也可能是对关注度、反应程度的社交期待的一种拒绝。出于上述原因,当对面的人关注他们的手机而不是我们时,就可能会被视作一种关系的消耗。根据社会交换论(socialexchangetheory),我们决定是否要维持一段关系,取决于我们对这段关系的成本与收益的持续评估。从本质上讲,我们是在给伙伴“记账”。为了让这段关系保持稳定,“收支平衡”是必需的。 但是在我和手机的关系里,我似乎总是付出更多的那一个。 除了花钱把它买回来、它可能会给我的生活带来科技干扰之外,手机还让我付出了很多额外的牺牲。最显而易见的是,手机是工作、生活和与朋友交往时最容易让我分心的东西。不管我在哪里,只要有电子邮件或短信弹出来,我就不得不拿起手机看看。看手机时,我还容易掉进探究的“无底洞”:本来我只想读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爱情概念的短文,结果两小时后我已经陆陆续续读了20位哲学家对爱情的不同定义。我十分感谢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SocialDilemma)和其他几部关于科技产业的纪录片,让我了解到这些强迫症行为的根源其实在于有目的的设计。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手机的猎物,而且是一只不满足的猎物。 从更宏观的社会角度来看,手机和其他科技产品的使用也可能导致不满足感。21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简·腾格及其同事的研究引起了媒体极大关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年里,美国青少年和刚成年的年轻人的科技产品使用率在增加,相应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也在上升。一时间,公众开始关注科技产品的使用,以及它可能导致的社交关系与个人心理健康的退化。该研究的结论认为:技术手段有助于我们形成社会关系,但现在每个人都窝在卧室里,通过手机或电脑与他人在线联络,却错过了面对面互动的机会,而这种面对面的互动才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幸福感,维持社会关系。更糟糕的是,长时间在网上冲浪、使用社交媒体使我们变得紧张、孤独和抑郁,特别是当它导向有问题的、强迫性的使用时。尽管一系列复杂的统计分析表明,科技产品的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总体负面影响较小,通过网络与人联系也有助于减轻孤独感,但这并没有减轻人们的担忧。 第五章 约会生存指南 返校节公主才能赢得彩票 如果能重返高一,我的愿望之一就是成为新生返校节的“公主”(homecoming princess),尽管有些人读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很老套:这也太符合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刻板印象了,但这是我的真实愿望。我们学校有一支很厉害的足球队。作为返校节活动的一部分,每年秋天,在备受瞩目的球赛中场休息时,三位返校节公主候选人会身着舞会礼服,被护送到球场,在全校师生面前加冕。其中一个女孩被加冕为“公主”,剩下两位分获亚、季军,并被授予“公主”宫廷中的职位。虽然现在我已经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场“加冕活动”,但对于一个年仅14岁、看着迪士尼电影和20世纪80年代浪漫电影长大的女孩来说,这一切令人心醉。 我们年级有大概200名同学,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女生。从纯统计学意义上讲,这意味着我可能有4% 的机会成为返校节公主。不过,实际上我的机会是0。而那个获胜的女孩则几乎是100%。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平等的。她身上有着更多人们观念中“返校节公主”的特质:她更漂亮,性格外向,有很多朋友。她不搞小团体,与人为善。每个人都喜欢她,在任何方面都无可争议。她就如教科书所定义的那样受人欢迎。 在线约会的概率就像评选加冕返校节公主,与买彩票完全相反。至少买彩票后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球,都有同等的机会赢得比赛。而在线约会的实际场景则是:100个人进入同一座竞技场,中间只有一个巨大的奖品 —— 爱情。彩票组织者会提前告诉我们,100个人中将有39个赢家,只需一个球,你就可以参与其中。很幸运,这里有足够的球可以分配 —— 彩票组织者手中有1000个球, 但他们并不打算平均分。相反,得球的数量取决于你的个人特质。 有些球代表你善解人意,有些代表你有魅力四射的外表,剩下的还有智慧、幽默感、创造力和适应能力等。这100个人中,有些人表现突出,能得到100个球,这相当于100次恋爱机会;有些人能得到50个、30个或10个;而有些人只有几个球,还有的人可能一个都没有,只能坐在场边看,好像他们在进入这座竞技场之前就已经输了。 我们找到爱情的机会既不公平,也不随机。 现实总是如此艰难:有些人觉得找到爱情很容易,另一些人则觉得这很难。由于互联网的不断延展、扩张,这两类人试图在网上寻找爱情时,都面临着“大海捞针”的挑战。大约五年前,我进行了一项还未公开发表的研究,题目是“一个人在一天内能找到多少段爱情?”我的朋友安娜当时25岁,住在芝加哥附近,注册了三个比较流行的约会网站并上传了她的个人资料(基本与Tinder上的一致)。她在每个网站都上传了三张照片:一张大头照和两张全身照,包括一张抱着狗的照片。如果在Tinder 上看到感兴趣的潜在匹配对象,用户可以主动使用“向右划”功能添加好友;为公平起见,安娜计划在三个网站上都使用了这种主动的参与策略。在Tinder上,看到感兴趣的个人资料时,她会使用“向右划”功能,如果匹配成功,她就立即给对方发送一条信息:“我看了你的资料,希望能更好地了解你。”在其他平台上,她会通过主动搜索找出她感兴趣的个人资料,并发送同样的信息。该计划执行了一天:我们选择在10月4日(星期日)进行,从上午10点到午夜之间(下午3点到4点除外,我们花了1小时吃午饭),安娜一直在约会网站上“冲浪”,给每个她感兴趣的账号发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收到信息的人几乎就是芝加哥地区所有她可能约会的男人(安娜是异性恋)。同样,为公平起见,她每次在同一个网站上操作的时间为30分钟,然后依次交替。 这漫长的一天,安娜向大约150名男性发送了信息。她在3个约会网站上共收到601个人发来的信息。其中108名男性回复了安娜的信息,493名男性(其中大部分是她不感兴趣的)在未经请求的情况下主动联系了安娜。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370条)都是在当天收到的,64条是在第二天收到的,其余的则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陆续收到的。信息的长度和内容各不相同,从“嘿”到更长、更吸引人的信息,人们会提到她的工作和兴趣,并提出见面的请求。有些人甚至给她发了不止一条信息,有个男人给她发了四次信息,但安娜都没有回复。在这一天中,安娜就收到了超过100个爱情彩票球。但即使她已经拥有这么多球,也不能保证这些男人中有适合安娜的那一个。 选择太多也有烦恼 在一些人看来,中了“爱情彩票”可能只是想象中的场景。当她真正面对如此多的选择时,安娜感到力不从心。这与社会理论家巴里 · 施瓦茨(Barry Schwartz)的观点一致,他认为拥有丰富的选择对生活满意度会产生负面影响 —— 就像我们在这个技术时代所感受到的一样21。过多的选择使决策变得困难,并可能使我们处于一种分析瘫痪(analysis paralysis)的状态,即因过度思考应做出的选择而无法向前迈进。希娜 · 艾扬格(Sheena Iyengar)和马克 · 莱帕(Mark Leppar)著名的果酱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现象。在田野调查中,他们选择了加州一家高档杂货店,购物者会碰到两种情况:面前有24种果酱或6种果酱。面对24种果酱时,的确会有更多人驻足,但两组停下来的人,基本上品尝的果酱数量相同。更重要的一点是,实际上选择较少的人更有可能购买果酱:有6种选择的人中,有30% 购买了果酱,而有24种选择的人中,买果酱的只有3%。 已经有人将这项研究对应到线上约会的场景中了。世界各地的研究都表明,在约会方面提供的选择越多,搜索人做出决定所需付出的认知努力就越大。况且,选择太多还会对选择的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为搜索目标的所付出的认知精力,会不断消耗人的资源、能量,使他无法做出最好的决定,产生“更多意味着更糟”的效果。当然,这种影响对每个人来说不尽相同,人们应对选择多样性的模式也存在着个体差异:有的人是最大化者,他们总希望得到最好的,在面对选择时似乎更痛苦;有的人是满足者,他们知足常乐,面对选择没有那么大的负担24。用列夫 · 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安娜 · 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的话说:“如果你追求完美,那么你将永远得不到满足。” 虽然海量的选择有时会对择偶的最初过程造成阻碍,但贯穿这个过程的首要问题是:寻找爱情的过程就像大海捞针(尤其是在网上)。信号检测理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认为,我们需要在噪声背景下破译出一个信号。将该理论大体应用于我们的情境,意味着寻找爱情需要你在茫茫人海中努力识别正确的选择。我们的在线约会研究仅仅关注了追爱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浏览个人资料,寻找感兴趣的人。事实上寻找爱情的过程要复杂得多,它涉及在关系形成的各个阶段所做的一系列决定。在每个阶段,人们要面对不同的人做出不止一个,甚至是许多个决定。以下是我罗列的“一个约会者可能要做的决定”清单: 第一阶段:初始搜索 在哪个场所寻找伴侣(线下实体空间还是线上应用软件)? 是否与某个特定的人建立联系,与他交谈、发信息或打电话? 在同一时间段内与多人建立联系,与他 / 他们交谈、发信息或打电话? 第二阶段:确认两人之间是否建立联系 要不要回应某个人? 回复对方的速度、频率如何? 要不要将线上聊天转为语音或视频通话交流? 要不要与对方“奔现”? 在同一时间段内与多少人聊天或见面? 第三阶段:确定关系的结构和时长 对方是否适合短期约会? 对方是否适合长期关系? 要不要结束一段关系? 如何结束一段关系? 以上的每个步骤都要认真决策,要消耗宝贵的认知精力,而这些精力基本都是从工作、朋友或家庭那里分散过来的。那些寻找爱情的约会者也不一定完全按照上面的清单一步步来,或者只专注 于一个约会对象。相反,人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已经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不错的对象,也在线下见过面,却又看到了其他感兴趣的个人资料,这时他 / 她就要决定 —— 要不要给后者发消息,前者是否适合建立长期关系。如果做这么多决定还不足以让你相信寻找爱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以技术为媒介的世界里,那么请你再思考一下这个决策过程的潜在持续时间 —— 它可能会一直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直到这个寻找爱情的人决定要单身,或者找到一个(或多个)建立了强关系的伴侣,才会决定放弃寻找。况且,在生命中的任何节点,他们都可以改变主意,转换方向。 超心理现象与棉花糖人 如果说这么烦琐的步骤还不足以让你觉得,建立恋爱关系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的话,那么你可曾想过,每一步都有可能出现错误——你可能选择了一些自己最终并不喜欢的人和事。人们常常对他人做出错误的评估,导致我们去追求错的人,花时间与他们相处。在这里,我必须再次提出警告,其实并没有什么“错”的人。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错的人往往是指那些你确定对方不适合与你发展关系(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人。但这种错误是如何产生的,爱情中的错误决定又是如何做出的呢? 达 里 尔 · 贝 姆(Daryl Bem)和 沃 尔 特 · 米 歇 尔(Walter Mischel)的研究能帮我们理解人们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还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贝姆就已经是学校里的知名教授了。我没有修过他的课,但他是心理学入门课的演讲嘉宾。课堂上,他带领在场的1000多名学生做了一个超心理现象测试(PSI Phenomena,即超感官知觉)。2011年,贝姆的一篇论文使他得到了很多关注,文章试图证明人的预知能力(即在刺激物显示之前对其作出反应)。这篇论文在心理学领域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要求他撤回论文,但《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发表了社论,指出保留这篇论文的理由。事实上,不仅在超心理现象领域,整个心理学领域都出现了大量相似研究。作为回应,贝姆和他的团队在2015年发 表了针对90个实验的后续元分析,对贝姆最初的发现进行了巩固论证,并再次提供了人们可以预测未来事件的证据。此后,其他知名研究人员也在顶级期刊上发文,提供了对不同类型超心理现 象的实证支持。然而许多学者对此仍持怀疑态度,甚至是强烈的批评。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对贝姆决定研究超心理现象刮目相看。通过研究超心理现象,贝姆确立了自己在该学科中略显反叛的学术地位。他不顾批评,走自己的路,这对学术界来说有时是很难做到的,我尊重他的勇气。 尽管如此,真正影响了我对人类的认知的并不是贝姆的超心理研究,而是他的自我认知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类并不擅长解读自己的情绪或态度30。根据贝姆的说法,我们从内部获取个人情绪线索的能力是很弱的,而且很难解读这些线索。因此,我们只能依靠对外部行为的解读来推断自我的想法和感受。如果将该理论应用到约会场景中,我们会发现:当有人问起你对正在交往的新对象有什么感觉时,你可能无法定义自己的情绪,因为这种感觉并不清晰、明确。因为内心缺乏安全感,你可能会说:“嗯 …… 我上周和他出去约会了三次,所以我觉得进展 还不错。” 最新研究表明,人体生理反应确实有助于解读人类的情绪。一个芬兰科学团队一直在努力开发“情绪身体地图”,关注当人们感受到某些情绪 —— 如爱、悲伤和惊讶时,身体的哪些部分会被“激活”。2020年的一项研究调研了包括109个国家在内的6559人,研究人员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当人们感受特定情绪时,机体被激活的部位是高度一致的32。“激活”的模式代表了情绪的“生理指纹”,当我们开始识别这些指纹,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也许对“读心术”的研究还太过遥远,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读懂自己的心似乎完全有可能实现。以上研究表明,解释自己情绪的技能是可以培养的,但在没有明显生理线索(如心率或呼吸频率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很难确定自己对某人的感觉如何。不过感觉是会改变的,即使我们能有效解释某一瞬间的情绪,一时的情愫也不一定就能预测长期的感觉。况且,人的感觉会随着情境变化而改变,换一个环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对人的感觉。这就引出了棉花糖实验的发明者 —— 米歇尔。为了测试儿童抵制诱惑的能力,他在参与测试的孩子们面前放了一个棉花糖(或其他美味的食物),孩子如果能忍住不吃,就能在之后得到两个棉花糖的延迟奖励。米歇尔强调,情境是一种能塑造行为的强大力量。这对当时的人格理论学家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人格具有一致性,人们可以被准确界定为具有某种稳定气质类型的个体。但米歇尔认为,人的行为在不同情境中具有很大差异;且行为变化不是随机发生的,也反映着个体的特质。确切地说,我们能够预想到,人们在家里和在工作环境中表现出不一样的性格;或者用更现代的角度观察——人们打字时和说话时的性格不一样,因为人的确在不同情境下具有差异性。那么,考虑到文本信息媒介的单一属性,用文字交流也并非同步,若仅通过网络交流就试图判断自己与对方是否合适,就很容易出错。即使对方并没有刻意隐藏真实的自我,他们在网络上呈现出的那个“自己”也很可能与现实生活中不尽相同。 决策的艺术 不论其背后动因如何,即便在择偶初期,犯下这些错误也会给你造成重大损失。比如,你选择给一号追求者发信息并与之见面,是因为你看上了他的照片,而且聊天时他幽默性感,命中了你的笑点和兴奋点。同时在跟你聊天的二号追求者既不好笑也不撩人,所以在两人之中你选择了前者。只可惜,与一号追求者约会那个夜晚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也许他在展现自我时撒了谎(71% 的线上约会者说,人们在网上撒谎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吸引人)。 当他与你面对面交谈时,跟在网上和你聊天时简直判若两人。无论如何,要么他不喜欢你,要么你不喜欢他,你和一号追求者的约会旅程就此结束。 实际上,我们很快就能判断出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个做决定的过程所需的信息比他人预想的要少得多。芝加哥大学研究人员纳达夫 · 克莱因(Nadav Klein)和艾德 · 欧布莱恩(Ed O’Brien)用一个精妙的绘画实验验证了这一理论36。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体验者和预测者。体验者会连续看到40幅同一风格的系列画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告诉研究人员:在看到第几幅画时,能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种风格;同时,预测者要做的是猜测体验者们的答案。两组人员先做了热身,速览了40幅画的缩略图,之后,实验正式开始。 在体验者组,平均每位体验者在看到3.38幅画后,就确定了自己对这种风格的偏好 —— 这个数字远低于预测者小组,他们认为,体验者至少需要看过16.29幅画之后才能做出决定。随后,研究人员又在一系列需要做出决策的任务中重复了这项实验,发现人们同样能对以下选择做出快速判断:是否喜欢某种饮料,某人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这个人是不是运动员、邻居、赌徒,甚至眼前人是不是个快乐的人,等等。同样,在所有情况下,预测者都高估了人们做出判定所需的时间。克莱因和欧布莱恩表示,尽管我们自己可以迅速做出判断,但仍会认为他人需要更全面的信息来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让一些工商管理系的硕士生来判断:招聘主管需要读多少篇文章才能决定是否雇用他们? 平均而言,这些学生得出的结论是至少需要读4篇文章,但事实上,一个招聘主 管只需要读两篇文章,就差不多能做出决定。我们能迅速对别人做出判断,对方也同样可以快速评判我们。 对于爱情,我们做决定的时间可能还会更短。当我们看到热恋对象的照片,甚至只是他们的名字时,大脑的愉悦中枢(即服用可卡因时可被激活的区域)需要不到30秒,甚至只需短短五分之 一秒的时间就会被激活。然而,若我们要决定某人是否能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就要深思熟虑了。一些研究显示,已婚人士平均需要173天的时间才能确定自己选定的结婚对象是那个“对的人”。但这却又比单身人士所认为的211天要少得多。然而,用30秒感受爱情的喜悦,花6个月找出自己的终身伴侣,在长达一生的时间范畴下,这似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如果你认为自己在择偶问题上做出的决定太过草率,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回到前文那两个追求者身上。根据现有信息,你可以完全确定,一号追求者并非那个“对的人”,甚至不能成为这个人的候选者,因此你又开始寻找其他选择。但是,当你想把二号追求者约出来时(在与一号追求者进行了糟糕的约会之后,你对二号追求者的评价变高了),他可能已经转而去追求别人了。最惨的情况是,实际上二号比一号更适合你,但你已在茫茫大海中“捞针”失败。 导致我们错过目标的不仅仅是行动。假如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被动接受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你可能会想起那个经典的伦理困境 —— 电车难题,作为旁观者, 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任由失控的电车撞上铁轨上的五个人;或者拉起操纵杆,让电车转移到另一侧轨道,去撞那一个人。这个两难悖论证明了: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选择。而在约会的情境下,比方 说,在与一号追求者进行了一次糟糕的约会后,你并没有立刻决定分手。你在持保留意见的情况下,继续与之约会、聊天,甚至可能进入了一段互相承诺的关系。当选择与一个并不能让你完全满意的人确立关系时,一种可能是走向成功 —— 因为你们可以也确实在互相妥协、做出改变。而另一种可能则是局面并没有发生改善,或许你就此错过了那个更适合你的人。 海里有许多鱼 以上情境让我想起一个自己研究了近十年的话题 —— 我将之称为“海里有许多鱼”现象。在皮尤研究所2019年度在线约会研究中,一位27岁的女性参与者说:“当约会网站或应用程序不断告诉你,你一直被优秀的单身人士所包围时,你很难在一段关系上下功夫,或者再给伴侣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你会觉得总有更好或更容易的选择。”她的观点恰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我理解这位女士的感受,但我认为她太迷信约会软件的宣传了。事实上,你身边本来就有很多单身人士,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优秀的。但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 如今似乎已创历史新高。 2018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超过1.1亿成年人称自己是单身,占当时所有美国居民的45.2%39。相比之下,1960年只有28% 的成年美国人是单身。同时,30年来的全球趋势显示出单身状态处于历史高位的部分原因:如今有更多4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离婚的人也更多,人口平均结婚年龄仍在逐步上涨。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正在约会的人比之前更有可能找到恋人。 当然,这位女士过于强调外部力量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了。真的只是网站让我们相信,总有一个更好的或更容易的选择吗? 还是说我们原本就相信这一点,只是网站给出的判断恰好反映出内 心的真实想法呢 ? 50多年前,关系学研究者探究了人们能维持一段关系的原因。当时普遍的理解基于心理学家哈罗德 · 凯利(Harold Kelley)和约翰 · 蒂伯(John Thibaut)的相互依赖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该理论认为,维持一段关系是基于一个人对关系的依赖程度或需要程度。人们是否选择在一段关系中停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满意度(即伴侣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我最重要的需求)和 替代者的质量(即我对这种关系的最佳替代者有多大渴望)。此后,心理学教授卡里尔 · 鲁斯伯特(Caryl Rusbult)将这一理论扩展为投资模型量表(investment model scale),这可能是如今使用最广的关系投资模型。鲁斯伯特添加了一个维度 —— 投入资源(即与关系相关的资源,也就是若关系结束就会失去的资源,如金钱、朋友和关系),她认为这一点也影响我们对伴侣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反过来又强化了彼此对这段关系的承诺,使其走得更长远。上述两个模型的共同点是,人们会不断评估身边是否有更好的选择。这很正常,也很普遍。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我存在的世界里,真的有一个更适合我的伴侣吗? 如果一个人正处于一段高承诺度和高满意度的关系中,他 / 她并不会对一个可能替代这段关系的人做出高度评价;但当满意度降低或投入资源减少时,人们可能会对身边的其他选择表现出更强的兴趣。一旦天平开始向后者倾斜,一段关系的承诺便岌岌可危,极有可能导致关系中的人去主动追求他们的“备胎”。 多年来,我和杰森 · 迪布尔(Jayson Dibble)、丹 · 米勒(Dan Miller)一直在研究所谓的“备胎”(back burners)问题。哪些人会有“备胎”,他们为什么会有“备胎”,“备胎”对现有关系的威胁 有多大? 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我们找了一些处于忠诚关系中的年轻人,让他们简单浏览自己的“脸书”好友列表,假设一下如果现在是单身,可能会与其中的多少人建立亲密关系。平均而言, 年轻女性会考虑与“脸书”好友中的3个人谈恋爱,可能发生性关系的有8人;男性则表示会考虑与其中8人建立恋爱关系,可能会跟列表中的26个人发生性关系。这仅仅是在脸书上,我们还没有 询问 Whatsapp 和色拉布用户,这些软件可是人们定期与“备胎”沟通的常用工具。 更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询问了所有年龄段的成年人,他们是否有“备胎”—— 这里的“备胎”是指人们在感情方面对其产生兴趣的人,与他们交流时,可能会建立一段浪漫关系。界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备胎”属性,就是看其是否会与当事人进行这种交流(暗示着一方正在追求另一方),而且在这些追求者心中,他们有可能会与“备胎”建立一段浪漫关系。从本质上讲,有可能成为“备胎”的人就是那些“大海里的鱼”。这个现象覆盖了所有年龄段的人群。现代科技打造的社交网络上,年轻女性平均每人拥有4个备胎;年轻男性则有8个。年长一些的已婚人士也有备胎,我将在下一章中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这些发现并不出人意料。关系模型表明,人们始终在不断评估周围可选择的对象。但令人惊讶的是,单身人士并不比恋爱中的人拥有更多的“备胎”。还有一点,无论是在感情方面还是在性方面,你的“备胎”数量与你对目前伴侣的投入资源及忠诚度并没有显著关系。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之前谈到的关系理论。那些处于高忠诚度关系中的人不是应该降低对潜在替代者的评价了吗?他们更不可能与这些“备胎”沟通吧? 真的不一定。鉴于现代技术手段对通信格局的建构,基于各种社交网络平台,与自己感兴趣的人交流变得越来越简单。只需几秒钟,而且完全是私密的。尽管这种交流起初只是纯粹的对话,没有任何浪漫企图,但在认识对方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开始这样想:“我也许可以想象自己在未来的某一天和这个人在一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就有了一个“备胎”。 大海捞针,分析瘫痪,海里有许多鱼。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结识新对象和约会的方式——这些活动可以在线上发生,也完全颠覆了现实世界的约会进程。当今世界,人们做出任何决定都可以依赖于网络。从购买面霜到挑选度假小屋,你可以通过成百上千条评价找出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也很难想象这些人不会用互联网来检索、审核他们的爱情。互联网提供了无尽的信息和机会——这是人类最渴望的两件事。但与此同时,一旦我们试图用互联网成就爱情,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 写到这里时,艾拉刚刚经历了一次分手。这段关系大概维持了8个月 —— 超过了173天,也就是能做出“是否要共度一生”决策所需的天数。但当她给出“是”的答案时,那个男人却说,他们的关系不会有任何进展了。艾拉彻底心碎了。她正在遵照互联网的指导,承诺在30天内不回复他的任何消息(或许是不适应她突然玩消失的不确定性,他已经发了五条消息)。艾拉回到了她的艺术天地,与她的乐队一起推出了新专辑。余下的时间里,她几乎都和朋友们在一起。每迈出大胆、勇敢、美好的一步,她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个帖子,社交媒体上的她说:“我过得很好。”现实中她向我承认:“我很痛苦。”也许那个男人会看到这一切,并请求她回到他身边;但如果没有,这个玩 Tinder 的灰姑娘也清楚地知道,海里还有无数条鱼在等着她。 人生各阶段亲密关系的诊断书 童年时代的“拥抱饥渴症”,恋爱关系中的“备胎心理”,中年夫妻的“无性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技术成瘾症”,老年时期的“社交孤立”,后疫情时代的“孤独大流行”描绘现代社会人生各发展阶段的典型生活场景,展现现代人的“孤独困境”,原来你不是一个人! 深入剖析现代科技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为什么技术越发达,联系方式越简单,我们的孤独感越强烈?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在线诊疗等新技术手段对人际关系产生了怎样积极/消极的影响?我们该如何利用新技术手段拉近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扎实的实验数据 鲜活的个体经历 真诚幽默的讲述 积极的生活态度 无需“烧脑”参悟心理学理论,丰富的实验 案例 典型生活场景,助你理清情感需求的底层逻辑,思考处理亲密关系的生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