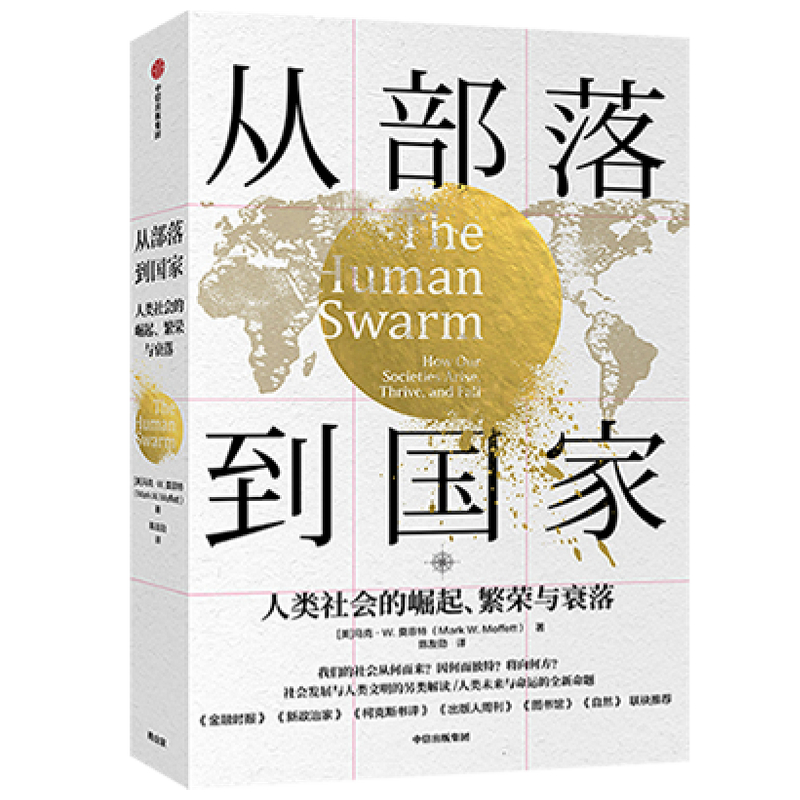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9.90
折扣购买: 从部落到国家(人类社会的崛起繁荣与衰落)
ISBN: 97875217175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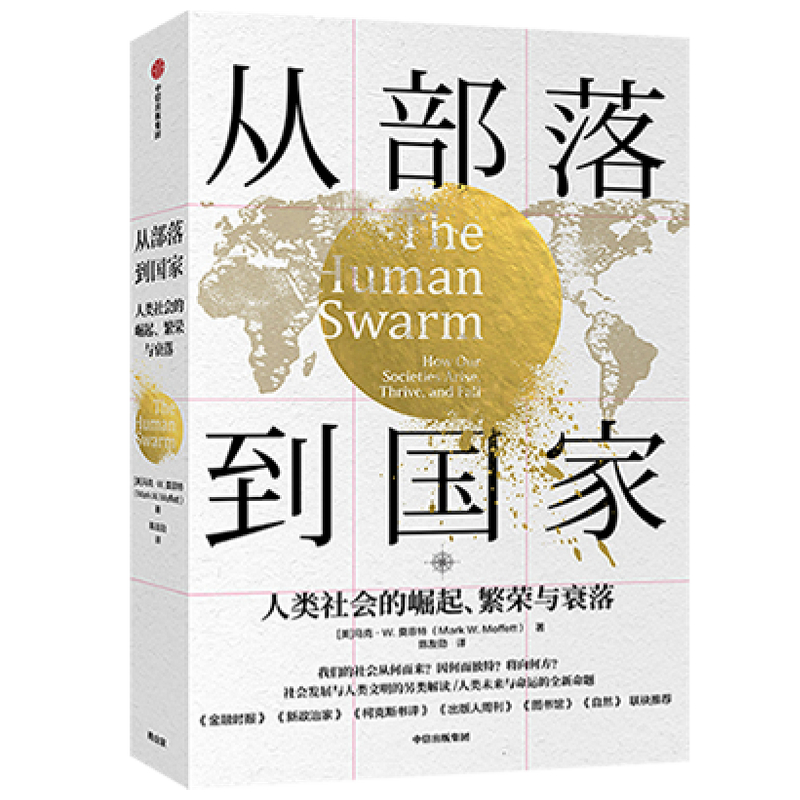
马克·W. 莫菲特(Mark W. Moffett) 史密森尼学会热带生物学家、研究助理,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系访问学者。他被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称为“勇敢的生态冒险家”,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昆虫界的印第安那·琼斯”。这是他写作并出版的第四本书。
只要社会存在,人们就觉得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已然改变,那些社会成员在他们的心目中俨然变成了高尚的人类。不过,虽然对社会的归属感会极大地提升全体成员的自我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高看来自其他社会的成员。相反,在他们眼中,那些其他社会的成员不但行为举止和自己大相径庭,而且有时形象丑恶、面目可憎。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把整个其他人群想象成某些非人的,甚至像害虫一样的东西。 他们觉得其他人群卑鄙丑陋,完全应当像虫子一样,被自己踩在脚下蹍成碎末,而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断上演,可谓经久不衰、层出不穷。让我们回到1854 年华盛顿地区的西雅图。当时,和这座新建城市同名的西雅图(Seattle),是苏奎米什部落(the Suquamish Tribe)的首领。他刚刚聆听了该地区新近任命的州长艾萨克· 史蒂文斯(Isaac Stevens)在部落长老面前发表的讲话。史蒂文斯通知他们说,所有苏奎米什人都将被迁到一个保留地去生活。于是,西雅图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眼前这个身材矮小的州长相比,西雅图显得高大威猛。他说着苏奎米什方言,首先对本部落与白人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鸿沟深表痛惜,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留给苏奎米什部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然而,对于族人的悲惨遭遇,他的态度却显得豁达而又坚忍:“部落新旧交替,国家彼此更迭,就像海浪一样,前赴后涌,永无止歇。这是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人类即使心有不甘,也无济于事。” 作为一名野外生物学家,我一直都在思考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在探索人类部落和国家的时候,我花了多年时间来对我们称之为“社会”的这个概念进行研究。我总是被一种异己性现象(foreignness)吸引:它能让一些实际上很细微的差别,变成横亘在人们之间的一条鸿沟,并且这种表现还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从生态到政治的各个方面。因此,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考察智人(Homo sapiens)以及其他动物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尽可能广泛、深入地对异己性现象进行揭示和研究。本书的主要论点可能听起来不甚入耳或让人感觉不适,但人类社会和昆虫社会其实非常相似,二者之间的相似程度甚至超出了我们乐于接受的范畴。 对人类而言,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能是异己性的表现,比如我在这方面就有很多亲身体验。当我在印度拿食物的手不对时,旁边围观的人们一脸羞愤。在伊朗,当我点头表示自己同意时,殊不知这个动作在当地代表着反对。在新几内亚高地,我和全村的人坐在长着苔藓的地面上观看一台老掉牙的电视中播放的《布偶秀》,而这台电视居然是靠一节汽车电池来提供能源。当一只猪——它可是当地百姓敬畏的神兽——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在屏幕上跳华尔兹时,当地的男女老幼都用一种嘲笑的神情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来自美国,而这个《布偶秀》节目就是在美国制作出来的。在斯里兰卡泰米尔民族冲突期间,我费尽唇舌才得以从机关枪下逃脱。当满腹狐疑的玻利维亚官僚试图弄清眼前这个奇怪的家伙究竟是谁、在他们国家干什么勾当,以及是否该允许我这么做时,我吓得直冒冷汗。回到家乡,我也看到美国同胞对外国人同样表现出不适和困惑,有时甚至对他们充满愤慨。出于本能,双方都认为自己对面的家伙极为怪异,尽管他们同样身为人类,彼此其实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比如都长着双臂和两腿,心中都充满了对爱情、家庭和亲人的渴望。 在本书中,我把社会成员的身份视作人类自我意识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最后几章中)。这一点应当与种族(race)和族群(ethnicity)一起加以考虑,因为后面这两种认同感也会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激起我们的情感共鸣。与构成我们身份认同感的其他方面相比,我们把社会——以及种族和族群——的重要性放到如此显著的位置,似乎显得有些荒谬。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就曾试图解释人们为何愿意把自己融入一个凌驾一切的群体身份当中。阿马蒂亚· 森以在卢旺达发生的致命冲突为例,深感痛惜地指出:“一名来自首都基加利的胡图族劳工可能会在当地主流舆论的影响下,认为自己只是一名胡图族人,并被煽动杀害图西族人。然而事实上,他不仅是胡图族人,也是基加利人、卢旺达人、非洲人,以及劳工中的一分子和整个人类中的一员。” 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将是后面章节要讨论的主题内容之一。当人们对社会的所属性质或它究竟代表哪方利益的信念出现分歧时,怀疑就会产生,而信任也将坍塌。 于是你会想到“部落主义”(tribalism)这种说法,它指的是人们被任何相同的事物吸引到一起,无论是出于对赛车的共同热爱,还是对全球变暖的一致否认。以这种宽松方式使用的部落概念,是许多畅销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然而,当谈到一个新几内亚高地的部落,或者谈到涉及我们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部落主义时,我们指的其实是一种终生维系的归属感,想到的是它如何激发出人们心中的爱意和忠诚。不过同时,我们还会想到在处理与外来者之间的关系时,这种归属感也会促使我们心生仇恨、产生破坏的想法或者充满绝望之情。 在讨论这些主题之前,我们将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那就是:什么是社会?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社会和社交——积极地与他人产生联系的行为——之间存在一个主要差别,并且在自然界中不太常见,因为我们所谓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独立群体,其成员由某个物种构成,还可以世代延续下去。虽然人们对于自己身为何种社会成员没有选择的余地,但关于其中哪些是重要社会成员,通常都心知肚明。而外来者,其外表、口音、手势及他们对周围事物所流露出的种种态度,包括对猪的看法以及是否把接受小费视为一种对自己的侮辱,都已经表明他们身上的异己性特征。这是显而易见、不会弄错的,因此他们很难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外来者只有接受时间的洗礼,经过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后,才能完全融入当地社会。 除了家庭之外,社会也是我们最经常宣誓效忠、为之战斗,甚至不惜牺牲的一种组织形式。但在日常生活中,社会的首要地位倒是表现得不太明显,它只是形成我们自我意识的部分内容,也给我们比较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提供了条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选择加入政党、书友会、扑克俱乐部,以及青少年团体等各种组织。甚至坐同一辆观光巴士的游客也会暂时团结起来,觉得自己这辆车上的旅伴比其他车上的游客更有存在价值。并且,这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团队而共同努力,从而卓有成效地解决当天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加入群体的倾向凸显出我们作为人类的个体特征,并且一直作为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而受到广泛的研究。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以自己的节奏继续运行,其表现一如既往,波澜不惊、自然平常,就像我们的心跳和呼吸一样容易被人忽视。当然,在民族艰难或亟待唤醒隐藏在人们身上的爱国热忱之时,社会的价值就得以凸显。发生一场战争、遭受恐怖袭击,或者一位领袖的去世,都可能对一代人产生深刻影响。但是,即使在和平年代,社会也为我们的生活定下基调,影响我们的信仰,并为我们个人提供广阔的活动背景。 如果你对不同社会——无论是像美国这样横跨大洲、人口众多的国家,还是位于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之间有时出现的不可逾越的差异现象进行思索,就会发现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难道社会的出现以及将他人贴上其他群体标签的做法是“大自然发展规律”的一部分,因此也就属于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吗?由于自我优越感的束缚,加上易受来自其他群体的敌意的影响,每个社会是否注定就像西雅图所认为的那样,要么会与其他社会发生矛盾冲突,要么社会成员之间会产生一种疏远感,这种感觉会逐渐蔓延,从而使社会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而走向衰落? 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覆盖的知识面极广,涉及自然历史学、史前考古学,以及人类变化无常的文明进程——从苏美尔的泥墙到脸书上浩瀚的电子资源,等等。行为科学家惯于在狭窄的语境框架中梳理人类的互动特征,例如通过使用策略游戏来阐明我们如何对待彼此的关系。但我试图联系更广泛的学科背景来开展研究。了解社会的起源、运行和解体——社会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产生的具体过程,以及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将会让我们了解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中的最新成果,其中还会涉及一些哲学知识。 ◎人类社会到底是从何而来?我们人类社会因何而独特?我们的社会终将走向何方? ◎尽管人类害怕外来者,但我们的社会为何能发展出像玛雅帝国或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巨大的规模? ◎为什么人类社会能保持独立地位,但却无法避免逐渐走向衰落的命运,直至最终灭亡? ◎如果人的秉性就是深深眷念自己的社会,为对其美化讴歌而不惜经常轻视、怀疑、贬低甚至憎恨来自其他社会的成员,那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以上人类表现出的不可思议之处,也是作者写作本书的原因。 ◎《福布斯》《金融时报》《新政治家》《柯克斯书评》《出版人周刊》《图书馆》《自然》联袂推荐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