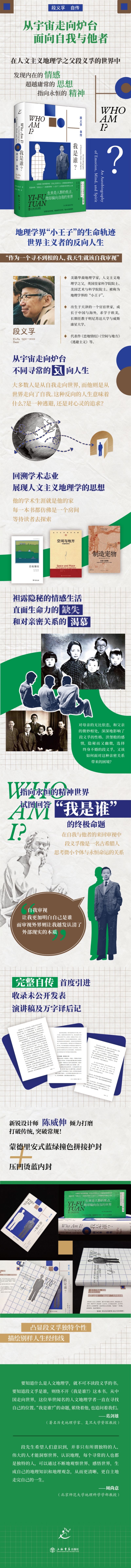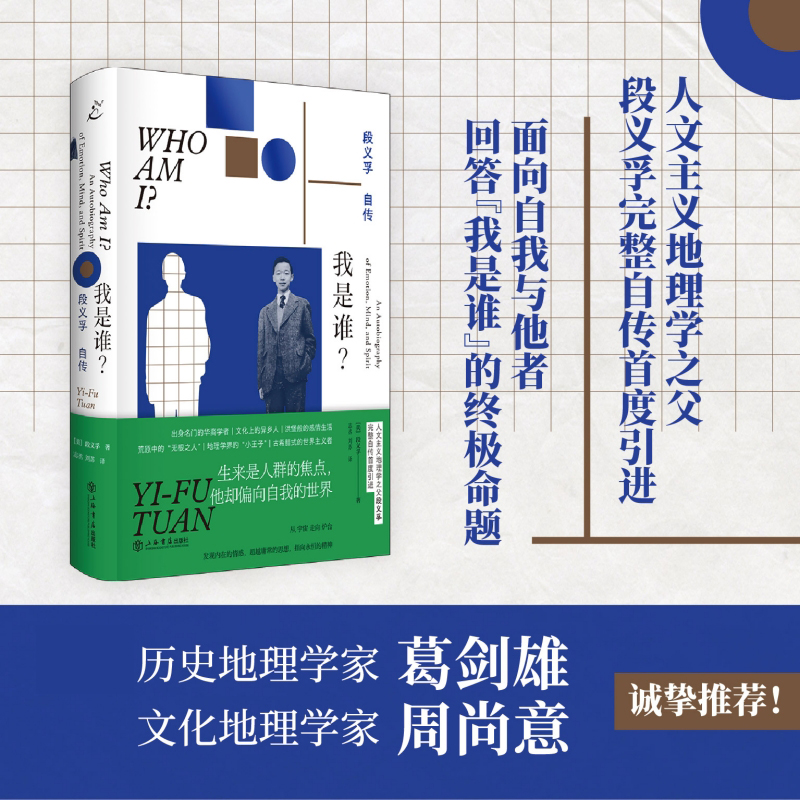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书店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5.60
折扣购买: 我是谁?段义孚自传
ISBN: 9787545822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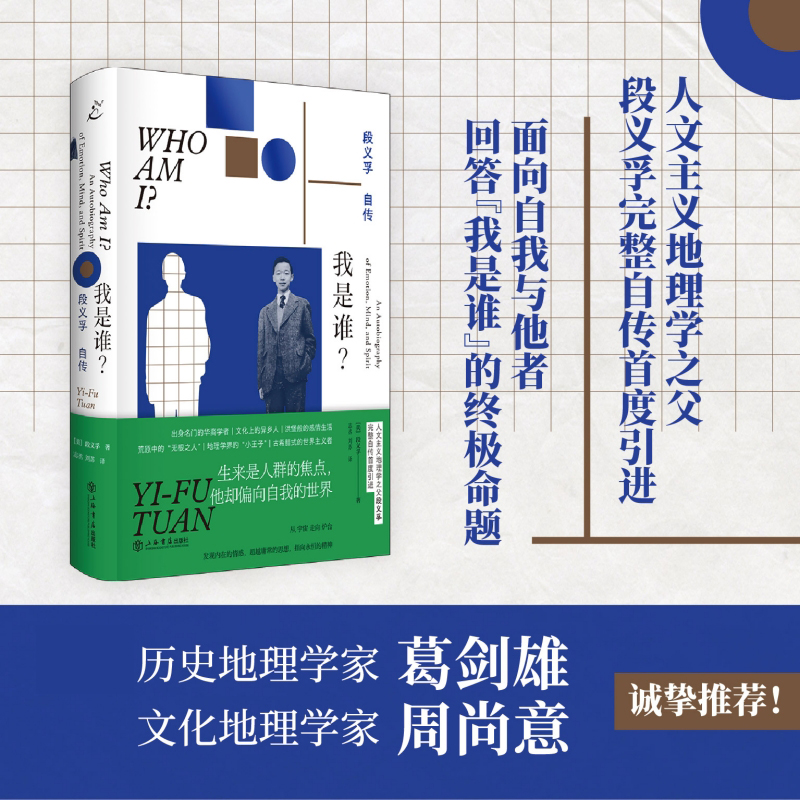
段义孚(1930—2022),美籍华裔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被称为地理学界的“小王子”。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官宦世家,成长于中国与海外,求学于欧美,长期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代表作有《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逃避主义》等。
段义孚先生69岁那年,创作了自传《我是谁?》,回忆了从童年到晚年的经历。先生为何要写这部自传? 首先,先生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根的人。正如他在开篇里所言:“作为一个寻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该自我审视。”因此,这部自传是他对自己大半生寻根历程的一次回顾与剖析。而之所以感到自己无根,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青年时期,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地方住满过五年。 我一直在不停地换住处,先是小时候与家人一起,长大后便独自一人。我的“家”换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卢明顿、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多伦多。 直到38岁,段义孚先生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和麦迪逊,在这两个地方各住了十四年,而这才是他最能感受到归属感的地方。 其次,在人际关系上,段义孚同样认为自己是无根的人。他终身未婚(这与他关于生命救赎的体验有关);另一方面,他无法完全融入西方社会。因此,身份认同对段义孚而言,始终是一个需要审视的问题。 之所以写作自传,有个体的原因,即某人欲对自己的人生展开一次全面的审视;也有社会性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土壤要有利于自传文学的产生。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环境来看,随着科技的迅猛革新、地域流动性的不断增强,人的身份危机开始凸显出来,进而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我是谁?”的问题。 “我是谁?”是新千年即将来临之际的一个时髦问题。似乎每个人都在问。不仅个人、团体,甚至国家都会问自己“我是谁”或“我们是谁”。 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借助自传文学这一途径对“根”展开了价值寻求。而段义孚的这部自传也正产生于这样的社会土壤。然而,这部自传却又与时下多数自传文学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在《我是谁?》里,时间线索和公共事件皆不突出,也无特别丰富、如数家珍的个人回忆。而这些要素却能体现在其他多数自传作品里。原因在于,段义孚并不像某些悲观主义者那样,甘愿被过去某些不堪回首的时光捆缚,进而主动遗忘了很多事情;同时,他一贯追求精神胜于追溯具体事件,因为在他看来,前者指向了永恒,后者却容易朽坏。 其次,通常用来吸引出版商和读者那种扣人心弦、轰轰烈烈的事迹在这部自传里很罕见。在他自己眼中,人生的大部分岁月都不如那些外向的自传者具有彰显自身的光彩,反而,他的成年时光多是独自过着一种“向内”的生活,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内在景观”(inscapes)——精神上的景观。因此,刻画“精神景观”正是这部自传的主旨。 再其次,与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不同,多数人是从童年的“炉台”迈向成年的“宇宙”,但段义孚的人生轨迹却是反过来的,即从世界走向了自我,从童年所处的公共领域走入了成年后的私人领域。但,这也绝不等于进入成年后,格局反而缩小;相反,他却愈益朝着由观念和思想构筑起来的宏大世界迈进。 因此,《我是谁?》的魅力,并不在于引人入胜、博人眼球的不凡经历,这些事物或许离普通人的生活太遥远;相反,它的魅力在于,在平凡的事物与事件里,去体察个体生命在不断破碎与重建、踟蹰与前行的过程里呈现出的意义与价值。难怪世界地理学最高荣誉奖的评委会,把段义孚比作地理学界的“小王子”,因为他们两人都常常在平凡微小的事物中用情至深。 宇宙与炉台:生命最初的底色 段义孚从童年到成年,是从“宇宙”走向了“炉台”。童年时期,他生活在世界的舞台上,经历着各种公共事件。成年后,他的世界缩小到了学术的角落里。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他一生的追求——心灵追求、关系追求与事业追求——均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奠定了最初的生命底色。 段义孚成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父亲段茂澜是一名外交官,这让童年的段义孚能频繁接触到世界性的事件与人物。他在自传里提到了与自己家庭关系颇深的三个人:段祺瑞、汪精卫和周恩来。 段氏家族起源于安徽,到了近代分为两支:一支家财万贯,住在合肥,是段祺瑞所属的一支;另一支家境贫寒,住在银山(可能在安徽芜湖附近),是段茂澜所属的一支。所以,段祺瑞一直资助段茂澜在南开中学读书。后来,段茂澜接受了西方教育,为段义孚的童年创造了中产家庭的成长环境。汪精卫是段义孚母亲的一位远房表亲。由于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段茂澜一家对他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试图与这位亲戚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在私人感情上又不得不有所顾念。周恩来是段茂澜的好友,虽然两人最终在政治路线上迥然不同,但私下的友谊却一直维持着。 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时,常常拜访段义孚家。段义孚说,父亲和周恩来在客厅里掰手腕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正因为父亲的外交官身份,他和众多世界级的政治人物都有或近或远的关系,这使得童年的段义孚总能亲历各种公共事件,生活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环境中,超越了狭隘的地方主义。 而同时,段义孚就读的小学也为他开启了世界主义的视野。战时的陪都重庆在段义孚的记忆里并非一处温暖的家乡,而是一个贫穷、战乱、充满死亡和迷信气息的地方。这或许同他家位于重庆乡郊有关。在那里,他每天都要忍受空气里的酸腐味、遭遇恶臭的泥浆、路过脏乱的小摊小贩和黑市上的交易,偶尔还能撞见村子里的迷信——预防诈尸的白事。与此相对的是,1938年,段茂澜和他的朋友们在南开发电厂旁创办了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段义孚在这所小学里获得了世界主义的启蒙教育。在课堂上,他不仅认识了牛顿、富兰克林、瓦特等伟大的科学家,还读到了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这些人物和故事都令他的思维超越了地方主义和国族主义的狭隘性,融入更崇高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宇宙”里。 段义孚在另一本半自传体作品《人文主义地理学》里回忆说: 我从未想过他们可能不是中国人。我——并且确定其他中国孩子,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当成值得钦佩的人,我想模仿他们的创造力、知识、勇气和孝义。在我们生命中的敏感阶段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个令人振奋的,不断扩大的广阔世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在以后岁月里从容面对残酷现实——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自身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段义孚童年的生活空间可以视为由两种环境组成:其一,战乱贫穷的农村,带给他死亡的恐惧,心灵无法扎根;其二,家庭与学校,虽然尺度上是更微观的两点一线,但却连接着更宏大的世界主义与公共舞台。在那里,段义孚感受到了精神的升华,奠定了他一生总渴望宏大而永恒事物的思想基调。 自我与永恒:四种爱的经历 自我,是贯穿《我是谁?》的主题。由上文可见,原生家庭是段义孚塑造自我的第一片土壤,给予了他世界主义的广袤“宇宙”。童年时期,他就已实现“炉台”与“宇宙”之间的穿梭。因此,“宇宙”的意象已融为他生命的底色,也是令他一生不断向往永恒之物的动力所在。 或许,正因为这般自我的成长与塑造,才让段义孚的情感轨迹与大多数人的情感轨迹不同。译者认为,段义孚的情感更接近于柏拉图式的爱——一种对超验之物的理念式的爱。古希腊人将爱分为了四种:抚爱(Astorgos)、友爱(Phileo)、情爱(Eros)与圣爱(Agape)。并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或多或少会经历这四种爱。那么,段义孚在这四种爱中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段义孚完整自传首度引进,收录未公开发表演讲稿及万字译后记。一次面向自我与他者的生命写作,全景呈现段义孚丰富而敏感的内心世界,交织着情感、思想与精神,在平凡的事物与事件中,看见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文化地理学家周尚意教授诚挚推荐! ★从宇宙走向炉台,记录段义孚不同寻常的反向人生。跟随外交官父亲的脚步,少年段义孚站在了世界的舞台,成为人群的焦点,然而成年的他却全身而退,回到学术的角落来思考人生。大多数人是从自我走向世界,而他则是从世界走向了自我。这种反向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是一种逃避,还是对心灵的追求? ★袒露隐秘的情感生活,直面生命力的缺失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慕。对母亲的无比依恋,与父亲的微妙相处,深深地影响了段义孚的个性。洪堡般的感情,隐秘而又幽微,选择终身不婚的段义孚,又该如何面对这种亲密关系带来的困境? ★回溯学术志业,展现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串起《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制造宠物》《逃避主义》等十本段氏著作,他的学术生涯就是他的家,每一本书都仿佛是一个房间,等待读者去探索。 ★指向永恒的精神世界,试图回答“我是谁”的终极命题。“自我审视让我更加明白自己是谁,而审视外界则让我越发认清了外部现实的本质。”在自我与他者的来回审视中,段义孚像是一名古希腊人,思考微小个体与永恒命运的关系。 ★新锐设计师陈威伸倾力打磨,打破传统,突破常规!蒙德里安式蓝绿撞色拼接护封,呈现后现代主义基调,凸显段义孚特立独行的个性。丝网印刷内封,以线条和色块表现段义孚所处的人生经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