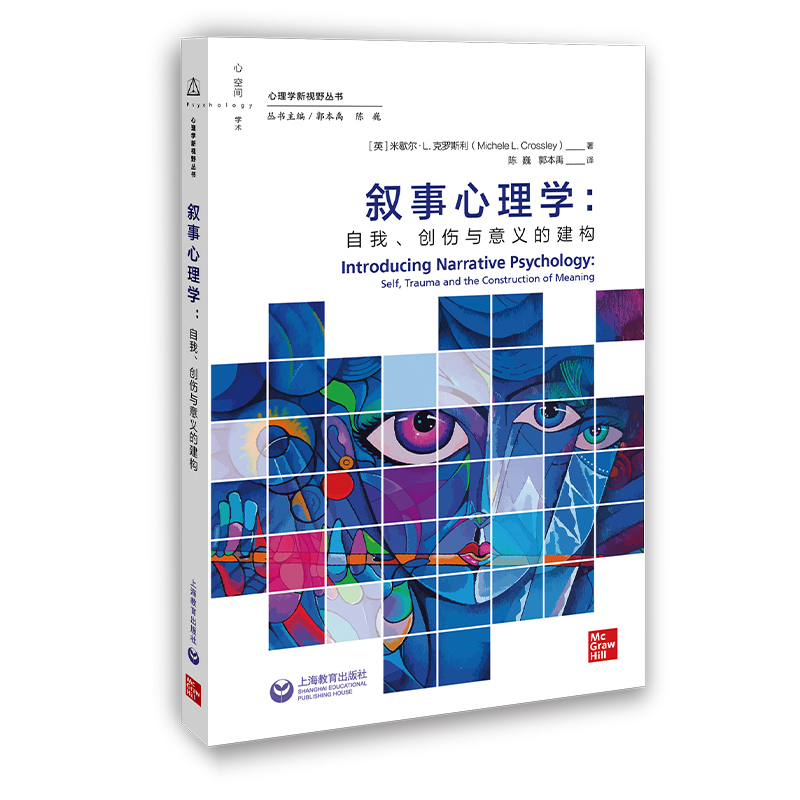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教育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1.90
折扣购买: 叙事心理学:自我、创伤与意义的建构
ISBN: 9787572003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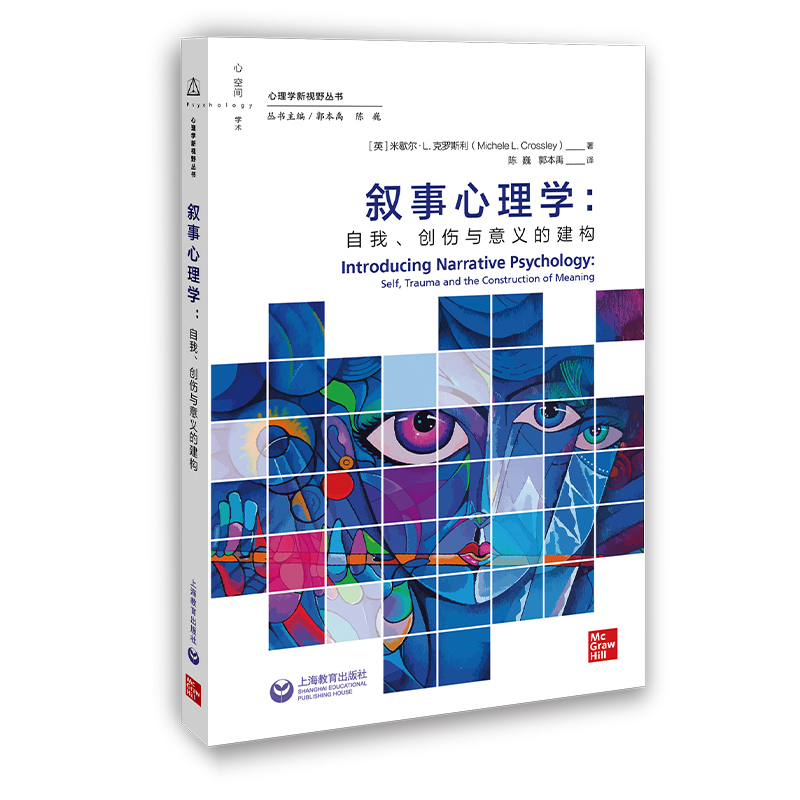
米歇尔·L.克罗斯利是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护理与初级护理实践学院教授,擅长健康心理学,尤其在创伤事件的心理与情绪方面有独到的研究。她是英国心理学界闻名的叙事研究专家,在该领域发表许多研究论文。本书是她长期研究的结晶。著有《治疗西维亚:儿童性虐待与同一性的建构》(1995)、《重思健康心理学》(2000)。
当代的自我概念:内部转向 泰勒的核心理论主要针对当代西方社会群体。在那里,关于价值和意义的基本问题主要以以下形式出现:“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它有重量和实质吗?”“它会变得一无所有吗?”现在,尽管这些问题是先前时代问题的延续,但是彰显出人类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去寻觅一种存在感和道德感,也仍渴望能够在与有关真善之处寻找落脚点,同时也突出人们在当代社会中体验到的迥异的自我意识。比如,泰勒认为困扰人们的这类问题主要是“生活的意义”“自我的意义”“我们将复归何处”“我们又正在做什么”。这些现代生活的“存在性困境”(existentialpredicaments),以及我们对“可怕的空虚”(terrifyingempty)、“失落”(loss)、“迷惘”(vertigo)和“意义缺失”(meaninglessness)的忧虑充斥着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这些困境非常不同于之前文明中体验到的。 泰勒认为,这类问题早些时候之所以还没被提上日程,是因为过去的人们生活在“不容挑战”的意义框架(frameworksofmeaning)中,这种意义框架对人们提出“蛮横要求”。虽然人们也体验到与真善方向有观点上的矛盾,但真善是实实在在的。相对来说,真善不是不存在任何问题而被视作一种理所当然。因此,如果我是一名在17世纪被视为通奸的妇女,我会像霍桑(NigelHawthorne)的小说《红字》(犛犮犪狉犾犲狋犔犲狋狋犲狉)中的主角赫斯特·普林(HesterPrynne)一样,要面对清教徒在我胸前烙上红色字母“A”以示警惩。虽然我可能会怀疑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但我更畏惧上帝愤怒的火焰中那不可避免的诅咒。这就是泰勒认为的理性和道德的实质性定义;我们关于真善的意识被视作与上帝创造的先在秩序的联盟。然而,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俗社会,我并没有这些恐惧。我甚至会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存在道德上的错误,这造成我在特定的道德与自我实现之间产生冲突。这是泰勒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意义框架”本身就变成问题。我们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同一个意义框架,这个意义框架已然不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人都可以为自己设立一个意义框架。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宗教和传统公共机构的衰落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有关 (Holifield,1983;Lasch,1984;Bellahetal.,1985;Cushman,1990,1995;Giddens,1991;McLeod,1997,pp.127)。尽管已经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意义框架仍然负有一定责任。我们在 穿越不同道路时不断协商和创造意义,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具有“追求目 标”(theobjectofaquest)(MacIntyre,1981)。较之前现代特有的理性和 道德的“实质性”秩序,我们现在关于上述两者的界定更多是一种“程序 性”模式(proceduralmodel)。在这一模式中,我们的行为依我们所属群 体规定的秩序而定,这个秩序由我们建构,而不是等待我们发现 (Taylor,1989,p.156)。 对现代自我概念的历史性回顾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泰勒认为,我们 现代的自我概念是由特定的内部转向意识(senseofinwardness)组成的 (Taylor,1989,p.111)。在当代用来理解自我的语言中,“内部”(inside) 和“外部”(outside)这两个对立的词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倾向于认为,“观念”“想法”和“感受”是存在于我们“内部”的,而世界上的物质是存在 于我们“外部”的。我们认为,自己是未经探索的处于黑暗之中的生物 (Taylor,1989,p.111)。我们对自我概念的认识如此自然,以至于想象 其他事物的存在方式对我们来说十分勉强。事实上,自我概念在现代西 方社会是非常明确的。正如格尔茨(Geertz,1979,p.229)说: 在西方,人被视为有界限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或多或少整合了动机和认知的系统,一个由觉知情绪、判断和行动构成的动态体系,一个不同于其他类别的独特整体,而且伴随社会和自然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人是世界文化背景下的独特概念。 当然,正如泰勒所认为的那样,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都有自我意识并区 分为内部和外部、内在(internal)和外在(external)。不过,现代西方社会 的自我概念中仍有一些部分是独特的。它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我 们的文化中,我们倾向于假设自我处于一定的客观地位,它显示出一定 程度的恒定性和统一性。尽管每个人一生经历的事情大不相同,而且这 些事件在外在上是变化的,但本质上我们认为是与自我一致的。在涉及 自我时,我们经常在它前面加一个定冠词“the”或不定冠词“a”。根据泰勒的理论,这种语言上的精确性反映了某些要素对当代自我认同的特殊 性和重要性(Taylor,1989,p.113)。这种典型的自我意识对我们的真善感和道德感有着重要的暗示作用。道德的操作性定义就是,道德行为不是由上帝制定的预先存在的规则决定,而是通过内部过程加以诠释和反映。 因此,这种内部感使得现代自我意识特征化,但“外在”是怎样转移到“内在”的呢?在“内部转向”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他撰写了一部名为《忏悔录》的自传。奥古斯丁认为,为了获取更高层次的存在感觉和道德感,并为真善找到合适的归宿,人们必须转向内部。他有一句名言:“切勿转向外部,复归你的内部。只有在内部人们才能发现真理。”(Taylor,1989,p.129)按照泰勒的理解,奥古斯丁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从外部客体转向内部的认知活动。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高级的存在感”在何处,我们必须转向内部,转向自我;我们必须选择泰勒所谓的“根本反省”(radicallyreflexive)的立场,站在“第一人称”的立场来反思(Taylor,1989,p.130)。这个指向“我自己”的举动将自我作为“经验的能动者”(agentofexperience)对推动现代西方文化的内部转向传统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将“根本反省的内化”延续并植入现代文化(Taylor,1989,p.131)。正是因为奥古斯丁, 我们看到人类存在的意义的一个新方向,看到描述自我世界的一种新方法,看到对“个人生活秘密源泉”(secretspringsofpersonallife)的一种新迷恋。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奥古斯丁关注的自我并不严格等同于我们 “现代”的自我概念。它们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奥古斯丁那个时期, 除了上帝就没有其他什么人可以影响个体成为存在和决定他以怎样的具体形态存在。实际上,这意味着奥古斯丁仍对实在(reality)持有实质性概念,即假设上帝创造了预先存在的合理秩序(preexistentrationallogos)。这种观点有时也被称为“本体法则”(onticlogos)理论,它本质上就是一套关于宇宙的法则,特指预先存在的真善是有秩序的(并由上帝创造)。直到另一位著名哲学家笛卡儿(RenéDescartes)的出现,假设预先存在道德秩序的“本体法则”理论才被抛弃,然后才出现更与我们自己相称的自我的概念。 叙事心理学的理论与应用一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