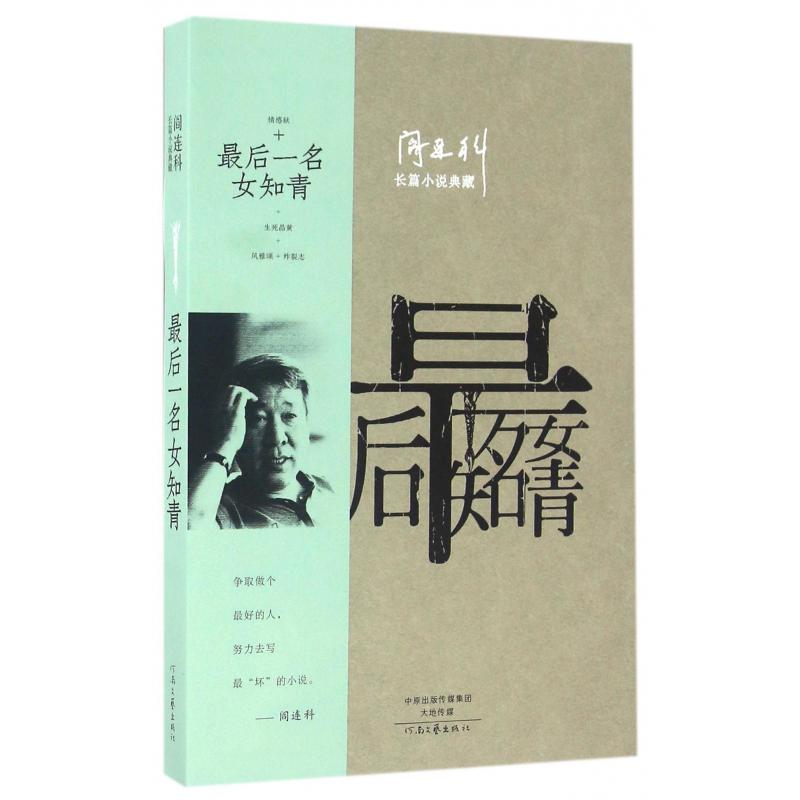
出版社: 河南文艺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9.80
折扣购买: 最后一名女知青/阎连科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555903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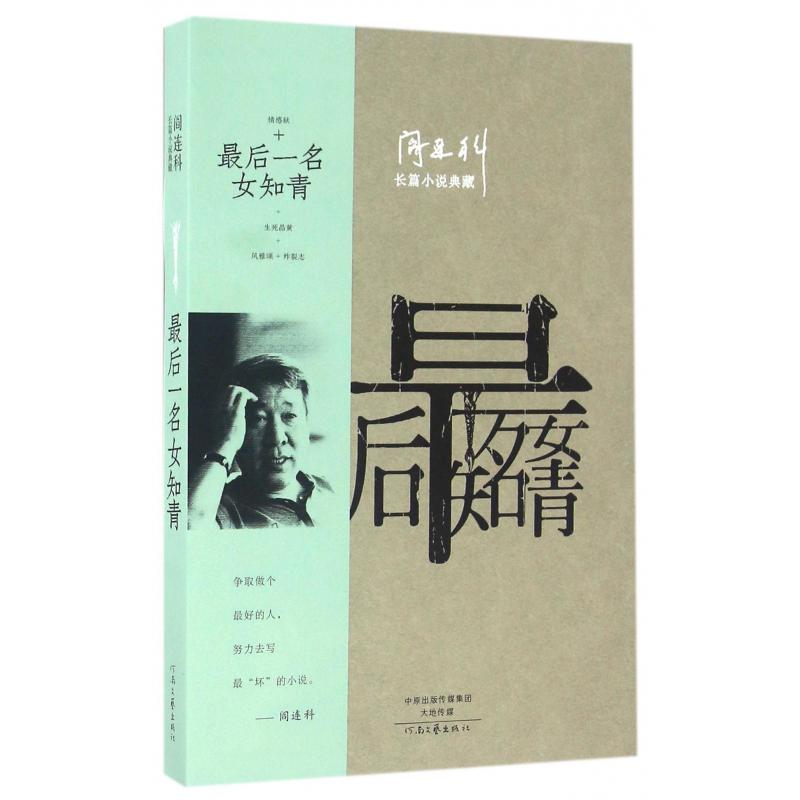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炸裂志》,中篇小说《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短篇小说《黑猪毛自猪毛》,散文《我与父辈》《711号园》等作品。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入围2012年度法国费米那文学奖短名单、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014年度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荷、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二十多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
1 黄黄是条极为极为大众的狗,其形象,也平常得 十二分可以,往足处去说,也无非同类的一般水平而 已。它的不凡之处,在于它记下了许许多多人类的破 绽。 在张家营子,黄黄时不时地凝视一日路程之遥的 正东。尤在太阳平南时候,它便常常看见这方百姓所 托寄以繁衍人世之希望的那脉名山之下,生冷地坐落 着一个监狱。狱门的外围,蔓生着悠然野草。不消谁 说,草间自然而然开了许多小花,白的或者黄的,粉 淡间或浅紫,各色各式,满目琳琅。黄黄还发现,监 狱不断地枪毙罪犯,寒凉的枪声,穿过一片温暖的红 色,四散开来,自然也走进它的耳朵。这当儿,就会 有一阵恶寒,从它背上穿过。它受了一个冷惊,不得 不从地上站将起来,朝着正东一阵狂吠。 这时候,狱墙下的野刺红、映山红、仿莲红、金 钟红、仲春红,而更多的是满世界的喇叭花,粉粉淡 淡,在枪声里红得川流不息,铺天盖地。红艳艳的枪 声,朝狱后白果树山升漫时,黄黄便凝视着山腰上的 小瓦庙,便见庙里坐着一个孤独的和尚,双手合掌于 胸前,念着佛语,普度着芸芸众生。也许在他的普度 中,那死了的人,来世或许是一个人物,亦未可知。 山上的小庙早已年久失修,扭歪的墙柱对你说, 它的倒塌,不在今日便在明日,决然不会超过后天。 然而,小庙却在风雨飘摇之中,终是挺过了许多年月 ,它伴着监狱一日日地站在山上,却不断地更换它的 主人。据说,如今那个和尚,虽非十分的正宗,却也 是灵山大寺中正堂住持的同姓同族。情况是否属实, 连黄黄也是道听途说罢了。 2 正午时分,镇子出现在了黄黄的眼里。 黄黄从山梁上下来,站在一座桥上。镇子比村子 要大,且镇子中央,还有一幢楼房,乡村的客车从那 开进开出。三月的流水,在桥下青青翠翠地流,舒展 如无头无尾的一匹绸布。桥下有镇子上的女人,她们 把洗好的衣物,搭在河边的堤上树上,先干的布衫、 裤子,便在风中飘飘扬扬,噼啪出猎猎之声。 一个女人说:“听到没?昨儿半夜的枪响。” 另个女人说:“听到了,脆得很。” 黄黄从桥上过去,踩着她们说话的声音,轻轻跃 跃。它的两个主人也已上了桥头。走过的山梁子,在 她们身后渐次地小下去。黄黄用它的尖嘴咬咬婆婆的 裤管,又扯扯儿媳的裤管,便又跳着跑往桥上。儿媳 说镇子到了。黄黄望一眼河桥,又抬头望一眼头顶的 太阳。太阳爽爽朗朗。奇怪得很,婆婆说,梅,几点 了?叫梅的儿媳抹开她的衣袖说,一点了。真是怪得 很,婆婆把肩上的包袱另换一个肩头,说每次从张家 营子来镇上,无论是天不亮出门,还是太阳走到村头 出门,到这桥头总是这个时辰,从不错时。叫梅的儿 媳望着婆婆的脸,疑问浮在脸颊之上。婆婆说是真的 。上次我去招子庙,吃过早饭才从家里动身,到这儿 是这个时辰,桥下有两个媳妇在洗衣物,洗旗子。这 次我们半夜起床,走完十里路还不见太阳出,到这儿 却还是这个时辰,还有两个女人在洗衣物,洗旗子。 儿媳便笑了。 婆婆正经着一张脸:“真的是这样。” 儿媳说:“不定今天又要扑空了。” 婆婆说:“和尚说过,三天之内,狱里肯定有人 要死的。” 儿媳笑笑,也就入了镇子。 镇上笔直的南北大街,劈破了许多民宅,粗暴地 横躺在镇子中央。有游街示众的人群穿街而过,威严 而又荒凉。 黄黄朝着示众的人群不知山高水低地狂吠起来。 儿媳说黄黄,你疯了! 婆婆说:“别提去招子庙的事情了。” 3 午时的镇子,照常是有几分冷清,更何况这个时 辰,正是人家的饭时。然在黄黄的眼里,已经远比它 的寄籍之地张家营子繁闹了许多。至少在张家营子, 见不到有一丛人群,将另外一人捆绑起来,胸前挂一 纸牌,让他在背后倒敲着铜锣,慢慢腾腾地穿街而过 。而别的人,貌似押解,其实在那人身后,并不真的 如何,各自吸着纸烟,闲谈了什么话题,只待那人倒 敲的铜锣,声音淡了,或敲得慢了,才想起朝他屁股 上踢去一脚,再或拿刚燃的烟头,小心地朝那持锣槌 的手上戳烧一下。烧一下,那人就要跳一下,将那铜 锣敲得响亮而又均匀,使一条街上,都滚动着铜的声 音。只要那铜声响亮,这丛人群,也就各持一身善良 ,说说笑笑,悠闲得如散步一般。这样的风景,张家 营子绝无仅有,就连那叫狐狸的知青,把张家营村的 六头耕牛全部杀死,村人也无谁动过他一个指头。 黄黄跟着游街的人众,一跑一跑直到路边的一架 井台之上,才忽然想起自己是同主人到白果树山上的 招子庙去,而不是来这镇上赶集。回头张望一眼,两 个主人远远走在后边,它就不得不坐在井台的青石条 上,稍事喘息等她们来到,现出一脸热闹丢失的懊悔 。 说起前往监狱的招子庙,黄黄对这宗秘密早已烂 熟于心。虽然自己身为一个畜生,无非一条黄狗而已 ,它却是主人家里极其重要的一员。发生在张家营子 的任何一桩事情,它都看在心里。任何一件事情,对 主人家有震动,它的胸口都要随之急迫地起伏。说起 来,它是同叫梅的女主人一道走进张姓的家门,而成 为张家真正的一员。事实上,张家有的事情,它比这 年轻的梅知道得更为详尽而具体。 但是,它却总是沉默着不言,它所知道的,你只 能从它那双小圆眼中看将出来。那双圆眼,不断地流 露出它隐藏秘密的全部漏洞。这时候,它端端坐在井 台的一角,冰凉的石条,使它一路的燥热立刻散去, 双眼显得神秘而又安详。末梢挂白的尾巴,舒展着贴 在石条上,发散着它内心激动的热气,模样儿极像昨 夜它卧在年轻的主人身边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在晚饭以后,村子里静得无声无息, 除了村落下面河沟的水声,正艰难地爬上山坡,在各 家院落试探着脚步以外,就是夜蝙蝠在头顶的飞响。 梅拾掇了锅碗,男主人在屋里批改学生的作业,婆婆 从屋里走出来,在月光中迟疑片刻,将梅从灶房唤出 ,坐到了黄黄的身边。 婆婆说:“梅,你嫁过来两年了吧?” 儿媳说:“有事?” 婆婆说:“我明儿想去白果树山的招子庙。” 儿媳便默下不语,朦胧的月光,洒在她的脸上。 她脸上的清瘦,如同秋天的一片黄叶,写满了将落的 苦愁。招子庙的故事,原在下乡之前,本是城里人对 乡土社会嘲弄的谈资,年少时听过一笑了之,剩下的 只是内心对乡下人愚昧的藐视。如今风云变幻,社会 动荡,使自己不得不沦为一个乡下的民办教师。和张 老师结婚,也本是为了对命运的解脱,以求一息安定 ,哪怕一生不再返城,只要心中能有闲适便好。同来 落户的知青,断断续续都又返回了郑州,最快的仅下 乡三个月,便回省城做了百货大楼的售货员。要知道 ,当时的政治形势,导致物资极其匮乏,乡下人买不 到火柴,用铁镰与石头撞击取火,是常见的事情。而 那做售货员的同学,却又专卖火柴、煤油、布匹等日 常用品,消息传来,同车来到张家营的八名知青,谁 的眼睛都红了半晌。就是最后离开张家营的,也在一 家工厂做了三年工人。活虽累些,但工资高得出奇, 还在学徒阶段,每月就拿到六十七元的钱。剩下的她 ,又在张家营孤独地守了整整三年,返城的人每年都 有,到她面前却总是没有名额。到了二十八岁,就是 在城里说出这个数字,对方也会暗自哎哟一声。她怀 着索性做一个农民的心境,完婚两年,却从未有过身 孕。当然,她不会同一般女人一样因此自暴自弃。医 院的医生又明确说你们夫妻都生理正常,只是年龄大 了。怀着信心有安排地进行夫妻生活,月经却总是如 期而至,从不错误一天,连怀孕的假象也未曾有过。 既然成家,当然渴望膝下有儿有女。要认真说来,倒 不怕无女无儿,丈夫是村里的老民办教师,不消说的 知书达理,操行高正,为人笃厚;婆婆虽不识字,却 因自己是落户的知青,凡事又都让着三分,真的不能 生育,想她也不会如常人一样指桑骂槐。可是自己却 受不了没有儿女的寂寞。 她用手梳理着黄黄背上的绒毛。问婆婆说:“你 不是已经去过了招子庙吗?” “和尚说无死无生。去的都不是时候。” “等谁死呢?” “那监狱不断有人死哩。” 她的手在黄黄的背上忽然僵住,月光在脸上冰出 一层青色。房墙下的蛐蛐,咯咯出刀切青菜一样脆生 生的叫声。村街上走动的脚步,踢踢踏踏,把从河沟 爬上来的流水声,踩得七零八落,如从树冠上漏落的 一片片月光。脚步渐渐远去,流水声又弥合着走进院 落的时候,她说明儿我和你一起去吧,倒真想看看那 和尚招子的戏法。 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