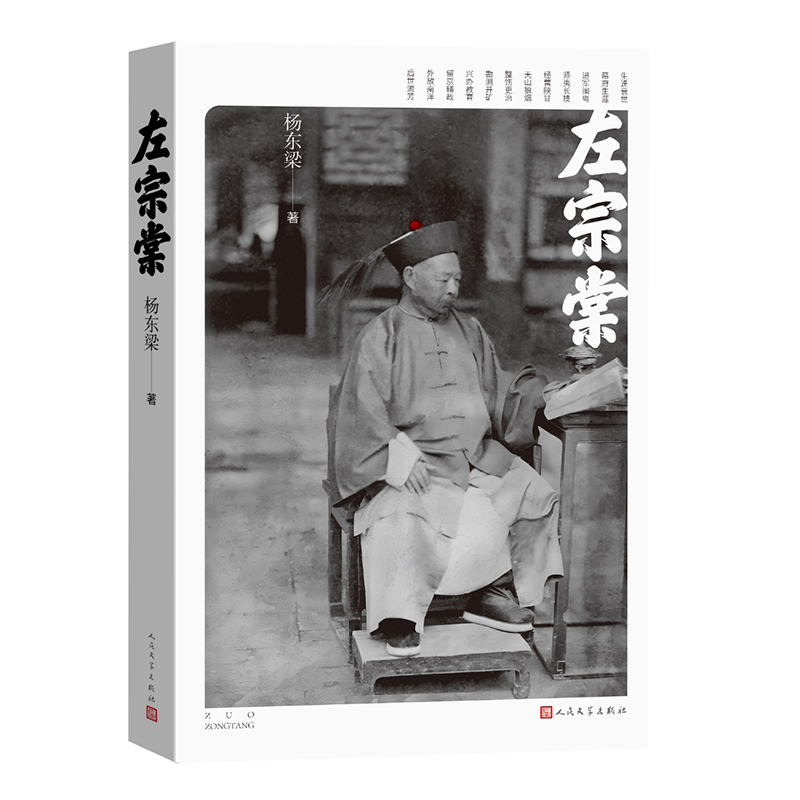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2.90
折扣购买: 左宗棠
ISBN: 9787020186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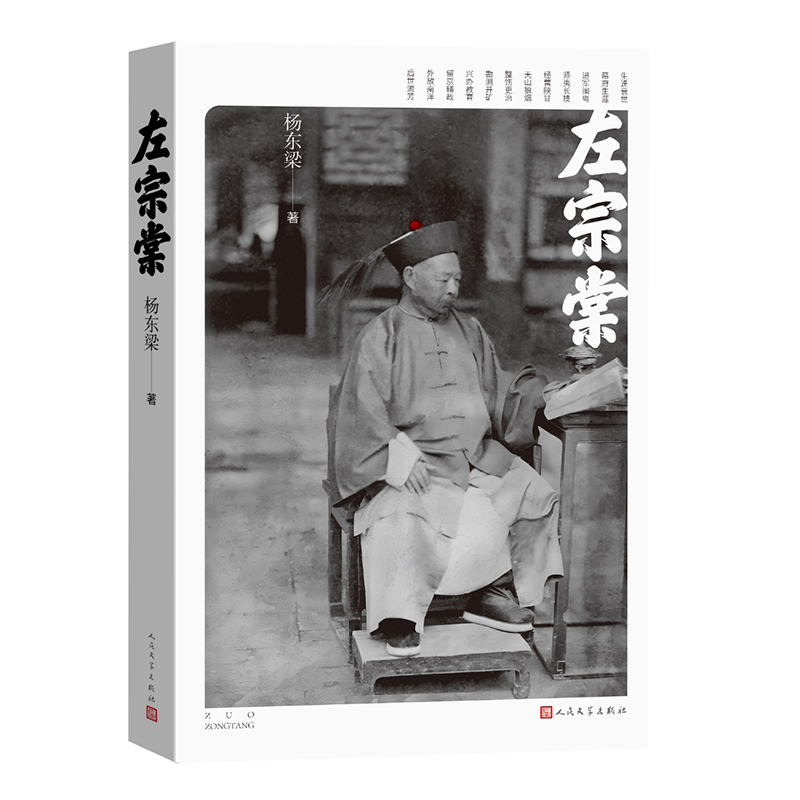
杨东梁,男,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等。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左宗棠评传》《甲午较量》《中国清代军事史》等10余部(部分为合著),主编丛书多部,发表文章百余篇。
二、孤贫发愤 左宗棠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祖上是在南宋时期(十二世纪)从江西迁到湖南的。他的曾祖父中过秀才(也称生员),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父亲左观澜,字晏臣(一字春航),为县学廪生(即“廪膳生员”,每年可领取廪饩银四两),也算得上是个书香门第。左人锦、左观澜都饱读诗书,却始终考不中举人(乡试中试者),这就意味着不能继续沿着科举的道路去做官。既做不了官,又没有多少田地,家里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遇上荒年,甚至难以糊口。嘉庆十二年(1807),湘阴大旱,全家只能用糠屑做饼度日。左宗棠出生时,他前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大哥宗棫十三岁,二哥宗植九岁)和两个姐姐。母亲余氏已经三十八岁了,由于家境不好,乳汁不足,只能用米汤来喂养这个不断啼哭的婴儿。也就在这一年,为了前程,左观澜离开家乡,到省城岳麓书院去读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在长沙开馆授徒,并把全家迁到省城。而生活来源只能靠左观澜的教书所得,所以左宗棠后来回忆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4页,以下简称《全集》) 左宗棠三岁时,祖父就在湘阴梧塘塾屋教他读书、识字,迁居长沙后,又与两位兄长一起跟随父亲读书。宗棠年龄虽小,却颖悟过人。有一次,左观澜为宗棫、宗植讲解《井上有李》一文,讲到“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时,问道:“‘二桃’的典故出自何处?”一旁的宗棠立即答道:“古诗《梁父吟》有之。”四岁小儿有如此敏捷的应对,让左观澜甚感欣慰。 嘉庆二十二年(1817),左人锦去世,左观澜也年逾四十,自己功名不就,更把“金榜题名”的希望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对他们也督促更严了。两年后,十九岁的宗棫进了县学,十五岁的宗植更进一步,进县学后,因科考成绩名列前茅,被补为廪生(一年可得“廪饩银”四两)。这让左观澜多少感到一些安慰,九岁的宗棠也被要求学作“制艺”(即八股文,是科举考试中官定的文体格式)。不久,宗棫补为廪生,宗植选为拔贡(贡生的一种。选品学兼优的生员送京师国子监读书者称贡生)。道光六年(1826),宗植进京参加“朝考”,列二等,被选为湖南新化县训导(县学副职,从八品)。也就在这年,已经十四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参加“童试”(儒童入学考试,包括县、府、院试三个阶段,合格的取得“生员”资格,俗称秀才)。翌年五月,应府试,名列第二,但因母亲病重未参加“院试”(由学政主持),也就和“生员”资格擦肩而过。十月,母亲去世,服丧期间,他更加勤奋治学。 道光九年(1829),左宗棠已满十七岁,但他并没有把精力集中于猎取“功名”的制艺上,而是好读“经世致用”之书。最早的经世之学发端于明清换代之际,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怀着复兴故国之心,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章沿革,皆极意研究”。但这股思潮很快沉寂下去,由于统治者的扼杀、打压,知识阶层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现实。他们或是不问世事,寻章摘句,皓首穷经;或是钻进故纸堆,把精力集中于古籍的整理与诠释上。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一股经世思潮重新崛起,一些学者提出“研经求实用”,提倡阐发“圣人”的经世之志(经世即是治世)。特别是当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之时,一些有识之士相继提出自己的应对主张和解决方案,试图复兴十七世纪的实学传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宗棠开始了他追求经世之学的道路。一次,年轻的左宗棠在书铺里买到一部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如获至宝,他被书中记载的山川险要、战守机宜深深吸引,于是潜心研读,直至了如指掌。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他读得很仔细、很认真,边读边做了详细笔记,这种阅读大大开阔了左宗棠的眼界。道光六年(1826)问世的《皇朝经世文编》(魏源代贺长龄编)更成了左宗棠案头的必备书,这套书每页留下的圈点、符号,是他悉心阅读的印记。左宗棠的特立独行为醉心八股时文的士子所不解,也招来了许多讥讽,但他不为所动,毫不理睬,仍坚持自己讲求实学的道路。 道光十年(1830)正月,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病重,元宵节后三天就去世了,终年五十三岁。左观澜读书半生,并没有给儿辈留下多少遗产,只有薄田几十亩,一年收的租谷不过四十八担,家中生活难以为继。此时,宗棠的长兄宗棫已早于父亲病逝,二哥宗植在新化做了三年训导,兄弟也难得相聚(宗植在湖南已有文名,与魏源、陈起诗、汤鹏等号称“湖南四杰”)。 家境的艰难并没有影响宗棠发奋苦读。恰在这年冬,著名的经世学者、江苏布政使贺长龄(1785—1848)丁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曾与江苏巡抚陶澍共同办理过漕粮海运,并请魏源以自己的名义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选收了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间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他家中藏书丰富,这对左宗棠真是难得的际遇。年轻的左宗棠既佩服贺长龄的学问和为人,更羡慕他家丰富的藏书,于是经常到贺家求教,并借阅各种典籍。贺长龄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七岁、求知若渴的青年人也很赏识,竟以“国士见待”(《全集》“书信”三,第460页),不但敞开自己的藏书楼,而且亲自登梯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每当宗棠还书时,一定要询问心得,互相考订,孜孜不倦,简直成了忘年交。 长沙定王台附近贺氏兄弟故居:城南书院旧址道光十一年(1831),左宗棠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二哥宗植则客游武昌。在生活无着时,左宗棠只能靠书院发给的“膏火费”度日(“膏火费”系指发给学生的津贴)。城南书院的正课生员除一个月的“年假”外,每月发“膏火银”八钱;另外,每月初三和十八日有“会课”,考试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一等首名银五钱,其余三钱,二等每名二钱。 城南书院位于长沙城南妙高峰下,历史悠久,南宋时,理学大师朱熹曾在此讲学,有一定社会影响。其时,山长(书院主持人)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煕龄。贺熙龄(1788—1846)字光甫,号庶农,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曾任湖北学政,于道光十年(1830)底丁忧回籍,时年四十三岁,在湖南颇有声望。他倡导义理、经世之学,认为读书是为了“经世”,许多读书人“学不知要”,陷于词章训诂 、寻章摘句不能自拔,而喜好经世之学的左宗棠自然得到贺熙龄的青睐,被赞为品行“卓然能自立”,学问“确然有所得”(贺煕龄:《寒香馆文钞》卷二)。左宗棠“十年从学”,深受其影响。可以说,贺长龄、贺煕龄兄弟成了左宗棠走上“经世致用”之道的引路人。 前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是人们熟知的、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那么历史上的左宗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百多年来,由于论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其立场、观点、方法、角度也有很大差异,真可谓见仁见智。 晚清时期,左宗棠被称为“中兴名臣”之一,因为他和他的同僚们帮助清政府度过了一个动荡、飘摇的时期,使这个衰败的政权不致顷刻颠覆。中国有句俗话,叫“盖棺论定”,意思是指一个人须等其辞世后,对他的评价、判断才能最终确定。左宗棠去世后,皇帝颁布“上谕”,称他“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而且赐谥“文襄”。按照“谥法”的解释,所谓“文”是指“道德博闻”“修治班制”“勤学好问”“锡氏爵位”;所谓“襄”是指“辟地有德”“甲胄有劳”“因事有功”。照惯例,做到大学士的高官,死后谥号第一个字一般可以用“文”,而第二个字“襄”则正是对他的“武功”,尤其是收复新疆的褒奖。《清史稿》“左宗棠传”在传后“论”曰:“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 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的斗士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前仆后继,对于维护清朝统治的所谓“中兴名臣”自然目为“汉奸”,加以鞭挞。《民报》增刊《天讨》在“过去汉奸之变相”的标题下,刊登过身为禽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头像。不过也有些革命宣传家对左宗棠并不一笔骂倒,像章太炎既指责左宗棠“为虏将兵,以敌洪氏”,又肯定他治军严谨,不扰百姓,“士卒有创伤平民者,必诛无贷”(章太炎:《革命军约法问题》)。章太炎还视左宗棠为从古以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物,赞叹“他那出奇制胜的方略,毕竟令人佩服”(章太炎:《演说录》)。 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值日寇入侵,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对历史上坚决抵抗外侮的爱国将领更有一种特殊的怀念。左宗棠因他收复新疆的功绩而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当时,《边铎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左宗棠治理新疆政策之研究》(作者方骥)的文章,其《前言》说:“作者因感于九·一八事变,深惧国防之可忧,故草斯文”;另外,《西北研究》杂志也发表了姚欣安《清末新疆政策底史的发展》一文,作者写道:“回忆清末时代新疆之危机,能不令人感到左宗棠之可钦乎!鄙人草此文之目的,亦在所以表彰民族之功臣,而不愿使之遗恨九泉也。”真可谓闻鼙鼓而思良将。 新中国成立后,强调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由于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陕、甘回民起义,所以只能在“刽子手”的行列中找到他的位置。当时一部很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就称左宗棠是“极端反动的屠户”,“万恶的民贼”。那么收复新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也被“忽视”了呢?除了研究深度欠缺外,主要是政治气候的影响。那时,学术界对窃据新疆的阿古柏政权的性质认识不清,有人甚至认为阿古柏领导的是“革命运动”,阿古柏本人则被吹捧为维吾尔族的“民族英雄”。随着研究深入,学术界才搞清了阿古柏政权是一个压榨新疆各族人民的外来入侵政权。值得注意的是,清军西征还涉及英、俄两国,特别是沙俄占领了伊犁地区,而左宗棠是坚决主张抗俄的。五十年代,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很好,这一政治因素也影响到历史研究领域,对沙俄的侵华活动采取了有意无意的回避,因此不谈或少谈左宗棠收复新疆这段历史,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围绕阿古柏政权性质的讨论,史学界对清军西征开始给予积极评价,范文澜的第九版《中国近代史》(1955年出版)谈及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曾肯定地指出:“这个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左宗棠研究也别开生面。1978年1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杜经国的文章《试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左宗棠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抵抗外国侵略,巩固祖国西北边防方面,曾经做出重要的贡献”,“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封建政治家”,从而为这个专题研究投进了一块激起波漪的石头。 此后,左宗棠研究重新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从1979年至1981年,共发表十二篇专论,主要集中论述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办洋务的活动。1982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王震对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意见,他提到“对历史人物要分析,不要简单化,不要有片面性”,并指出:“像左宗棠这样的人物也要具体分析,一方面他镇压人民是有罪的;另一方面他在后期也捍卫过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抵抗了英国和俄国的扩张,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有功绩的”。1983年8月,王震在会见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北京化工学院教授)时,充分肯定史学界重新评价左宗棠是“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并着重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历史地看问题,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左景伊:《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此后,左宗棠研究全面铺开,研究、介绍左宗棠的论文、文章时有发表,数量不下几十篇。《湖南师院学报》还开辟了“笔谈左宗棠”的专栏。1984年和1985年连续两年,在苏州和长沙召开了全国性的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更为可喜的是,从1983年起,研究左宗棠的学术专著开始问世,短短几年中,竟达四部之多,这在历史人物研究中也是不多见的。 左宗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位名人,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相当影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贝尔斯(Bales.W.L.)、日本人西田保都曾为左宗棠作传。曾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1944年路过兰州时,曾说:“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左宗棠抱有崇高敬意!”(转引自华中师大图书馆:海外资料《左宗棠专辑》)2000年,适逢公历纪元中的第二个一千年,美国《新闻周刊》第一期开辟了“千禧年一句话”的栏目,这个栏目共刊载了最近一千年中全世界四十位“智慧名人”,其中中国有三位,即毛泽东、成吉思汗、左宗棠。可见,左宗棠不仅是一位中国名人,同时也是一位世界名人。 还有一件外国人“关注”左宗棠研究的趣闻值得一提。那是我在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时的事。1981年2月1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写的一篇论文《“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没想到此文竟会引起美国国务院的关注。故此,美国驻华使馆通过正式途径约见我。当年6月12日,通过校方的安排,我在人民大学会客室接待了美国外交官。他开门见山,表示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并问及此文“是否同中国对苏联和台湾的政策有关”,“是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你是不是认为对付苏联比对付台湾更重要”?等等。我如实回答了他,基本意思是:“历史不是现实,类比是不合适的,用历史来比附现在是不可取的”;“我的文章是史学论文,只反映我个人的观点。别人怎么猜测,是他自己的事”。说到这里,那位美国外交官轻松地笑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和笑话呢?我想,一方面当时“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外国人对中国媒体的审视还很难摆脱陈旧的眼光;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中美关系还存在不够成熟的一面。 我研究左宗棠是从1979年开始的。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1978年入学),1981年6月完成学位论文,定名为《左宗棠研究》。论文充分肯定左宗棠收复新疆和举办近代企业的功绩,认为他“在民族敌人面前表现出崇高的气节,不屈服、无惧色,斗争到底”,“成了中华民族的英雄”,并说,“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起了‘脊梁’作用的。他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看,甚至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岳飞和林则徐所不能比拟的”。论文初稿曾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著名史学家余绳武先生审阅,征求意见。余先生关心晚辈,奖掖后进,在认真读完后,即于1981年7月25日致函作者,予以鼓励:“大作不乏理论勇气,甚佩。史实也许稍嫌简略,将来似可在此基础上加以充实,扩大成一本学术性的《左宗棠传》。”余先生又建议说:“据我所知,王震同志对左宗棠问题颇感兴趣。我意您可考虑将此稿寄呈王震同志审阅,争取得到他老人家的指导。如果您有不便,我可以托人转呈。” 前辈学者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遂经近代史所刘存宽先生与时供职外交部的鲁桂成先生联系,经鲁先生(曾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直呈王老,并很快得到回复。王老在送呈论文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批注,可见阅读之细以及对左宗棠研究的高度关注。1981年9月10日,王老还在论文扉页上写道:“我深觉杨东梁同志写得好,读了甚获教益。”又建议作者继深造,并要求转达他的意见,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研究生毕业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左宗棠评传》的书稿,并于1985年8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出版后,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年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左宗棠学术研讨会”的主要推荐成果。198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还为此书发表书评。1986年3月10日,王震老在读完拙著后,致函作者云:“您送我的《左宗棠评传》一书,已收到,谢谢。我先读的序言、后记,而后把正文粗略读了一遍,感到您治学态度严谨,蒐集史料丰富,很好!”他还建议“就左氏晚年的爱国思想写专文发表,以激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此书于1987年11月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上所述就是我和左宗棠研究之缘。 之所以要把我研究左宗棠其人的经过做一简介,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项研究在三十多年前还存在一些人为的障碍,这是今天的青年学者难以理解的,介绍出来,会让他们更珍惜今天宽松的研究氛围。当时,一些传统观念还在束缚人们的头脑,我的论文由于提出了某些有悖“常理”的观点,有可能在答辩会不予通过。有的老师出于好意,建议做些修改。我原本坚持文责自负,不愿摈弃自己的观点。后经思考再三,觉得不应辜负师友们的良苦用心,于是同意把有可能引起争议的章节暂时撤下来,并把论文题目改为《左宗棠——我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者》。即使在王老的意见传达后,我仍坚持此议,算是一种折中处理办法。只是后来出书时都补上了。第二个原因是此事后来在社会上曾引起一些传言,甚至被某些著作提及,而其表述与事实真相颇有出入。为以正视听,借这次重写左宗棠传记的机会,予以披露,也是想还事情以本来面目。 拙著《左宗棠评传》出版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在此期间,陆续有一些有关左宗棠研究的论文、专著问世。特别是湖南岳麓书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整理出版了《左宗棠全集》,共十五册。新版《全集》不仅比清末编辑的《左文襄公全集》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共辑得左宗棠各类佚文约八十万字),而且以清末刻本为底本,订正了原刻本中诸多错讹、颠倒、衍文、脱文等,并酌加校注,这为更深入地研究左宗棠,提供了极其便利的资料条件。 2011年下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盛情邀我写一部较为通俗的左宗棠传。这些年来,我虽然一直关注左宗棠研究,但因忙于其他事务,难得有暇静下心做点深入思考。目前又因参加国家清史编委会传记组的工作,亦难分身。为不负编辑先生的雅意,遂尽量挤出一点时间,在原著《左宗棠评传》的基础上,费时一年完成了一部新的《左宗棠》传,新传不但在内容上做了增、删,在史实、文字上做了订正,在写法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并增补了部分图片。我脱稿的这部新传,就算是对这位中国近代爱国名将逝世一百三十年的一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