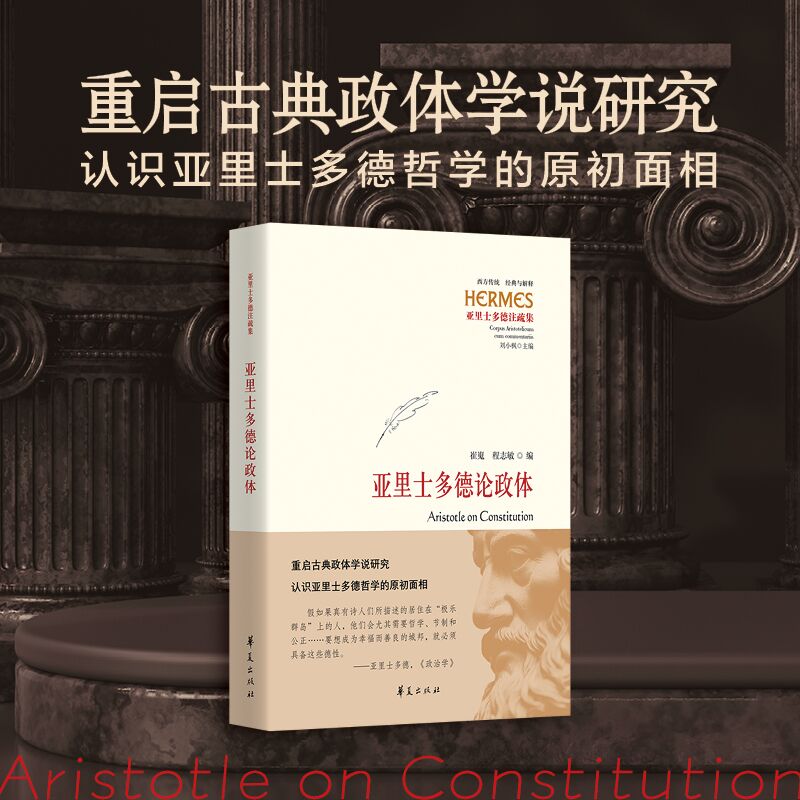
出版社: 华夏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3.32
折扣购买: 亚里士多德论政体
ISBN: 97875222047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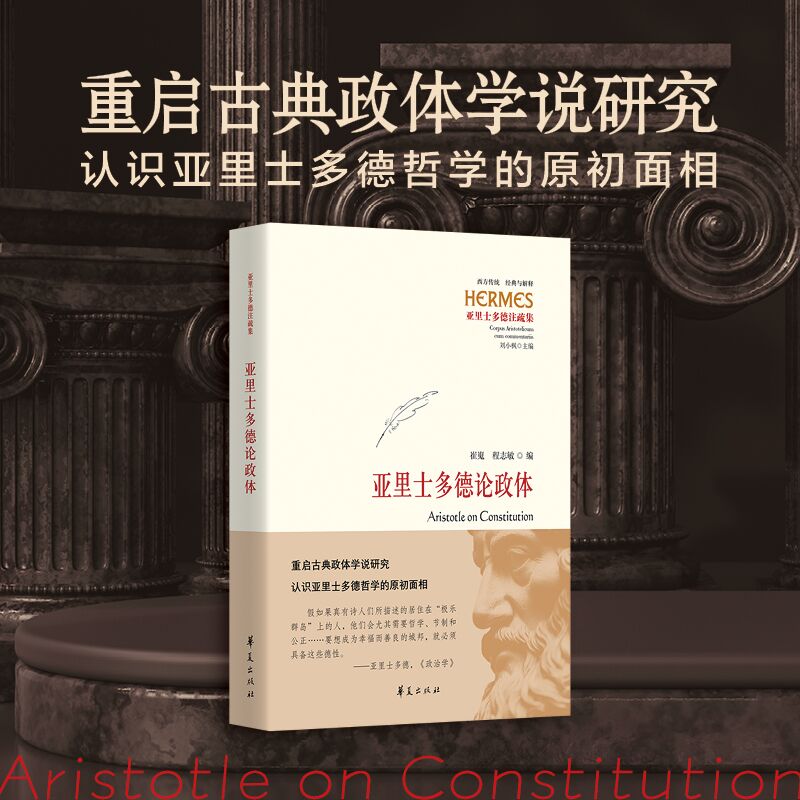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驳斥柏拉图 (摘自《亚里士多德论理想政体》,米勒(Fred D. Miller,JR)撰) 亚里士多德从多个方面批判了卡洛斯城邦(Callipolis)——即苏格拉底描述的“美好的城邦(beautiful city)”(《王制》卷七,527c)。 政体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辩驳了苏格拉底的假设: 整个城邦愈一致便愈好,但是,一个城邦一旦完全达到了这种程度的整齐划一便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倾向于整齐划一为度,那么家庭将变得比城邦更加一致,而个人又要变得比家庭更加一致,因为作为“一”来说,家庭比城邦为甚,个人比家庭为甚。所以,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性也不应当这样去做,因为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政治学》2.2.1261a16-22;亦参《王制》4.422d1-423b6,5.462a9-b2) 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希望卡洛斯城邦如同个人一般归一化。但亚里士多德反对其论点:城邦是许多人的组合,许多人又是不同的种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1261a22-b10),城邦的目标不在于归一化,而在于通过劳力的分工使得城邦能够自给自足(1261b10-15)。亚里士多德也不赞同柏拉图重复提到的观点——理想的城邦是“超越个人(super-individual)”或“超越组织(super-organism)”的(参波普尔[Popper])。 然而,柏拉图的支持者否认,柏拉图试图赋予这两个词极其精确完美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只是在用主观推测批判柏拉图的言论。 整个城邦政体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同样驳斥了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关于幸福的构想: 再次,他剥夺了武士的幸福,并说立法者应当为整个城邦谋幸福。但是,如果整个城邦的大多数,或所有人,或某些人没有享受到幸福,整个城邦就不可能有幸福可言。在这方面幸福与数目中的偶数原则不同,偶数只能存在于总数中,在总数的各部分中就不存在了。幸福并不是这样。如果武士们无幸福可言,那谁又会幸福呢?当然工匠或其他庶民也不会。有关苏格拉底所倡导的政体的种种疑难我们就举出这些例子,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大的疑难问题我们就不多说了。(《政治学》2.5.1264b15-24) 就苏格拉底提到的“我们的目的是看到城邦作为整体,享受极大的幸福”(《王制》4.419a1-421c6,亦参5.465e4-466a6),亚里士多德也做出了极概括性的论述。苏格拉底举出给塑像上彩的例子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令人敬佩的人,请你别认为我们必须把眼睛描绘得如此漂亮,以致它们不再像眼睛,其他部分也如此,相反,请你仔细观察我们是否加上了与各个部分相称的颜料,美化了整体。(《王制》卷4,420d1-5)。 但是,柏拉图的拥护者声称(包括弗拉斯托斯[Vlastos]和安纳斯[Annas]),苏格拉底仅仅表示,法律不能以牺牲某一群体的幸福为代价而为另一特定群体服务(参5.466a2-6,7.519e1-520a1)。 哲人王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柏拉图把哲人王视为理想政体的关键(5.473d3-5),而亚里士多德却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由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言论总结他对此的反对。在《王制》中,统治者亦是匠人,要求具备形式(Forms)的哲学知识——这种形式超越样式(patterns)或模式(models),以定义事物的本质,并为事物提供关于完美的客观标准。忽略这种形式的统治者如同失明的画家, 那些对每一存在的事物缺乏认识的人和瞎子难道有什么区别,他们在自己的灵魂中并没有清晰可见的模式,不能像画家那样看到最真实的物体,一贯能在那里得到参考,并且能以最大的精确度观察它,正因这样,他们不能在这里确立关于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高尚的标准,如果它们必须得到确立,即使确立了,他们也不能看守好它们。(6.484c7-d3) 善的形式(Forms of the Good)也很重要。 你们每一个人必须轮流下去和其余的那些人住到一起,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观察那些朦胧不清的东西。因为,一经习惯,你们就会远远比那里的人们看得更清楚,并且会知道那里的各种图像是什么、代表什么,因为你们看到过优秀的东西、正义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的真正面目。(7.520c) 苏格拉底认为理想城邦自身可能存在于这种形式的领域之中: 太空中也许屹立着一个典范,它为某个想看到它、看到它后又想让自己定居于此的人而存在。(9.592b) 亚里士多德可能对此无动于衷。按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形式的哲学知识,即使果真如此,也不会在任何
亚里士多德驳斥柏拉图 (摘自《亚里士多德论理想政体》,米勒(Fred D. Miller,JR)撰) 亚里士多德从多个方面批判了卡洛斯城邦(Callipolis)——即苏格拉底描述的“美好的城邦(beautiful city)”(《王制》卷七,527c)。 政体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辩驳了苏格拉底的假设: 整个城邦愈一致便愈好,但是,一个城邦一旦完全达到了这种程度的整齐划一便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倾向于整齐划一为度,那么家庭将变得比城邦更加一致,而个人又要变得比家庭更加一致,因为作为“一”来说,家庭比城邦为甚,个人比家庭为甚。所以,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性也不应当这样去做,因为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政治学》2.2.1261a16-22;亦参《王制》4.422d1-423b6,5.462a9-b2) 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希望卡洛斯城邦如同个人一般归一化。但亚里士多德反对其论点:城邦是许多人的组合,许多人又是不同的种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1261a22-b10),城邦的目标不在于归一化,而在于通过劳力的分工使得城邦能够自给自足(1261b10-15)。亚里士多德也不赞同柏拉图重复提到的观点——理想的城邦是“超越个人(super-individual)”或“超越组织(super-organism)”的(参波普尔[Popper])。 然而,柏拉图的支持者否认,柏拉图试图赋予这两个词极其精确完美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只是在用主观推测批判柏拉图的言论。 整个城邦政体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同样驳斥了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关于幸福的构想: 再次,他剥夺了武士的幸福,并说立法者应当为整个城邦谋幸福。但是,如果整个城邦的大多数,或所有人,或某些人没有享受到幸福,整个城邦就不可能有幸福可言。在这方面幸福与数目中的偶数原则不同,偶数只能存在于总数中,在总数的各部分中就不存在了。幸福并不是这样。如果武士们无幸福可言,那谁又会幸福呢?当然工匠或其他庶民也不会。有关苏格拉底所倡导的政体的种种疑难我们就举出这些例子,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大的疑难问题我们就不多说了。(《政治学》2.5.1264b15-24) 就苏格拉底提到的“我们的目的是看到城邦作为整体,享受极大的幸福”(《王制》4.419a1-421c6,亦参5.465e4-466a6),亚里士多德也做出了极概括性的论述。苏格拉底举出给塑像上彩的例子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令人敬佩的人,请你别认为我们必须把眼睛描绘得如此漂亮,以致它们不再像眼睛,其他部分也如此,相反,请你仔细观察我们是否加上了与各个部分相称的颜料,美化了整体。(《王制》卷4,420d1-5)。 但是,柏拉图的拥护者声称(包括弗拉斯托斯[Vlastos]和安纳斯[Annas]),苏格拉底仅仅表示,法律不能以牺牲某一群体的幸福为代价而为另一特定群体服务(参5.466a2-6,7.519e1-520a1)。 哲人王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柏拉图把哲人王视为理想政体的关键(5.473d3-5),而亚里士多德却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由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言论总结他对此的反对。在《王制》中,统治者亦是匠人,要求具备形式(Forms)的哲学知识——这种形式超越样式(patterns)或模式(models),以定义事物的本质,并为事物提供关于完美的客观标准。忽略这种形式的统治者如同失明的画家, 那些对每一存在的事物缺乏认识的人和瞎子难道有什么区别,他们在自己的灵魂中并没有清晰可见的模式,不能像画家那样看到最真实的物体,一贯能在那里得到参考,并且能以最大的精确度观察它,正因这样,他们不能在这里确立关于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高尚的标准,如果它们必须得到确立,即使确立了,他们也不能看守好它们。(6.484c7-d3) 善的形式(Forms of the Good)也很重要。 你们每一个人必须轮流下去和其余的那些人住到一起,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观察那些朦胧不清的东西。因为,一经习惯,你们就会远远比那里的人们看得更清楚,并且会知道那里的各种图像是什么、代表什么,因为你们看到过优秀的东西、正义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的真正面目。(7.520c) 苏格拉底认为理想城邦自身可能存在于这种形式的领域之中: 太空中也许屹立着一个典范,它为某个想看到它、看到它后又想让自己定居于此的人而存在。(9.592b) 亚里士多德可能对此无动于衷。按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形式的哲学知识,即使果真如此,也不会在任何领域产生什么专门知识: 所有的科学都在追求某种善,并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充实,而把善自身摆在一边。由于它的帮助是如此微不足道,也就无怪技术家们对它全然无知,而不去寻求善自身了。谁也说不清,知道了这个善自身,对一位织工,对一个木匠的技术有什么帮助;或者一旦树立了善的理念,一位将军将如何成为更好的将军,一个医生如何成为更好的医生。(《尼各马可伦理学》1.6.1096b31-1097a11) 相似的,善的形式的知识过于抽象,难以在伦理学或政治学中提供引导。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智慧(sophia)与实践智慧(phronêsis),前者表达于哲人们关于永恒现实的展示中,而后者表述于关于某事的行为对于人类而言是好是坏的思索中。哲学属于前者而非后者;政治科学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尽管理想的城邦需要明智的统治者,但这些统治者不必成为哲人。 亚里士多德对《王制》的批判引发了不同的反响。有些人认为亚里士多德见解深刻,卓尔不群,而有些人觉得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刻薄无情,有时直接造成误解。我们应当批判性地、仔细地阅读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反对(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立场,艾尔文和桑德斯[Saunders]持反对态度,梅休[Mayhew]与斯塔雷[Stalley]持支持态度)。 亚里士多德驳斥柏拉图 (摘自《亚里士多德论理想政体》,米勒(Fred D. Miller,JR)撰) 亚里士多德从多个方面批判了卡洛斯城邦(Callipolis)——即苏格拉底描述的“美好的城邦(beautiful city)”(《王制》卷七,527c)。 政体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辩驳了苏格拉底的假设: 整个城邦愈一致便愈好,但是,一个城邦一旦完全达到了这种程度的整齐划一便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倾向于整齐划一为度,那么家庭将变得比城邦更加一致,而个人又要变得比家庭更加一致,因为作为“一”来说,家庭比城邦为甚,个人比家庭为甚。所以,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性也不应当这样去做,因为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政治学》2.2.1261a16-22;亦参《王制》4.422d1-423b6,5.462a9-b2) 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希望卡洛斯城邦如同个人一般归一化。但亚里士多德反对其论点:城邦是许多人的组合,许多人又是不同的种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1261a22-b10),城邦的目标不在于归一化,而在于通过劳力的分工使得城邦能够自给自足(1261b10-15)。亚里士多德也不赞同柏拉图重复提到的观点——理想的城邦是“超越个人(super-individual)”或“超越组织(super-organism)”的(参波普尔[Popper])。 然而,柏拉图的支持者否认,柏拉图试图赋予这两个词极其精确完美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只是在用主观推测批判柏拉图的言论。 整个城邦政体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同样驳斥了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关于幸福的构想: 再次,他剥夺了武士的幸福,并说立法者应当为整个城邦谋幸福。但是,如果整个城邦的大多数,或所有人,或某些人没有享受到幸福,整个城邦就不可能有幸福可言。在这方面幸福与数目中的偶数原则不同,偶数只能存在于总数中,在总数的各部分中就不存在了。幸福并不是这样。如果武士们无幸福可言,那谁又会幸福呢?当然工匠或其他庶民也不会。有关苏格拉底所倡导的政体的种种疑难我们就举出这些例子,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大的疑难问题我们就不多说了。(《政治学》2.5.1264b15-24) 就苏格拉底提到的“我们的目的是看到城邦作为整体,享受极大的幸福”(《王制》4.419a1-421c6,亦参5.465e4-466a6),亚里士多德也做出了极概括性的论述。苏格拉底举出给塑像上彩的例子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令人敬佩的人,请你别认为我们必须把眼睛描绘得如此漂亮,以致它们不再像眼睛,其他部分也如此,相反,请你仔细观察我们是否加上了与各个部分相称的颜料,美化了整体。(《王制》卷4,420d1-5)。 但是,柏拉图的拥护者声称(包括弗拉斯托斯[Vlastos]和安纳斯[Annas]),苏格拉底仅仅表示,法律不能以牺牲某一群体的幸福为代价而为另一特定群体服务(参5.466a2-6,7.519e1-520a1)。 哲人王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柏拉图把哲人王视为理想政体的关键(5.473d3-5),而亚里士多德却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由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言论总结他对此的反对。在《王制》中,统治者亦是匠人,要求具备形式(Forms)的哲学知识——这种形式超越样式(patterns)或模式(models),以定义事物的本质,并为事物提供关于完美的客观标准。忽略这种形式的统治者如同失明的画家, 那些对每一存在的事物缺乏认识的人和瞎子难道有什么区别,他们在自己的灵魂中并没有清晰可见的模式,不能像画家那样看到最真实的物体,一贯能在那里得到参考,并且能以最大的精确度观察它,正因这样,他们不能在这里确立关于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高尚的标准,如果它们必须得到确立,即使确立了,他们也不能看守好它们。(6.484c7-d3) 善的形式(Forms of the Good)也很重要。 你们每一个人必须轮流下去和其余的那些人住到一起,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观察那些朦胧不清的东西。因为,一经习惯,你们就会远远比那里的人们看得更清楚,并且会知道那里的各种图像是什么、代表什么,因为你们看到过优秀的东西、正义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的真正面目。(7.520c) 苏格拉底认为理想城邦自身可能存在于这种形式的领域之中: 太空中也许屹立着一个典范,它为某个想看到它、看到它后又想让自己定居于此的人而存在。(9.592b) 亚里士多德可能对此无动于衷。按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形式的哲学知识,即使果真如此,也不会在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