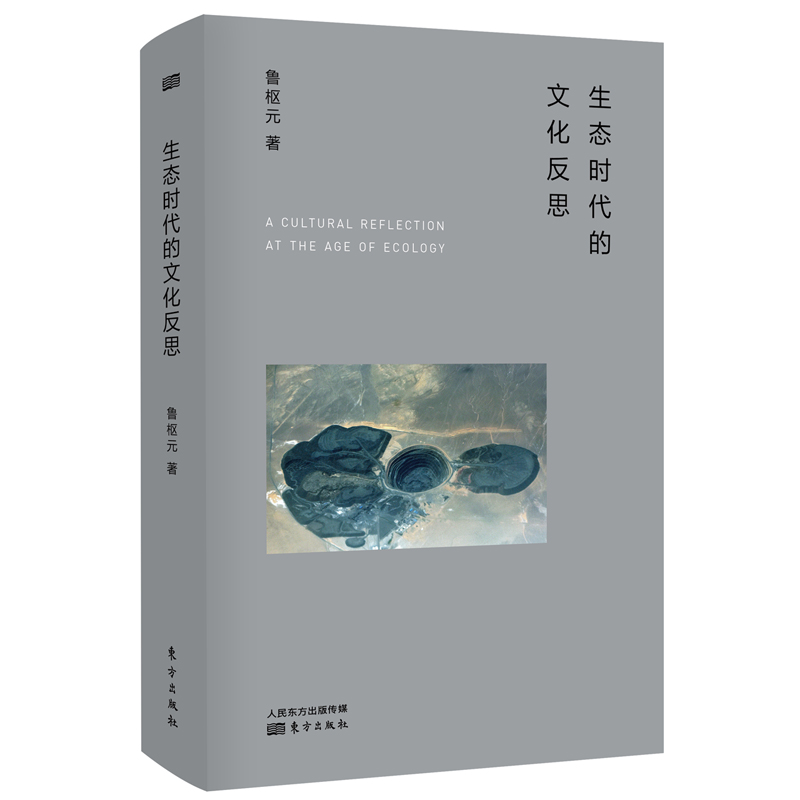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
原售价: 79.00
折扣价: 51.40
折扣购买: 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
ISBN: 9787520701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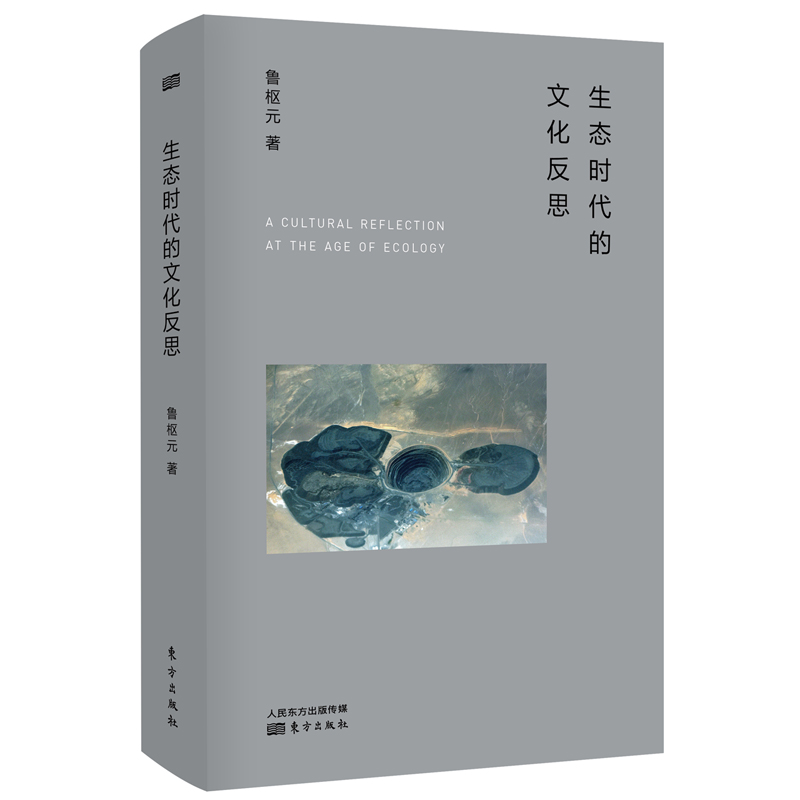
鲁枢元(1946— ),人文学者,1988年国务院人事部命名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现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长期关注生态问题,致力于生态文化建设。出版有《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陶渊明的幽灵》及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A Case Study of Tao Yuanming等。曾荣获国家图书奖、鲁迅文学奖及柯布共同福祉奖。著名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认为“鲁枢元是中国生态批评里程碑式的人物”。柯布共同福祉奖授奖词中称其为“中国生态文艺学及精神生态研究领域的奠基人”。
生态学(Ecology)原本是一门学科的名称、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正如牛顿的物理学在300 年前开启了一个时代——工业时代;生态学如今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系统与主导观念,这个“新时代”就是“生态时代”。 生态学原本属于自然科学,自从美国女作家蕾切尔? 卡逊(RachelCarson,1907—1964) 的《寂静的春天》问世,生态学便深深地契入现代人类与环境、自然、社会、自我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从而启动了这一学科的人文转向。生态问题开始迅速蔓延到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宗教、伦理、审美、教育等各个领域,成为一个涉及人类历史与未来的精神文化问题。 上个世纪80 年代,我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时多借助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原理,这使我较多地关注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关注现代人的生存方式、行为模式及其与环境的矛盾冲突。我时时忧虑,多年来由于重经济轻文化、重物质轻精神、重技术轻感情,人类的生态境况呈现多方病变,遂导致文化的滑坡、情感的冷漠和精神的颓败。有人说这是社会改革必然承受的痛苦和必须经过的阶段,我不完全相信。我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在价值导向上出了偏差,这已经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严重危机。三十年过去,事实证明我的这些担忧并没有过时,甚至危机还在日益加剧。 就在这部书稿编纂结集之际,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世界肆虐蔓延。一时间飞机停飞,火车停运,工厂停产,高速公路关闭,大中小学暂停开学,封城、封村、封户,娱乐、饮食、旅游等行业接近于停摆,基本生活物资断供,失业人口剧增,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整个国民生活停止了正常运转。人类费尽全力营造的现代社会系统在小小的病毒面前竟如此脆弱。 在这种小小病毒的侵袭下,让现代人颇为自豪的“全球化”显得不堪一击:已经打开的边境被重新关闭、跨国公司产业链纷纷断裂、世界贸易大大削减、股市熔断、国际货币组织一片惊恐、诸多国际联合组织支离涣散。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一时间还激起不同国家之间的争端、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攻讦、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撕裂。 就是这样一些在一般显微镜下都瞧不见的病毒,短短数月内“搅得周天寒彻”,让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蒙受重创,给人类带来的损失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 看来,现代人对“全球化”的热烈向往,是应该转为对“人类纪”的冷静思考了! 人类曾在地球上几乎杀尽了狮子、老虎、大象、蟒蛇,却败给了最最渺小的生物——病毒,或许这就是“自然的报复”?新冠病毒并非偶然,不久前曾经接连发生过疯牛病、禽流感、埃博拉病毒、SARS,那么之后呢? 有专家提出,为了根治此类传染病,要将这些病毒的寄主蝙蝠、刺猬、穿山甲、土拨鼠施以“生态灭杀”。蝙蝠、穿山甲虽然相貌丑陋、惹人生厌,但从生态学的基本常识看,它们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但它们,即使比它们更卑微的细菌、微生物乃至病毒,也都是地球生物圈中合理的存在。人类无权立法将其“灭杀”!不管人类是否情愿,人类必须学会与野生动物、细菌、病毒长期共存。声言“灭杀”,多年来人类对其他物种的“灭杀”难道还少吗?这样灭杀下去,最终灭掉的只能是人类自己。现代人需要学会“克己复礼”,与万物和谐共处。 目前,人们把解救这场灾难的努力投放在社会管理与科技攻坚上,显得有些临时抱佛脚。从根源看,从长远看,此类生态灾难还与现代人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生存理念、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生态问题必然牵涉到伦理、信仰、教育、哲学等问题,说到底或许还是一个文化问题。 疫情期间,白天的天空比起以往反倒更蓝,夜晚的星星更璀璨,空气显得更新鲜,据说连威尼斯的海水也变得更清澈。偶尔看到有民众在网上发表议论:疫情期成了地球的休闲日,大自然不再超负荷运转,野生动物露出了少见的笑脸,“新冠”成了环境保护的严苛教员!我顿时感到,民众对于生态观念的接受比起我们的某些专家、学者要更容易些。 二十多年来,在“生态文化”研究领域,我写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一些著作,同时也在不同场合讲了一些话,与学界友人有过一些交流,如今择其要汇集成书。 我不认为我所讲的都是正确的,但我说过的话首先是我自己相信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自然也希望我在不同时期说过的这些话能够得到读者的共鸣与回应,自然也包括对我的指教与批评。 过去300年里,理性之光使人类陷入“整体的无明状态”,启蒙的结果竟是弥塞天地的“启蒙之蒙”。现代人的生存空间日益困窘,时代在日渐富裕的同时也在日趋贫乏。 精神与生态,或许是现代人死里逃生的一个出口。只有“前现代的思想遗存”与“后现代的思想萌芽”联手,跳脱“二元对立”与“人类中心”的思维藩篱,颠覆“发展迷思”与“资本逻辑”的社会模式,用一种有机论的眼光看待自然、世界和人的关系,人类社会或许才能进入怀特海哲学中那片充满灵光的精神领域、充满绿意的生态领域。 作者关于生态社会的种种构想,相对于强大的现实政治经济来说,或许只是一个永远在地平线上隐约呈现的乌托邦。但作者始终相信:“与其在痛苦中终结,不如在无望中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