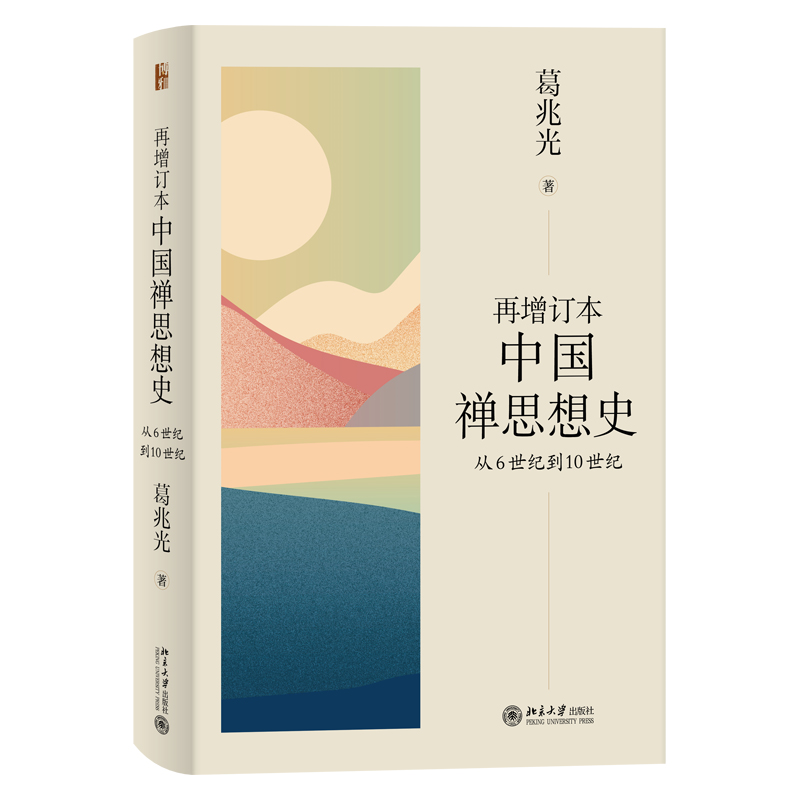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87.10
折扣购买: 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精)
ISBN: 9787301327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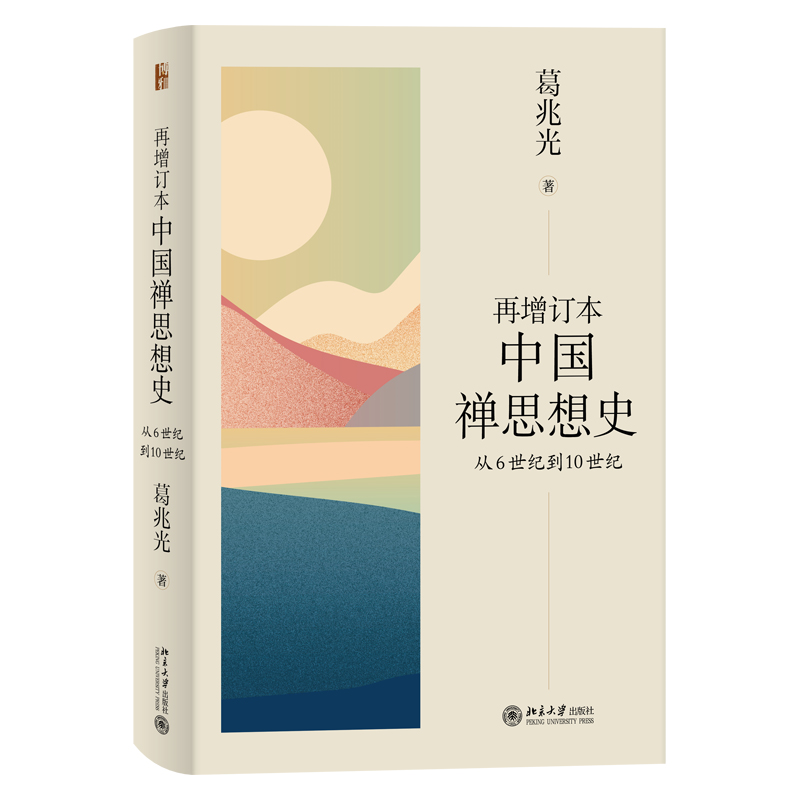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1950年生于上海,198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何为中国:疆域、族群、文化与历史》等。
四 当代新方法潮流中:胡适的禅宗史研究方法过时了吗? 法裔美国学者佛尔在《正统性的意欲》中,对过去相对研究不是很充分、并且评价相对较低的北宗禅,进行了一个新的研究。按照佛尔的说法,过去胡适接受了宗密的观点,站在南宗神会一边,以顿、渐分别南北,虽然胡适批判了后世各种禅宗文献的“攀龙附凤”,但他把南宗、北宗“谁是正统”的问题,看成是历史的真实内容。而佛尔则不同,他把“谁是正统”这个问题,看成是禅门各个系统的“正统性意欲”,就是追求政治承认的运动,认为这一本来暧昧甚至叛逆的运动,成为后来三个世纪禅宗主导的和支配的意识,形成了禅宗的革命历史。换句话说,就是禅门各种派别各种文献,都在这种“正统性意欲”的支配下,在建构禅宗系谱。 他把这个追求正统性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一)6世纪,禅师在北方中国宣称达摩为祖师,试图在中国北方立足,但是不很成功;(二)7世纪中叶,东山禅门在南方崛起,但未曾与北方禅门建立联系;(三)7世纪末,神秀逐渐接近中央政府;(四)神秀的成功与神会的崛起,在安史之乱中成功成为正统;(五)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的衰落和新禅宗宗派在各地的兴起,正统性转向马祖道一。对这个禅宗史系谱,我大体上可以同意。不过我的问题是,根据各种西方新理论重新建构的这个系谱,究竟与过去根据敦煌文书等新材料,由胡适以及其他人重新叙述的禅宗史有什么区别?似乎没有。佛尔在书中,征引了包括福柯、利科、海德格尔等等理论,也采用了很多新颖的术语,可是,是否禅宗这样的历史研究,就一定需要结构主义、诠释学、知识考古及系谱学等等那么复杂和时尚的理论?这些都值得深究。 另一个近年去世的美国学者马克瑞(John McRae,1947—2011),在佛尔的法文本博士论文之后、英文本著作出版之前,也出版过《北宗与早期禅佛教的形成》(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1986)。这部书比起佛尔的著作来,似乎比较偏向历史学与文献学的风格。有趣的是,他们两位其实都受到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的影响,而柳田圣山则受到胡适的影响。但是,西方知识背景和欧美学术传统中的佛尔和马克瑞,似乎都不太像柳田圣山那样,恪守历史学和文献学的传统边界,对目前可以看到的初期文献如敦煌文献保持着尊重和敬畏,并以这些文献为判断标尺。马克瑞就批评说,“来自敦煌写本的证据,大都只被用来在原有的传统图像上加绘一些更美的特点,只是在前述的系谱模式上加添知识上引人瞩目的细节”。如果说马克瑞的《北宗》一书还没有太多的理论表述,那么,后来出版的Seeing Through Zen: Encounter,Transformation 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里面,就比较明显地借用后现代理论,并且把历史与文献放置在理论视野之下重新考察。这部书的一开始,他就提出了所谓的“马克瑞禅研究四原则”(McRae’s Rules of Zen Studies),这里固然有他的敏锐,但也有其过度依赖“后”学而过分之处。在这四条原则中,第一条是“它(在历史上)不是事实,因此它更重要”(it is not true, and therefore it’s more important);第二条是“禅宗谱系的谬误程度,正如它的确实程度”(lineage assertions are as wrong as they are strong);第三条是“清晰则意味着不精确”(precision implies inaccuracy),据说越是有明确的时间和人物,它就越可疑;第四条是“浪漫主义孕育讽喻”(romanticism breeds cynicism),据说,说故事的人不可避免要创造英雄和坏蛋,禅史也同样不可避免,于是历史将在想象中隐匿不见。 也许,这一理论太过“后现代”。这些原本只是禅宗历史上特殊的现象,在马克瑞的笔下被放大普遍化了,当然也要承认,我们如果回到最原始的文献中去看,唐代禅宗史中确实有这种“攀龙附凤”的情况。不妨举一个例子。以我个人的浅见,近几十年中古禅宗史研究最重大的收获之一,也是海外学者对于中古禅宗史研究的重要成绩之一,就是法裔美国学者佛尔和日本学者伊吹敦,通过一块碑文即《侯莫陈大师寿塔铭》,证明了法藏敦煌卷子P.3922、P.2799的《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是智达禅师(也就是侯莫陈琰,他是北宗禅师老安和神秀的学生)在先天元年(712)撰写的。联系到另外一份敦煌卷子P.2162,即沙门大照、居士慧光集释的《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这篇《论》原来被误认为是神会南宗系统的,现在被证明,其实它们都是北宗的。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归属于北宗的人们,居然也都讲“顿悟”,甚至比号称专讲“顿悟”的南宗神会要早得多。这样一来,禅宗史就摆脱了传统的“南顿北渐”的说法,也许,还是神会剽窃了北宗的思想,反而在南北之争中倒打一耙,使得后来形成了“南顿北渐”的固定看法。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可是需要指出,这发现不是得益于后现代理论和方法,而恰恰是传统历史学与文献学方法的成果。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胡适当年不用后现代的理论和方法,其实也达到了这样的认识,为什么今天的禅宗研究一定要弄得这么玄虚呢?1993年,福克(T. Griffith Foulk)撰写了《宋代禅宗:神话、仪礼以及僧侣实践》,这篇被认为是“过去的十五年关于中国禅宗史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据说它的意义是指出“我们对唐代禅宗史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代文献的产物”,但是,这不是胡适早就指出的现象吗?从胡适以来,学者们已经知道所谓唐代禅宗史基本上都是以禅宗自己书写的灯录为基本线索的,这些宋代以后撰述的传灯录只是后人对禅宗史的叙述,这在中国禅宗史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共识或常识。因此,胡适才会提倡,如果能够更多地依赖“教外”资料比如文集、碑刻和其他佛教徒或非佛教徒的记述,也许就可以看到,各种灯录和在灯录之后的各种研究著作中,究竟禅史被增添了多少新的颜色,又羼入了多少代人的观念和心情。 中国的禅宗史研究者理应向胡适致敬。国际禅宗研究界也许都会察觉,在禅宗研究领域中,各国学者的取向与风格有相当大的差异。在中国学界,类似西田几多郎似的禅宗哲学分析并不很普遍,类似铃木大拙那样从信仰与心理角度研究禅宗的也并不发达,对于禅宗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分析,恐怕也还没有太多关注,倒是历史学与文献学结合检讨禅宗历史的路数,始终是中国学界的风气与长处,而不断从石刻碑文及各种传世文献中发现禅宗历史,把佛教史放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史背景之中讨论,更是中国学者擅长的路子。 这也许正是拜胡适(也包括陈寅恪、陈垣)之赐。 结语 在胡适的延长线上继续开拓 最后,我要越出“中古”的范围,大胆地讨论一下,在敦煌文书逐渐被发掘殆尽的情况下,我们在禅宗史研究上是否还可以获得新进展?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禅宗史研究者继续努力发掘呢?我想针对中国学界说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这里不限于“中古时期”,也不限于“中国禅宗”。 首先,对于禅宗在亚洲更广大区域的传播、变异和更新,非常值得研究。这一点,佛尔在《正统性的意欲》中已经提到,他说应当“打破流传至今的中日(Sino-Japanese)视角所带来的限制”,他说,要注意禅宗曾经在唐代作为一种思想(我觉得同样重要的是,禅宗作为一种生活艺术和文学趣味),曾经传播到了中原和日本之外,比如中亚、吐蕃、越南、朝鲜,所以,应当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区域中“恢复它的原貌”。虽然,所谓“恢复原貌”有一点儿违背了他这本书“后现代”的立场,不过,我们确实应当承认这个建议有道理,关注禅宗的传播、影响、适应以及变化,并且更注意这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原因。像8世纪末北宗禅宗与印度佛教在西藏的争论,像禅宗文献在西域的流传,像中国禅宗在朝鲜衍生支派,像日本禅僧对中国禅的重新认识,像明清之际中国禅宗在中国西南与越南的流传等等。这方面,戴密微的著作《吐蕃僧诤记》就值得学习。 其次,禅宗在各国政治、社会、文化上的不同影响,以及它在各国现代转型过程的不同反应和不同命运,其实是很值得讨论的。以中国和日本的历史看,我们看到,后来的中国禅宗,虽然经过宋代的大辉煌,但是它的世俗化(从“佛法”到“道”,转向老庄化,不遵守戒律的自然主义,自由心证下的修行)很厉害,自我瓦解倾向也很厉害。所以,它一方面成为士大夫文人的生活情趣,一方面在世俗社会只能靠“禅净合流”以拯救自身存在,即使明代出现几大高僧,似乎重新崛起,但仍然昙花一现,一直到清代它最终衰败。这个历史和日本很不一样,日本僧侣的独立化、寺院化与仪式化,经历五山、室町、德川时代的昌盛,到了近代仍然可以延续。它一方面通过介入世俗生活深入民众,一方面依靠与王权结合成为政治性很强的组织,它不仅可以与武士道、葬仪结合,禅僧也可以充当将军的幕宾和信使,所以即使后来遭到现代性的冲击,禅宗仍然可以华丽转身,与现代社会结合。后来出现很多像铃木大拙、西田几多郎、久松真一这样的学者,当然也出现深刻介入军国主义的宗教现象,更出现宗教的现代大学和研究所,这与中国大不相同。所以,这些现象很值得比较研究,也许,这就是把禅放在“现代性”中重新思考的研究方式。 再次,我希望现代学者研究禅宗史,不必跟着禅宗自己的表述,被卷入自然主义的生活情趣、高蹈虚空的体验启悟、玄之又玄的语言表达,也不一定要把禅宗放在所谓哲学那种抽象的或逻辑的框架里面,分析(发挥)出好多并不是禅宗的哲理。这不是现代的学术研究方式。反而不如去考察一下,禅宗除了这些虚玄的思想和义理之外,还有没有具体的生活的制度和样式,在寺院、朝廷(或官府)、社会(或民间)是怎样存在的。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百丈清规》以下,有一些关于禅僧生活的规定,好像和他们说的那些高超玄妙的东西不同。如果你看《禅林象器笺》就会知道,禅宗寺院里面有各种器物,他们还是要维持一个宗教团体的有序生活。所以,研究禅宗不要只是记得超越、高明、玄虚的义理,也要研究形式的、具体的、世俗的生活。 最后,我要引述几句胡适关于禅宗史研究的话,来结束这篇论文。胡适曾经评论日本禅学者和自己的区别,说“他们是佛教徒,而我只是史家”;他又提到,“研究佛学史的,与真个研究佛法的,地位不同,故方法亦异”。他在1952年批评铃木大拙谈禅,一不讲历史,二不求理解,他认为,研究禅宗“第一要从历史入手,指出禅是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些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以历史的角度揭示禅的发展,由思想的脉络解读禅的流变,由文化与影响评估禅的意义。——关于中国禅史、思想史的经典著作,大幅度修订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