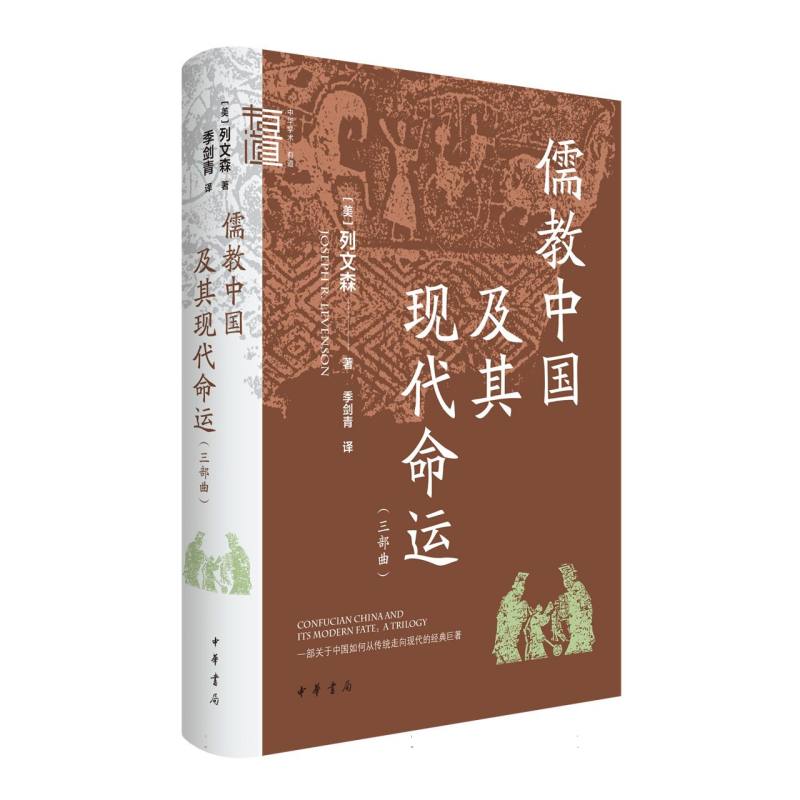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2.80
折扣购买: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
ISBN: 9787101162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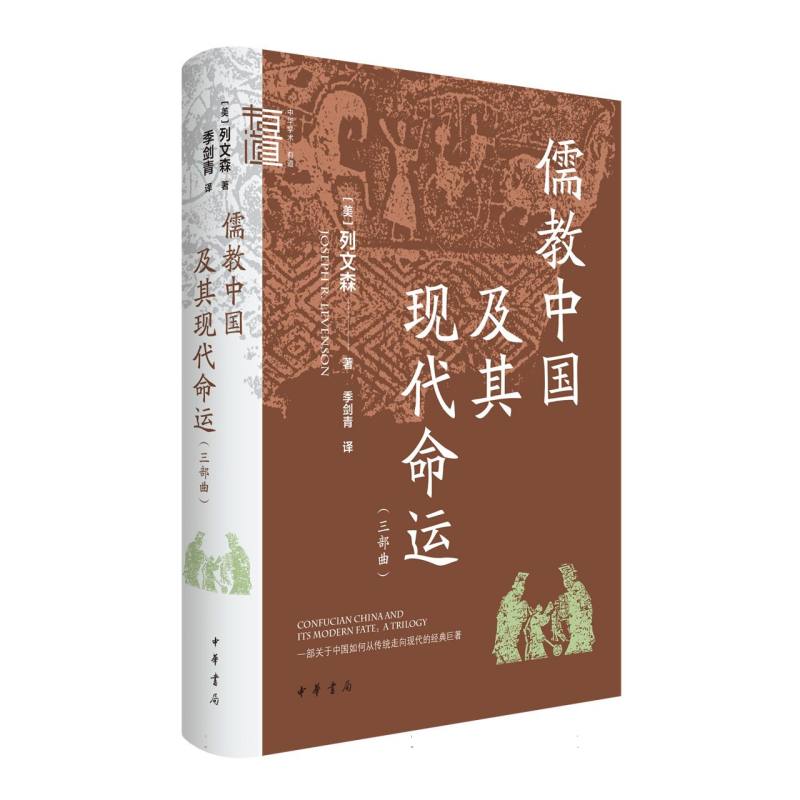
第二卷第九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儒家文化的一个突出的 、无处不在的价值就是它的反职业主义。儒家个人教养 的理想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业余主义,而儒家教育在反职 业的古典主义方面,也许在世界上享有最高的地位,这 种教育相应地发展出一种帝国的官僚体系,在这个体系 内,人际关系远比抽象的工作网络重要(就像在一般的 儒家社会中,人际关系远比法律关系重要一样)。在这 些方面——这一点绝非偶然——它不同于现代工业化的 西方的官僚制,而且至少在观念上,也不同于中华民国 的官僚制。把清代的幕僚或幕友与民国的科长秘书做一 番比较,也许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清代和民国的所 有这些头衔,都是用于行政首脑的私人秘书和顾问。他 们的角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与各自长官的 关系以及他们的法律地位却有很大的差别:民国的秘书 顾问是正式的官吏;而在清朝,这一类的人物则属于官 员的朋友,职能上不是部属,或者说不受公家的俸禄。 就像张謇——一位有现代思想的实业家(后来成了袁世 凯的支持者,尽管他是出于老交情而非复古心态,并且 是怀着不安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以讽刺的口吻评论 的那样,从省级到地方,清代所有的官员都能自己任命 助手,就像汉代和唐代的“幕职”那样,任用熟人来进 行治理。 民国对“官”的强调以及对“臣”的排斥,标志着 它对一个职业化的、反文人的世界的明确的现代追求, 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工业和进步的观念(所有这些都 具有非个人的因而也是非儒家的含义)都被要求放置到 首位来考虑。这不仅是优先选择哪一项的问题。一段时 间以来,这个世界确实已经在改变和接管中国,不仅制 造了反传统主义者,也改变了传统主义者。“臣”作为 文明的主人和产物,是有很高教养的非专业化的自由人 ,他把“工作”,把政府的“事务”(当然,这些即便 在旧制度中也是必要的,但却多少有些让人讨厌,它们 更像是需要付出的代价,而非通过声望而赢得的奖赏) 贬低到“官”的范畴,但这样的“臣”是那无法挽回的 过去的人物了。从“官”和“臣”的帝国到“官”的民 国,意味着真正的改变。 帝国在“革命”中解体了。“革命”本身失去了它 的传统上的字面意义,被比作现代的革命,它解放了人 们的心灵,使他们意识到中国文明的内容在发生变化。 中国的帝国形式变成了不合时宜的事物。“臣”作为其 中之一,其意义也发生了像“革命”那样的变化,而正 是“革命”毁掉了真正属于它的世界。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臣”不仅与“官 ”并举,而且在清朝也与“奴”并举。“奴”是用来指 满族官员的词,它把他们和满族君主的清朝联系在一起 ,而中国皇帝的清朝则把儒家“臣”的身份留给了汉族 的官员,这种身份代表了大臣与君主之间的那种经典意 义上的高贵关系。然而,革命党的共和主义却扩大了“ 奴”这个词的应用范围,并且由此也就标志了“臣”的 世界的消灭。教条主义的共和主义者剥夺了“奴”一词 字面上的专门含义(这一含义一直是用在满族官员身上 的,他们在法律的意义上是“奴”,尽管他们用这个词 似乎只是出于礼仪),使得它在比喻的意义上能够用来 表示九五之尊的所有臣民。正如民国的部长伍廷芳在 1912年发给蒙古王公的一封安抚性电文中所说的,所有 人——汉、满、蒙、回、藏——在清朝统治下都经受了 奴隶之苦,而在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内,所有人都是兄弟 。于是,站在共和主义者的立场上来看,为“臣”就不 是把自己和奴隶区分开来,而是做奴隶。因为没有哪个 “臣”是没有“王”或“君”的,没有哪个儒家士绅置 身于王权之外——至少在理念上是如此,无论在现实情 况下这种王权与儒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多么紧张。( 儒者本就需要帝国,即便他们憎恶秦始皇。)作为天命 之更换的“革命”原本是要在一个继续存在下去的帝国 官僚体制中取消“奴”(满族官员)而保留“臣”(汉 族官员)的地位。但是现代革命意义上的“革命”—— 它不只是在形式上反对帝制——回过来头来把“臣”和 “奴”混为一谈,把它们全都取消了,仅此就宣告了帝 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