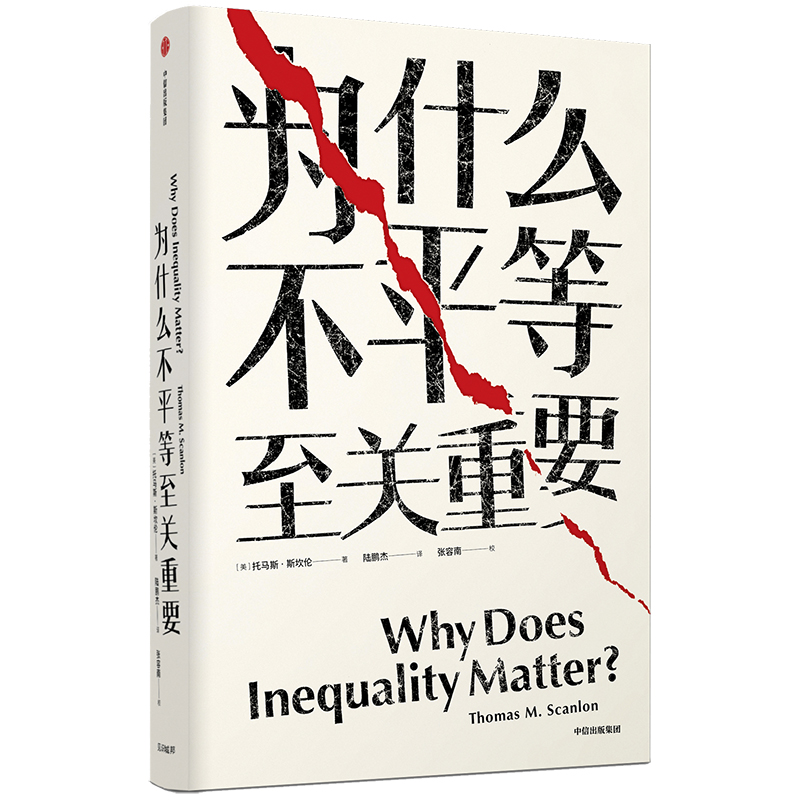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0.80
折扣购买: 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精)
ISBN: 9787521703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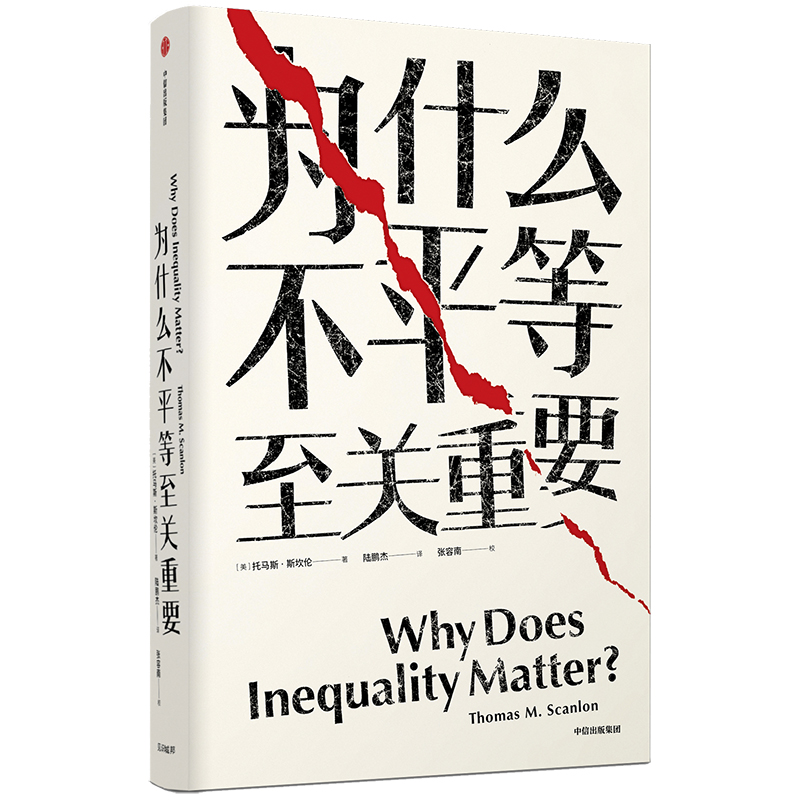
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M.Scanlon,1940— ) **哲学家,哈佛大学阿尔弗德自然**讲座教授(荣休),专*伦理学与政治哲学。1940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84年任教于哈佛大学。他拓展了卢梭、康德与罗尔斯的契约理论;也是继罗尔斯之后,当代道德契约主义代表人物。曾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斯坎伦与托马斯·内格尔一起创办了享誉**的哲学刊物《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and Pu**ic Affairs),并担任该刊的副主编,现任该刊顾问。 陆鹏杰(译者) 广东潮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分析进路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学。
序言 本书是我的尤希罗讲座(Uehiro Lectures)的扩展修订版,我曾于2013 年12 月在牛津担任过该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我要感谢朱利安·萨伏列斯库(Julian S**ulescu)和尤希罗基金会邀请我发表演讲,并感谢我当时的评论人—约翰·布鲁姆(John Broome)、大卫·米勒(D**idMiller)和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给出了深刻的评论。 呈现在这里的想法,*早可以追溯到我1996 年的林德利讲座(Lindley Lecture)—“对不平等的反驳的多样性”。那次讲座的内容后来发展成了一篇以《平等何时重要?》作为题目的论文,并且我把那篇变得越来越长的论文展示给了*多的听众,多到我无法把他们列举出来。我从那些场合中收到了许多评论和建议,它们都让我*益匪浅。尤希罗讲座的邀请提供了一种***欢迎的激励,它促使我将那篇未完成的论文扩展成三次演讲,而那些演讲的内容现在又被扩展成十个章节。 在这个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许多人给了我宝贵的帮助。以下诸君为我*稿中的某些章节,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整本书的*稿,提供了有益的评论: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约瑟夫·费希金(Joseph Fishkin)、塞缪尔·弗里曼(Samuel Freeman)、尼科·克洛德尼(Niko Kolodny)、马丁·奥尼尔(Martin O’ Neill)、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汤米·谢尔比(Tommie Shelby)、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曼纽尔·瓦尔加斯(Manuel Vargas)和保罗·威特曼(Paul Weithman)。此外,我收到的另一些犀利而富有启发的评论,则来自2016年春季学期我的政治哲学研讨会的参与者,尤其是弗朗西斯·卡姆(Frances Kamm)和杰德·卢因森(Jed Lewinsohn)。我衷心感谢他们。拥有如此慷慨大方且让人*益的朋友和同事,真是太美妙了。我也要感谢理查德·德·费利皮(Richard de Filippi)跟我讨论了人们在医疗服务的获取途径和健康状况上的不平等,并感谢诺尔·多明格斯(Noel Dominguez)为我提供了研究上的辅助。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妻子露西(Lucy)的支持。此外,在吃早餐和晚餐的时候,我曾反复尝试向她解释为什么我觉得不平等是一个如此难以著述的议题,我还要感谢她对我做出了深思熟虑且富有耐心的回应。 第九章 收入不平等 近几十年来,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已经大大加剧。2014年,美国收入总额(来自薪酬、利息红利和销售利润)的21.2%流向了收入处于前1%的人,而收入总额的4.9%则流向了前0.01%的人。这是不平等的一种显著的加剧。此外,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1979 年至2014 年之间,前1%的人的税前收入增长了174.5%,而后20%的人的税前收入仅仅增长了39.7%。(在这些情况下,收入包含了诸如福利金之类的**转移支付。)税后收入的增长差异甚至*加尖锐:前1%的人的税后收入增长了200.2%,而后20%的人的税后收入只增长了48.2%。(收入处于后21%和后80%之间的人的增长率只有40%。)在这一时期的*后(即2014年),前0.1%的人的平均年收入(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为6 087 113 美元,总体上是前1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20倍。 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反映出许多不同的现象,包括:**,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皮凯蒂称之为“**管理者”)的薪酬在增加;第二,金融领域的盈利能力在上升和增长;第三,国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资本回报(returns to capital)的形式。 关于**个现象,我在**章中提到了这些事实:1965年,在美国*大的350 家公司之中,高管的平均薪酬是其员工的平均薪酬的20倍。这个比例“在2000年达到了376∶1的高峰”。2014年,这个比例是303∶1,“ 高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的任何时期”。此外,“从1978年到2014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高管的)薪酬增长了997%,几乎是股市增长的两倍,远远高于同期普通员工的年薪的缓慢增长,因为后者只增长了10.5%”。这种程度的不平等看起来显然会令人感到不安。问题在于:为什么它应当令人感到不安,以及这是否可以用我在前面几章讨论过的那些反驳来加以解释。 首先考虑一下那些基于不平等的后果而对不平等所提出的反驳。在我看来,上述的不平等之所以应当*到反对,并不在于它会造成那些应被反对的地位伤害。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当下美国的穷人确实遭到了这些伤害,即遭到慈继伟所说的“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但是,这看起来并不是由**富豪的高收入造成的,也不是由他们和穷人的收入差距导致的。富人确实过得和我们其他人(尤其是极其贫困的人)**不一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设定的标准并不会使得我们有理由感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相对这个标准而言是有缺陷的。穷人遭*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所参照的标准是由“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设定的,而不是由**富豪的生活方式设定的。因此,这种不平等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会产生某些应被反对的地位差异。 1.银行劫匪启发哲学家。长期执教哈佛大学的哲学家,从银行劫匪口中看破不平等的起源。所谓的多元社会,不止意味着开放与共融,还带来了不平等的*多模式。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重量级学者、牛津大学公共政策系教授乔纳森·沃尔夫**。 斯坎伦从银行劫匪威利·萨顿的名言“因为钱在那儿”开始,梳理了种族、贫富、意识形态、名声地位等人与人之间各式各样的不平等。不平等针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且*益多元化。在多元社会,解决不平等*加不能用“均贫富”一刀切的方法。由于不平等的复杂性和体系化,**不平等和一个**内部不平等的趋势难以遏制。 2.穷人永远是穷人。不平等的社会机制与设计,让穷人陷入***困境。 不平等在当代社会是多元的。对穷人来说,这种多元的不平等却是致命的。社会机制与层级制的设计让穷人处于人际关系网的底端,不论是种族问题、贫富差距、教育不公平、社会地位与体面,穷人几乎占据了所有这些难题的*害一方。同时,穷人因为医疗困境、收入困境,也没有条件享*一般程度的自由。由此可见,平等与自由从来不对立,斯坎伦也借此解开了平等与自由截然对立的哲学迷思,现实地看待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3.“机会平等”太虚伪。机会平等人人都高喊“机会平等”,斯坎伦却要撕毁机会平等的虚伪面具,把不平等的残酷真相揭示给你们看。 我们经常夸大机会平等的作用,甚至认为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要达成成果,就看个人能力与努力。其实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从来都没有谋求任何一种层面上的平等。地域歧视、贫困歧视、行业歧视充斥各种场合,精致的社会等级制度擅长以机会平等的假面来为不公平提供“合理的”借口。*现实的情况是,就连机会平等距离我们都很遥远。所以,机会平等值得追求,却不应被夸大。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机会平等只是现实不平等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4.剑指坐拥话语权却麻木不仁的媒体与企业。指出舆论工具和媒体的荒谬逻辑,戳破媒体与企业口中道德的谎言。 当效率、能力与发展成为现代媒体与企业标榜的金字招牌,斯坎伦尖锐指出,个人能力与努力不能成为社会不平等的理由。过得*差的人应该有某种形式的优先权,而且这种优先权不能以效率、能力或社会发展的借口来取消。效率和能力不能成为控制他人和剥夺他人正常权利的帮凶。人获取财富和权利的逻辑不是凭个人能力和努力去争夺,而是在事业选择与决策时准备充分,判断明智,以合理的方式获得。 5.大错特错的996。个人能力与奋斗不能成为社会不平等与剥削的借口。 一个合理的制度,不应该因为单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让他成为地位*高的人,为他开启不平等的特权绿灯。斯坎伦认为,努力就算与财富和地位相关,也是因为太多人认为自己没实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是因为没努力——而这种荒谬的观念必须被驳斥。真正能说明不平等是合理的情况是:一个人在做出选择和决定时,他自身已经积攒了足够的条件,让这种社会优势水到渠成。而不是进行投机和内幕交易,让社会平等为了个人利益而倾斜。
